读书人的精神家园
一辈子的读书、思考
一辈子的智慧追寻
作者冯克利,原载《读书》2001年第1期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时至今日仍未听过这句话的人,已经不多了;知道此言是出自阿克顿(1834~1902)勋爵之口的,大概也不乏其人。但是了解阿克顿其人其事的,可能却依然极不多见。
1887年,他在给《英国历史评论》主编克莱顿的一封信中,写下这句令人过目不忘的至理名言,然而它仿佛是流传于街头巷尾的谚语,人们并不十分关心它的来源,这似乎是因为它的来源并不十分重要。
从某个角度看,确实如此。阿克顿晚年自称一生碌碌无为,他除了做过《剑桥近现代史》首任主编,为世人留下半部体例独特的史学著作外,未曾写下过什么黄钟大吕之作,因此我们今天看到他唯一的那本文集《自由与权力》,也不过是几篇演说、文稿和若干宗教文章的结集。
然而,有个问题是,如果谁随便那么讲下一句话,过后能像民间谚言那样世代流传,那我想一定是因为它包含着某种智慧。
显然,阿克顿先生也并非碰巧说出一句至理名言,他没有用系统的著述来陈述自己的思想,并不意味着他没有自己系统的见解。
汤因比先生曾非常惋惜的说,阿克顿是时代精神的一个奇特牺牲品,工业社会不断逼使人们发掘史料,迷信劳动分工,使这位自由史的研究者手足无措,结果是“近代西方史学家中最伟大的头脑之一”,变成了一名才华虚掷的编辑。
在我看来,汤因比这些话自有他的道理,如果他拿自己的鸿篇巨制《历史研究》与阿克顿相比,有如此惋惜之言当属难免。然而,如果说这颗头脑“全为现代化的劳动分工所害”,却实在不太令人信服。
阿克顿生活的年代,适逢英国和欧洲的沧桑巨变
事实上,阿克顿在史学上无所成就,以今天许多人的眼光看,其主因并非分工使他无所适从,而是他的“史以载道”,即西人所谓“read the faith into history(援经入史)”的倾向实在过于明显,这使很多人以某种先验立场来判定他无法做到就史言史。
希梅尔法伯专门给文集作序,按照他的说法,阿克顿最伟大之处在于:“他给政治带来了先知的道德热忱,给宗教带来了自由主义政治家的人道关怀;他给这两者同时带来一个真理——权力,不管它是宗教还是世俗的,都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腐败的力量”。
这段文字,不仅极恰当地指出了阿克顿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的性质,也标明了它的两个重要来源:阿克顿坚定不移的天主教信仰,和他对人类自由的深切关怀。通常,现代史学为避免曲笔,辄以“不做道德法官”为治史者必须恪守的诫律。以此观之,阿克顿在这两者之间建立起的紧密关系不仅令人费解,并且显然是犯了“大忌”。他虽曾师从德国史学巨擘兰克,却一反老师的教诲,把历史视为“宗教的真实证言”,始终坚持“以道德评史”为史家无可推卸的职责。
在宗教势力已破相百出的世纪,他却依然笃信超然于人类之上的基督并未失败,因为在他看来,神的统治智慧并不体现于世界的完美,而体现于世界的改善;在这种改善中,自由则是人类所获得的一个最重要的“道德成果”。
他那些文约义广的史论文章,执意要在史实中寻找信仰和自由价值的佐证,表现出一派正宗的“春秋笔法”气象,使我们今天读来,也不时有钱钟书先生所谓“如获故物、如遇故人”之感了。
邪恶盛行的唯一条件,是善良者的沉默。——英国思想家、政治家艾德蒙·柏克
美国史学家亨利·李认为,阿克顿爵士所力主的“以道德评史”是大错特错的,其著述甚至被人讥为“阿克顿通谕”(借用了“教皇通谕”的说法)。如果按照某种“独立史观”的立场来看,这种评价当然是不足为奇的。
但是我们平心而论,阿克顿清醒地知晓,史实与道德说教的确相去甚远。
他赞赏那些满怀理想之士的前仆后继,警醒人们提防僭主和暴君,并且不断宣扬“神法高悬于邪恶的统治者之上”,这多半会使我们想起儒家尤其是孟学;他认为自由的启示源自神的教诲,却不是科塞所说的那些神游于形而上世界的“理念人”——他并不认为自由的实现完全来自于先验的力量,而取决于“进步文明的各种条件的汇合和共同作用”。
他十分清楚“金钱、土地或人数取得优势,从而破坏权力平衡的做法,充斥于全部历史之中。”他不时表现出对历史经验的明识,常使我们无法相信有人对他的评价——他“在细节上全错了,其信仰却是正确的”。因此,很多“科学史观”的论者时常垢病阿克顿“文为史以载道”,也多少失去了凭据。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阿克顿在史学中传达信仰的做法?也许,我们可以说:作为一名基督徒,他“永远怀着感激生活”,把我们在生活中已得到或可能得到的、而不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幸福,都归于上帝的恩赐。

他在谈述英国宪-政发展时有一段布道式的话语,或可视为这一点的佐证:“(英国人民)令人自豪的特质令人瞩目,这离不开我们的历史背景。……无论外国神学家的教权精神,还是法国神学家特有的君主制偏好,都没有在英国神学院的作者身上留下痕迹。源自衰落帝国的罗马法,变成了欧洲大陆专-制权力的共同支柱,却被排除在英国之外。教会法受到限制,而且这个国家从不接受宗教法庭,也没有完全接受酷刑,而欧陆王权却借此制造了许多恐怖。后来,我们的绅士阶层保持了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地方自治的办法。教派的分立导致宗教宽容。混乱的普通法教导人们,他们最好的卫士就是法官的独立与一致。”
正是英国历史中这些已然的事实,才使他能够“一直用双眼紧盯着上帝之光照亮的空间”,坚信“引领我们的上帝之光仍未熄灭,使我们遥遥领先于其他自由国家的因缘仍未穷尽”。
英国的议会传统、辉格党的宪-政精神延续至今
因此,阿克顿的信仰,是一种不脱离经验与制度嬗变的信仰,既如“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类言论,我们与其把它完全当作一种出自形而上人性论的断语,倒不如说是一种来自经验的概然性知识。而且这完全谈不上是创见,只能算是他对西方古老的政治思想传统的一个回应。
它不但是基督教原罪说在政治学中的逻辑延伸,甚至前基督教世界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也早就说过:“把权威赋予人等于引狼入室,因为欲望具有兽性,纵然最优秀者,一旦大权在握,总倾向于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蚀。故……法律是排除了激情的理性,因而它比个人更可取。”阿克顿的言论虽充满一个信仰者的执着,但阿克顿所以为阿克顿的感人之处,还来自于他从史实中总结出的警言。
阿克顿的史论中最可引起今人所注意之处,是他无论何时谈到的“权力”,并无特定的人称属性,而是泛指的。
不管是信仰者的权力,王公贵族的权力,人民的权力,代表人民的、代表金钱的权力,或自称代表自然法、“进步力量”、正义与和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权力……总之不管什么权力,只要它以暴力为后盾(而事实上这是必然的),只要它失去制衡,成为“绝对的权力”,都会倾向于残暴、腐败和不义。
只有这样的权力观,才有可能为我们提供观察二十世纪残暴政治的人都能从中汲取教益的识见。在他看来,政治生活中最可怕的局面,莫过于“道德与宗教不分,政治与道德不分;在宗教、道德、政治诸方面,只有一个立法者和一个权威”。
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始终贯穿着一个中国春秋笔法的本土史学中不得见的基本立场,即人间所能享有的无论宗教自由还是世俗自由,皆是权力平衡的产物。
在论及古典时代的文明没落的原因时,他说:“个人、家庭、团体和属地(这些当然都是保持权力平衡所必需的社会要素)是如此卑俗,以至于统治权力可以把它们用于自己的目的。共同体支配着公民,一如主子支配着奴隶。由于忽视私人利益,忽视人民的道德生活及其进步,希腊和罗马都丧失了维系国家繁荣的关键因素。”
苏格拉底之死:“多数人暴政”导致自由城邦崩解
他从这种现象中,读出了“侵害今日政治社会的种种谬误——功利主义,对专-制与权威、不法与自由的混淆”的源头。
对于这些谬误的主义与混淆的观念,一百多年后的我们,肯定要比阿克顿有更切肤的感受。
因此当我们看到阿克顿说,“只要某个单一的目标成为国家的最高目的,无论该目标多么远大高尚,无论是实现某阶级的优势地位、国家的安全、多数人的幸福,还是一个抽象观念,此时的国家都会不可避免地走向专-制”,我们不知是该佩服他的远见卓识,还是该为我们的愚妄而扼腕痛惜。
阿克顿对私人和公共领域的多元化在制衡权力中的作用多有论述,作为近世最重要的古典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家,他这方面的言论,也是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但往往被许多反自由主义者所忽视的另一面是,它也构成了现代知识传播或交往理论中的基本成分。
今天人们谈论甚多的公共交往学说,许多论者只往批判理论或哈贝马斯处追索,却没有看到自由主义有关共同体生活的大量言论,适足构成这种公共交往思想不可缺少的一环。
一个社会共同体形成的各项有利于个人自由的制度,既为我们提供了一道保护私人生活的屏障,更是一个有利于群聚与合作的架构,一个促进群体生活演变调适的对话环境,就此而言,阿克顿所秉持的自由主义传统,虽可名之为“个人主义” 的,但它也是一种有关千千万万的个人如何共处与合作的“群体之学”。像某些“批判理论”一样,自由主义把这种对话共同体的存在,视为一个让各种尚不知对错的观念和行为模式在和平的环境下得以展开的过程,因为这是人们形成共同体的道德规范和公共目标所必需的社会学前提。
在哲学认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大量有关“真理”如何产生(或无法产生)的言论,有心者不妨把它们与自由主义的共同体理论做一比较。譬如被国人忽视而近年来又因利奥塔等人宣扬而重新走红的美国哲学家皮尔士,他最宝贵的思想遗产之一,便是他在“真理”问题上仍坚持客观主义立场,但也认为“真理”只能存在于一个在(科学)共同体的自由对话中逐渐形成或展开的无尽过程之中。再譬如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也把“正确”语用的形成,归因于一个语言群体习惯性交往的过程。其实,不惟真理和语言用法,遵约守信的习惯、权钱关系纳入法治、特权变为平权的过程,也莫不如此:没有参与的自由,没有对话,是不可能建立起取得共识的交往规则的(虽然它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真理”)。在政治哲学的领域,此类识见可以说随处可见。
波普尔:真正的无知不是知识的缺乏,而是拒绝获取知识
姑不论以鼓吹“开放社会”著称的卡尔·波普尔,不管是阿伦特的古典共和主义,还是保守主义者奥克肖特的“公民社团”理论,我们都可从中看到大量有关这种开放性共同体的思想。即或被许多人拿来与自由主义抗衡的哈贝马斯,不但明确认为市民阶层(“资产阶级”)是一个促发现代性的“对话伦理”的共同体,而且把它视为一支与专-权和僵化体制相抗衡的最重要的力量——当然,没有哪个自由主义者会反对这样的思想。因此,就公共领域在对话中产生基于自由的共识的作用而言,西方自由主义和一些左翼思想流派的分歧,也许被人们做了过分的夸大——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从这个角度来解读阿克顿有关教会和民族问题的文章,我们即可看到,他为解决教会和信众的分歧所提供的办法,其中既有坚定的保守主义信念,更包含着丰富的“对话交往理论”。
对他而言,教会更像是一个对话的共同体,而不是一个刻板严厉的“组织”,它对于信徒的价值,在于它为讨论和取得共识提供了一个场所。他说,“在教会中长期得到坚持和许可的神学观点及其他观点,是在时间的磨砺中获得真知灼见,并因教皇的默许而确立了具有一定约束力的权威地位,因此如果不是出于轻率,便不能轻言放弃。”
他在这里触到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至关重要的政治学问题,即自由和权威的关系:教会虽是一个权威机构,但它真正的合法性并不来自它的制度化权力本身,而在于它和信徒的普遍信念相一致。只要它大体做到了这一点,激烈否定其权威不但不会带来变革,反而会引起分裂或反动,因为“硕果累累的胜利来自于天主教信众在知识、观念和信念上的逐渐演变”,它将迫使传统的代言人与新的环境相适应,最终克服抛弃成规的优柔寡断。因此最合理的改革方式应当是,在影响权威之前先影响它的信众,使其看法缓慢而平静地作用于教会,这样的改变“既不会产生任何破坏道德的冲突,也不会导致丧失体面的屈服”。
但是这种体制中不言自明的另一面是,这一切都要以一个开放的“信仰共同体”为前提:教会不能禁止对“教令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进行审查,就让理智和良心上作出让步”;信众也不能“因为权威被滥用便抛弃权威”,因为“这两种做法同样都是罪过,一方是背叛了道德;另一方是背叛了信仰。将维护宗教真理的全部责任抛给教会戒律的执行者,并不能使良心得到解脱;干脆叛教也不能让良心释然。”
这种共同体哲学,也被阿克顿延伸到了他对当时正在崛起的民族主义的认识中。
依他之见,他那个时代有三种最重要的“社会批判理论”,即“平等主义、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它们所反对的,都是统治者因自私和滥用权力而造成的秩序。尤其是“得势前景最为看好的”民族主义,它“不仅是革-命最强大的助手,而且是近三年来各种运动的真实本质”。虽然它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但是“在它宣布已经进入的革-命时代,它必定始终保持着力量”。
伯林曾在其名篇《民族主义》一文中断言没有哪个十九世纪的思想家预见到民族主义在二十世纪的重要影响。博学如伯林者竟未看到阿克顿的《论民族》一文,不能不说是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伯林:民族主义是民族情绪的一种发炎红肿的状态
但是不难想见,以一个天主教徒的普世情怀,阿克顿虽洞察到这股潮流的强大,却不可能对其表示完全认同。在他看来,民族主义固然有其提醒压迫的存在、提出改革方向的正面作用,却不能将它视为重建世俗社会的政治基础,因为单纯的民族主义“可以服务于截然对立的政治原则和各式各样的党派”。它把集体意志看得高于一切,把人们的各种利益全都纳入一个虚幻的统一体,要求其牺牲自己的习惯和义务。它也许会以民族自治、人民的自由和保护宗教为旗号,其实它却“只为自己说话”,“如果它无法和它们结合在一起,它为了获胜不惜让民族牺牲所有其他事业”。读到这里,我们也许更易于理解,为何在二十世纪狭隘民族主义常常与好战黩武的军国主义形影不离。
不过这只是民族主义的一极。阿克顿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是那种由启蒙运动培养出来的世界主义者,他不否定还存在着一种健康的民族感情。
哈耶克在二战结束前夕一次题为《历史学家与欧洲未来》的演说中,曾特别建议把阿克顿的民族理论作为战后消除德国狭隘民族情绪的基本原则之一。这不但因为他要求史学家必须像阿克顿那样,不以价值中立为由回避道德判断,敢于说出“希特勒是坏人”,还因为在他看来,阿克顿持有一种十分开放的民族观。
阿克顿所肯定的另一种民族观,除了在反对专-制宗主国或殖民政府这一点上与民族对抗的思想相同之外,其他没有任何共似之处。他认为民族利益虽然是决定国家形式的一种重要因素,但它并非至高无上。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天然地具有多彩多姿而非千人一面、和谐而非大一统的潜能,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多民族的共存还可构成对国家权力膨胀的最终限制,有可能被民族国家牺牲的私人权利,有机会因民族差异而受到保护。它以“分别存在的”乡土感情(我想这里有必要指出,这才是“patriotism——爱国主义”的本来含义),影响和牵制着统治者的行动。因此阿克顿也把一个主权国家内若干民族的共存比作教会的独立,认为它们可以发挥维护权力平衡的相同作用,“避免出现在单一权威的笼罩下四处蔓延的奴役状态”。他乐观地(也许是过于乐观了)认为,“同一国家之下若干民族的共存不仅是自由的最佳保障,而且是对自由的验证” 。由此他也否定了约翰·穆勒所宣扬过的一种近代自由主义的主流学说:“政府边界与民族边界相一致,一般而言是自由制度的必要条件。”
当然,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也可以印证现代知识理论中的一条重要原理,即差异是人类合作从而促进知识进步的一个必要条件。正如他所说,“不同民族结合在一国之内,就像人们结合在一个社会中一样,是文明生活的必要条件。生活在政治联合体中较次的种族,可得到智力上更优秀的种族的提高。力竭而衰的种族通过和更年轻的生命交往而得以复兴。
多元的价值观是人类的宝贵财富——周-孝-正
在一个更强大、更少腐败的民族的纪律之下,由于专-制主义败坏道德的影响或宪-政制度破坏社会整合的作用而失去组织要素和统治能力的民族,能够得到恢复并重新受到教育” 。这些言论中虽然些许透露出盛行于他那个时代的种族主义色彩,如果我们用今日的“民族平等”或“优势互补”之类说法加以纠正,我想阿克顿是不会反对的,因为在他的笔下,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国家,并不具有单一种族文化的神秘性,而是应当成为一个“促进融合的大熔炉”,它所逐渐形成的自由制度,可以使习俗、活力、创造性上各有所长的不同群体,相互传播他们的优点,扩大人们观察生活的视野。民族差别处理不当固然会导致严重冲突,但是只要待之以恰当的自治,它也能为国家带来巨大的好处,可以使每个人都能“在邻居中找到自己的利益。……使文明和宗教的利益由此得到促进”。
虽有这些在当代公共哲学中仍充满活力的思想,但是在今人看来,阿克顿是不是一个很老派的人物?
其实不只是我们,即使在一百多年前他的同代人眼里,也难免会让人产生这样的想法。他的贵族身份,他坚持让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与自由主义并行不悖的努力,他的普世主义情怀和保守立场,在与此后百多年来精神生活的大气候格格不入。
当年哈耶克创立“朝圣山学会”之初,曾建议用阿克顿和托克维尔的名字来为学会命名,这就几乎让到会的美国人拂袖而去。
美国的自由主义者不乐于把阿克顿引为同道,似乎也并非没有他们的道理。大概他们对阿克顿曾为美国宪政做过的出色辩护并不领情,倒是忘不了他不但有美国主流文化所讨厌的贵族身份,而且还给南方坚信联邦制的蓄奴分子说过好话——这也是一个从正确的理由推导出来的错误结论,因为阿克顿总是固执地认为,在维护自由上,权力的平衡比权利的平等更重要。
其实,从阿克顿经常受人冷落的思想遭际中,我们看到的还是政治世界为价值排序这个几乎无终极解的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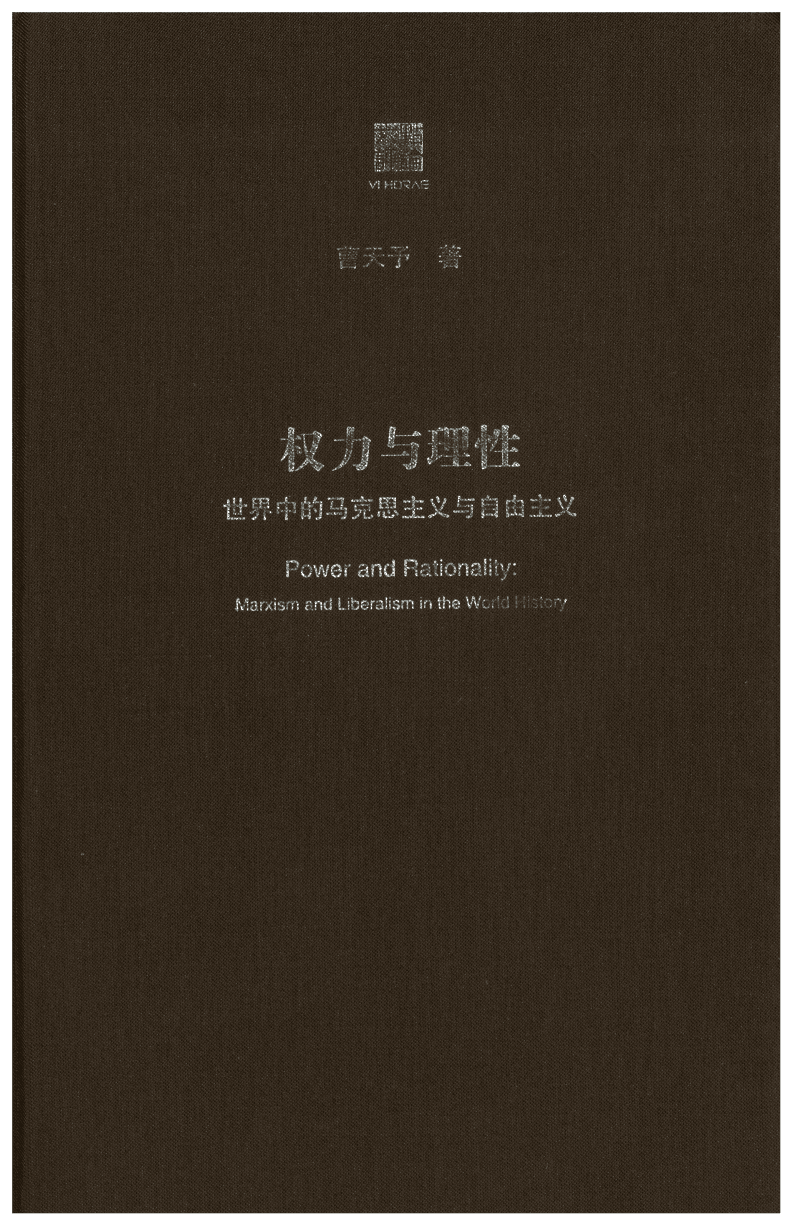
当代自由主义难题——平等消解自由
一时一地的问题,决定着一个社会在选择价值上的优先顺序。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民族独立,公共精神,私人空间等等,如果撇开时间因素不谈,无一不是极可取的价值,但它们又是只能在历史中,在具体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中才能被人类选择,从而得到真实生命形态的价值。阿克顿所做出的选择,是自由和信仰无条件地高于其他价值,并且认为能够保证其安全的,只有建立在权力制衡原则上的宪-政制度。
我们可以把这看作只是他本人的信念,甚至是一个历史学家一厢情愿的反历史的偏见,不少人也会因此而批评他在平等、民主和人-权方面的思想缺失。
可是我们也没有理由忽视他教给我们的智慧:无论什么样的统治,只要存在不受限制的权力,都有走向腐败的倾向。
他为此提供的一个重要理由,便是绝对权力有可能“败坏良知,麻木心灵,使它失去对环境的理解力”。
和阿克顿给人留下的史以载道的印象相反,他这些反复强调权力制衡的观点,说到底并非单纯来自他的信仰或理念,而是一种以信仰为根基的经验主义,或曰史家的智慧。
阿克顿勋爵语录整理
关于自由
我所说的自由,意指这样一种保障:个人在尽其信奉的义务时,皆应受到保护,不受权力和多数习惯和意见的影响。
判断一个国家是否真正自由,最可靠的检验办法就是其少数受到保护的程度。
少数的压迫是邪恶的,但多数的压迫更邪恶。因为民众中隐藏着的力量若被唤醒,少数人几乎无法抵挡它们。面对全体人民的绝对意志,无可吁求,无可救助,无可躲避,唯有背叛。
自由和良好的统治并不互相排斥。自由并不是达到更高政治目的的手段,它本身即是最高的政治目的。
自由构建于权力之间势均力敌的相互斗争的对峙的基础上,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使自由得以安然无恙。
自由之核心和最高目标是良知的统治。
宽容谬误是自由之必需。
财产,而非良知,是自由的基础。
厌恶私有制的民族,缺少自由的第一要素。
法律具有地域性或者民族性,自由则没有。
自由鼓励多样性,而多样性又提供了保护自由的组织手段。所有那些支配人际关系,调整社会生活的法律,皆是民族多样化的结果,是私人社会的创造物。
权威和秩序只是维护人类眼前的现时利益——自由则是要维护人类永恒的精神利益。
自由的本质就是不要信奉过去和往事的神圣不可侵犯性。
自由在政治生活中表现为不依附各种利益、各种狂热激情、各种偏见或各个阶级的一种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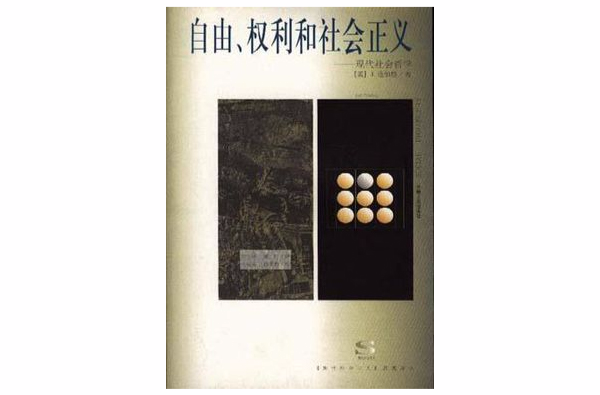
自由能促使我们不受国家、社会、无知和错误的干扰而履行我们的义务。我们自由度的大小是同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为生存竞争所进行的搏杀以及与诱惑、性格发生的冲突这些障碍成正比的——这些障碍乃自由之内在敌人。
自由所追求的事业就是正义和德行所追求的事业——反对自由就是反对正义和德行,也就是在捍卫错误和罪行。
自由的本义:自我驾驭。自由的反面:驾驭他人。
自由是一种义务范畴,而非权利范畴,要求为了实现一种超现世生活的目标而付出痛苦和牺牲。一种权利可以被放弃,但义务却不能。因此,自由作为一种权利比作为一种义务更缺少安全性。
当公民的义务模糊了人的义务时,它便是一种罪过。
自由不是天赋而是后天习得的;它不是处于静止的僵化的状态,而是处于不断努力、不断生长的状态;它不是一个起点而是一个运行过程的结果。自由是发达文明的一种产物,而不是自然状态的产物。自由是文明的最高成果。
自由,像宗教一样,一直既是善行的动力,又是罪恶常见的借口。每个时代,它总是受着它的天敌——无知与迷信、征服欲与贪恋安逸、强人对权力的渴望和穷人对食物的乞讨——的阻挠。
自由包括五方面内容:一是对身处弱势的少数人权利的保障;二是理性对理性的支配,而不是意志对意志的支配;三是对超越于人类的上帝所尽的义务;四是理性支配意志;五是公理战胜强权。
关于权利
持久的生存斗争剥夺了人们的政治志趣和洞察力,使他们为一口浊汤而急于出售自己的天赋权利,却不知所弃之物的宝贵。
自然法优于成文法,奴隶制违反自然法,人没有权利为一己之私而损人利己。
没有任何与个体私人目标相对立的公共目标值得以牺牲个体灵魂和精神的代价去换取。相反,习以为常的原则应该是个体利益优先于无所不包的国家利益才对。
民族是一个以种族为基础的理想单位,无视外部因素、传统和既存权利不断变化着的影响。它凌驾于居民的权利和愿望之上,把他们形形色色的利益全部纳入一个虚幻的统一体;它为了满足更高的民族要求,牺牲他们的个人习惯和义务,为了维护自己的存在,压制一切自然权利和一切既定的自由。无论何时,只要某个单一的目标成为国家的最高目的,无论该目标是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国家安全或权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还是对一个抽象观念的支持,此时国家走向专制就是不可避免的。
一个无力满足不同民族需要的国家是在自毁其誉;一个竭力统一、同化或驱逐不同民族的国家是在自我戕害;一个不包含不同民族的国家缺乏自治的主要基础。
一个将献身祖国看作最高义务的人,与一个让所有权利都屈从于国家的人,在精神上是息息相通的。他们都否认权利高于权威。
当法律不再神圣,它的捍卫者也不会得到同情。法律的保护者和执行者比违法者更邪恶。合法权威的罪行比不法平民的罪恶更严重。
良知只对自己而不对他人产生足够的影响力。它尊重别人的良知。因此它倾向于控制权威而扩大自由,它是一种自我管理的法则。
有悖于人类良知的任何命令都是无效的。
两个人之间的差别将人类联合在一起,不仅是因为这种差别为共同生活的人提供了好处,而且因为它用一条社会或者民族的纽带使社会结合在一起,使每个人都可以从他人中找到自己的利益。
走向进步的心灵,旁边是静静的传统。
关于历史
史学家不露面时,才会有最杰出的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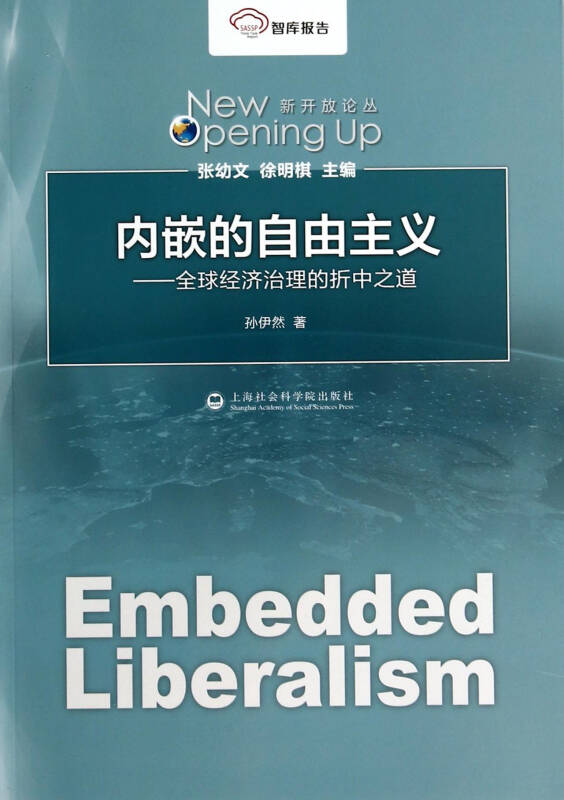
革命者的凯旋,使史家无立足之地。
评价权威著作,权衡历史记述,要比发现新课题更有价值。
近代史讲述着我们自己的故事,是我们自身生活的记录,是那些未曾放弃未曾停息的努力的记录,是那些仍然牵制着人类的步伐、困扰着人类心灵的问题的记录。
史学家必须与这些诱惑作斗争:他的特殊生活方式的诱惑,来自他的国家、阶级、教派、学派、党派、权威人物、亲朋好友的诱惑。这些影响因素中最可尊敬者乃是最危险者。
历史是个邪恶的老师,只对自由人述说真相。唯有自由人才有资格和能力从中汲取历史教训。
要从历史上升到哲学,把握永恒的问题,免于局限短暂易变之物。
宗教和政治中作为真理的思想,就是历史的力量。
关于权力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大人物往往是坏人物,即使在他们运用影响而非权威之时。
绝对的权力败坏社会道德。伴随着暴虐权力而来的往往是道德的堕落和败坏。
反抗暴政的能力并不意味着建设一个法治政府取而代之的能力。
任何一种政体都需要不断改进和发展,只有当它承受得起这种变革进步的要求时,这种政治体制才是值得称道的。
有许多事情是政府不能做的——即使是许多出于美好愿望的事情也不能做,政府必须把这些事情留给社会上的其他企业去做。政府不能对人民实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包办政策,不能代替人民去发财致富而让人民坐享其成。政府也不能充当人民的教师爷,对人民指手画脚。政府更不能强行改革或迫使人民信仰或者放弃某种宗教。
国家是不能履行良知的功能的。国家镇压犯罪行为,但却不能镇压人们心中的邪恶感。
法律拒绝法典化,目的是延续人的权力的效力。
狂热通过民众展现自己,但民众是极少狂热的。狂热所引起的罪行通常都是出于冷静的政客的谋划。
舆论状态比法律更重要。
不能为某种行为辩护时,就赞美其精神。这已成为一种惯用的手法。
革命的目的是防止以后再发生革命。专制的政府只能通过实力来制衡。
妥协理论折射出政党政治的精义。
关于真理
对溺死的恐惧,已胜过饥渴之苦。
真理有望大获全胜,但依靠的不是自身的吸引力,而是逐步消灭谬误,它不承认任何危险的政治承诺。
真理只能通过揭露错误和战胜异议而使人信服。因此,自由是真理的卫士。
在公众透彻了解法律之前和真理已经变得丑陋之前,法律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