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狄更斯《双城记》中这段著名的开头,用来形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恰如其分,用来形容当代中国似乎也并不过分。信仰普遍缺失,规则被毫不羞耻地破坏,法律“失却其神秘性和权威性以及在宇宙宏伟图景中的位置,乃是一只过于孱弱的芦苇。”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怀疑,法律,乃至社会,是否真的处于失序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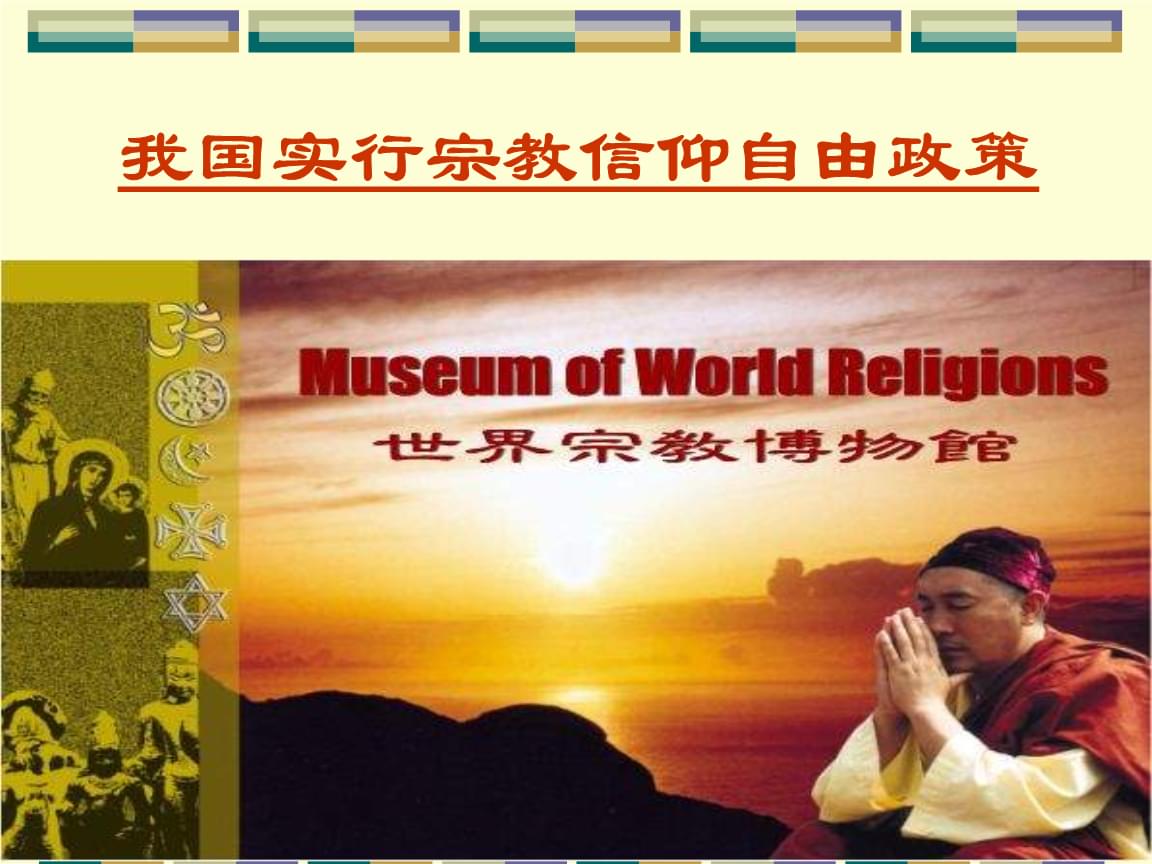
面对这种社会现状,伯尔曼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句话仿佛法律本身一样,被无数人信仰。然而,法律为何被信仰?到底是因其正义性,还是因其有用性?换言之,到底是该持有“对神法或为神圣信念所唤起的自然法之信仰”,还是该相信“法律的世俗主义”?
伯尔曼无疑支持前者的观点,认为“法律不只是世俗政策的工具,它也是终极目的和生活意义的一部分。”他指出,“法律与超理性价值联系和沟通的主要方式有四:这四种要素――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存在于所有法律体系,一如它们存在于所有宗教里面。它们提供了一种语境,任何一个社会的法律规则都是在这一语境中被宣示,并且从中获得其合法性。”因此,尽管即使从尽可能宽泛的含义上来看,宗教和法律仍然分别被视为人类对神圣的意识和对公正的观念不可能合一,然而,伯尔曼仍然相信,法律与宗教的综合,以及对法律的信仰,将构架理想中的新世界。换言之,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可以说伯尔曼把法律等同于宗教,至少是把二者看成一个整体,甚至可以说他希望创建一种“法律宗教”,同时具备宗教的神圣性和法律的正义性,类似于中古的西方社会,对社会有着强大控制力的教会“试图使道德法律化,同时使法律道德化”,法律因道德而被套上了神圣光环,被赋予了一种神圣正义性。在伯尔曼看来,法律本身因其正义而神圣,因其神圣而被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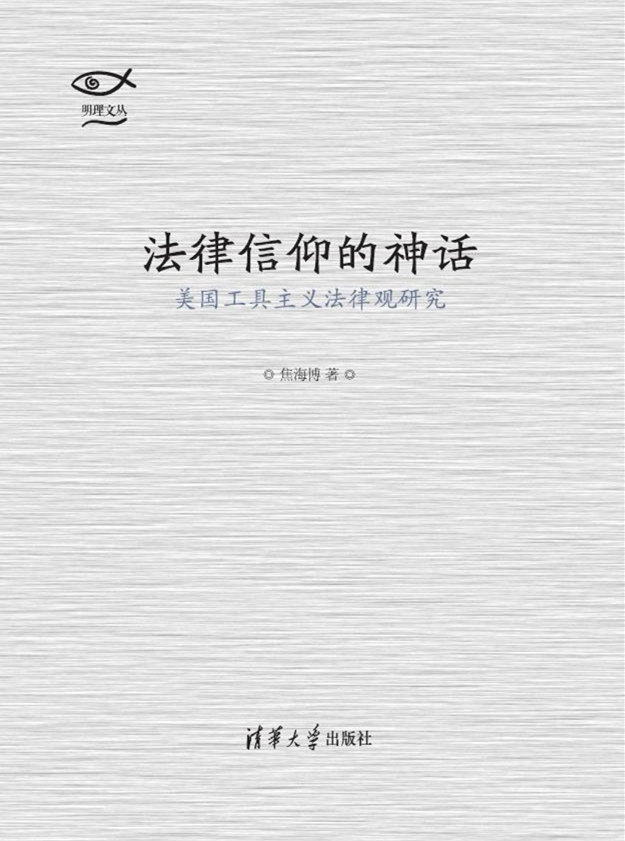
然而,谈及所谓法律应该像宗教一样被信仰,在现在,尤其是现在的中国看起来似乎有些滑稽。因为在法律与宗教的关系上,中国是缺少宗教这一基本的规则体系的。虽然有西方学者称儒学为“儒教”,儒学本身仍然不能被称之为宗教。总之,在中国不信仰宗教的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对于这一点,也许可以用古朴的实用倾向来解释。可以肯定的是,中华文明有区别于西方文明的重大不同,中国的宗教因素在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小到几乎可以忽略,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决定了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宗教在我们的社会规则体系之下,影响依旧甚微。一个对宗教缺乏信仰的国家,谈何“如信仰宗教一般信仰法律”呢?
由此,基于法律有用性的法律信仰认为,西方人相信法律不只是因为法律有信仰基础,而是法律能给人世间带来秩序,能够恢复社会的平稳运作。西方宗教改革后,教会失去了法律效能,新教的怀疑主义使法律实证主义的出现成为可能。19世纪七十年代后,随着实用主义的盛行,法律与宗教的二元对立被人们普遍接受。也就是说,如果强求一个法律根本不能起任何作用的地方的人民去信仰法律,无非是愚人或愚己。指望人民相信没用的东西如同缘木求鱼一般可笑。只有让人民看到法律的作用,法律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个稳定的秩序、可预期的未来时,人们才会去相信法律。

然而,我个人认为,这种基于功能派的观点有失偏颇。这种观点把法律视为一个纯粹的工具,而工具的价值就在于有用。换言之,如果出现一个比法律更有用的工具,法律将被抛弃。事实上,如果有好的集权者,的有用性并不逊于法律,例如中国中央集权的“人治”历史源远流长。这是否意味着,只要选择好的集权者进行,就可以抛弃法律了呢?显然是不可能的。除了法律的稳定性因素以外,对法律所代表的正义本身的信仰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先决条件。对法律完全没有敬畏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就如同信仰基督教一样,一个人要想形成对于基督教的信仰,必须信仰上帝,必须相信上帝是存在的。为什么那些信仰宗教的人可以对一个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它存在的上帝信之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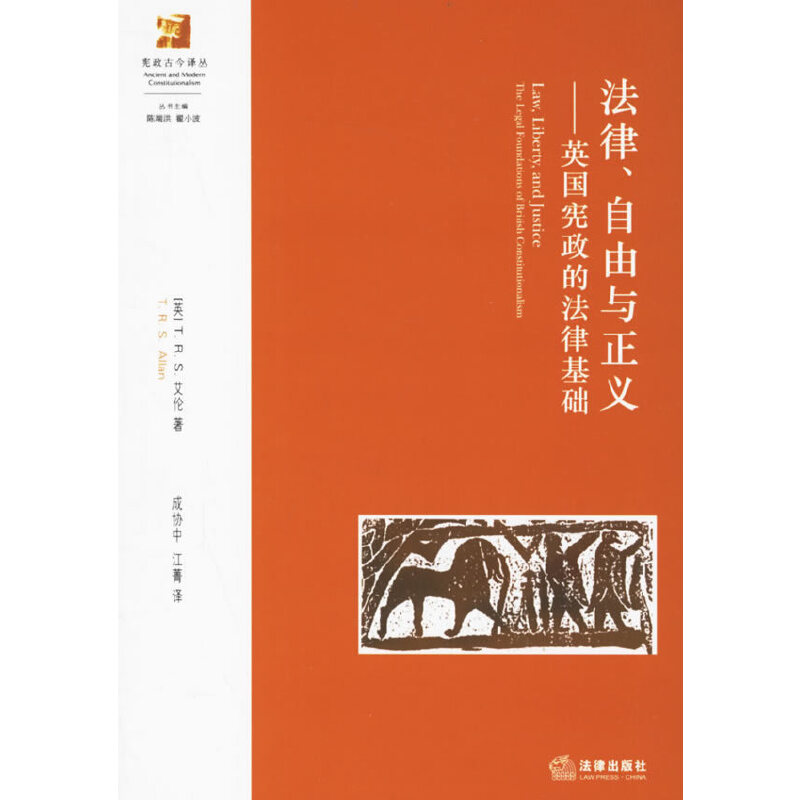
这其中的原因也许在于基督教教义中本身存在的正当性源泉。即基督教教义是符合基本的人性要求,是为大多数人所赞同,也是符合基本的人基本的道德观念。基督教教义中存在着诸多“爱你的敌人”“宽容”“十诫”之类的教令。这无论在哪个社会都是为人所尊崇的善品。而我们今天的法律同样如此,法律必须有正当性基础。法律中所弘扬的必须是善的,抑制的内容必然是恶的。而且必须符合社会公众心目中一般的善恶标准。所谓的对法律的信仰也是指对正义的法律的信仰,对法律体系和法制过程的信仰。
“只有当我们承认法律不仅是社会功利问题,而且也是、且主要是生活目的和终极意义的一部分,承认法律关系到人的全部生命,即不仅关系到他的理想和一只。而且还关系到他的情感和他的信念,我们正在经历的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法律信任危机才可能得到应对和解决。”确实,法律的作用有规范作用,法律的价值有工具性价值,但它位于法律价值位阶的最下面,人们正是通过法律的秩工具性价值:秩序,来实现平等和自由的最终价值,这才是目的性价值。

“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法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如果没有对法律的信仰,那么法律的施行将会受到极大的阻碍,法律施行的效果大打折扣。但前提是,制定的法律是正义的法律。即,法律本身所代表的是正义。
波尔曼理想的新世界是对同时具备“神圣性”和“正义性”的法律完全信仰的世界,我们现如今的世界显然相去甚远。然而,该如何创建,或者说改造成理想中的新世界呢?个人认为,对于正义性的追求是人类的天性,对于神圣性的崇拜与信仰亦然。正因如此,法律必将因其正义性而被信仰。
“希望就在综合的新时代”,所谓“综合”,绝非“合一”,更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法律因其正义性而被信仰,社会也将因这种希望而获新生。








![[中文摘要]对话教学的实践策略琛指导 [中文摘要]对话教学的实践策略琛指导](/uploads/img/timthumb/Timthumb.php?src=/uploads/allimg/20221115/1668492168756_0.png&q=90&w=196&h=146&zc=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