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有次冬天的严重雾霾中,我提醒出租车司机关上车窗,他竟有点不情愿,且不屑地说:“死生天注定,有人口罩捂得严严实实没准儿还就得病呢。”是的,坏事不一定就降临到自己头上,我们往往听从的不是真实,而是用来代替真实的幻觉。因此宁愿不思考,宁愿要虚假的快乐,宁愿全然地绝望。但是抑郁现实主义者不是这样,他们忧患种种公共危害,怀疑精心编织的谎言,这让他们自己焦虑、孤独,也破坏自我欺骗者的欢乐,但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忧患和怀疑,使本真和自由的价值不至从社会完全陨落。
逆境忧患与抑郁现实主义
文 |徐 贲
(《读书》2017年5期新刊)
忧患感(忧患意识)可以有两个不同的意思,一个是对突发不利情况的担忧,善于察觉生活中的危机,预见坏事的发生,也就是孟子说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另一个是对悲苦、灾祸、死亡、贫困、挫折、人间不幸、世道艰难、世态炎凉等等有敏锐的感受,是一种饱经忧患、备尝艰辛、悲天悯人的心境或气质。
忧患的情感或心境包含着特定的认知,“忧思”既是“忧”,也是“思”。忧患主要不是指一时性的忧愁情绪,或对某事的不安或担心,而是指一种比较固定的思维习惯和性格特征。在大多数情况下,忧患者遇到事情会从不利处着想,负面考虑多于正面考虑。忧思者大多是多虑、沉稳、谨慎、多思和内向的。
“不能确定是我太偏激,还是只是对现实拥有敏感的感知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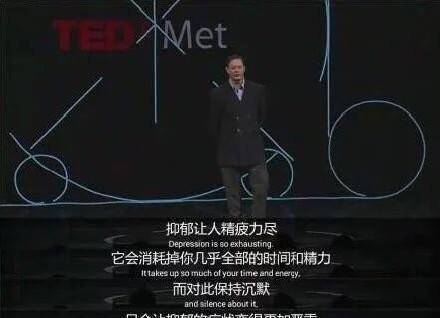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是在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对立概念关系中理解忧患思虑,忧思被推向悲观那一头。但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心理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打破这种乐观—悲观两分对立的新概念,那就是“抑郁现实主义”(depressive realism)。它让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生存逆境中的忧患感,也让我们对抑郁有了一个新的透视视角。我们可以由此来理解和描述忧患意识或忧思的一些重要特性,也可以避免把“忧虑”想当然或简单地当成精神病学的“忧郁症”或“抑郁障碍”。
一作为认知策略的忧思
抑郁现实主义是作为“乐观幻觉”(optimism illusions)或“乐观偏误”(optimism bias)的对比概念而提出来的。为了避免“抑郁”一词与精神病症状的联想,我在此称“抑郁现实主义”为“忧思现实主义”。是什么让“抑郁”跟“现实主义”发生联系的呢?美国心理学家劳伦·阿洛伊(Lauren Alloy)和林·阿伯拉姆森(Lyn Y. Abramson)于一九七九年提出“抑郁现实主义”这一说法,是从“抑郁”与“真实”(现实)的接近程度着眼的。他们认为,抑郁者对现实的认知比非抑郁者更接近真实,“比起非抑郁者(他们经常高估自己的能力)来,抑郁者在判断自己处理的事情时把握更加准确。他们是那些‘吃一堑,长一智’(sadder but wiser)的人,非抑郁者太容易屈从于自己的错觉,用美好的眼光看自己和环境”。忧思的“接近真实”是与非抑郁的“乐观偏离”比较而言的。忧思所纠正的不是乐观主义,而是乐观幻觉和由此而生的“乐观偏误”。
劳伦·阿洛伊:《变态心理学》(McGraw-Hill Education; 9 edition,2008)
乐观偏误又称“不现实乐观主义”(unrealistic optimism)或“比较性乐观主义”。它让人错误以为,在碰到坏事的时候,自己不会像许多其他人那样受害或倒霉。例如,许多人认为专制是一种不好的制度,但又同时认为,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专制制度是个例外,从这个先入之见出发,他们会选择性地寻找证据,证明自己信任“这个专制”是合理和正确的。乐观偏误在私人或公共生活中相当普遍,是一种鸵鸟式的自我欺骗。例如,吸烟的人知道吸烟与肺癌的关系,但认为,得肺癌的不会是他自己。对造成公共危害的雾霾的看法也是如此—雾霾致病,但这等坏事不会落到我的头上。有的人明明知道股市并不是按市场规律在操作,许多人都在赔钱,但却认为自己能在这样的股市里捞到一笔。而拒绝乐观幻觉的抑郁现实主义对现状的估计虽然也会有偏误,但会比较接近真实。历史学家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说:“我们深受其害的首先是我们自己的幻觉,而不是我们的恶习或软弱。我们听从的不是真实,而是我们用来代替真实的幻觉。”正因为普通人很容易把幻觉当成真实,抑郁现实主义的纠偏作用和价值才受到了重视。
丹尼尔·布尔斯廷

弗洛伊德认为,幻觉对绝大多数人未必是一件坏事,“幻觉对我们有吸引力,因为它省却了我们的痛苦,让我们可以快乐。因此,就算幻觉有时候与现实有一些矛盾,会因此而被现实粉碎,我们还是应该接受幻觉”。乐观幻觉可以有积极的心理作用,如增强自信、自尊,激励进取心。但是,我们并不因为乐观偏误有某些积极作用,就不把它当作一种偏误。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抑郁现实主义有接近真实的推理作用,就也不把它当作一种偏误。
抑郁现实主义的纠偏作用来自它的现实思考,而不是抑郁本身。抑郁是因为现实思考让人看到了太多的阴暗和丑恶,隐蔽的和暴露的,因而有了一种疲惫和无力感。承认自我的软弱和无助本身就是一种现实主义的人生态度。抑郁现实主义的“抑郁”是轻微的,就像心理学家们所说,快乐的人也会抑郁。抑郁现实主义的“抑郁”是勤于思考的结果,是一种思考者的抑郁。这与中度到重度抑郁患者有思考障碍是完全不同的,后者的特征是极度的不自信,觉得做什么都是错的,对未来生活中的一切充满焦虑和丧失信心,甚至厌世。这样的抑郁者,他们的认知也就无关乎什么现实不现实了。他们因幻觉而造成的焦虑、沮丧、绝望已经不属于忧患意识的范围。
心理治疗医师和作家科林·费尔什姆(Colin Feltham)在《我们不让自己走出黑暗》(Keeping Ourselves in the Dark)一书中有专门一章讨论抑郁现实主义,他认为,许多人害怕从美好的错觉世界跌入到一个他们不想看见的现实世界,这个现实世界让他们感到无所适从,“冷漠、懒惰、郁郁寡欢、无创意或回应、惊慌、孤立、失败、看不到前景”。抑郁现实主义能够帮助人们应对这样的现实。费尔什姆在一次关于抑郁现实主义的访谈中指出,抑郁现实主义以怀疑的态度看待人的存在,关切的主要问题是“死亡、无意义、世界对于苦难的冷漠、社会的荒诞、生活中的错觉和谎言,以及我们对这些的绝望应对方式:否认、逃避、抑郁、自杀、人口控制论(antinatalism),等等”。
科林·费尔什姆:《我们不让自己走出黑暗》(Nine-Banded Books; First edition,2015)
抑郁现实主义虽然是一个新概念,但它关切的忧思主题却非常古老,从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到现代的卡夫卡、哈代、萨特、加缪和法国文坛的人气作家米歇尔·韦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以孤独、虚无、荒诞、讽刺闻名),在宗教、文学、哲学中的例子数不胜数。可以说,所有的反乌托邦文学大家,H. G. 威尔士、赫胥黎、奥威尔,都是富有忧患意识的抑郁现实主义代表人物。
抑郁现实主义很容易被误会成悲观主义,其实二者之间有着重要的区别。忧患意识与悲观主义的最大区别在于行动,包括行动的动机和能力。悲观主义会使人在颓废、失望和沮丧心情下变得冷淡麻木、浑浑噩噩,也成为行动上的失败主义者和无为主义者(做与不做都一样)。忧患意识则会激励行动,它有判断,有目标,所以才更多地考虑到实现目标的难度。悲观主义因前景黯淡而放弃努力,但忧患意识则会因预见不利和困难而先做准备或加倍努力。例如,在就业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悲观主义者也许会心灰意冷、意气消沉、萎靡消极、自暴自弃,但是有忧思意识的人会早早做好思想准备。他不会因为工作难找而放弃寻找的努力,不会放弃每一个面试的机会。
就行动方式而言,忧思也是有别于乐观幻想的。例如,乐观幻想的求职者会因为过分良好的自我感觉和前景预感,对工作挑挑拣拣,但忧思者则会更珍惜每一个机会。往最坏处着眼,往最好处努力,这就是忧患意识者常抱的“但问耕耘,莫问收获”心态。

二快乐与真实
抑郁现实主义对我们每一个人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快乐和真实哪个比较重要。每个人对这个问题都可以做出他自己的回答,没有人能替别人回答这个问题。即使对重度抑郁病患者,快乐和幸福也不是一个多余的问题。重度抑郁病也是可以治疗的,荷兰有一项研究表明,大多数患有精神疾病的人至少在有的时候也是“快乐”的。
忧思者往往是一些看起来不快乐,或者不容易快乐起来的人,他们内向、多虑、多疑、孤独,遇事顾虑重重,看待事物的方式比较黯淡、保守。正因为如此,他们一般比较诚实和正直、不愿意说假话,也不愿意欺骗自己。这样的人大多讨厌虚伪,鄙视官场或社会中的随波逐流和附膻逐腥,不屑于做那些歌功颂德、趋炎附势的事情。他们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失德和堕落痛心疾首,无情鞭挞,因此经常被芸芸众生的世人视为特立独行、难以相处,甚至愤世嫉俗、自讨苦吃的“怪人”。
真实与快乐就像是鱼与熊掌,难以兼得。挪威—加拿大哲学家赫尔曼·汤勒森说,人必须在真实与快乐中两选其一。乐观主义是一种快乐的生活观,任何乐观主义都难免有错觉或幻觉的不真实成分,乐观主义的不真实使它显得肤浅和虚幻。一味乐观的箴言励志空洞浮泛,经常被嘲笑为“心灵鸡汤”。统治权力所制造和宣传的“幸福感”类似于此。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里每个人可以定量享受的“舒脉”,就是这种乐观主义的迷幻剂。在乐观迷幻的社会里,抑郁病患者成为给幸福生活抹黑,让幸福社会没面子的“异类”。他们遭到权力的仇恨、社会的嫌弃和排斥。
阿尔多斯·赫胥黎(1894-1963)
弗洛伊德是一位有开创建树的精神治疗大师,他对精神治疗有期待,也有信心。他所设想的精神治疗,其现实目标不是让患者兴高采烈地快乐起来,变得豪情满怀,饱含对什么主义的深情,而是为了帮助他们摆脱歇斯底里的悲苦,不要过度不快乐,只要恢复到常人的不快乐程度就好。许多称职的、有同情心的心理治疗师也是这么劝导病人的,抑郁来自人类进化本身,人无须因为自己的抑郁而觉得可悲、可耻、自卑或有负罪感。对自己,包括对自己的精神和心理软弱彻底诚实,接受真实,这才是克服心理疾病的最好办法。
其实,对于每个神志清醒的人(包括轻度抑郁者)来说,真实或快乐未必完全是他理性选择的结果,他的心境、气质、城府、性格往往替他做了这个选择。当然,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具体的社会环境里,由特定的经验或遭遇所形成的。忧思者不是不相信或不喜欢快乐,而是认为,快乐是一种偶然的,一时的感受,再多这样的快乐,也未必就能累积为人的幸福。在他们看来,歌舞升平、莺歌燕舞的“幸福生活”不过是海市蜃楼。统治者往往会刻意制造这种幸福生活的幻觉,引诱和鼓励人们生活在这样的幻觉中,因为这符合他们的利益。对这样的盛世,抑郁现实主义者无意做什么“盛世危言”,因为那个被称为“盛世”的,在他眼里,本就是一个骗局,或是一个乐观幻觉。

心理学家和心理治疗师一般认为,对于任何快乐或幸福来说,某种程度的幻觉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快乐或幸福需要幻觉,那么真实也就会被牺牲掉。对那些很在意真实的人们(其中包括抑郁现实主义的忧思者)看来,依赖于幻觉的快乐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柏拉图认为真实高于诗歌,就是因为他更在意真实。
然而,倘若一个人相信存在着某种绝对的真实(真理),相信他自己就是真理斗士,少了他别人就不知道如何寻找真实,那也是一种不真实的错觉或幻觉。凡是人,多少有一些错觉或幻觉,但对错觉或幻觉的自觉程度却甚为悬殊。抑郁现实主义比乐观幻觉更接近真实,但它自己并不就是真实。抑郁现实主义也不可能知道什么就是真实,它只是一种把寻找真实看得比真实更为重要的现实主义。正如费尔什姆所说:“我们不能肯定抑郁现实主义就是真实,它也许是倒数第二的真实(the penultimate truth)。”忧患意识并不能自动去除它自己可能包含的错觉或偏误。忧思者之间也会有谁对自己更为诚实的问题。自以为是的忧思者意识不到自己也会有错觉,这是一种自我欺骗。相比之下,有自知之明的忧思者则会对自己的偏误有所自觉认识,是忧思者当中比较诚实的一类。
三孤独的忧思者
乐观主义在任何社会里都是受欢迎的,因为乐观能让一般人快乐起来。乐观主义的励志和鼓舞也是每个社会都需要的。乐观主义看到的是正面的人生,因此经常会忽视人性中存在的荒诞、阴暗、软弱。乐观主义对人的情感脆弱、认知扭曲和心灵幽暗也缺乏应有的重视。因此,乐观主义会显得浅薄。著名英国犹太小说家霍华德·雅各布森(Howard Jacobson)说:“我写的每一本书都是末日幻想(apocalyptic),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有智识的乐观主义者。”
霍华德·雅各布森
在抑郁现实主义者看来,乐观主义的心灵鸡汤在社会里之所以如此供不应求,恰恰表明这个世界是多么不容乐观,多么缺乏幸福。对渴求心灵鸡汤的芸芸大众,抑郁现实主义的影响力永远不可能与乐观主义相比,明智的忧思者永远不会奢求拥有抗衡乐观幻觉的力量。这也是他们对励志说教的作用多有疑虑,忧心忡忡的原因。
忧思者是孤独的,他们不可能像乐观主义者那样拥有众多的粉丝、拥趸。不管他们多么一片苦心,多么为社会或世界的前景担忧,他们的忧思都只会吓跑那些他们想要劝诫的“快乐人群”。他们搅扰了快乐人群的乐观幻觉和安稳,就一定会招致众人的厌烦、憎恶和仇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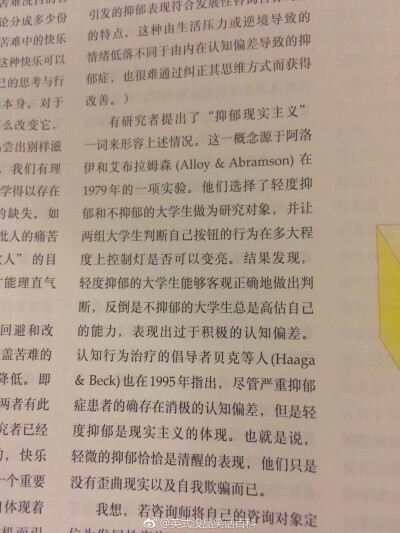
其实,渴求心灵鸡汤的芸芸大众并不可能单靠乐观幻觉生活,他们对世态炎凉、人心叵测、世道险恶不会没有经验的体会。正是因为他们需要平息自己内心的不安、焦虑、害怕,他们才越加需要心灵鸡汤的抚慰。古代的民间智慧中就已经有了许多包含忧思的经验之谈。在童蒙书《增广贤文》中有这样的例子:“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
快乐人群实际上生活在一种自我欺骗的矛盾状态中,他们在同一时间有着两种相互矛盾的想法——世界美好,世道险恶。这两种同时存在的矛盾观念让他们处于焦虑、不安、不能释怀的紧张状态。这就是社会心理学家费斯汀格所说的“认知失调”。费斯汀格指出,人在意识和知觉到自己有两个彼此不能调和一致的认知时,会感觉到心理冲突和化解冲突的需要。因此,认知冲突引起的紧张不安会转变为一种内在动机作用,促使个人放弃或改变两个认知中的一个,而迁就另外一个,借以消除冲突,恢复调和一致的心态。乐观幻觉就是为快乐而放弃真实的结果,而抑郁现实主义则相反。
在快乐人群看来,抑郁现实主义看待世界的方式是消极悲观,一片昏暗的——上帝不存在、政治制度失灵、社会道德崩塌、爱情维系于金钱、友谊变质为利用关系、教育无效、启蒙失灵。人在这样的世界里还怎么生存下去?但是,抑郁现实主义对现实有所忧虑(可能过于严重),并不会因此罹患抑郁症,而是保持一种旁观者的清醒,虽然悲观,但并不至于颓废或厌世。例如,存在主义哲学家和作家许多是对这个世界持警惕和怀疑态度的忧思者,他们看到人类生存境况的荒诞,但同时却比任何人都更坚持自由和本真的价值。
忧思者对现实的看法比较接近真实,这是一般化的假说,不同的忧思方式接近真实的方式是不同的。忧思的价值也许并不在于它究竟有多接近真实,而是在于,它虽不能找到那个可以确定无疑的“真实”,但却把追寻真实作为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追寻真实,这也使得抑郁现实主义与犬儒主义区别开来。在犬儒主义那里,既然人无法确定什么是真实,那么追寻真实也就没有意义,这也就导致了彻底的虚无主义。抑郁现实主义不接受这种虚伪主义。例如,一个抑郁现实主义者由于痛感世道的黑暗,发出对政治和政客的绝望悲呼:“天下乌鸦一般黑。”这个对现实的看法比起“大多数官员是好的”或者“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这类乐观的看法,应该是更加接近真实和现实。“天下乌鸦一般黑。”也经常是犬儒主义的说法。抑郁现实主义这么说,是认为当官的可以不像,也不应该像乌鸦,只要他们不像乌鸦,就可以有不贪不腐的官员。犬儒主义这么说,是认为,当官的不可能不像乌鸦,期待当官的不贪不腐,那是在白日做梦。
“所有人都在撒谎”
虽然抑郁现实主义会把现实看得很糟糕,但不像犬儒主义那样全然绝望,它还总是对转变的可能不死心。抑郁现实主义者追求真实,但从不放弃一种智识上的怀疑主义,包括怀疑他自己。这是一种挑战,考验他是否真的能够接受一种不包含(或尽量少包含)幻觉的生存意识。人总是会需要有某种提供给他安慰或幸福感幻觉的东西——宗教、信仰、政治理念、群体归属、民族身份等等。去除这些东西里面的幻觉就像要在沉思冥想时去除杂念一样,虽然可以一点一点地逼近,但很难进入一个全无杂念的纯净境界。沉思冥想的境界是一种孤独的体验,越是纯净,越是不可能传递给别人,更不要说让别人也复制他的体验了。抑郁现实主义的忧思者或许也是一样,就像你不能在人群里沉思冥想一样,你无法在一个组织或群体里与众人一起忧思。
抑郁现实主义只能是一种独思的方式,一种个人化的生活态度。一个人趋向于抑郁现实主义,经常是因为有了某种饱受挫折和不顺的经验,身处道德不明、善恶难辨的环境,或者像犹太人或真正的佛教徒那样,对自己的生存处境和人的命运有一种深刻的悲苦意识。但是,并不是所有拥有这类经验或身处相似环境的人们都一定会接受抑郁现实主义。是不是接受这样一种生活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一个人的性格或气质,而这种性格和气质则又与他的智识有关。但是,并不能反过来说抑郁现实主义者就一定都有智识。智识是勤于思考、善于思考的结果,而不会自动来自人的某种性格或气质。我们应该以勤于思考和善于思考来要求抑郁现实主义,只有这样,它的忧患意识和忧思才能变得更加成熟,也更加现实。
(Colin Felthan, Keeping Ourselves in the Dark, Nine-Banded Books, 2015)
*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