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之际与“秩序”格局:兼谈宋代士大夫对于《周易·家人》
在对于 中国 古代女性 历史 的 研究 中,“内”与“外”的界定与关系 问题 ,受到学者们持续而热切的关注[1]。
“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周易·家人》中这段彖辞的 内容 ,被古往今来的研究者作过种种阐发;对其议论与批评,频频出现于谈及传统中国女性地位的著述之中。
这一说法简单明了,并无晦涩聱牙之处;但在笔者个人的感觉中, 目前 的讨论就所涉及之层面而言,尚不能令人满意。对于与之相关的中国古代性别史研究中的一些实质性问题,例如内与外的关系、伦常秩序与“正位”的关系、“正家”与“治天下”的关系等等,有必要更加深入地思考。
一、关于“内外”之际
如研究者所指出,“宋代的妇女问题在 社会 史上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它与社会结构和家族制度的转变息息相关。”“从礼教、家长制、家族组织日趋严密这个较大的角度来看,妇女问题只是这个大趋势的一个环节,并不是独立的问题。”[2]
对于“内”“外”区分的问题,也有必要从“较大的角度来看”。讨论这一问题,首先涉及到的, 自然 是当时女性的实际活动空间。近些年来,这一方面的研究已经具备了相当的深度与广度,本文不拟笼统重复。
值得注意的另一相关方面,是强调“内”“外”区分的士大夫们的认识框架。当时的士大夫无疑在竭力规范女性的行为,但他们的这种努力,并不仅仅是针对女性的;这只不过是他们规范整个社会秩序之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即朱熹所谓“内正则外无不正矣”[3]。因此,如果我们想要真正瞭解这些范畴的实际意义,就不能不对当时的整体观念背景予以进一步思考。
(一)
内、外本来是一組空间概念,而它一旦与男、女对应起来,便涉及到观念中对于内外的判别,彰显出了一层道德文化的含义。刘静贞即曾指出:“对宋人而言,所谓妇德主内,妇人无外事,不单只是社会分工的现象,而且带有道德价值判断的意义。”[4]正因为如此,内外之际的分隔认定绝非简单问题。
我们所接触到的史料,几乎都是透过当时士大夫们的观察、思考而存留给后人的。不仅形形色色的列女传、墓志铭中寓有强烈的道德教化色彩,即便是“存于家”的记叙文字,目的也是“庶使后世为妇者有所矜式耳”[5]。在这种情形下,要讨论“内、外”的问题,就不可能脱离开当时士大夫的观念体系。
宋代士大夫对于“严内外之别”的强调,屡见不鲜。研究者所频繁引述的,是司马光《书仪·居家杂仪》[6]中的以下一段文字:
凡为宫室,必辨内外。深宫固门,内外不共井,不共浴堂,不共厕。男治外事,女治内事。男子昼无故不处私室,妇人无故不窥中门。有故出中门,必拥蔽其面(如盖头、面帽之类)。男子夜行以烛,男仆非有缮修及有大故(大故谓水火盗贼之类),亦必以袖遮其面。女仆无故不出中门(盖小婢亦然),有故出中门,亦必拥蔽其面。铃下苍头但主通内外之言,传致内外之物,毋得辄升堂室、入庖厨。
众所周知,这段话脱胎于《礼记·内则》中涉及男女行为空间的相应内容:
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内,不啸不指,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夜行以烛,无烛则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如若我们将二者稍加比对,即不难发现,《居家杂仪》对于《内则》之“ 发展 ”主要在于两处:一是以“中门”为限,强调了内外分界:“妇人无故不窥中门”,而当“有故”之际,所出也只能是“中门”,这样就从规范上把女性完全框在了宅院之中[7];二是把《内则》中“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的说法,直白地阐释为“男治外事,女治内事”,从而点明了“言内”与“言外”的实质含义。[8]
内外之分,就唐代的墓志来看,似乎较少正面具体的强调。唐代(特别其前期)的女性墓志铭高度程式化,往往依照一定的书写范式甚至套语敷衍而成。墓志中对于所谓“开芳兰蕙之姿,曜彩荆蓝之德”“内外之所取则,宗党之所归仁”一类“母仪女德”的赞颂,使读者体味到这类固定范式中所渗透的主流文化理念。
摆脱了靡丽模式的宋代女性墓志铭[9],对于“内外之分”的问题有许多直接的阐述。妇人不预外事,这在宋代当然被男女两性所认同。墓志的撰著者们既意识到明确内、外区分在伦理观念及整体秩序建设中的重要性,又显然意识到如此区分与之俱来的矛盾。
吕祖谦曾经说:“门内之治,女美、妇德、母道,三而有一焉,既足自附女史”云云[10],宋代士大夫所做女性墓志铭,经常刻意强调女性相对于父母、舅姑、丈夫、子女的家内身份及其相应的责任与义务。例如“以孝力事其舅为贤妇,以柔顺事其夫为贤妻,以恭俭均一 教育 其子为贤母”[11];“在父母家为淑女,既嫁为令妻,其卒有子为贤母”[12];“为妇而妇,为妻而妻,为母而母,为姑而姑”[13]等等。即便内容最为空泛的女性墓志,也很少忘记对于墓主人身份合宜之赞颂称扬。
在宋代的士大夫们看来,“内”之作用,无疑是辅助“外”的:丈夫们“尽心外事不以家为恤者,以夫人为之内也。”[14]“士大夫出仕于朝,能以恭俭正直成《羔羊》之美,必有淑女以治其私。用能退食委蛇,无内顾之忧。”[15]正是这种“辅助”带来了沟通与跨越的可能。“辅助”本指分担家内事务;而进一步的积极“辅助”,则势必逾越内外界线,过问乃至介入夫君子弟掌管的“外事”。
这使我们感到,在讨论“内/外”问题时,更为切近于主题、更能揭示其实质的,并非所谓“内”与“外”的隔离区划,而更在于二者相互交叉覆盖的边缘,在于其联系与沟通。
这一边缘地带的实际意义在于,它没有固定不变的界域,作为“内”与“外”两端的衔接面,它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内”或“外”,而可谓亦内亦外。在这样一个充满灵活度的弹性场域中,最容易观察到诠释者区分“内”“外”的判断标准及其如此区分的主观意图。这种互相连结、互相定位,甚至互相转换的模糊性,才是蕴涵“内外之际”真谛之所在。
(二)
《道乡集》卷三七有邹浩为周师厚妻范氏(范仲淹侄女)所做墓志铭,据说这位范夫人在子婿被贬逐之际,深明大义地说:“吾妇人不知外事,但各愿其无忘国恩而已。”在铭文中,邹浩继而赞曰:
惟文正,笃忠义,忘乃身,徇国事。习见闻,逮女子,施于家,率由是。自其夫,暨后嗣,助成之,靡不至。要所存,似兄弟,若夫人,可无愧。
所谓“习见闻”,是指范仲淹的处事精神被范氏经耳濡目染所自然继承,随后而“施于家”。而“笃忠义,忘乃身,徇国事”是士大夫们处理“外事”的原则,本来与“不知外事”的“妇人”无干。对此,最为方便恰当的解释自然是“自其夫,暨后嗣,助成之,靡不至”。在这里,“助成”二字轻而易举地将“内”与“外”联系贯通起来。
有一组例子颇有意思。梅尧臣在称赞他的妻子谢氏时,说到她的一种习惯做法:吾尝与士大夫语,谢氏多从户屏偷听之间,则尽能商榷其人才能贤否及时事之得失,皆有条理。[16]
无独有偶。苏轼在为其亡妻王弗所作墓志铭中也说:
客言于外,君立屏间听之,退必反复其言曰:“某人也,言辄持两端,惟子意之所向,子何用与是人言。”有来求与轼亲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与人锐,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17]
还有一位符氏,她丈夫张公雅
居常与士大夫议论,夫人多偷听之。退而品第其人物贤否无不曲当。[18]

另有一例,在《东莱集》卷十所收“汤教授母潘夫人墓志铭”中,吕祖谦不仅概括地称赞这位潘夫人“厘身治家,皆应仪矩”,而且具体地讲到她为教育儿子而养成的一种素习,即每逢客人到来,她总要“立屏间,耳其语”,亲自判断谈话内容有益与否。
这里有两个不同层次的相似之处使我们感到有趣。一是这些夫人行为举措的相似:她们显然都感觉到了自己处身于“内”“外”之间的为难,也都在找寻着“内”“外”之间可供她们存身的罅隙。曾经“立于屏间”的谢氏、王氏、符氏、潘氏夫人[19],都有一定的文化修养,而且显然对于“外事”一向有所瞭解;她们在家中有发言权,夫妻母子间能够有所沟通。这些夫人所站立的“户屏之间”,正是前堂与后室、外厅与内房的联系空间。就位置而言,因其处于牖户之后,可以归入“内”的范围;而选择此处站立,显然又是因其通向“外”室。就站立者关心的问题而言,亦属内外兼而有之:一方面“偷听”的是夫君子弟接触的“外人”与“外事”;而另一方面,这些外人、外事又因其与夫君子弟的关系而变成了“内人”们有理由关心的内容。正因为如此,夫人们似不因站立位置的尴尬而介意,丈夫子弟们也未因受到暗中的“偷听”而不快。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记叙者所持态度的类似。今天的读者似不必追究户屏间的`绝妙位置是夫人们自己选择或是墓志作者为她们安排,这些细节被堂而皇之地记载于她们的墓志之中,正反映出在欧阳修、梅尧臣、苏轼、陈襄、吕祖谦等人看来,这些“在深闺隐屏之中”[20]的女性关心外事(当然是与夫君子弟有关的“外事”)而遮掩行迹的做法相当“得体”。在陈襄为符氏所做的墓志中,干脆称她“事人有礼,居家有法”,“内以辅佐君子始终顺睦无须臾之失”[21]。在这里,“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的框架仍在,但其生硬粗糙的隔绝方式事实上被沟通内外的做法极大地软化了。
宋代士大夫撰写的女性墓志铭所载夫人们对于夫君、子弟的劝勉规戒,不必赘举;她们对于夫君、子弟经管的狱讼、政务乃至军事行动的说三道四甚至直接干预,也屡见不鲜。这些“无外事”的夫人们被记载下来的类似举动,经常受到赞许,称其夫君的成功“繄夫人之助乎!”[22]仁宗朝重臣孙沔的夫人边氏,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例。孙家不仅“家事无大小,决于夫人”,而且这位夫人相当积极地介入着丈夫对于“外事”的处理。据《陶山集》卷一六《陈留郡夫人边氏墓志铭》:
皇祐四年,广源蛮侬智高反,据邕州,朝廷倚公讨贼,乃除广南东西路经略安抚使。公以任重,尝退朝深念,夫人辄请公曰:“曷念之深也,如闻河陕之间骑卒精锐,宜若可使者。”适与公意合,遂请以从。厥后破贼,卒以骑胜。公还,上乃特赐夫人冠帔。[23]
如果说这位边夫人还是在内室之中参与谋议,那么南宋和州守臣周虎的母亲何氏则更走出了屏帷,在宋金和州之战中“巡城埤,遍犒军,使尽力一战”,事后宋廷封其为“和国夫人”[24]。
执掌家政的主妇所介入的“外事”,即便与夫君子嗣没有直接关系,如救济赈灾、水利兴修、寺庙整葺等区域性公益活动,也会因其有利于其家其族,有利于一方一时,有利于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而被予以肯定[25]。
看到这些材料,我们不禁想到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在当时的社会中女性们能动力之强。不少女性的所作所为,尽管仍然与她们的夫君、子弟之事业相联系,却明显地超出了“女教”、“女训”中对于她们的直接要求;而她们敢当危难的举措,显然又与她们所处的环境背景、所渐染的道德文化教养有关。
其次,或许更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于女性这样一些非同寻常的举动给予的“识理过人”之类评价[26]。士大夫乃至朝廷对于这些女性行为的认可、赞许与表彰,使我们想到,时人并非生活在单一的思维框架之下,所谓的“话语体系”也并非一成而不变。作为导向的严内外之别,并不能成为衡量女性行为的唯一尺度;日常年代中的“内外”界限,也并不适用于非常岁月。对于女性名份所要求、所允许的活动界限的确认,即使在传统社会中,行用标准也是多元的,是因时、因事而异的;其中发生作用的,并非一二僵滞固定的规范。社会意识的褒贬、传统观念的导向,首先是由具体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二、秩序:伦常与正位
(一)
在《礼记·内则》“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句下,有郑注曰:“谓事业之次序”。寥寥数语,将“内”“外”区分与“次序”——亦即次第秩序——明确地联系起来。这正提醒我们,要想对于宋代特定语境中的“内外观”有比较清晰的理解,亦须将其置于时人心目中理想的整体“秩序”格局中来认识。
所谓“秩序”,是指由高下次第、内外层次构成的井然而有条理的 网络 状系统。在这种网络系统中,人被充分地“角色化”了[27]。中国传统社会中,这种秩序的核心是区别尊卑等级、内外差次。
宋代士大夫对于秩序的强调,产生于对五代乱离教训的 总结 之中。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卷三四《一行传(序)》中,慨叹道:
呜呼,五代之乱极矣!……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
五代之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
宋儒们努力自根本处入手,以期杜绝这种“礼崩乐坏”局面的再度发生。他们对于“内圣外王”的追求,对于《周易》等儒家经典的重视与再阐释,正是出现于这一背景之下。宋代的儒家学者们,都强调《易》是圣人忧患之作[28]。欧阳修的同道石介在其《辨易》中说:“夫《易》之作,救乱而作也,圣人不得已也”;又说“作《易》非以为巧,救乱也。《易》不作,天下至今乱不止。”[29]李觏在其《易论》终篇也曾大声疾呼:“噫!作《易》者既有忧患矣,读《易》者其无忧患乎?”他继而讲到安危、存亡、治乱,忧患感的集中之处正在于社会秩序[30]。学术“以《易》为宗”的张载,其代表作《西铭》以“乾称父,坤称母”开篇,通篇阐述的,是他心目中的道德规范与理想秩序。宋儒都将《周易》视为寓意深远、体现“明体达用”精神之书[31]。
《易经·序卦》中追溯自然与社会的本源说: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这里所说的天地、男女、夫妇、父子、君臣,并非强调个体角色,而是讲相对的位置关系。这样一系列位置关系构成的,正是由“礼义”所规定所制约的社会秩序。《温公易说》“履”卦中,司马光说:
先王作为礼以治之,使尊卑有等,长幼有伦,内外有别,亲疏有序,然后上下各安其分而无觊觎之心。此先王制世御民之方也。
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关系的理想规范正是这样一种“尊卑有等,长幼有伦,内外有别,亲疏有序”的伦常秩序。依亲属差序格局组织起来的家,是礼的社会载体和物质保障,是使礼不断获得再生的丰沃土壤。强调礼的重要必定包含着对于家的推重;而强调家的组织与秩序,同时即巩固着礼的地位[32]。
《礼记·乐记》中说“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所谓“礼辨异”,是说礼的功能在于“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33],是“先王制世御民之方”。而正如贞观年间魏徵等人指出的,礼“非从天下,非从地出,人情而已矣。人道所先,在乎敦睦九族,九族敦睦,在乎亲亲,以近及远。亲属有等差,故丧纪有隆杀,随恩之薄厚,皆称情以立文。”[34]
尊尊亲亲。儒家理想中的这种社会秩序模式, 影响 了中国历史数千年。费孝通先生在其《乡土中国》中论及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的“差序格局”时说:
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潘光旦先生曾说:凡是有“仑”作公分母的意义都相通,“共同表示的是条例、类别、秩序的一番意思。”
一方面,家庭中有等级伦序,亦有亲情。在既有体系的背景下,等级与其相应的伦常规范,恰恰是维系亲情的手段;从整体结构上说,这正是保证伦理秩序所要求的。另一方面,秩序实际上是权力结构的基础。既有的等级秩序被不断强调、复制,形成为阻滞性的心态与结构性因素,从而限制了新的伦理秩序的产生。
(二)
在《易经》的诠释史上,对于“利女贞”的“贞”字历来有两种解释。一种释为“卜问”,一种释作“贞固”、“正”[35]。
宋儒大都继承释“贞”为“正”的说法。例如,“泛通《六经》,尤长于《易》”[36]的范仲淹在其《四德说》中讲道:
夫贞者何也?道之守者也。于天为行健,于地为厚载,于人为正直为忠毅,于国为典则为权衡,于家为男女正位、为长子主器,于物为金玉为獬豸,其迹异其道同。统而言之,则事干也。[37]

这种理解,显然反映着当时士大夫讲求义理的取向。具体到《家人》一卦,范仲淹解释说:
家人:阳正于外而阴正于内,阴阳正而男女得位。君子理家之时也。……圣人将成其国,必正其家。一人之家正,然后天下之家正;天下之家正,然后孝悌大兴焉。……故曰: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38]
内外家国的格局,是保证有效的社会控制所必需;“将成其国,必正其家”的思想,也是追求“内圣外王”的宋代士大夫之共识。欧阳修《易童子问》中,也将“利女贞”解释为“利女正”,并且说:
家道主于内,故女正乎内,则一家正矣。凡家人之祸,未有不始于女子者也。此所以戒也。呜呼!事无不利于正,未有不正而利者。圣人于卦,随事以为言。故于《坤》,则利牝马之正;于《同人》,则利君子正;于《明夷》,则利艰正;于《家人》,则利女正。
自戒惕“家人之祸”入手,作者上升到具有普遍意义的概括:“事无不利于正,未有不正而利者”;同时也指出“圣人于卦,随事以为言”,对于《易经》须作通贯的理解,才能明白每一卦中的含义。《易童子问》与前引范仲淹的《四德说》,其实已经显现出其后被程朱大加发扬的“理一分殊”思想。
所谓“正”,在程颐的心目中,主要是指中直不偏,合于规范;不失其中,各得其宜[39]。程颐《伊川易传》卷三《家人》对于“利女贞”的解释是:
家人之道利在女正。女正则家道正矣。夫夫妇妇而家道正,独云利女贞者,夫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女正则男正可知矣。
张浚在其《紫岩易传·家人》中说:
自古家国兴亡,莫不一本于女。……女贞,则无往不正也。故家人以女贞为利。……夫治乱自家始,家治自女贞始。[40]
“家国兴亡,一本于女”的说法,似乎凸显出通常被认为卑弱之女性的能动作用,较“凡家人之祸,未有不始于女子者也”的说法略显中正。但究其实,“女贞,则无往不正也”、“夫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其潜台词都预设女性自身道德被动而不易“正”;如若主家事之“女正”,则家内教化风气必然会“正”。
与“正”直接相关的,是所谓“正位”。程颐在解释“《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一段时说:
男女各得其正位也。尊卑内外之道正合天地阴阳之大义也。[41]
张栻在为吕祖谦《阃范》所作序言中,开篇即云:
天地位而人生乎其中,其所以为人之道者,以其有父母之亲、长幼之序、夫妇之别,而又有君臣之义、朋友之交也。是五者,天之所命,而非人之所能为。有是性则具是道,初不为圣愚而损益也。[42]
这就是说,“位”是随天地而来,既成且固定的。人生存于天地之间,只能顺乎其道而恪守其序。唐代孔颖达《周易正义·家人》中,说“尊卑有序,上下不失而后为家道之正”,这就是“正位”的实际含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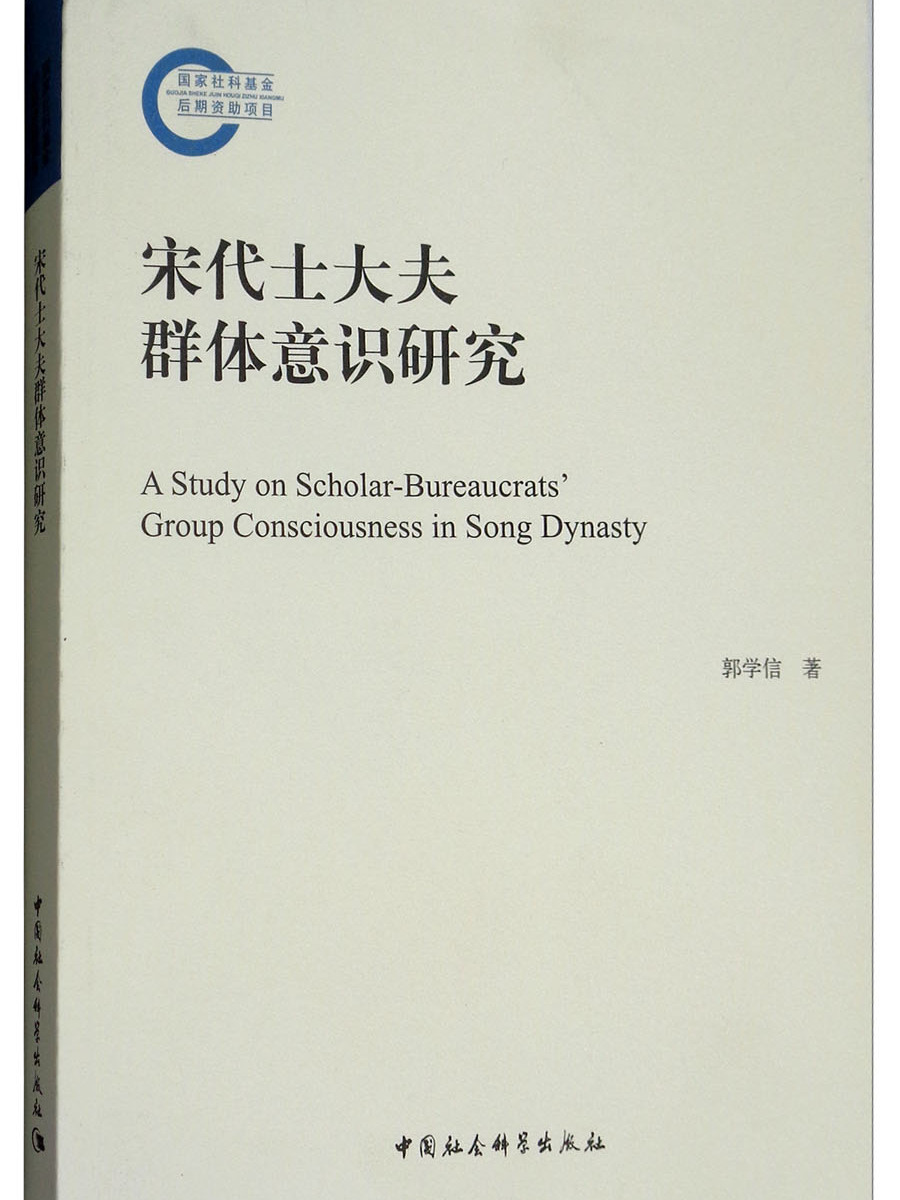
“正位”一词,突出了秩序格局中逐个位次的肃正不苟。唐代后期的李翱,在其题为《正位》的文章中说:
善理其家者,亲父子,殊贵贱,别妻妾,男女高下内外之位,正其名而已矣。古之善治其国者,先齐其家,言自家之刑于国也;欲其家之治,先正其名而辨其位之等级。名位正而家不治者有之矣,名位不正而能治其家者未之有也。[43]
看来,这里的“位”指的是“名分”、“名位”。“正位内外谓名分”[44],“名位不同,礼亦异数”[45]。“正位”建立在“别异名分”的基础之上。通过“别异”这种分化性的强制力,使群体得以组织成为一个层次性的秩序结构[46]。
儒家学者们通过对于《家人》的阐发,组接出了一串理想形态下的链条:女正——家道正——天下正。而当付诸实践时,这组链条的作用形式实际上是:正女——正家道——正天下;链条运转的推动者,则首先是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男性士人。这正如杨万里所说:“女非自正也,盖有正之者。孰正之?男也。正女以男,正男以父之身,正身以言行。”[47]宋代盛行的家训族规,社会上流传的诸如“教妇初来,教子婴孩”、“妇训始至,子训始稚”[48]一类谣谚,都使我们注意到“正女”的努力。
(三)
宋代的士大夫们对于感召“和气”与振饬“纪纲”两轴有着特殊的关心。贯穿这两端的,实际上是对于“礼治”秩序的追求。所谓“和气”,是指天地阴阳上下内外之间的和谐;所谓“纪纲”(纲纪),是指维持特定秩序的制度法规。司马光曾经说,“何谓礼?纪纲是也”;并且说:
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49]
这里所强调的名分位置固定、“上下粲然有伦”的内外秩序,是感召和气的基础;而这种秩序,又必须以“纪纲”来维持、通过“纪纲”来体现。这正是朱熹对孝宗皇帝说过的:“一家有一家之纲纪,一国有一国之纲纪。”[50]
北宋中期,程颢在回答“如何是道”的问题时说:“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妇上求。”[51]这是要通过对于秩序关系的体认来把握“道”[52]。释《归妹》卦,程颐反复讲“夫妇常正之道”,讲“男女之际,当以正礼”;称“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妇有唱随之礼,此常理也”。视男尊女卑为“序”,视夫唱妇随为“礼”,并将其认定为“常理”、“可继可久之道”。南宋初年,张浚释《家人》卦说:“家人,以礼为本。”[53]作为内外纲纪的礼制规范,渗透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之中。
从这里,我们又想到宋人的“内外观”。现实与理念的交错,使得“内”与“外”的界定颇不容易。就其宽松意义而言,与“家”、“家道”有关的一切皆可能被认定为“主内”者有理由过问的事务。“内”“外”之间界域的认定,并非完全取决于由门户构成的空间位置;女性跨越内外的活动是否能被认可,归根结底决定于亲亲尊尊的礼制规范,决定于当时需要维护的整体秩序格局。这里的关键不仅在于女性是否曾经介入家门之外的事务,更在于她们自身是否安守“名分”,她们的举措是否有利于召内外和气、立上下纪纲。守名分而保秩序,即可以被纳入“妇道”之列,被认为合于“礼”而居位“正”。
三、“正家”与“治天下”
(一)
程颐、朱熹等人对于《周易》的解释,基本上继承了王弼以来讲求义理的思路。但即以《家人》卦为例,我们又可以看出宋儒在阐释方面的侧重与发展。
据《周易正义》[54],“家人,利女贞”条,王弼注云:
家人之义,各自修一家之道,不能知家外他人之事也。统而论之,非元亨利君子之贞,故利女贞,其正在家内而已。
共2页: 1
论文出处(作者):未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