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朱良志,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教授。
摘要
中国传统艺术哲学存在着一种“无量”的艺术观念。这里从以物为量、大制不割、小中现大和一即一切四个方面来讨论这一观念。这四个问题都是由传统哲学引入、在艺术观念中深深扎根的重要理论命题:以物为量,重在放下以人为量的位置,会万物为一体;大制不割,突出传统艺术的浑一无分别观念;小中现大,超越有限与无限的相对性,在无小无大的非计量境界中,实现审美超越;而一即一切,重在说圆满俱足的道理。
关键词
艺术哲学;以物为量;一即一切;小中现大
中国传统艺术中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国的体验哲学,根本特点之一是对量的超越。它所呈现的是一种生命境界,这一境界是“无量的世界”。本文依次讨论以物为量、大制不割、小中现大和一即一切四个关键理论问题,以期见出传统艺术哲学这方面的思考。这四个问题都是由传统哲学引入、在艺术观念中深深扎根的重要理论命题。四个命题从不同角度,体现出“无量”艺术观念的内涵:以物为量,重在放下以人为量的位置,会万物为一体;大制不割,突出传统艺术的浑一无分别观念;小中现大,超越有限与无限的相对性,在无小无大的非计量境界中,实现审美超越;而一即一切,重在说圆满俱足的道理。
无量的哲学观念对传统艺术的形式创造产生重要影响。
一、以物为量
中国艺术哲学中有一种独特的“秋水精神”。
明沈周《卧游图册》十七开,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其中一开山水,画秋风萧瑟中,一人岸边树下,临水而读,老木萧疏,秋水澹荡,读书人神情怡然。其上有诗云:“高木西风落叶时,一襟萧爽坐迟迟。闲披《秋水》未终卷,心与天游谁得知。”在水净沙明的秋水边读《秋水》,心与秋水同在,进而与天地同游。画家就画这“心与天游”的共在。人此时是世界的“在”者,而非世界的观者。
《秋水》虽处《庄子》外篇,却是理解庄子思想的关键,此篇发挥《逍遥游》《齐物论》之大旨,带有提挈庄子思想的特点。前人曾有“吾读漆园书,《秋水》一篇足”的说法[1],以《秋水》篇概括庄子思想。在文学艺术领域,秋水精神,成为人与世界共成一天的代语。董其昌(1555—1636)说:“曾参《秋水》篇,懒写名山照。”[2]他读了《秋水》篇,就懒得去画名山了,因为有名山,就有无名之山,有名、无名的观念,乃是知识的分别,这样去画山水,是无法画出人独特的生命体验的。
《秋水》篇通过河伯与北海若的对话,重点讨论“量”的问题。秋水时至,百川灌河,两河之间,不辩牛马,于是河伯(河神)高兴不已,咆哮着、喧嚣着顺流而下——它见到了汪洋无边的大海。河伯本来以为“天下之美尽在于己”,而在大海面前,“乃见(现)尔丑”。河伯为大海巨大的体量而赞叹,而北海若(海神)却说,“吾在于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天地之间,物类繁多;时间绵延,无有穷尽;祸福相替,生生不已;美丑互参,因人而立,等等。若以知识的眼看世界,世界被人的知识分割,便没有了世界本身,唯留下世界的幻影。本篇大旨在超越大小多少、高下尊卑、美丑善恶等“量”的斟酌,将人从世界的外观者,变成世界的参与者。秋水精神,是洋溢着浓厚生命情调的从容自适精神,当人闭上知识的眼,开启生命的内觉,将生命的小舟摇进世界的芦苇深处时,水平风静,此时人与萧瑟的芦苇同在,与高飞的沙鸥并翼,哪里会有什么大、小、美、丑的分际。
从知识的的对岸回到生命世界的“秋水精神”,集中体现了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齐物哲学。秋水精神,也就是郭象所说的人与世界“共成一天”的意识[3],沈周所说的“心与天游”,也即此意。
秋水精神,要建立一种独特的“量”观,庄子将此称为“以物为量”。这四个字真可谓传统艺术发展的法宝。
“洞庭张乐地”是中国艺术的重要境界,出自《庄子·天运》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该篇写道:“北门成问于黄帝曰: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吾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荡荡默默,乃不自得。”[4]所表达的观点,表面看,其中“和”的思想与《礼记·乐记》“大乐与天地同和”的思想相似,然却有本质差异。《乐记》说:“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小大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显然,这是一种秩序的和谐,是高下尊卑的契合,是“量”的衡度。而洞庭张乐地的基本出发点,由惧到怠、由怠到惑逐步递进,乃在于荡去“量”的因素,“和”在无量中。
对于北门成的问题,黄帝的回答分成三部分,也即三“奏”。初“奏”使人“惧”:“四时迭起,万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伦经;一清一浊,阴阳调和,流光其声;蛰虫始作,吾惊之以雷霆;其卒无尾,其始无首。一死一生,一偾一起。所常无穷,而一不可待。汝故惧也。”阴阳调和、清浊有体的世界,是“量”的世界,人在此尊卑高下的“人境”,闻《咸池》之乐,忽如身置荒天迥地,顿生恐惧之感,恐惧中震落了秩序和知识的沾系,由“人境”向“物境”转换。由“惧”入“怠”,进入以物为量、当下圆满的境界中。黄帝说:“吾又奏之以阴阳之和,烛之以日月之明;其声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坑满坑;涂卻(隙)守神,以物为量……倘然立于四虚之道,倚于槁梧而吟。目知穷乎所欲见,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 形充空虚,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以物为量,泯灭人我的界线,消解无限与有限的分别,与万物相委蛇,此为无量之世界。第三境是由“怠”入“惑”,此描绘至乐之境的体验,齐同万物,无言而心怡,从而充满天地,苞裹六极,圆满而俱足。庄子说:“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载而与之俱也。”三“奏”之说,由量至于无量,由无量而至于充满圆融的“备物”之境,清晰展示了庄子无量哲学的大体思路。
“ 洞庭张乐地”的核心,是彰显生命的“真性”,其中提出的“与物为量”四字,在庄子哲学中具有重要意义。关于它的解释,郭象说,意同老子的“大制不割”。成玄英疏:“大小修短,随物器量。”[5]林希逸释云:“随万物而为之剂量,言我之作乐,不用智巧而循自然也。”[6]而清林沄铭所言更清晰:“此言乐之盈满,无所不周也……以物为量,因物之大小随其所受也。满谷满坑,就地言;涂卻守神,就人言;以物为量,就物言。”[7]
涂卻(隙)——堵住知识的缝隙,守神,所谓“塞其兑,守其光”,从而以物无量。以物为量,不以人为量,就是不以知识之量为量,随处充满,无少欠缺,在谷满谷,在坑满坑,以世界之量为量。此正是传统艺术当下圆满体验哲学的理论精髓。
庄子的“以物为量”,放弃知识之“量”,并不意味以外在客观真实为量,而是以无量为量。当然,以“无量为量”,也不是对“量”的否定。若如此,还是会落入知识分别中。以物为量的核心是对“量”的超越。《庄子·山木》说:“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以物为量,即是“以和为量”——从世界的对岸回到世界中,成就人与世界共成一天之境界。
正因此,庄子“以物为量”,其实就是“以物为怀”,没有直接的生命体验,也不可能出现物化于世界的无量境界。《庄子·齐物论》说:“圣人怀之,众人辩之。”怀,是体验的;辩,是知识的。庄子提倡“兼怀万物”的哲学,强调从知识的岸回归生命的海洋,因为知识的岸是无水的,相忘于江湖,才是生命久长之道。
“ 圣人怀之”“兼怀万物”的“怀”,与老子“为腹不为目”的“腹”意义相当。《老子》第十五章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目”,指代以人的感官去分别世界的方式,其结果只能是人对世界的界定,造成人与世界密合关系的破裂。而“腹”,是以整体生命去体验世界。“腹”,与后世艺术论中所言“澄怀观道”、禅宗“智慧观照”的“观”意思相当,它是生命的内觉,是超越主客的纯粹体验活动。
“怀”“腹”“观”三字,是标示传统哲学体验法门的重要概念。没有体验,也就没有这里讨论的一花一世界的艺术哲学。中国艺术哲学的“一花一世界”观念,乃是超越知识的生命体验之道。它是由对“知”的反思所带来的生命颖悟。抑制了“人”的成分,一朵小花才能成为一个圆满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一花一世界的哲学,就是创造一个“非人”(非知识、非名利、非情感、非美丑)的世界,还世界以本相,将世界从人的霸凌中拯救出来,从知识、情感之“封”中解救出来。
董其昌说:“知之一字,众妙之门;又有云:知之一字,众祸之门。”[8]对于知识,中国哲学注意它的两方面特点:知识是力量,知识也是障碍。知识的累积是文明推进的重要标志,而自先秦始,中国哲学就对知识持有警惕的态度。从老子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庄子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到禅宗的“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哲学,都反映出这种思想倾向。中国不少思想者看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冲突,但解决之道,不是以知识去征服它,以人的力量去战胜它,而是超越知识藩篱,克服人目的性活动,在顺应自然之势中拯救生命。在西方,是“我思,故我在”,而在中国很多思想家看来,却可以说是“我思,故我不在”。这绝对不意味中国人提倡蒙昧主义,是反智论者,它反映的是中国传统思想发现并展拓生命内在动能的努力。
秋水精神,以物为量,兼怀万物,三者说法不同,意则一也,都指向超越知识分别、会归于万物一体之境界,它是以体验为中心的传统审美认识方式形成的基石。
二、大制不割
郭象以“大制不割”四字来注释“以物为量”,二者意思相近,理论侧重点则不同。以物为量,强调融与物的态度;大制不割,则突出一种哲学观念:无分别见。
《老子》第二十八章云:“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9]
挣脱人的知识观照,幽暗,混茫,空空落落,无边无际,是朴——未被打破的圆融世界,在这里没有知识分别,如同婴儿一样自然存在;没有争斗,保持着永恒的雌柔;就像天下的溪涧,就像清气流动的山谷,空灵而涵有一切,流动而不滞塞,虽柔顺而具有无穷力量。
老子以“大制不割”来描绘素朴世界。大制,最高的制式和原则。割,裁割,分别[10]。老子认为,最高的制式、最根本的裁制,是不分别,是“朴”。朴者,未散也,未分也。他说:“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素朴、浑沌,是与知识分别相对的世界,纯全未雕,也即他所说的拙、愚之境。本章所说的“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也是言此。婴儿者,未分之浑然状态;无极者,未有知识分别之初始境界。圣人,老子常用其形容最高境界的人。官长,即庄子所说的“官天地、府万物”(《德充符》)。圣人以此无分别之法,去裁制群有,贯通天地。
大制不割,与老子的“抱一为天下式”为同样道理。所谓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云云,这个“一”,是不分别的世界,也即“不割”。老子思想归宗于“一”,这与《维摩诘经》纵论之“不二法门”,可谓不谋而合,虽然论述侧重点有不同,但不分别之意旨则是一致的。
老子的思想并非强调原始的和谐,而是要以自然无为取代人工强为,以素朴纯全代替矫揉造作,以平和平等代替世界的你争我夺,以空灵之心去涵括天下的美。大制不割是人与世界共生之道,具充满圆融之美。

以不分别的心去官天地,府万物,裁制世界,是“当下圆满体验哲学”的理论核心。
《庄子》发展了这一思想。《应帝王》说:“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这是内篇最后一段话,一般认为,内篇为庄周所作,这段话庄子带有总括自己思想的意味。
甚至可以说,庄子的哲学就是浑沌哲学。知识、理性的世界是清晰的,浑沌的世界是幽暗的。但庄子认为,世人所认为的清晰世界,是真正的不清晰,以表面的合理,打破了生命的原有秩序。而浑沌世界虽幽暗不明——没有以知识去“明”——但却是清晰、纯粹的。其实,老子的“明道若昧”“见小若明”等,说的也是这个意思。理性的世界秩序化,有条理,浑沌世界无分别,是无“理”的世界。但在庄子看来,人们热衷于建立的那种秩序、理性多为荒诞不经,与人的真实存在相违背,人的知识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人套上枷锁,而浑沌世界没有这样的招数,它是人的生命存在之所。
大制不割的思想,给中国艺术发展注入特别动力。没有这种思想的出现,可能传统艺术的道路会向另外方向发展。带来的不是效法天地的传统,而是与世界融通一体的精神,中国艺术当下圆成的体验哲学,便是在此理论基础上形成的。这是形成中西艺术差异的根本思想观念之一。这里讨论两个问题。
(一)与天为徒
在西方哲学中,自古希腊开始,就有一种系统的模仿自然的思想,而在中国,师法造化,也是其根本原则。《周易·系辞上传》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法象天地,效法自然,以造化为最高范式,这是中国文化的根本原则。艺术观念也深受其影响。如“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中国艺术的最高纲领,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巧夺天工,追求天趣,这些观念深刻影响着传统艺术的发展。这一思想极为复杂,我们不能简单将此判为“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将其理解为对外在自然的效仿。
即就天人一体哲学来看,也有不同的理论侧重点:一是以人合天,以主体为主,通过人的创造,去融合天地,进而达到天人之合一,这是一种形式。此中的天,是理性、秩序的存在。二是以天统人,以天为效法对象,匍匐在天地之下,甚至认为“自然全美”——自然具有比人更全面、更完美的体现,天工开物,鬼斧神工,以宗教的感情对待外在自然,这也是一种形式。此中的天,是信仰之对象。但是,与上述两种形式不同的是,既非以人合天,又非以天统人,而是没有天,没有人,只有一个浑沦的世界。不将人从天中划出,人即天,天既不在心内,又不在心外,这是生命体验论中的天人一体论,这是第三种形式。在唐宋以来的艺术传统中,这第三种形式最具影响力,它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早期的效法天地的创造模式,由天人一体哲学转化出一种生命体验的理论。
庄子曾提出“与天为徒”的思想,这很容易被理解为“师法自然”。表面看来,“与天”——与天相处,说的是人与天之关系;“为徒”,说以徒的态度对待天。这样,天是师,人是徒,反映的是人以自然为师法对象的态度。这就像以“向外重视客观自然,向内重视主观创造”的内外结合论来理解“外师造化,中出心源”是误读一样,将“与天为徒”理解为以自然为师,也是对庄子哲学的绝大误解。
《庄子·大宗师》说:“古之真人,其状义而不朋……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真人,至高的理想人格。“不朋”,如石涛所说“古人之法在无偶”的“无偶”[11],是浑朴、绝对而无分别的,也就是“不割”。郭象注此云:“其一也,天徒也;其不一也,人徒也。夫真人同天人、均彼我,不以其一异乎不一。”“真人”好之在“一”,指的是“一”而不分之境界。所厌恶者也是“一”,这里的“一”与“不一”相对,是分别的。而“真人”所好之“一”并非与“不一”相对,它是“不割”,是绝对的。以佛学的概念说,是不二的。所谓“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既不“一”,又非“不一”。同天人,齐万物,与物为春,以物为量,兼怀万物,一体而已。故“天人不相胜”,天与人为一体,不存在与谁争锋的问题。它与传统哲学所言“天人交相胜”的观念迥然不同。
正因此,庄子所言“与天为徒”,无天人之别,也无师徒之关系。人不是效法天,以天为师法之对象,而是浑合天人,所谓“休乎天均”是也。“与天为徒”句式结构,如“予方将与造物者为人”“与物为春”一样,我“为徒”像天一样,天是如何“为徒”,天无所师,也不为徒。故“与天为徒”的意思,就是无徒,无师。天何师也,自师也。自本自根,自发自生。
其实,这也是老子的思想坚持。《老子》第二十五章说:“天大,地大,道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人居其一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所说的人、地、天、道、自然五个概念,极易使人理解为层级关系,人效法地,地效法天,天效法道,道效法自然,层层递进,如果这样理解的话,“抱一为天下式”便无从着落,乃是明显的“割”——分别之见了。道是独立无待的,是一种自然无为原则,当人挣脱有为的束缚,也即归于道的真实中。道之大,不是体量之大,而是天地自然中所存有的自己而然、无为不作的特性,如山谷之空,无有穷极,无所不在,弥所不包,故称为大。道即是自然,道法自然,不是在道之外有一个自然,即道即自然即天地。人放弃了分别的见解,乃臻于“即道即自然即天即地即人”的境界。庄子的“与天为徒”所包孕的正是此一思想。
揆此之论,来看古代艺术论中的师法自然说。明末董其昌关于师法自然有系统论述,请看以下三段论述:
画家以天地为师,其次以山川为师,其次以古人为师。故有“ 不读万卷书,不行千里路,不可为画” 之语,又云“天闲万马吾师也”。然非闲静无他,好萦者不足语此。噫! 是在吾辈勉之,无望庸史矣。(《自题画稿》,《珊瑚网》卷四十二引)
画家初以古人为师,后以造物为师。吾见黄子久《天池图》,皆赝本。昨年游吴中山,策筇石壁下,快心洞目,狂叫曰“黄石公”。同游者不测,余曰:“今日遇吾师耳。”(《跋黄子久浅绛色山水》,《珊瑚网》卷三十三引)
画家以古人为师,已自上乘,进此当以天地为师。每朝起看云气变幻,绝近画中山。山行时见奇树,须四面取之。树有左看不入画、右看不入画者,前后亦尔。看得熟自然传神,传神者必以形,形与心手相凑而相忘,神之所托也。树岂有不入画者,特画收之生绡中,茂密而不繁,峭秀而不蹇,即是一画眷属耳。(《容台集》别集卷四)
第一段话中谈及三个师法对象,山川和古人,意思同他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知识和经验的累积。令人诧异的是,为何在山川之外,还另立“天地”一目? 这正是董其昌的慧心之处。此天地,非日月丽天、江湖行地的具体自然,而是指体验之真实、心中之造化。这个天地之师,乃是“天闲万马”之境。《庄子·马蹄》中说:“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董其昌“天闲”之境本此。他以天闲万马为师,即天人一体、外无所师、师心独见之谓也。董其昌论艺,既强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知识积累,又强调“气韵不可学”的内在性灵颖悟(此非指先天禀赋),二者并行不悖,但始终将“一超直入如来地”的当下直接体验作为最高生命境界。它不是对知识的排斥,而是对知识的超越。
第二段话中的以古人为师、造化为师,与第一段话前两个师法对象相同,而“今日遇吾师”之师,乃在“师心独见”,在自己当下的体验。第三段论述也如此,它强调的“以天地为师”,也就是“形与心手相凑而相忘”的体验境界。“天地”不是外在于我的对象,而是当下所发明的生命真实,“天地”是一时敞亮的生命境界。
由此来看唐代张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它显然不是有的论者所说的向外效法自然、向内重视内心的主客观结合,这种二分的观念,不符合传统艺术哲学的事实。清戴熙说:“画以造化为师,何谓造化,吾心即造化耳。吾心之外皆习气也。故曰恨古人不似我。”[12]造化不离心源,不在心源;心源不离造化,又不在造化。造化即心源,心源即造化。脱心源而谈造化,造化只是纯然外在之色相;以心源融造化,造化则是心源之实相。即造化,即心源,即实相,此乃“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思想内核。
(二)追求无限
大制不割思想的影响,也使传统艺术哲学对有限与无限的关系,有了独特的理解思路。
有限与无限的关系,是传统艺术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有限与无限是一对矛盾,中国哲学重视由近及远,推己及物。心灵的推展,是中国艺术的命脉。汉代人就有一种“大人游宇宙”的心态,推崇“大其心”,与天同流,从而“包括宇宙,总览古今”。魏晋以降,高蹈之风吹拂于士林,士人的理想人格是那无古无今的大人先生,这是一种超越有限、臻于无限的人伦典范。所谓“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抗心乎千秋之间,高蹈乎八荒之表”。晋人在观照自然时说:“江山辽落,居然有万里之势。”这种心态也影响了处于草创之初的山水画,山水绵延无际,而人目所见不过数里,要图之于绢素,真是神笔难追。因此在早期山水画论中,就把山水之“大”和图画之“小”相对而言,并且提出以“势”来克服“小”的局限,复现山水之“大”。宗炳《画山水序》云:“且夫昆仑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则其形莫睹,迥以数里,而可围于寸眸。诚由去之稍阔,则其见弥小。今张绢素以远映,则昆阆之形,可围于方寸之内。竖画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杜甫《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中也说:“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在有限中追求无限之趣,成为一种艺术趣尚。
宗白华先生认为,对无限性的向往是中国艺术的重要特色。他说:“古希腊人对于庙宇四周的自然风景似乎还没有发现。他们多半把建筑本身孤立起来欣赏。古代中国人就不同。他们总要通过建筑物,通过门窗,接触外面的大自然界……‘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诗句),诗人从一个小房间通到千秋之雪、万里之船,也就是从一门一窗体会到无限的空间、时间。这样的诗句多得很。”他将此当作小中见大的典型,通过人的感觉器,由小空间引入大空间,丰富了美的感受。“外国的教堂无论多么雄伟,也总有局限的,但我们看天坛的那个祭天的台,这个台面对着的不是屋顶,而是一片虚空的天穹,也就是整个宇宙作为自己的庙宇。这是和西方很不相同的。”[13]
但是,放到大制不割的无分别哲学来看,这样的说法又有值得斟酌的地方。依此无分别见,必然是有限与无限的弥合。而纯粹体验的境界是没有有限与无限的,当下圆足,就意味着对无限的消解。小中现大,不是由小去看更广阔的世界,以有限去追求无限,而是大在小中,无限就在有限中,或者说没有大小,没有无限与有限。心性的俯仰舒卷,所谓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是对当下此在心灵悦适的描绘,而不是由近及远、俯视群伦、仰望苍穹所带来的满足。在体验境界中,独成其天,小就是一片“天”,此天就是一个充满的世界。所谓“但教秋思足,不必月明多”是也。实际上,在陶渊明的观念中,就有对无限性消解的思想,他的“万物自森著”“寒华徒自荣”的哲学,绝灭了无限的引领,赋予东篱下瞬间观化体验的整全意义。
要言之,唐宋以来的艺术观念的变革,是在无分别哲学基础上对艺术本质的反思。礼乐文明,比兴传统,载道指向等,构造出中国独特的艺术思想传统,从本质上是以表面的合理,打破生命的原有秩序,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艺术的题中应有之义。当下圆满的艺术体验哲学,是为了归复真性,归复艺术表现的根本对象——生命的原有秩序。我们在艺术中看到的枯木寒林、荒寒寂寞的表现,不是欣赏趣味的变味,而是为了打破那表面的合理秩序,那些被说成是天经地义的原则。
三、小中现大
文徵明说:“我之斋堂,每于印上起造。”[14],小中现大,心中的方寸天地可以再造一个世界。这个浪漫说法,关乎传统艺术创造的一条重要原则。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传为董其昌所作之《小中现大册》,乃仿宋元名家山水之作,所仿者有范宽、董源、巨然、王诜、高彦敬、赵孟頫、黄公望、吴镇、王蒙、倪瓒等,书和画共二十二对幅。册前所题“小中现大”四字,当为董其昌的手笔[15]。
“小中现大”四字,本于《楞严经》,该经卷四云:“我以妙明不灭不生合如来藏。而如来藏唯妙觉明,圆照法界,是故于中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小中现大,大中现小,不动道场遍十方界,身含十万无尽虚空,于一毛端现宝王剎,坐微尘里转大法轮,灭尘合觉,故发真如妙觉明性。”[16]《楞严经》讲“性觉妙明”和“本觉明妙”的道理。性觉,以不缘他体而自具的觉性去妙悟,照彻无边法界。本觉,是本心被妄念染著,经修习而破除迷妄,还归本明。无论本觉、性觉,觉者都具如来藏清净本然觉性,此觉性不生不灭,无小无大,彻内彻外,一片光明。
“小中现大”四字,不啻为文人画真谛之发现,所重即在本然觉性的发明。古今演绎“文人画”之义多矣,其中最关键一点,就是一己真心之发明。没有这“一点灵明”,就无法出“真”境;有了此“一点灵明”,就能超越一切知识形式的“量”观,而圆明自照。本心是发明,而不在造作。小中现大,此心是普遍的,人人具有,像佛教所说的人人都有的如来藏清净心。人本有其心,因妄念遮蔽而难现,在妙悟中引出“心源”之光,使其“现”之,哪里需要外在光明照耀! 北宋苏辙说:“大而天地山河,细而秋毫微尘,此心无所不在,无所不见。是以小中见大,大中见小,一为千万,千万为一,皆心法尔,然而非有所造也。”[17]小中现大之法,是独特的心法,发明生命本性之智慧,以一点灵明照彻无边法界的大用。它直指本心,不是外在的刻意造作。此乃传统艺术哲学之要则。
关于大和小的驻思,伴着中国思想史甚至艺术史的发展过程。人的生命短暂而脆弱,大,意味着对超越有限的无限境界的向往,在冲突中对人类力量感的推重,在征服中对权威和控制的迷恋。而小,则意味对人类无法真正左右世界能力的承认,选择自制、约束的道路,专注于自我、当下的作业。大,是向外的推展;小,是向内的收摄。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从重视大到重视小的过程(如先秦思想重视“大”,孟子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易传》推崇“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的“大人”品格,等等)。反映在艺术中也是如此,汉唐气象与宋元境界,就有明显的不同,前者浑穆而崇高,后者精致而玲珑;前者重视力的图式,后者更重视内觉的发明。
有僧问赵州大师:“如何是和尚大意?”赵州说:“无大无小。”[18]“无大无小”四字,是一种不同于大小之别的思路,在中国思想史中具有重要价值。小中现大哲学的核心,乃在无大无小。大小之观,乃量上斟酌,与本然真觉相违逆。在先秦时,此一思想即露端倪。老子以“大”名“道”,然其尚大而不在大,立意在无大无小。《老子》二十五章将道称为“大”,所谓“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但他有时又称“道”为“小”。第三十四章云:“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道无所不在,是为“大”,功成而弗居,是为“小”,老子以此非量的境界,来粉碎人们大小多少、高下尊卑的知识考量。
从庄惠之辩中也能看出这一点。《庄子·天下篇》引惠子语道:“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大一,是无穷大的宇宙;小一,是无穷小的世界,惠子说的是有限与无限的相对性。他是博物学家,泛爱万物,曾叹云:“天地其壮乎!”他肯定天地的“大”,这“大”是就体量上所言。惠子以“大而无当”讽刺庄子。庄子所向往的境界,总在“广漠之地”“无穷之门”“无极之野”“无何有之乡”。惠子说庄子的理论“大”,意思是说他所言太空泛。而庄子所言“大”,与惠子有本质区别。他的“大”是一种超越知识的生命情怀,而非数量之观。《庄子·德充符》说:“眇乎小哉,所以属于人也! 謷乎大哉,独成其天。”人是小的,天是大的。人何以会小? 不是体量上小,而是人处于大小多少、尊卑高下的知识体系的网罗中,从而局碍了心灵,故而为小。他要返归天之“大”,休乎天钧,与造化同流,不以大为大,故能成其大[19]。惠庄之“大”,一就体量言之,一超越体量,二者划然有别。
“无量”的思想,照耀着中国审美的传统。通过生命体验而创造一个无量世界——独特的生命境界,成为唐宋以来艺术创造的重要理想。这一境界不需通过量的广延,来实现其意义;又没有沦为象征媒介,使存在的意义被剥夺。它是自足、无待的,又是非给予、非从属的。它超越物的控制性思维,而进入自我当下的纯粹体验中。它是“寓意于物”(此寓意非指象征寓意,而指融意于世界中),而非“留意于我”,它在物我一体的世界中实现圆满。
南宋冯多福《研山园记》论园林说:“夫举世所宝,不必私为己有。寓意于物,固以适意为悦。且南宫研山所藏,而归之苏氏。奇宝在天地间,固非我之所得私。以一拳石之多而易数亩之园;其细大若不侔,然己大而物小,泰山之重,可使轻于鸿毛,齐万物于一指,则晤言一室之内,仰观宇宙之大,其致一也。”[20]元杨维桢(1296—1370)为顾瑛(1310—1369)所写斋记中说:“大地表里,皆水也,大罗竟界,一渣之浮急,旋水中央,而人不悟,悟者必在旋之外也。吁,天,一大瀛也;地,一大舫也;至人者,以道为身,入乎无穷之门,超乎无初之垠,斯有以见大舫于舫之外。”[21]沈周《题许由弃瓢图》诗云:“一物有一累,吾形犹赘然。区区此勺器,亦合付长川。浩浩天地间,吾亦一瓢耳。吾哉与瓢哉,大观何彼此!”[22]
这里反映出传统艺术中超越大小的思维,人在天地之间如一瓢之微,树立生命之“大观”,开宇宙之目,发明庄子所说的“謷乎大哉”的“天”之见,便没有了彼此,腾踔于蓬蒿与天地之间,遁乎大小多少之羁縻,于舫内见舫外之思,由物中得物外之趣,卒然而成就生命之高蹈。于此之时,小筑亦可成大观,勺器也可合大川,一拳顽石就是一个宇宙。深通艺道的明代艺术家唐顺之(1507-1560)《小砚铭》云:“大者凝然利以居,小者翩然利以行。不有居者墙壁户牖,谁与供十年之著述? 不有行者苍山白水,谁与收五岳之精英?”[23]他所谓小,怡然自足心灵气象之谓也。
此大观之法,或可称为“无量艺术哲学”,它与艺术论中一些强调量的广延的思想旨趣大异:
第一,它不是传统哲学和艺术观念中流行的概括之说。像《周易》“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以大”的类的推衍思想,《文心雕龙·物色》中所说的“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都属于一种概括论,以少概括多,通过某些方面的强调反映更丰富的内容,终究还是出于量的考虑,与此“无量艺术哲学”不同。
第二、它也不是实景的微缩化,如今天城市景观中流行的微缩景观,将实际景观按比例缩小,从而使人在较短时间里领略丰富的景色,这是按比例的“量”的斟酌。
第三,它更不是西方艺术理论中的典型,二者一强调体验,一强调再现,有根本差异。
这种“无量艺术哲学”对传统艺术形式创造有深刻影响,如以下形式创造原则:
(一)不在繁简
程正揆(号青溪,1604—1676)说:“画有繁简,乃论笔墨,非论境界也。北宋人千邱万壑,无一笔不减,元人枯枝瘦石,无一笔不繁。”[24]
身为明末清初一位大艺术家,青溪是真懂中国艺术的人。世传他论画主张“画贵简,不贵繁”,其实他的真实思想是:不论繁简,唯论境界。繁简乃数量之观,境界乃生命创造,这是文人艺术的根本形式法则。
清金农画一枝梅花,题云:“损之又损玉精神。”损,是老子自然无为哲学的重要概念。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损,显然不是减少,或者做减法,不是数量上的变化。它与“为学日益”相对,损道乃超越知识的无为之道。一枝梅花,并不见其少,满幅乱梅并不觉其多,其中关键在于人本心之发现,而不在形式之多寡。正因此,损道是性灵大全之道,是生命创造之道。中国艺术重视简约,不能从形式繁简论上考量,在文人艺术中更是如此。书画中重视空灵,也不能简单理解为“留白”,疏处可走马,密处不透风,其妙并不在形式的通透和滞塞;中国艺术重视简淡,也不意味艺术家认为淡然无味比浓郁灿烂好。数枝红蓼畔,一片白云孤,皆可成妙境,关键是心之体验。
五代青莲寺的大愚禅师,与荆浩为友,想得到荆浩的画,作《乞荆浩画》诗以求:“大幅故牢健,知君恣笔踪。不求千涧水,止要两株松。树下留盘石,天边踪远峰。近岩幽湿处,惟藉墨烟浓。”荆浩欣然为之画,图成,答以诗云:“恣意纵横扫,峰峦次第成。笔尖寒树瘦,墨淡野云轻。岩石喷泉窄,山根到水平。禅房时一展,兼称苦空情。”[25]
求画者以“不求千涧水,止要两株松”相请,作画者以“笔尖寒树瘦,墨淡野云轻”作答,二者通过深层的心灵交流,陈述着删尽繁冗、走向真实的道理。水无喧嚣之势,山在有无之间,将人带入飘渺淡然的境界中。此一对话,在中国艺术中颇具象征意义,外在的体量和形势,不是文人艺术追求的中心,而心灵境界的呈现,方是艺术家理想之天国。
“一勺水亦有曲处,一片石亦有深处”[26],这是清初恽南田(1633—1690)的重要观点。对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国的哲思,南田体会极深。他说:“云林画天真澹简,一木一石,自有千岩万壑之趣。今人遂以一木一石求云林,几失云林矣。”[27]云林的画是不论繁简、唯论境界的典范,如渐江《画偈》有诗云:
“传世云林子,恐不尽疏浅。于此悟文心,简繁同一善。”[28]简繁同一善,画到无繁无简处,方时达到至
境时。
( 二)不在多少
传统绘画有折枝一种,起于五代,大盛于南宋,元以来又有发展。此类画构图简省,往往树取一枝,花出几朵,倏尔成相。五代时黄筌、赵昌花鸟时有折枝之作,这类作品重视写实,往往取一个截面,对形式作简约化、微缩化处理。南宋纨扇小品中折枝之作甚多,注重装饰性,追求生动传神地表达。
传统绘画中有另一类作品,形制有纨扇、册页,间有卷轴之作,类型上有山水,也有花鸟,这类作品追求高逸情致,构图简单,颇为文人艺术所重。北宋文同善画一枝竹,南宋扬补之善画一枝梅,南宋末年赵子固善兰花,往往画面就是一株,元柯九思、倪云林善潇洒出尘的竹枝,明沈周善写生之趣(如《卧游图册》),清金农喜画损之又损的墨梅,等等。这类作品虽然很难概括为统一的形式,但在生命境界呈现上却有一致追求,它们与传统折枝画在构图上有相似之处,都很简约,但与折枝之作却有根本差异,它们将境界作为艺术创造的根本追求,并不在形式上呈现的物象之多寡。
此类作品,是当下圆成生命哲学的活泼呈现。文同画竹枝,时人有“参差十万丈夫”之评,一花一叶,构成独特的生命境界,传递人微妙的生命感受。元延祐年间“山村居士”题赵子固《四芗图》:“淡墨英英妙写真,一花一叶一精神。繁香曾入庐山梦,遗佩如行湘水春。”[29]这一花一叶一精神,是一种生命的展现,写真者,不是为人为花造影,而是为世界“泻”出真趣。
北京故宫藏元陆行直《碧梧苍石图》,是陆存世孤本[30]。此画画湖石、梧桐、柏树,笔墨清润。湖石当中而立,孔穴多多,如同岁月苍莽,留给人梦幻记忆。其上陆行直题云:“‘候蛩凄断,人语西风岸。月落沙平流水漫,惊见芦花来雁。可怜瘦损兰成,多情因为卿卿。只有一片梧叶,不知多少秋声。’此友人张叔夏赠余之作也。余不能记忆,于至治元年(1321)仲夏廿四日戏作碧梧苍石,与治仙(按:即陆留,上有陆留题跋)西窗夜坐,因语及此,转瞬二十一载,今卿卿、叔夏皆成故人,恍惚如隔世事,遂书于卷首,以记一时之感慨云。”张叔夏,即南宋大词人张炎(1275—1349 后),《清平乐》词中所言“只有一片梧叶,不知多少秋声”,虽从古语“落一叶而知劲秋”化来,却表达出艺术家斯时斯地微妙的生命体验,俨然成为传统艺术的审美理想世界。
元人好竹卷,所谓“水墨一枝最萧散”,可能受文同影响,元人常画一枝竹,却敷衍为长卷,这是极难的创作,赵子昂、顾安、柯九思、倪云林等均善此类。上海博物馆藏柯九思墨竹图两段,曾经明末大书家邢侗鉴定,前段唯有一枝竹,上有伯颜不花之题:“予旧藏东坡枯木竹石一小卷,每闲暇,于明窗静几间,时复展玩,不觉尘虑顿消,愿得佳趣耳。一日,友人赠我文湖州墨竹一枝,与坡仙画枯木图高下一般,不差分毫,喜曰:此天成配偶也。”跋中涉及“墨竹一枝”的由来及其独特价值。
云林毕生喜画竹。传统竹画追求“此竹数尺耳,而有寻丈之势”,他却对“势”——一种独特的动感——的追求并不热衷,却更愿意通过竹画来表达随处充满、无少欠缺的精神。他喜画一枝竹,其《竹梢图》,没有繁复的形式,只是略其意趣。题云:“此身已悟幻泡影,净性元如日月灯。”台北故宫藏其一竹枝册页,上云林题云:“梦入筼筜谷,清风六月寒。顾君多远思,写赠一枝看。”[31]同样藏于台北故宫《春雨新篁图》,也画一枝竹,上有多人题跋,其中叶著跋云:“先生清气逼人寒,爱写森森玉万竿,湖海归来已蝉蜕,一枝留得后人看。” [32]他的一枝竹中有不凡的思考。
(三)不在小大
这里在由园林营造来略加讨论。英国哲学家培根(1561—1626)论园林说:“文明人类,先建美宅,营园较迟,因为园林艺术比建筑更高一筹。”[33]在中国情况也是如此,园林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虽肇端于建筑,却又与之不同。汉代之前,中国就有园(《说文》:“所以树果也。”)、苑(《说文》:“所以养禽也。”)、囿(《说文》:“囿,苑有垣也。”)、圃(《说文》:“所以种菜曰圃。”)、墅(《集韵》:“院,田庐也。”),等等,这些与后代的园池、园林还是有所不同。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园林是后起的艺术[34],大体产生于东汉到六朝时期。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二说,当时司农张伦的宅宇华丽,“逾于邦君园林山池之美”,说明当时“园林山池”已普遍存在。园林是融入自然的艺术,它与累起亭台楼阁的建筑设计不同,驰骋的是人与自然密合的心理,将人所依居的宅宇与山水林木融合起来,是园林艺术考量的关键。早期的园林多出于世家大户,豪奢之风浓厚。读西晋石崇《思归叹》,即可感受扑面而来的豪奢气,所谓“晚节更乐放逸,笃好林薮,遂肥遁于河阳别业。其制宅也,却阻长堤,前临清渠,柏木几于万株,江水周于舍下。有观阁池沼,多养鱼鸟,家素习技,颇有秦赵之声。出则以游目弋钓为事,入则有琴书之娱”,几有皇家宫苑的气势。巨大的体量是其根本特点。两晋以来,与自然融合一体的小园开始受到人们重视,像陶渊明珍爱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的小园,所谓“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就是代表。南朝庾信《小园赋》是一篇论小园价值的划时代文献,所谓“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壶之中,壶公有容身之地”,数亩林园,寂寞人外,即可全其心志。此对后代小园营建产生重要影响。
唐宋以后,园林在实用功能(宅居)、审美功能(韵人纵目)之外,更重视其安顿人心的功能(云客宅心),造一片与自然融会的世界,不仅是给眼睛看,更是为心灵谋一个宅宇。像白居易所说的“天供闲日月,人借好园林”,园池之观,与人的生命关怀相符契,成为颐养身心、伸展自我生命的世界,一花一世界的当下圆满哲学在园林艺术中发酵,酿造出最醇浓的生命意味,“小园香径独徘徊”,成为传统艺术颇富象征意味的理想世界。
建筑学家童寯说:“造园妙处,在虚实互映,大小对比,高下相称。”[35]清人沈复在《浮生六记》卷一中也说:“若夫园亭楼阁,套室回廊,叠石成山,栽花取势,又在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或藏或露,或浅或深。”园林的空间创造,不能没有大小虚实的考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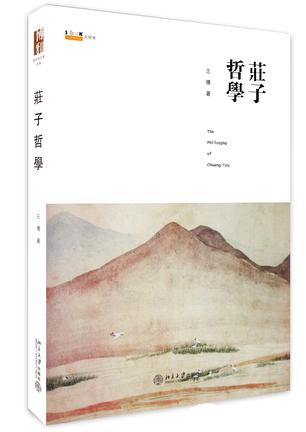
但此一考虑,必须服务于境界——人的生命体验世界的创造。巧于因借,是传统园林艺术的无上法则。因,是宜山则山,宜水则水,强调的是与自然的融合,创造一个人与世界一体的空间;借,非园林之景,即园林之景,隔帘风月借过来,强调的是,观园之人即主人,你来了,园中诸景,园外风月,才真正活起来,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只有在观者心灵中才能实现。所以,传统园林特别强调创造一个与世界对话的空间。园林诸景,有小有大,有虚有实,有高有下,有内有外,总在心灵回环中,总在你登此园、览此景片刻之性灵连接。便面,是为你打开心灵的窗;云墙飞檐,是为你加入轻云飘渺中而设;曲桥回廊,是为你与世界周流贯彻而建;假山瀑泉,是为牵引你驰骋山河大地的狂想……总之,一切都是为你来设计的,为了你加入世界的序列,将你从世界的对岸请到世界中来,你不是来园中看风景,你就是园中人。
正是在境界追求中,中国人来看小中现大、大中现小。小不是真小,说的是你足踏入其间的此在;大不是体量上的巨丽,是你身与之游、放旷世界的腾挪。大的腾挪由你此在发出,小的盘桓不离那飘渺的云、远逝的水,不忘与清风明月同在。计成说:“掇石须知占天。”[36]作假山,要在虚灵廓落中划出一道丽影,园林的创造者(既指造园者、又指观园人)目有天地,胸罗文章,纳千顷之浩荡,收四时之烂漫,蹈虚逐无,因实入空,留下属于自己的生命片刻,是“我亦与焉”的自适。在体验的哲学背景中产生的中国园林艺术,是世界园林艺术中的别类,其特别之处正在于她是一种生命体验的艺术。在体验中,随处充满,无少欠缺。
正因此,园林中说“一拳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顷”[37],此并非如周维权先生所说的,“把广阔的大自然山水风景缩移摹拟于咫尺之间”[38]。周维权先生是当代园林研究的领先者,我一直敬心承领其研究的惠泽,但也有我不能同意的观点。如他说:“园林里的石假山都是真山的抽象化、典型化的缩移摹写,能在很小的地段上展现咫尺山林的局面、幻化千岩万壑的气势。”[39]我以为此一观点,不符合中国园林思想的真实传统。文人园林重视的是生命体验,而非体量的缩放和典型的概括。
四、一即一切
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在唐宋以来的文人艺术中,此一理论如同一把利剑,劈开知识的密林,直指生命的真性。这里讨论三个相关的艺术哲学命题。
(一)一即一切
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作为中国艺术哲学的重要观念,受到道禅哲学影响。老庄哲学在这里起到基础作用。一即一切的根本,是要归于“一”。“一”是非知识、无分别的境界。老子的“抱一为天下式”的“一”正是如此。在中国佛教哲学中,此一命题具有复杂理论形态,天台、华严、禅诸家有不同的理论主张[40]。传禅宗三祖僧璨《信心铭》说:“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是,何虑不毕! 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语道断,非去来今。”此数句概括禅宗这方面的观点。传统艺术引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观念,强调生命创造的思想。
《二十四诗品》作为《诗家一指》一部分,反映了元代学者虞集(1372—1448)关于艺术创造的思想。其中《含蓄》品说:“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难,若不堪忧。是有真宰,与之沉浮。如渌满酒,花时返秋。悠悠空尘,忽忽海沤。浅深聚散,万取一收。”所论含蓄,不是文学修辞上的方法,而是境界创造的原则。此含蓄可以说是一种“无量的含蓄”。一粒微尘就是茫茫大千,一朵浪花就是浩瀚海洋,在浅中有深致,在散处有凝聚,万“收”于“一”中,“一”可囊括万有,所突出的正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思想。
《 石涛画语录》讲“一画”学说,其实就是讲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道理。“一”是浑然,是归宗,是真性,由一笔一画起,乃是自我心中出。“一画”,是发自根性的妙悟之道,也是“大全”之道。《一画章》说:“行远登高,悉起肤寸,此一画收尽鸿濛之外,即亿万万笔墨,未有不始于此而终于此。”又说:“一画之法立,而万物著矣。”《氤氲章》说:“自一以分万,自万以治一。化一而成氤氲,天下之能事毕矣。”《资任章》说:“以一治万,以万治一。”都在说“一画”乃大全之法。一就是一切,一画就是万画,正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发自于真精神、真命脉的创造,都是“大全”。
在石涛,“一画”超越知识计量,万法归一,以“一”而生万有。“一画”有体用两端,《氤氲章》的“氤氲不分,是为混沌。辟混沌者,舍一画而谁耶”就包括体用两面。就体上说,它是氤氲未分的混沌,膺有本原的“自性”,也可以说是创造的本体(creative itself)。就用上说,“一画”具有创造的动能,也就是他所说的“辟混沌者,舍一画而谁耶”,处于将发未发的状态,以“自性”去创造。这两端若以佛学词汇来表达,就是“智本慧用”。
“一画”既不是一个具体的起点,也不是一个终然的归结。石涛提出“一画”,不是要归于某个抽象的“道”,某个更合理的、具有决定性的真理,“一画”将一切创造的起点交给生命真性,交给艺术家集纳于平素、濬发于当下的直接体悟。他的大全之道,即如其《题卓然庐图》诗中所说的:“四边水色茫无际,别有寻思不在鱼。莫谓此中天地小,卷舒收放卓然庐。”[41]小中现大,当下圆满,挣脱时空铁网,在无分别境界中,一任真性发出,一切知识的、计量的盘算烟消云散,“量”之不存,何有大小多寡!
《二十四诗品》与《石涛画语录》的“一”都不是绝对真理和终极价值。“不二法门”超越“二”——生灭是非等分别见,也超越“一”——终极价值追寻的思想。正如《信心铭》所说:“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万法无咎。”万法归“一”,“一”归何处? “一”,意味着无所归,归于自心、归于自己当下直接
的体验。所以“一”心之不生,才能真正达到“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不是由“一”生出“一切”;“一切即一”,不是由“一切”归于一个终极的“一”,而是没有“一”,没有“一切”,有了“一”与“一切”的相对,就是量的见解,就不是发自真性的生命体验了。
(二)月印万川,处处皆圆
清恽南田在评董、巨画时说:“月落万川,处处皆圆”。这是传统艺术哲学的重要命题。苏轼《次旧
韵赠清凉长老》诗云:“但怪云山不改色,岂知江月解分身。”南宋王十朋注云:“佛书云:月落千江。又《传灯录》:僧问龙光和尚,宾头卢一身何为赴四天供,师曰:千江同一月,万户尽逢春。所谓‘月印万川’。但怪云山不改色,山河依旧,色色如此。一即一切之谓也。”苏轼诗中所涉就是“月印万川”问题。沈周的“天池有此亭,万古有此月。一月照天池,万物辉光发。不特为亭来,月亦无所私”,所体现的也是“月印万川,处处皆圆”的思想。
此命题本由佛学转出。在中国佛学中,华严宗自称为“圆教”,武则天曾命华严宗师法藏说华严之妙,法藏就以皇宫门口狮子作比喻来说法,他说:“一一毛中,皆有无边师子(即狮子);又复一一毛,带此无边师子,还入一一毛中。”[42]每一物都有其圆满的自性,每一物都是大全。南宋理学家陈淳(北溪,1159—1223)释“太极”云:“总而言之,只是浑沦一个理,亦只是一个太极。分而言之,则天地万物各具此理,又各有太极,又都浑沦无欠缺处。”“譬如一大块水银,恁地圆,散而为万万小块,个个皆圆,合万万小块,复为一大块,依旧又恁地圆。陈几叟‘月落万川,处处皆圆’之譬,亦正如此。”[43]几叟之论,是为了说明理一分殊的理论。
南宗禅所论,与传统艺术哲学的观念最为接近,也是艺术哲学此类讨论的主要源头。禅宗强调触处皆是,当下圆成,所谓西方就在目前,当下即是充满。慧能弟子永嘉玄觉《证道歌》说:“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碧岩录》所说的“一尘举,大地收;一花开,世界起”,也是此意,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观念的另一种表达。但“月印万川、处处皆圆”这一说法,更突出圆满特性。“一”,意味着当下直接的生命体验,不待他成,当下圆足,无所缺憾。如希运《传心法要》所说:“深自悟入,直下便是,圆满具足,更无所欠。”[44]禅宗的盘山禅师说:“心月孤圆,光吞万象。”[45]孤,无所对待;圆,无少欠缺,说的正是此理。
月印万川,处处皆圆,不是万千月亮都有一个月亮统领,那是就整体和部分而言,而是赋予每一个存在以自身的意义,存在的意义不是在其高度的概括性,如我们平常所说的在特殊中体现出一般,在有限中体现出无限。存在的意义就在其自身。在这里没有有限和无限的区分,没有一般和特殊的总属关系,也没有全体和部分。当存在脱离人的量论的束缚,恢复生命的真实时,所在皆是圆满。一个小园,就是俱足的世界;一朵野花,无绚烂之色彩,属卑下之花种,又处在偏僻的地方,也无所缺憾。
(三)芥子纳须弥
芥子纳须弥,也是由佛学引发、在传统艺术哲学中形成的一个命题。它是“一即一切”思想的另一种表达。
李渔有芥子园,胡正言有十竹斋,都言其小,然而小中可见大,芥子可纳世界。清戴熙画烟溪云水小景,题云:“或谓数寸之楮安能容千丈之山、百尺之树,然人目才如豆,视微尘一瞬,视泰山亦一瞬,大千世界纳入须弥芥子,世尊岂欺我哉。”一位朋友藏奇石,他为之画七十二峰阁图,并题云:“许澹庵家有七十二峰,构一阁贮之,属写此图。或曰:澹庵之峰在阁中,画中之峰何乃罗列阁外? 答曰:苏端明壶中九华,九华自在云表。又曰:‘袖中有东海’,东海故接混茫也。须弥在芥子中,芥子在须弥中。解人当无滞相。”[46]解人当无滞相,一物即是一世界。
芥子纳须弥,是佛经中的比喻,《维摩诘经·不思议品》:“若菩萨往是解脱者,以须弥之高广,内芥子中,无所增减。”(内,通纳)《楞伽师资记》引《璎珞经》云:“芥子入须弥,须弥入芥子。”[47]芥子,芥菜之籽,佛经中形容极小之物。佛教宇宙观中,以须弥山为世界中央,又称妙高山。须弥入芥子,磅礴无边的须弥山,纳于一颗芥子中,此说一无量、无量一的道理。禅宗以“须弥纳芥子”来表示彻悟境界,《景德传灯录》卷七记载:“江州刺史李渤问师(庐山归宗)曰:‘教中所言须弥纳芥子,渤即不疑。芥子纳须弥,莫是妄谈否?’师曰:‘人传使君读万卷书籍,还是否?’李曰:‘然。’师曰:‘摩顶至踵如椰子大,万卷书向向处着?’李俯首而已。”[48]超越大小尊卑凡圣等见解,以诸法平等心会通世界,此为须弥芥子学说之根本旨归。
在艺术领域,以须弥芥子来表达小中现大的无量哲学。北宋末年董逌(字广川)说:“当中立有山水之嗜者,神凝智解,得于心者,必发于外,则解衣磅礴,正与山林泉石相遇。虽贲育逢之,亦失其勇矣。故能揽须弥于一芥,气振而有余,无复山之相矣。”[49]他形容范宽作画时的状态,解衣磅礴,物我两忘,荡涤一切束缚,臻于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境界。须弥芥子在此表达精神的超越。
宋代诗僧道璨推崇“八荒入牖户”的境界,其《仙巢海棠洞》诗云:“领客坐花阴,饮客酌花露。先生自家春,八荒一牖户。凄其望前修,一枝阅世故。鹤车来不来,东风吹日暮。”[50]先生自家春,八荒一牖户,其实就是芥子纳须弥,是自家的春色,从真性中观照,就会揽天地八荒入一牖户中。
“先生自家春”隐括禅宗“如春在花”的话头,春天百花齐放,如同“春意”——这创造的真性,洒向千千万万花木的枝头,使群花绽放。所以春是一,花是万,天下万万千千花朵,都来自这“春之一”,由“一”而为“一切”。花团锦簇,处处皆春,朵朵都是春意,即花即春意,即万即一。这就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道理。清张潮说:“春者,天之本怀;秋者,天之别调。”[51]正是此理。
道璨另一首赠别诗,也表达类似的思考:“宇宙入八窗,芙蓉制衣裳。两眼挂万古,深柱书传香。笔端肤寸合,要作天下凉。余事亦演雅,簸弄正未妨。颠倒走百怪,陆离罗众芳。气焰压牛斗,何止万丈光。笑他儿女曹,白道空茫茫。秋风三尺剑,尘土压下方。斫却月中桂,及此鬓未苍。我欲援北斗,酌以椒桂浆。文章于此道,太山一毫芒。洙泗到伊洛,波澜正泱泱。多少遡流人,褰裳复回翔。孰知方寸间,一苇直可航。勉哉吴夫子,此事当毋忘。”[52]这首诗写得痛快淋漓,表达的道理深可玩味。宇宙入八窗,芙蓉制衣裳,以包括天地宇宙的精神,做人生最美的衣裳,世间种种执着,种种拘牵,裹挟着人,演绎着那么多的荒唐,不如在沉醉人生中,高蹈远逝,从容回环,“孰知方寸间,一苇直可航”,一片灵苇,犁破世界的万顷波浪,如回环于闲庭信步间。
回到上引戴熙的论述中,他谈须弥纳芥子时,所引“袖中有东海”,诗出东坡,东坡从东海蓬莱阁下,带回一些与海浪相战形成的如“弹子窝”一样的小石,以养石菖蒲,作诗有“我持此石归。袖中有东海”之句[53],山谷以此为诗中眼,后禅家以此为上堂的话头,如北宋袁觉禅师曾说:“东坡云:‘我持此石归,袖中有东海’;山谷云:‘惠崇烟雨芦雁,坐我潇湘洞庭。欲唤扁舟归去,旁人谓是丹青’,此禅髓也。”[54]
带回几片东海石,如将东海藏袖中,这是一种俯仰人生、连接天地的情怀。东坡名其石曰“壶中九华”,
也是此意。沈周有写奇石的诗中说:“已藏东海从深袖,便卷沧波答小诗。”[55]正是此意。

下滑阅读
参考注释
[1]马定国:《读庄子》,见元好问编《中州集》甲集第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1页。
[2]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五著录《董文敏为王奉尝画山水立轴》,并题云:“逊之尚宝以此属画经年,漫应,非由老懒,每见其近作,气韵冲夷,动合古法,已入黄痴倪迂之室,令人气夺耳。因题诗一绝云:‘曾参秋水篇,懒写名山照。无佛地称尊,大方家见笑。’己巳又四月卄一日,青龙江舟次,其昌。” (《中国书画全书》第八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 年版,第1121 页)图作于1629 年,今不见。
[3]郭象解释天籁云:“夫天籁者,岂复别有一物哉? 即众窍比竹之属,接乎有生之类,会而共成一天耳。”(郭象注、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版,第26页)
[4]洞庭乃无所涯际之托词,成玄英疏:“洞庭之野,天地之间,非太湖之洞庭也。” 宣颖云:“洞庭,犹广汉。” 见郭象注、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第290 页。
[5]郭象注、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第292 页。
[6]林希逸:《庄子鬳斋口义校注》卷五,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重印本,第231 页。
[7]林沄铭:《庄子因》,历代文史要辑注释选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151 页。
[8]董其昌:《容台集》别集卷一,邵海清点校:《容台集》,杭州:西泠印社2012 年版,第572 页。
[9]此段从通行本王弼本。易顺鼎《读老札记》、马叙伦《老子校诂》和高亨《老子正诂》等均认为自“守其黑”至“知其荣”六句,为后人窜入,帛书甲、乙本也无此六句。张舜徽《老子疏证》、党圣元《老子析义》咸以古人引书常有省略之习,《淮南子·道应篇》就引作“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通行本义理通畅,故从之。
[10]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认为“大制不割”意为:“大即二十五章所说‘强为之名曰大’ 之‘大’,指道、朴。‘制’,说文:‘裁也。’‘大制’,意为以道制裁万物。”(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版,第77 页)
[11]南京博物院所藏石涛《狂壑晴岚图轴》上自跋诗中之句。
[12]题《密林陡嶂》,《习苦斋画絮》卷五,《中国书画全书》第十四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 年版,192 页。
[13]宗白华:《中国美学史论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第43 页。
[14]此见戴熙《习苦斋画絮》卷二所引:“ 鄂士整理盆石,予弗能也,偶写于画。文待诏云:‘ 我之斋堂,每于印上起造。’醇士盆玩,亦于腕下运也。”(《中国书画全书》第十四册,第159 页)文徵明文集不见此语。
[15]上海博物馆也藏有类似册页,关于这两套册页的真正作者,研究界争议较大。
[16]《楞严经》,唐中天竺沙门般剌蜜帝译,大正藏第十九册。
[17]苏辙:《洞山文长老语录序》,《栾城集》卷二十五,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429 页。
[18]赜藏主编集《古尊宿语录》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94 年版,第224 页。
[19]王夫之解释庄子的大小无待之说:“寓形于两间,游而已矣。无小无大,无不自得而止。其行也无所图,其反也无所息,无待也。无待者,不待物以立己,不待事以立功,不待实以立名,小大一致,休于天均,则无不逍遥矣。”(王夫之《逍遥游题解》,《庄子解》卷一,《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编校《船山全书》第十三册,长沙:岳麓书社1988 年版,第81 页)
[20]明正德修:《京口三山志》卷七,明正德七年刻本。
[21]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十八,《书画舫记》,四部丛刊本。
[22]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五十五画卷二十五所引,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 年版,第2068 页。
[23]唐顺之《荆川集》卷十三,四部丛刊本。
[24]程正揆语,见周亮工《读画录》卷二,朱天曙编校整理:《周亮工全集》第五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年版,第94—95 页。
[25]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 年版,第42 页。
[26]吴企明辑校:《恽寿平全集》中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327 页。
[27]吴企明辑校:《恽寿平全集》中册,第339 页。
[28]见汪世清等编:《渐江资料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32 页。

[29]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四十五画卷十五,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 年版,第1745 页。
[30]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编:《元画全集》第一卷第二册,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40 图。
[31]张光宾:《元四大家》,台北:故宫博物院1975 年版,第301 图。
[32]《石渠宝笈初编》御书房(卷三十八)著录。上有云林题诗云:“今朝姚合吟诗句,道我休粮带病容。赠尔湘江青凤尾,相期往宿最高峰。”款“辛亥秋写竹梢并诗奉赠次宗征士,瓒”。作于1371 年秋。傅申认为此作存疑,他认为“书迹与同时期者极似”,而绘画水平与云林水平不符,如果是真迹,可能“是他心绪不佳时的作品”(《倪瓒和元代墨竹》,《倪瓒研究》,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 年版,第298 页)。
[33]据童寯《中国园林对东西方的影响》一文所引,《童寯文集》第二卷,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年版,第347 页。
[34]此处论述参陈植《中国造园史》绪论之说,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年版,第1—3 页。
[35]童寯:《江南园林志》,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 年版,第16 页。
[36]计成:《园冶》卷一,营造学社本。
[37]文震亨:《长物志》卷三,第24 页。
[38]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35 页。
[39]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第27 页。
[40]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圆融无碍思想,禅宗、华严宗论述最为周备。然二家所持有重要差异:华严的一多互摄理论,建立在现象本体相融相即的理论之上,真如本体体现于一切现象中( 舒现),一切现象体现真如本体( 卷藏)。“一”是本体,“一切”是现象;“一”为单一,“万”为总体。自“一”观“万”,即是量的差异,一毛一切毛,一物一切物。南宗禅所破的正是这现象本体的分别智。同时,华严宗圆教理论强调,世界上存在着千千万万差别的事物,每一物都有其自性,故而显示出差异性,差别的事物中有共同的理。而禅宗则是彻底平等观,它认为事物的差别是人分别智所造成的,物的存在本身并无差别,也无量的区别。
[41]石涛:《卓然庐图轴》,今藏上海博物馆,作于1699 年。
[42]方立天:《华严金师子章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版,第64 页。
[43]陈淳:《北溪字义》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45—46 页。这里所说的陈几叟,即陈渊(? -1145),字子叟,师杨时。
[44]据瞿汝稷:《指月录》卷十,成都:巴蜀书社2011 年版,第300 页。
[45]《五灯会元》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版,第149 页。
[46]以上两段引文均见《习苦斋画絮》卷一,《中国书画全书》,第十四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 年版,第155页,第152 页。
[47]《大正藏》,第八十五册。
[48]朱俊红点校:《景德传灯录》卷七,海口:海南出版社2011 年版,第182 页。
[49]《题范宽画》,《广川画跋》卷六,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 年版,第95 页。
[50]《柳塘外集》卷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道璨(? —1271),宋代临济宗大慧派僧,吉安(江西)泰和人,号无文,为笑翁妙堪法嗣。俗姓陶,渊明后人。曾于饶州(江西) 荐福寺开堂,后任庐山开先华藏禅寺住持,工诗文,著《柳塘外集》等。
[51]张潮:《幽梦影》卷一,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 年版,第14 页。此为该社所出《艺文丛刊》之一种。
[52]《柳塘外集》卷一《吴太清有远役以诗寄别次韵》。
[53]《文登蓬莱阁下石壁千丈,为海浪所战时有碎裂,淘洒岁久,皆圆熟可爱,土人谓此弹子涡也,取数百枚以养石菖蒲,且作诗遗垂慈堂老人》,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三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版,第1651—1652 页。
[54]《五灯会元》卷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版,第1292 页。
[55]《谢顾天祥送将乐石》,《石田诗选》卷二,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原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5 期,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投稿
请登录本刊网上投稿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