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8年第2期,原题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体系与核心——评郭英德教授《探寻中国趣味》”。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两翼之——作家心态
文本是研究者与作者沟通的桥梁。当然,我们要充分理解“桥梁”一词的意义,也就是说,阅读或研究文本,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文本获得意义。不过,对文本意义的追寻仍有一个不可忽略的中间环节,那就是作家的心态。因为文本正是作家创作的,研究作家的心态,其实正是在追索文本的“初心”。郭英德教授也指出对于文本的研究是“借助于现存的文学文本,发掘并重建古人的心灵世界,进而深入地审视古人的文化心态”。因此,这组文章正是希望通过对作家心态的抉隐发微,从而获得对文本更深度诠释的可能。本组文章也可以分为三类,即文人个体的心态揭示、文人心态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及从教育角度研究文人心态的生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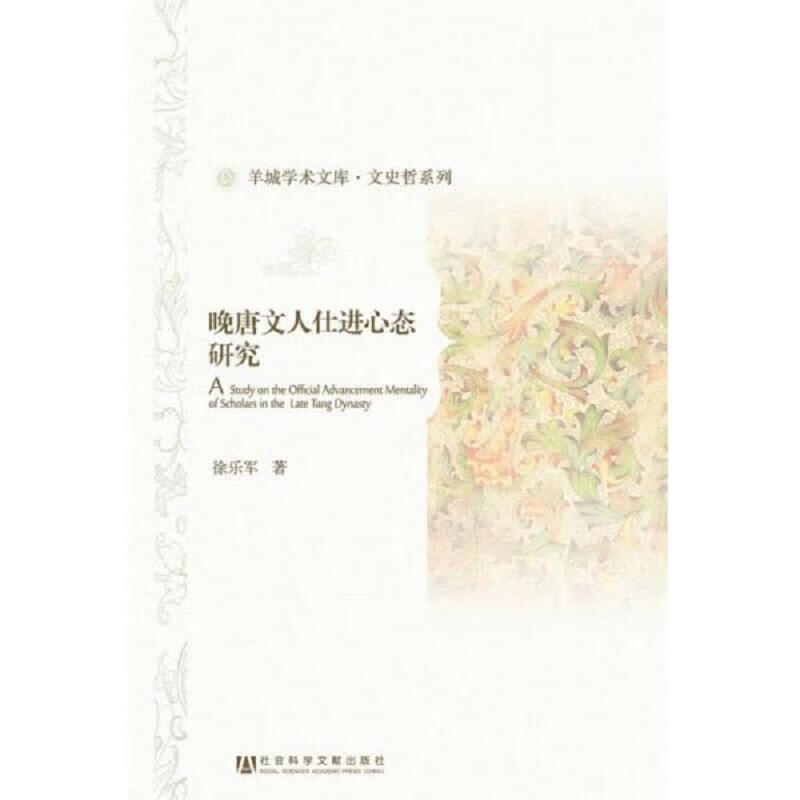
在文人心态的揭示中,《蒲松龄文化心态发微》(1990)一文有着重要的意义。《聊斋志异》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煌煌巨著,在小说一体中,一直被认为是“七大杰作”之一,但不可否认的是,对它的研究却一直无法深入,与明代四大奇书或同时稍后的《红楼梦》等都无法相比,其原因多在于若想对此书深入讨论,就会陷入一个悖论,即深入研究要求统一而有机的理论框架,但《聊斋志异》作为一部文言小说集其实无法提供这样的框架,理论建构能力强的学者自然可以强行切削而搭建,却也无法避免“切削”带来削足适履的弊端;但若放弃整体观照,篇自为政,又无法以整体的力量呈现此书的价值和意义——事实上,也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带有普遍性的理论难题,这当然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呈现方式有关。郭英德教授此文给这一难题带来一种解决的可能性,那就是从蒲松龄的文化心态入手,来构建整体观照的学理基础。基于此,作者指出蒲松龄“人生大半不如意”的科举心态,并将其对科举的态度与顾炎武、吴敬梓对比,从而揭示出《聊斋志异》中有关科举的篇目的阐释向度;从“翠珠绕围索解人”的理想追求出发,则蒲氏笔下多写美丽之女性,一方面承认此为补偿心理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指出此实亦香草美人传统的接续;从“缘来缘去信亦疑”的宗教意识指出,蒲松龄的宗教意识不过是“汲取象征性的宗教信仰、理想性的宗教情感和超越性的宗教思维”而已。
这些层面的阐释不但在很大程度上为《聊斋志异》的研究奠定基础,更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其他研究有启发意义。比如《关汉卿杂剧的文化意蕴》(1989)一文即又一例证。关汉卿《窦娥冤》一剧最为有名,王国维曾评其“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但由于此剧极易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来解读,于是,在很长的时间里,此剧便被简化为阶级迫害的图解,研究者似乎忘了王国维此语前还有“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的评析。本文即指出,《窦娥冤》的冲突有三个层面,其中的社会冲突是最浅层次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还带有偶然性,作为解读此剧的核心逻辑显然并不具有普适性。而且,其实质“毋宁说是道德与非道德的冲突”,此后,作者更进一步指出了道德冲突的内化与深化的第三个层次,甚至是“关汉卿所未尝明确认识,但他地以生动的艺术笔触尽情描绘出来的戏剧冲突,历来都为研究者们所忽略”,那就是意志冲突,是“不安于现状与不得不安于现状的冲突;不信天地鬼神与不得不信天地鬼神的冲突;明知道德无用与不得不遵从道德的冲突”,这一解读将王国维的评价细化、深化,实际上也更指向了中华文化的道德内化传统。作者再将此解读移于关汉卿的其它杂剧,自有势如破竹之效。《论汤显祖文化意识的悲剧冲突》(1987)亦与此类,指出“极力寻求社会和人生的出路而终究无路可走的两难心理和汲汲不息地探索追求却终究归于失败的悲剧精神,是汤显祖的文化意识的基本内核,也是其价值所在”,从而可以帮助我们深入汤显祖的文化意识,从而触摸到临川传奇的悲剧意蕴。
当然,正因为文人心态是文本与社会、历史意义之间的环节,所以,对文人心态的梳理也必然包含社会的维度。《“守之俟来哲”:顾炎武的遗民心态》(1999)与《黄宗羲的人生定位与文化选择——以清康熙年间为中心》(2002)二文即是这一思路的范例。前文是一篇煌煌大作,其大不仅在于长近六万言的篇幅,更在于视野的宏阔与识见的超拔,作者将顾炎武这样的一代大儒放回到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还原出顾氏在改朝换代的历史情境中的遗民心态,从而梳理出顾氏心态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正如作者所云,“著书立说,以待后王,这种坚定不移的文化行为方式,决定了顾炎武的人生价值,不是取荣当代,而是扬名后世”。而对于与顾炎武相似又相异的黄宗羲,作者也同样在细致的梳理中标定出他的人生定位和文化选择。
如果我们通过文本去梳理作家的心态,并通过文人心态的把握向内指向作品,向外指向社会,那么,我们也会有理所当然的一个追问,就是作家的文化心态是如何养成的,《论剧作家李渔的文学教育》(2010)一文就是为了解答这一追问的试例。此文原为作者《中国古代文学与教育之关系研究》中之一章。“文学教育,指的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经由文学文本的阅读、讲解与接受,丰富情感体验,获得审美愉快,培养语文能力,进而传授人文知识,提高文化素养、陶冶精神情操的一种教育行为”,可以看出,这一概念的提出与梳理已经突入教育、社会的领域,既是儒家“游于艺”的教育理念的重申,又是西方公民素质养成观念的回应。不过,我们都应该承认,由于教育尤其是文学教育非常难于在量化角度进行观测与评价,所以这一课题虽然非常重要,但也充满困难。郭英德教授在这篇文章中作了非常好的示范,一方面,作者从李渔的文学教育与知识结构、创新精神深入论述,钩稽相关资料,令人信服地指出李渔之所以如此,实有文学教育上的渊源,不过,作者也并不讳言“文学艺术创作才能,究竟是本于先天,还是得之后天”的质疑,这或许永远没有答案,但就李渔而言,“他从小所接受的文学教育与他的戏曲文学创作之间的因缘关系,仍然是有迹可循的”,“探讨一位剧作家文学教育的实际状况,可以更清晰、更全面地了解剧作家艺术道路的选择、创作个性的来源和艺术风格的形成”。这其实也是中国传统文学最为关注的地方。实际即是述与作的关系。
应该说,作家心态的研究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有其逻辑上的暗合之处,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有“知人论世”之传统(作者亦有专文梳理此论,参下文,可知以此为理论基点并非巧合),作家之写作行为自然也被纳入这一传统之中,因此,作家心态与文本之关系较之西方要紧密、复杂得多,而中国古代文学的文本呈现又非出之以西方的“有机”面貌,故其研究之涉足作家心态,并非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而是必不可少的雪中之炭。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两翼之二——历史风貌
作家心态的研究是向作家一端寻求解密文本的思路,事实上,一个文本必然连接着两端,一端是作家,另一端则是社会历史。所以,对历史风貌的描摹、还原也是我们研究的重要任务。这一任务既与前述“知人论世”之传统有关,亦与史官文化的影响有关。
前节曾引郭英德教授之语,其尚有后文,即云“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为形象而直接地触摸历史的脉搏,也可以帮助我们更为透彻地认识中国文化的真谛”。也就是说,由文本而至文人心态,还未能探骊得珠,还要再由心态入于史,方有更多深广的理解。
《探寻》的第二组文章即属文学史论的范畴。以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可依次分为三类:即从历史梳理考察文学风貌,由文学探寻历史以及文学与历史相互作用。
《光风霁月:宋型文学的审美风貌》(2003)与《向后倒退的革新——论明末清初的求实文学观念》(1996)两篇文章都是从历史梳理考察文学风貌的佳作。前文从文官政治与士人风范、三教融通与理性精神及文化普及与游宴享乐的历史语境出发,深入讨论了宏观历史语境如何沉积于宋代文学的审美风貌之中,并精辟地指出,宋型文学具有鲜明的政治化和道德化色彩,也富于思辨精神和超越精神,并且洋溢着浓郁的书卷气和学问气,从而形成了宋型文学“光风霁月”的基本审美风貌。后文的题目十分有趣,既梳理了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问题,即明末清初求实文学观念纠正了明代拟古的隔膜与性灵的逃避,因此是一种文学观念的革新;又指出这种革新实质却是倒退回传统之中——而且,这一矛盾在清代仍有继响,一方面,主情文学稍有回归,如袁枚再次扬起性灵大旗,曹雪芹以“情”结构作品,但总体来说,倒退的步调却明显加快,传统意识全面复归。可以说为我们显现出近数百年中国文学发展中最根本的一个矛盾。此类研究既要有对历史语境清晰的把握,又要能精准地将其落实于文学风貌的描述之中,其实是最难的研究,因为无论是对历史语境还是文学风貌的把握,都非常需要功力,而尤要者又在于两者全无枘凿的对接。以此来看,此二文足称相关研究的典范。
第二类则以文学为基点,再将文学的触角伸进社会层面去。其中,《论晚明清初才子佳人戏曲小说的审美趣味》(1987)是本书所收撰写时间最早的文章,但已能看到作者驾驭宏大命题的功力。才子佳人小说戏曲时代不同,作者不同,甚至文体也不同,但“当我们将它当作一个文学现象放在文学史发展的长河中做整体的、宏观的研究时,我们完全可以采取求同存异的方法,发掘其由一定时代、一定社会、一定阶级的审美理想所决定的共同的审美趣味”——即理想人格结构及爱情婚姻主题,更重要的是,作者的目的并不在此,因为这无法解决晚明清初对此类作品截然不同的审美评价,作者指出,这种审美趣味的实质,“揭示了这种近代审美理想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所能达到的极致,以及知识阶层对近代审美理想的追求终竟无法超越古代意识与近代意识的临界状态,并不可避免地复归封建文化传统的必然归宿”。《黄宗羲明文总集的编纂与流传——兼论清前期明代诗文总集的文化意义》(2000)一方面从文献的角度对黄宗羲所编明文总集进行梳理,另一方面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指出清前期编选明代诗文总集的历史意识和历史价值。这种研究正为作者专擅之领地,即由对文学“趣味”的探讨进入对历史的感知。
第三类则由文学与历史的相关关系中探究二者互动的机制与肌理。《明清文学教育与戏曲文学的生成》(2008)探讨的是,明清时期文人从社会环境中所得到的文学教育如何成为戏曲文学的营养,如前所言,这是非常难以讨论的一个话题,但作者非常擅长搭建合理的理论框架,从而将问题引入可以讨论的层面,此文便将戏曲文学划分为三个层面,即本体、建构与载体,再分别从文学知识、文学思维与文学表达三部分的文学教育来对应这三个层面,从而形成完整的论说结构。《元明的文学传播与文学接受》(1999)一文同样如此,即文学传播与文学接受也是难于论述的,作者则将文学传播分为三种类型,即书籍的借阅和传抄,书籍的抄刻和买卖,戏剧的演出和说书活动,也即人际传播、商业传播和娱乐传播三部层面,在各个层面再细述其传播与接受的样貌,从而将复杂的问题清晰地显现出来。

《传奇戏曲的兴起与文化权力的下移》(1996)一文更是一篇带有典型郭式风格的宏文,即一方面有大气象,敢于下大判断;另一方面却不蹈空而论,而是注重文献与历史细节。作者指出明成化至万历间文人自我意识的高涨与主体精神的张扬,促成了文化权力由贵族而文人的下移趋势,这种下移的历史大势也选择了南曲戏文来重建新的文化传统,文章不但严密论证了文化权力下移与传奇戏曲的兴起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从传奇戏曲的梳理突入了历史文化的疆域,为晚明文化变迁的大势提供了清晰的学理支持。事实上,由此文始,“文化权力下移”成为晚明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判断,也成为试解晚明历史文化研究之灵钥。
在古代文学研究这一翼中,有一种倾向值得反思,即学界颇有对古代文学研究者“为史学打工”的担忧,抛开具体语境,抽象探讨此论,笔者是不敢苟同的。这一担忧若置于西方文学研究中,似尚可成立,而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实为伪命题,因为中国古代原无纯文学传统,今所视之文学作品,均难与历史剥离,所以,对其之研究本来就当有历史的潜台词,我们当下的研究已经按西方文化传统强分畛域了,如果在研究方法上再切断文史之间本来丰茂的联系,则我们研究的格局与境界将日渐萎缩与狭小,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注释略)
声明: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与本平台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