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是一场与世界同步的先锋文化运动
“
“五四”从思想启蒙到文学革命再到社会革命,是顺其逻辑的一个必然的完整发展。虽然借助了外部推力,但究其实质,“五四”是一场中国文化传统进行自我涅槃的文艺复兴。并且,放之四海,它是一场与世界同步的先锋文化运动。
”
整理|钱亦蕉
“五四”百年,更多的专家学者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进行深入的探索和研究。作为五四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中文系资深教授陈思和先生从历史人文角度,深刻解读百年前的那场变革,给我们重读这场文化启蒙运动以一个新的视野。

他提出:“五四”从思想启蒙到文学革命再到社会革命,是顺其逻辑的一个必然的完整发展。虽然借助了外部推力,但究其实质,“五四”是一场中国文化传统进行自我涅槃的文艺复兴。并且,放之四海,它是一场与世界同步的先锋文化运动。
回眸百年,从文化精神层面进一步解读五四内涵,对我们当今青年人了解历史、辨明是非,传承五四精神、建设当代文化,都是十分有意义的。
《新民周刊》:陈老师,今年是五四运动百年纪念。但我们一般说到“五四”,总是包含着两个层面,一个是指1917年开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另一个是指1919年在北京发生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前一个代表着“启蒙”,后一个代表着“救亡”。您怎么理解“五四”的这两重性?
陈思和:在今天来说,“五四”是一个含义混乱、相互矛盾的概念。不仅仅是指1919年的学生爱国运动。“五四”是一个系列事件,可以往前推到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即后来的《新青年》)。1917年初陈独秀携《新青年》北上,加盟于蔡元培担任校长的北京大学,吸引了一批旨在革新的进步师生,可以说,《新青年》到了北大才声势壮大,而北大也是缘了《新青年》而改变风气,两者相得益彰;1917年另一个事件是胡适的加盟,开始提倡白话,鼓吹文学革命;这就是你说的代表“启蒙”的思想运动。上世纪80年代学术界提出了“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观点以后,推导出这样一种看法:起始于1915年到1917年前后的思想革命,旨在批判和扬弃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语言形式,介绍引进西方新思想和文学,同时为了更好地向国人宣传以及帮助国人了解世界新潮,更准确地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感情,又必须在语言上作进一步的改革:推广白话。这是一个完整的逻辑发展过程。然而1919年发生的学生爱国运动,则是在国际列强(尤其是日本对华的侵略政策)刺激下激发起来的民族救亡运动,它在中国的实际影响引发了大众革命元素介入现代政治,由此催生国民党的改组和共产党的崛起,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命运。“救亡”压倒“启蒙”的“变奏”,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典型的例子。但是,我们似乎也可以反过来理解:思想启蒙和语言改革的目的,不就是要唤起民众来改变中国的落后现状吗?启蒙不可能对民众教育毕其功于一役,但很可能在社会精英中间率先达到这个目的,因此,当时在北京的大学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启蒙运动的第一批觉醒者。从思想启蒙到文学革命再到社会革命,也同样是顺其逻辑的一个完整的发展。“两重性”也可以理解为是一元的逻辑发展。

但是,无论把1915—1919年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视为“两重性”还是“一元”的逻辑发展,它对以后的中国命运产生了巨大影响,把它理解为中国自晚清开始的现代化进程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期,并不为过。
《新民周刊》:一般来说,无论是西方进步思潮的东渐影响,还是西方与我国不平等条约的刺激,五四运动的发生无疑是受到了外部推力,但您的观点是觉得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因素对“五四”的发生也起了很大作用,“五四”是一场中国文化传统进行自我涅槃的文艺复兴,这个观点怎么理解?
陈思和:是的。学界对于“五四”系列事件的发生原因的探讨,一般都集中在西方思潮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或者是世界列强对华的不平等外交政策的刺激,尽管这两个方面有很大相异性,但都是外部推力对中国施加了影响。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提出问题:为什么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时刻,会发生影响如此深刻的“五四”系列事件?这还是要从中国历史传统内部的某些基因上来探讨。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五四”系列事件是文化事件。“五四”新潮的发起者,是几个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响应者是一帮手无寸铁、唯有热血的学生,鼓吹新思想的场所就是大学校园和课堂,传播新思想的媒介就是《新青年》等几种杂志。伴随着爱国学生的外交政治诉求的,还有新思想的传播、新文学的创造、新语言的普及……这是中国现代史上很少发生的由文化运动带出政治运动,进而导致中国革命走向的转变——由中国文化来决定中国的未来命运。
周策纵教授和余英时教授都把“五四”学生运动与中国古代太学生干涉内政的传统联系起来讨论,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还不够,因为“五四”不仅仅是学生参与的运动。从更广泛的范围看,成熟的中国古代政治体制本身就具备了君主与士大夫共同执政的模式。在这个“明君贤臣”的理想模式下,士大夫集团尽管派系林立,互相倾轧,常常屈服于君权专制,但从体制上说,它与君主皇权构成政坛上的权力平衡。
这样一种古代士的统治集团的文化传统,在君主专制鼎盛时期往往难以显现出高贵的一面,君权高于一切的时候,儒家文化表现出特别自私、冷漠和无耻的一面;然而奇怪的是,一旦天下失范王纲解纽,儒家文化立刻就显现出自觉的担当意识。这样的时期,思想文化的创造力也特别活跃,思想专制让位给百家争鸣,学术思想大放异彩。周衰而诸子蜂起,汉衰而竹林长啸,唐在安史之乱后,诗歌风骨毕现,宋在亡国南渡后,理学应时盛行,明末思想界更是空前活跃,顾炎武明确分出了“一姓之亡”与“天下兴亡”的区别,显露出真正的儒家本色。稍稍回顾历史,这已为规律,颠扑不破。
所以,仅仅把“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看成是古代太学生干涉内政的现代版,还是缩小了“五四”与传统的联系。在我看来,可以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看作是中国古代士人传统的一个自然延续阶段,犹如南宋、南明时代的读书人面对异族入侵、国破家亡之际激起的一场场新的思想革命,而西方新思潮只是为这一场思想文化运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这是一场中国文化传统进行自我涅槃的文艺复兴,在中国政治社会的现代转型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新民周刊》:那么,“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猛烈地批判传统文化,积极倡导民主(德先生)与科学(赛先生),您认为从本质上说,这仍然是儒家文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传统再生?这批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人,像严复陈独秀他们其实都是真正的爱国者?
陈思和:当然应该这么理解。我们现在讨论的爱国者,不是指那种把什么封建专制体制下的旧传统旧文化都说成宝贝的前清遗老,也不是那种把所有来自西方的思想学说都视为洪水猛兽的狭隘民族主义者——严格地说,这两类人都是不配称为爱国者的。“五四”新潮的兴起,表面上看,是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儒家文化的否定和批判,批判武器主要也是来自西方的思想学说。但我们还是要考虑到以下两个事实:
首先是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进入了现代化的历程,一部分汉族士大夫的“天下”观发生变化:他们发现有一个叫做“世界”的空间,不但比大清帝国的天朝大得多,还直接制约了天朝盛衰的命运。这个“世界”丰富而且复杂,不但有邪恶的洋枪洋炮欺侮中国,更有焕然一新的思想文化强有力地吸引着中国的读书人,于是就有了洋务运动、改良变法、革命共和等等,最终形成了一个由现代知识分子领导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因此,“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猛烈地批判传统文化,倡导民主与科学,从本质上说,仍然是儒家文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传统再生。他们与时俱进,研究新的天下观(世界大势),并以此为参照,来批判君权专制,批判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愚昧政策,强调只有打破落后之国的一切文化藩篱,才可能让中国容纳到“世界”这一新的“天下”的格局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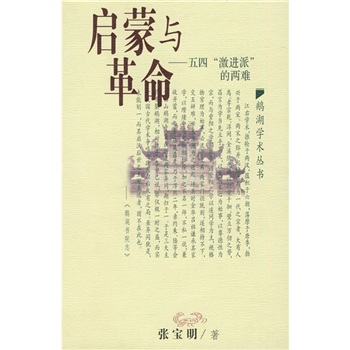
其次是两千年的中国历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经历过四分五裂和异族入侵的惨剧,而维系着中华统一的,唯有汉文化的优秀传统(包括语言文字和学术思想)。清朝统治者是少数民族,原来是游牧民族,有自己的宗教文化和传统,但在长期统治与被统治的磨合中,汉文化传统在大清统治中反而占了上风。为此,汉族知识分子一向有“文化高于政权”的认知。晚清以来,清政权风雨飘摇,但士大夫集团对文化传承并没有丧失信心。严复在戊戌变法失败时,写信给朋友说:“仰观天时,俯察人事,但觉一无可为。然终谓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抑所为皆非,但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沦胥;即不幸暂被羁縻,亦将有复苏之一日也。”严复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世界格局里要发生变化,唯有与时俱进,唯有容纳新知,才能救国保种;万一国家“被羁縻”,只要文化能够更新发展,仍有重见天日的机会。所谓“守旧”、“维新”无非是政策路线之争,如文化上不能吸收新知,不能更新发展,政治前途则是“两无一可”。而“五四”启蒙运动,正是严复“开民智”主张的必然结果。
鉴于上述两个事实,我们似乎不难认识到:每当君主集权统治处于土崩瓦解之际,一定会有以文化顾命臣自居的士大夫(现在就被称作知识分子)挺身而出,他们未必能挽救末世颓运,但在思想文化传承上却往往有大突破,文化传统由此更进一个境界。“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把中国古代文化蜕旧变新,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台阶新的阶段。
《新民周刊》:您以前专门写过一篇论文,界定“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先锋运动,它与世界是同步的。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观点。
陈思和:上世纪末,海外汉学界曾经流行一种学术观点,认为从现代性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现代文学史,应该从晚清为起点。因为晚清文学已经具备了各种现代性因素,“五四”反而不重要,某种意义上还“压抑了”晚清的现代性。我是针对这种观点,从晚清到“五四”的文学发展整体观而言,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界定为一场先锋运动,而且是一场与国际现象同步的先锋文化运动。在世界大战前后,欧洲各国都出现过先锋文化运动,它以猛烈批判资本主义文化传统、批判市民社会平庸和异化的姿态、以惊世骇俗的艺术方法,表达自己的政治文化诉求。“五四”文化形态非常接近西方这类先锋文化,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不是直接接受了世界性先锋文化影响而发生的,它几乎是与世界性先锋文化运动同时期发生,但又具有独立而鲜明的中国文化传统的特点。它具有一种世界性因素。欧洲的先锋运动是在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和民主政治充分发展以后,作为人性异化的对立物,它是在各种反对资本主义的尝试都失去了效应以后出现的极端反叛形式,而中国的“五四”显然不是。“五四”是在中国封建专制崩溃、新的民主政治体制还没有健全形成之际产生的先锋运动。与“五四”系列事件同时发生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结束,欧洲各国资本主义体制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俄罗斯在十月革命中建立起新的苏维埃政治体制——所以,封建君主专制体制的残余、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衰败以及新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尝试,构成了极其复杂混乱的文化思想,以极端形式引导了“五四”系列事件——“五四”在思想上的不成熟与它以批判的形式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影响,构成了作为先锋运动的两大文化特征。
但是,思想的不成熟和反叛精神的彻底性,决定了任何先锋运动都是爆发性、短暂性的运动,它不可能持久下去。“五四”也不例外。先锋运动的失败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足够强大的资产阶级政府有能力包容先锋运动的反叛性,使反叛者最终成为受到主流社会欢迎的明星,这样,被资产阶级宠爱的浪子,就不再是先锋了;另一个是作为小团体的先锋运动,本来就不足以与强大的国家机器和社会主流抗衡,所以它要坚持自己的反抗使命,只能被吸收或融汇到更强大的实际的政治力量中去。在这个意义上认识“五四”系列事件,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胡适之与陈独秀的分道扬镳;不难明白为什么五四精神培养出来的学生精英基本上都走上了从政道路,在以后的国共两党恩仇史上有声有色地表现了自己;也就不难明白,1949年大陆建立新政权,大多数知识分子尽管对未来社会并不了解,也未必全部认同,但他们还是心甘情愿地把身体留在大陆,准备随时听从召唤,为新的政权服务。如要探究这些原因,从浅表层次上说,是先锋文化的必然趋势;从纵深里说,其背后有传统士人的道统力量起着制约作用。
(本文参考陈思和《士的精神·先锋文化·百年“五四”》一文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