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是科学哲学的首要问题。当代西方科学哲学正是以划界问题为主线,形成了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和后现代科学哲学几个发展阶段。然而,时至今日,关于科学与非科学文化的划界问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陷入了困境,得出了科学与宗教、文学、巫术并无区别的结论。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这一结局。科学与非科学的人文文化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本文循着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在划界问题上的发展历程探讨了这一问题,认为,没有处理好科学与其它人文文化的辩证关系,使二者保持必要的张力,这是导致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在划界问题上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
1 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就是能够被经验所证实
逻辑实证主义是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第一个流派。它继承和发展了笛卡尔-康德的知识论思想和孔德-马赫的实证论思想。为了实现“科学是唯一的知识、永恒的真理,任何现象都要以科学加以说明”这一笛卡尔科学主义的理想,他们建立了“意义-证实”或“理论-经验”认识论模式,认为“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注:M.石里克:《意义和证实》,引自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9页。)就是得到经验的证实,不能为经验证实的命题便是无意义的“妄命题”,“形而上学的虚构句子、价值哲学和伦理学的虚构句子,都是一些假的句子”(注:R.卡尔纳普:《哲学和逻辑句法》,引自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集》,上册,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460页。),逻辑分析已经表明,这个领域内的所谓陈述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据此,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是建基于经验的唯一确实可靠的知识。在科学与非科学的其它文化之间存在着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能否为经验证实(或确证)就是区分科学与各种非科学的绝对标准,凡是能够为经验证实或确证的就是科学的,凡不能为经验证实或确证的都是非科学的、无意义的。科学与非科学之间不仅界线分明,甚至水火不容。其所提出和系统阐发的“合理重建”纲领、归纳主义方法论、“中国套箱”式的积累发展模式以及关于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的区分、发现范围和辩护范围的区分、理论和方法论的区分等,实际上都是其唯科学主义理想和“意义-证实”(或“理论-经验”)认识论模式的具体铺展。
逻辑实证主义以“经验证实”这一过分简单化的原则割裂了科学与其它文化的关系,否定了其它文化对科学的作用。
2 批判理性主义:科学就是能够被经验所证伪
首先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划界标准提出挑战的是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波普的批判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逻辑实证主义把划界问题和意义问题混为一谈是根本错误的。他指出,“发现一个理论是非科学的或形而上学的,并不会因此而发现它是不重要的、无关紧要的、‘无意义的’或‘荒谬的’。”(注:K.波普:《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54页。)第二,“经验证实”不能为科学与非科学“提供一个适当的分界标准”。因为经验证实依赖于归纳推理,而归纳推理面临着严峻的“休谟问题”,“严格的全称陈述是不能证实的”(注:K.波普:《科学发现的逻辑》,1977年,英文版,第70页。)。因而,可证实性“这个标准太窄了(又太宽了):它几乎把所有事实上典型地属于科学的东西都排除掉(然而实际上并没有排除掉占星术)”(注:K.波普:《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57页。)。在波普看来,能否为经验所证伪才是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理论的科学性的标准,就是理论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注:K.波普:《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37页。)。属于科学一方的,是各种在逻辑上或事实上有可能被经验所证伪的理论,包括各门经验科学;属于非科学一方的,是那些不可能在逻辑上或事实上被经验所证伪的理论,包括宗教、神话和各种伪科学以及形而上学理论。
以划界问题为契机,结合对逻辑实证主义“意义-证实”模式的批判,波普阐发了与逻辑实证主义很不相同的科学哲学思想。①波普涉及了科学发现问题,超越了逻辑实证主义关于发现与辩护的区分,扩大了科学哲学的研究领域;②波普不仅不否认形而上学的意义,而且肯定形而上学对科学的作用,认为“如果没有一种对某些纯粹思辨的、有时甚至是非常模糊的观念的信仰,科学发现便是不可能的”(注:K.波普:《科学发现的逻辑》,1977年,英文版,第38页。);③波普否定了观察语言与理论语言的区分;④波普肯定科学研究中包含着非理性因素,甚至认为“每一个发现中都包含有一种‘非理性因素’”(注:K.波普:《科学发现的逻辑》,1977年,英文版,第32页。);⑤波普否定了逻辑实证主义的积累发展观,提出了科学通过理论的不断证伪而发展的模式。
诚如我们所共知的,波普的思想的确构成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但是,就基本哲学倾向和思想内容来看,波普是逻辑主义者而非历史主义者。因为,他仍然是在“理论-经验”模式下讨论问题,仍然坚持理论与方法论的区分,仍然认为科学与非科学有着泾渭分明的界线,并且仍以“经验”作为判别科学与非科学的唯一标准。其实,波普对证实标准的许多反驳也完全适用于他的证伪标准。例如他对“纯观察语言”的否定,就不仅反驳证实标准,也同样反驳证伪标准。如果说“经验证实”不能作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那么“经验证伪”也同样不具备这个资格;如果说逻辑实证主义所刻划的科学模型脱离甚至歪曲了实际科学,那么批评理性主义也同样如此。历史主义正是把波普学派和逻辑实证主义一同作为逻辑主义加以批评的。
3 历史主义:划界问题走向消失
在历史主义看来,无论是证实标准还是证伪标准,都严重脱离和歪曲了实际科学,因而根本不可能对科学与非科学作出正确的区分。他们要求从实际科学史出发研究科学。库恩正是通过科学史的研究,阐发了他的“范式论”的划界思想。

库恩从科学史出发对波普的证伪标准提出了三点批评。第一,波普作为划界标准的可证伪性或可检验性是对基本理论的检验,即所谓判决性试验,这样的检验在科学发展中是很罕见的,在科学的常规发展中甚至根本没有这样的检验。“只是在相当特殊的情况下,检验才是针对现行理论的;在常规研究中,科学家不仅不检验现行理论,而且必须以现行理论作为博奕规则。”(注:载I.拉卡托斯、A.马斯格雷夫主编《批判与知识的增长》,1970年,英文版,第5页。)第二,证伪标准并不能把占星术等非科学排除在科学之外,因为占星术等也同样作出可检验的预测,并且承认这些预测有时候失败。第三,证伪标准“模棱两可,无法详细地规定是新假说在接受检验还是背景理论在接受检验”(注:载I.拉卡托斯、A.马斯格雷夫主编《批判与知识的增长》,1970年,英文版,第4页。),因而无法对其是否科学作出实质性的判断。在这个批评的基础上库恩提出了他的看法,“只要仔细关注科学事业就会发现,正是常规科学而不是非常科学,最能把科学和其它事业区分开来”。(注:载I.拉卡托斯、A.马斯格雷夫主编《批判与知识的增长》,1970年,英文版,第7页。)而一个领域进入常规研究的标志,就是拥有一个“范式”,“拥有一个范式,有了范式所容许的那种更深奥的研究,这是任何一个科学部门达到成熟的标志”。(注:T.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李宝恒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因此,按照库恩的看法,把科学与一切非科学(哲学、艺术、前科学等)区分开来的标准既不是证实,也不是证伪,而是在于有无范式以及是否在范式的指导下进行解决疑难的活动。
那么,范式真的能够担当起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重任吗?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范式”到底指的是什么。尽管库恩对“范式”一词有多种用法,但其基本含义则为两条:一是“包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仪器设备统统在内的范例”(注:T.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李宝恒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8页。);二是“告诉科学家自然界包括和不包括各种实体”(注:T.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李宝恒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89页。)等类似于形而上学的信念。即如他后来所说:“‘范式’的一个意义是总体性的,包括一个科学家集团的一切共同的信念,另一个意义把一个特别重要的信念孤立起来,因而是第一个意义的一个子集。”(注:T.库恩:《再论范式》,引自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页。)这就是说,“范式”是包含了价值、信念等形而上学因素的。既然范式自身就包含了大量非科学因素,它还怎样对科学和非科学作出区分?其次,库恩建基于范式的科学发展观本身就使科学陷入了非理性主义。因为,他认为科学的发展就是“一种范式经过革命向另一个范式的转换”,而这种转换则是“一种不能强迫的皈依的体验”(注:T.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李宝恒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125页。),是“根据信念作出决定”,其最高标准就是“有关团体的赞成”(注:T.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李宝恒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78页。)。既然连科学自身都成了非理性的东西,那么还有必要对科学和非科学作出区分吗?
库恩以后,历史主义沿着两条路线发展。一是拉卡托斯、劳丹的路线,力图在符合科学史的前提下为科学寻找经验基础,对科学作出合理性的说明;二是费耶阿本德的路线,继续发展库恩理论中的非理性主义因素,走向多元知识论,把科学视作人类众多意识形态之一种。但由于历史主义在划界问题上所面临的上述困难,无论是拉卡托斯、劳丹的路线,还是费耶阿本德的路线,最后都得出了科学和非科学无法分界的结论。
拉卡托斯首先对库恩的非理性主义作出回应。他仿照库恩的“范式”提出了“研究纲领”概念。他试图通过对研究纲领内在结构的精确分析,排除“范式”中的非理性、非科学因素,把科学及其发展重新置于经验的、理性的基础之上。然而,拉卡托斯并未达到他的目标。他对“新研究纲领如何产生”的回避,他的“对自相矛盾的反驳并不淘汰一个研究纲领”的观点、科学家“不管实际反例”继续进行研究的观点、允许相反的研究纲领长期并存的观点等,所有这些都并不比库恩的“范式论”更理性、更有经验基础。正如费耶阿本德所说,“被拉卡托斯所软化的科学方法不过是一个装饰品,它试图让我们忘记我们实际上在采用‘怎么都行’的原则”。(注:载I.拉卡托斯、A.马斯格雷夫主编《批判与知识的增长》,1970年,英文版,第229页。)
鉴于拉卡托斯所遭到的批评,劳丹已大大退却。他的“研究传统”已变为“有关该研究领域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的一套本体论和方法论的信念”(注:L.劳丹:《进步及其问题》,1977年,英文版,第80页。)。同时,与拉卡托斯把“研究纲领”作为科学的最高层理论不同,他强调“特定理论是更大的传统或‘大理论’的部分,……没有这些更大单元的历史进化知识,我们就无法妥当地评价它们的次级理论”(注:L.劳丹:《历史方法论:一种立场和宣言》,载《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6年第4期。)。伴随着“研究传统”向“本体论”和“信念”的扩展,伴随着评价单元向“历史进化知识”的扩大,必然是理性的弱化和非科学、非理性因素的大举侵入,必然是科学和非科学分界问题的消失。正如劳丹后来在《分界问题的消逝》中所明确指出的:“习惯上被视为科学的活动和信念都具有明显的认识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提醒我们注意,寻找分界标准的认识形式可能是无效的。”(注:L.劳丹:《分界问题的消逝》,载《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8年第3期。)
与拉卡托斯和劳丹不同,费耶阿本德不是去强化和精致库恩的范式,而是把“范式”更进一步弱化为“背景知识”。在他看来,科学“只是人所发展出来的许多思想形式之一”,还有“神话、神学教条、形而上学,以及其它许多构造世界观的方法”(注:P.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1975年英文版,第180页。),“如果我们要理解自然界,如果我们要支配我们的物质环境,那么我们一定要使用一切的思想,一切的方法”(注:P.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1975年英文版,第306页。)。因此,他认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离不仅是人为的,而且对知识的进展是有害的”。(注:P.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1975年英文版,第306页。)他还把问题引入更加深刻的层面,指出,科学目前“已成为太强大的,太富于进攻性的”意识形态(注:P.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1975年英文版,第217页。),“要克服我们的科学技术时代的紧张忙碌的野蛮状态”,就必须进行“国家和科学的分离”,并对科学进行管制。(注:P.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1975年英文版,第299页。)
正是以科学和非科学的分界问题为线索,劳丹和费耶阿本德构成了历史主义通向范·弗拉森和罗蒂的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最后一环。
4 后现代主义:科学只是一种解释文本
如果说历史主义对传统划界理论的批评还留有基础主义痕迹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则通过对基础主义的批判、通过对“客观”、“真理”、“实在”等概念的解构,彻底摧毁了科学作为知识典范的地位,彻底取消了科学与文学、艺术、宗教、神话等非科学文化进行分界的前提。相对于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则是真正的釜底抽薪。
范·弗拉森从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出发,要求摆脱传统经验论的束缚。他认为,“上一代哲学的错误是缠绵于证实,总的说是囿于认识论的基础主义”(注:Van Fraasen:After Foundationalism:Between Vicious Circle and Infinite Regress,in Proceedings of Conference on the Philosophy of Hilary Putnam,Taxco,Mexico, Aug.1992.),而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的认识论相对主义也是一种新的基础主义形式。要达到对科学的正确理解,就必须彻底摆脱基础主义“幽灵”。因此,他从语义学和语用学来理解科学,认为,科学是由语言构成的,理解科学就是理解科学语言,科学知识的增长也就是科学语言的不断创造和丰富。所以,“科学活动只是……适合于现象的模型建构,而非发现关于不可观察物的真理”(注:Van Fraasen:The Scientific Image,Oxford 1980,P5.),而“科学理论只是一个开放的文本,是有分歧的解释——即理论把现象描绘成什么,这本身不是一种硬证据。”(注:Van Fraasen:Interpretation in Science and in the Arts,Forthcoming in G.Levine(ed):Realism and Representation,Uniu.of Wisconsin Press.)“没有任何证据使我们相信所接受的理论为真”(注:Van Fraasen:The Scientific Image,Oxford 1980,P271)。范·弗拉森终于为科学滑向宗教、神话提供了哲学根据。
罗蒂也是在反基础主义和对“客观”、“理性”、“真理”等概念进行解构的“大文化”背景下来考虑科学。他指出,“与其提出任何象观念-事实,或语言-事实,或心灵-世界,或主体-客体的区别,以说明我们关于有些东西存在于彼岸,它们该对事物的产生负责的直觉,倒不如抛弃这样的直觉”。(注:R.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88页。)在他看来,所谓“客观性”就是“主体间性”,所谓“理性不是准确地表象实在的能力,也不是使用或遵守既定的方法,而是心胸开阔、有好奇心、依靠说服而不依靠压服”(注:R.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作者序。);而所谓“真理只是对一个选定的个体或团体的现时的看法”(注:R.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81页。),“它可以同等地运用于律师、人类学家、物理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的判断”(注:R.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80页。)。据此,他认为,科学“不过是文化中告诉我们如何预见和支配将会发生的事情的那个部分。这是值得去做的事。但预见和支配的成功并不表明较之在政治思考和文学批评中的成功,我们更‘接近于实在’或更‘受硬事实的制约’”(注:R.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作者序。);“无论是牧师,还是物理学家,或是诗人,还是政党都不会被认为比别人更‘理性’,更‘科学’、更‘深刻’。”(注:R.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5页。)因此,在罗蒂看来,科学与一切非科学文化一样,或者同样具有“客观性”、“合理性”、“真理性”,或者同样不“客观”、非“理性”、无“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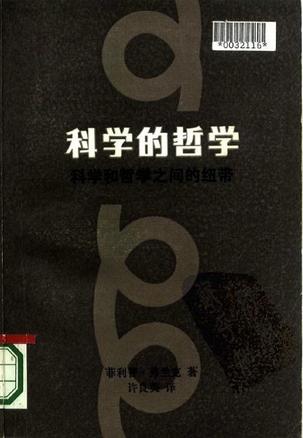
既然科学活动只是“模型建构”,科学理论只是“文本”;既然客观性只是“主体间性”,真理只是“团体的看法”;既然科学并不比文学批评更“受硬事实制约”,那么,科学与宗教、神话、文学、艺术等非科学还有什么区别呢?还有必要进行区别吗?至此,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在划界问题上完全陷入了困境。
5 辩证认识论视野中的划界问题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之所以在划界问题上一步步陷入困境,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处理好科学与非科学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没有使二者保持必要的张力:它们要么以科学的特有属性去整合、排斥人文文化,要么以人文文化的特有内涵去整合、解构科学。逻辑实证主义(包括波普学派)认为科学是最高的知识,他们不仅要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而且要以科学特有的“理论-经验”模式去整合其它文化,致使其所建构的科学模型严重脱离实际科学;历史主义则走向另一极端,他们把科学史中发现的非理性社会、心理因素无限放大,而根本无视科学的客观性、经验性基础,又使科学完全陷入了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泥沼;后现代主义更进一步,他们索性抛弃了“客观”、“真理”等概念,完全采用解释、解构的人文方法去审视科学,致使科学彻底沦为与宗教、神话、文学、巫术为伍的一种“文化经验”。
不可否认,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还是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都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科学的某些特征,都从一定的角度揭示了科学与其它文化之间的关系。但是,正如其演变过程所表明的,它们各自所描述的科学都是片面的。要想正确地解决划界问题,要想全面地说明科学与非科学文化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对它们进行辩证的综合。
首先,科学与非科学文化之间是有着重大区别的,这个区别的最根本方面就是科学的经验基础和严密的逻辑性。逻辑实证主义所倡导的“理论-经验”范畴,其从经验解释科学理论的基本思路是应当肯定的。毕竟,科学是探究自然界的规律的,其有效性、真理性需要有客观的经验基础来保证。退一步说,即使科学只是“文化中告诉我们如何预见和支配将会发生的事情的那个部分”,也仍然回避不了如何“预见和支配将会发生的事情”这样的经验命题。但是,以此否定科学的其它方面,割裂科学与其它文化的联系、否定科学作为人类文化所具有的一般文化特征,则是片面的、错误的。
其次,揭示和把握科学中非理性的社会、心理因素,揭示和把握科学的人文文化侧面,也是必不可少的。正如历史主义所表明的,科学的确决不仅仅是由纯之又纯的经验命题构成的,而是由深层的形而上学信念和价值观念与表层的经验命题共同支撑的。同时,科学也确有后现代主义所揭示的侧面,科学作为一种人类文化的确具有宗教、神话、文学、艺术等所具有的一般人类文化特征。事实上,科学从一开始就与宗教、艺术等非科学文化密切相关,而今天更存在着科学与社会人文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启发的整合化趋势。从文化的高度揭示和把握科学与非科学文化的共同特征,对我们正确地理解科学、发展科学的确十分重要。但以此否定科学的经验基础、否定科学与其它人文文化的区别,甚至认为科学与文学、宗教、巫术等同样具有“客观性”、“真理性”或同样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则也是片面的、错误的。
最后,科学与非科学文化之间的关系决不是以一方去整合、否定另一方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相互制约的辩证统一关系。“理论-经验”模式揭示了科学相对于非科学文化的基本特征,但它有其不可克服的狭隘性,必须以“文化-科学”范畴来补充。即使逻辑实证主义所致力的“科学理论的结构”这一问题,“理论-经验”模式也并不绝对成立,因为观察渗透理论。另一方面,“文化-科学”模式也必须以“理论-经验”模式补充,否则,不仅会抹煞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连人们的文化思维方式也将退回到原始思维水平。
划界问题、科学与非科学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当前,面对后现代主义颇具破坏性的剧烈冲击,加之我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特殊国情,全面、正确地揭示和把握科学与非科学文化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希望本文能抛砖引玉,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原文参考文献:
[1] M.石里克:《意义和证实》,引自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9页。
[2] R.卡尔纳普:《哲学和逻辑句法》,引自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集》,上册,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460页。

[3] K.波普:《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54页。
[4] K.波普:《科学发现的逻辑》,1977年,英文版,第70页。
[5] K.波普:《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57页。
[6] K.波普:《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37页。
[7] K.波普:《科学发现的逻辑》,1977年,英文版,第38页。
[8] K.波普:《科学发现的逻辑》,1977年,英文版,第32页。
[9] 载I.拉卡托斯、A.马斯格雷夫主编《批判与知识的增长》,1970年,英文版,第5页。
[10] 载I.拉卡托斯、A.马斯格雷夫主编《批判与知识的增长》,1970年,英文版,第4页。
[11] 载I.拉卡托斯、A.马斯格雷夫主编《批判与知识的增长》,1970年,英文版,第7页。
[12] T.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李宝恒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
[13] T.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李宝恒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8页。
[14] T.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李宝恒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89页。
[15] T.库恩:《再论范式》,引自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页。
[16] T.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李宝恒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125页。
[17] T.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李宝恒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78页。
[18] 载I.拉卡托斯、A.马斯格雷夫主编《批判与知识的增长》,1970年,英文版,第229页。
[19] L.劳丹:《进步及其问题》,1977年,英文版,第80页。
[20] L.劳丹:《历史方法论:一种立场和宣言》,载《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6年第4期。
[21] L.劳丹:《分界问题的消逝》,载《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8年第3期。
[22] P.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1975年英文版,第180页。
[23] P.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1975年英文版,第306页。
[24] P.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1975年英文版,第306页。
[25] P.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1975年英文版,第217页。
[26] P.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1975年英文版,第299页。
[27] Van Fraasen:After Foundationalism:Between Vicious Circle and InfiniteRegress,in Proceedings of Conference on the Philosophy of Hilary Putnam,Taxco,Mexico,Aug.1992.
[28] Van Fraasen:The Scientific Image,Oxford 1980,P5.
[29] Van Fraasen:Interpretation in Science and in the Arts,Forthcoming in G.Levine(ed):Realism and Representation,Uniu.of Wisconsin Press.
[30] Van Fraasen:The Scientific Image,Oxford 1980,P271
[31] R.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88页。
[32] R.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作者序。
[33] R.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81页。
[34] R.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80页。
[35] R.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作者序。
[36] R.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