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6月14日)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马克斯·韦伯逝世100周年。
韦伯一生基本默默无闻,但其后他的名声呈几何级数增长:他开创了一些重要思想,对理解资本主义的运作和未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他认为新教使得资本主义得以发生。与卡尔·马克思截然不同的是,马克思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唯物主义观点:认为科技创造了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系统。而韦伯提出了唯心主义的观点:认为是一组理念在事实上创造了资本主义,推动了新生的科技和经济发展。韦伯虽生性谨慎,但却出乎意料地给出了许多如何改变事物的理念。他提醒我们要改变国家,思想可能远比工具和金钱更重要。
作为凡人的韦伯,早已经随着他的祖国德意志第二帝国烟消云散了;而作为学者和思想家的韦伯,屡屡面对这样的命运——每当有人宣称,韦伯的理论是错误的或是过时的时候,他就又一次获得了“新生”。
韦伯
德国海德堡山顶墓地里埋葬着一个人。他的墓志铭是其妻从《浮士德》中挑选的一句话:尘世一切皆寓言,自此吾辈再无君。这个人就是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
韦伯,已然成为了一块人们无法轻易绕过的现代性界碑。他站在了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转折点,用自己的著作标界出了日后理论界的分殊要害。无论是广为人知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还是艰涩冗长的《经济与社会》,抑或是振聋发聩的《学术与政治》,总是被人们反复阅读、误解、附会、诅咒、批判、阐发和捍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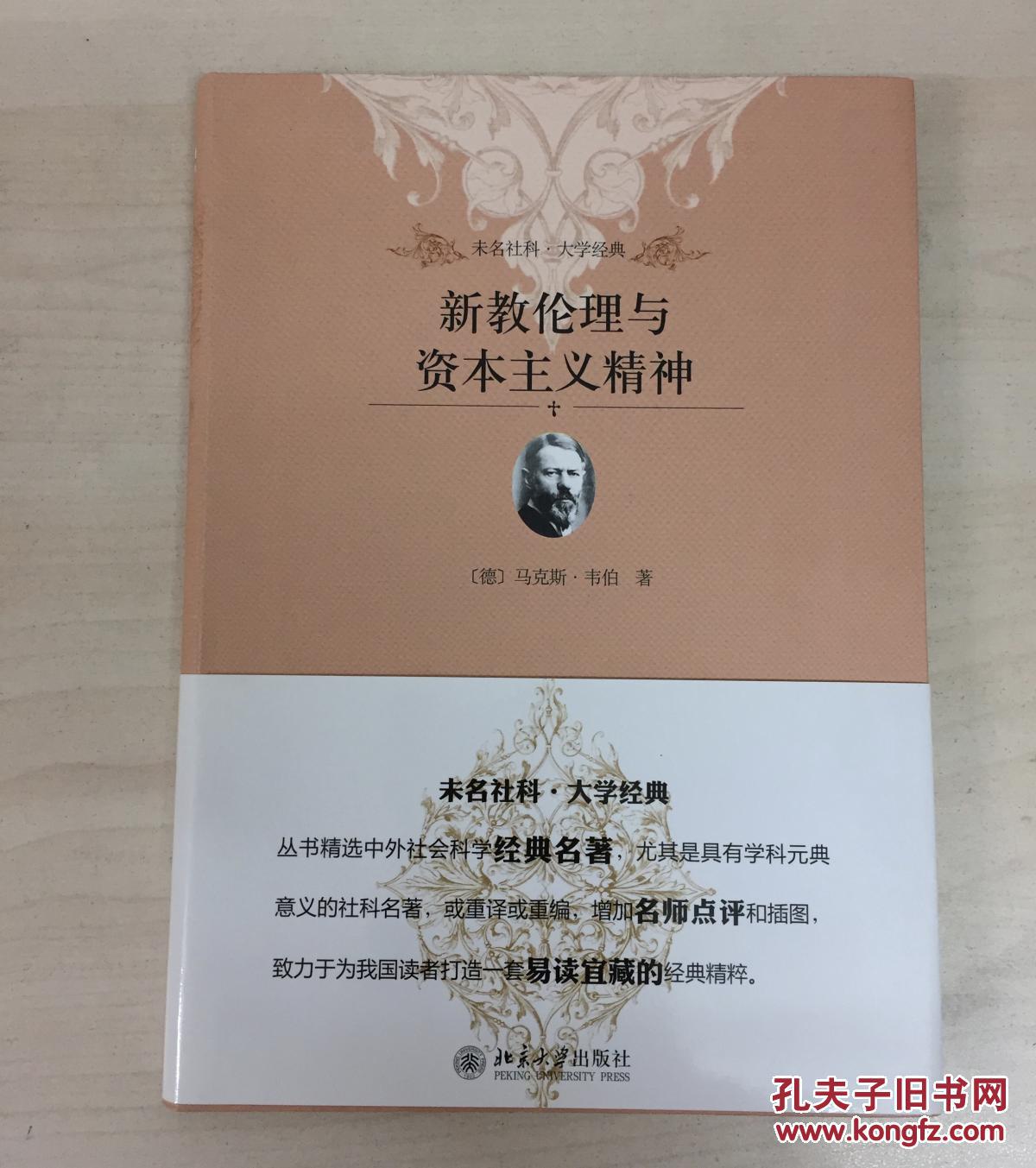
对很多人而言,韦伯是一个谜一般的大师。他拥有众多令人眩晕的头衔:例如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者之一(另两位为卡尔·马克思和埃米尔·涂尔干)、公共行政学的创始人、法律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的开创者……然而必须坦承,如果韦伯活在当下,几乎没有可能成为大师——他既没有子嗣,也没有众多的徒子徒孙;甚至,他担任教授的年份加在一起也屈指可数,大部分时间他只是一个“业余研究者”。
1864年,韦伯出生在德国中部图灵根州埃尔夫特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父亲老韦伯是律师和高级公务员,母亲出身于一个拥有贵族血统的教育世家。韦伯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学术道路上可谓一帆风顺。
马克思韦伯与妻子
他在海德堡和柏林上大学,25岁就获得了博士头衔,27岁通过了大学授课资格考试。1894年,30岁的韦伯获得了弗莱堡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职;两年之后,他又接受了母校海德堡大学的教职。
但是,好景不长,韦伯很快就因为严重的神经官能症而病休。在病情没有可能好转的情况下,韦伯最终在1903年10月辞去了海德堡大学教职,此后一直赋闲在家写作。
一战中,他短暂地担任过预备役医院的管理工作,战后还参与了凡尔赛和会。他曾经想重拾教鞭,在慕尼黑开始自己的第二次学术生涯。不料命运弄人,1920年6月,韦伯因肺炎而离世。
韦伯的内在精神世界是他所处时代的一个缩影——高度紧张而充满矛盾。他一辈子一直处在双重身份的纠结中:一方面,他曾经以学术为“天职”;另一方面,他却认为自己不属于讲台,而想要投身政治。
韦伯是一个爱国者,他希望德国能够迅速崛起,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但韦伯更是一个学者,他坚持不懈地追求自由和真理。作为学者的韦伯对自己的祖国,保持着批判和警醒。他从欧洲乃至人类文明的视角,审视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走向

按照德国学者迪尔克·克斯勒的整理,韦伯一共留下了226个学术文本。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德国摩尔齐贝克出版社开始整理出版《韦伯全集》。全集分为三个部分——著作和演讲、书信、讲课和讲课记录,共40余卷,预计将在2019年出齐。
一般认为,韦伯的所有著作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韦伯博士论文和教授资格考试论文中关注的国民经济学和经济史的研究。韦伯在1892年到1894年,还对东易北河地区农业工人状况进行了系统调查。
第二部分是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研究,其中包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1906)。《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发表之后,韦伯收到了大量的评论和批评,他对此作出了回应和反批评。在一战的隆隆炮火中,韦伯重拾问题,将研究视野扩展到了世界范围内的比较研究,着手开始了《诸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1916-1919)的写作。
第三部分是他的一般社会学的研究,包括法律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统治(又称“支配”)社会学和音乐社会学。
第四部分是韦伯对社会学研究方法论问题的反思,其中包括《罗舍尔和克尼斯与国民经济学中的逻辑问题》(1903)、《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的“客观性”》(1904)、《论理解社会学的一些范畴》(1913)等。
由此,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也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解读韦伯的两个不同重心:一些学者把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文集》(1-3卷)作为重点,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韦伯死后出版的巨著《经济与社会》才最能体现韦伯思想的整体性。
韦伯以下,也形成了解读韦伯的几个总命题。例如,罗伯特·贝拉《德川宗教》(1957)和艾森斯塔特的《新教伦理与现代化》(1968)均将“现代化”作为韦伯的总命题。而田布洛克《韦伯的作品》(1975)和施路赫特则将“理性化”和“祛魅”作为理解韦伯的门径。在社会学家和社会理论中,帕森斯和哈贝马斯特别继承和发展了韦伯的行动理论。当然引起争议最大的始终是韦伯理解社会学的一些基本方法和规范,例如价值判断无涉、理想型等。
“资本主义精神”的宗教特质
宗教
韦伯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种“情结”——无论是反对韦伯的人,还是支持韦伯的人,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韦伯问题”:为何在西方近代发展出了“合理资本主义”?韦伯最初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篇论文中讨论这个问题的。
事实上,韦伯明确区分广义和狭义两种“资本主义”:广义的资本主义存在于人类的各个历史时期和多个文明当中,中国亦不例外;而狭义的资本主义是近代西方所特有的,它具有一种独特的“精神”。韦伯认为,这种精神的特征是将赚钱作为劳动的唯一目的,并将本杰明·富兰克林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代表。恰恰是这种“精神”,帮助人克服了资本主义的大敌——“传统主义”,即那种倾向于享受悠闲、知足的心态。
韦伯之所以聚焦于新教伦理,并非出于神学考虑,而是因为一项人口学的发现。韦伯的学生马丁·奥芬巴赫在1901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在德国西南部的巴登地区,新教徒的人均课税几乎是天主教徒的两倍;此外,虽然这一地区天主教徒比例占优,但是在各级学校中,新教徒比例都比天主教徒高。这说明新教徒在经济上比天主教徒更为成功,且新教家庭更重视教育。由此韦伯认定,造成这些差异的因素在内在的宗教特质中,而不是在外在的环境因素。
在随后的章节中,韦伯重点考察了宗教改革之后的加尔文派。他认为,加尔文派的两个神学教义——神恩蒙选和预定论,塑造了一种“入世苦行”的伦理。神恩蒙选说认为,一个人是否获得拯救,仅仅取决于上帝的意旨。
而预定论则认为,上帝在创世之前已经决定了哪些人获得拯救。由此,加尔文派信徒会陷入一种空前的孤寂感中。他们将荣耀上帝作为世俗生活的唯一目的,并要体现在其职业劳动中。这种生活方式要求消除无拘无束、充满本能的生活享受,坚持不懈地在俗世中进行各自的职业劳动。
韦伯研究专家沃尔夫冈·施鲁赫特认为,在方法论层面上,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一种理念如何在历史中真正发挥作用?韦伯认为,一种理念必须通过真心诚意相信并践行它的人群——理念“承载者”的具体伦理实践和生活方式——才能在历史中发挥作用。在这一点上,韦伯不同于哲学上的理念论者。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韦伯问题”的回答并非无可指摘。有的学者用更为详尽的经济史数据和资料举出了反例:在某些天主教为主的地区,例如16世纪的威尼斯、17-18世纪的爱尔兰,资本主义同样欣欣向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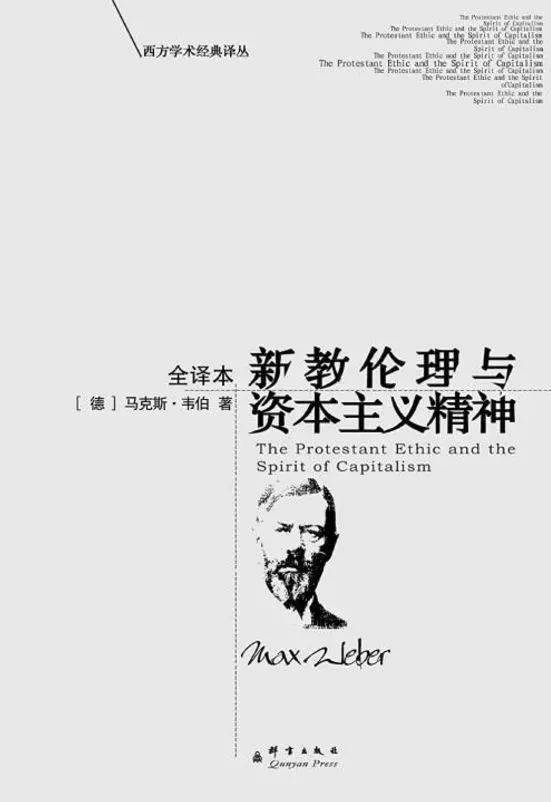
还有经济学学者指出,韦伯很可能忽略了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变量——教育和识字率对提高人力资本的作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亚洲地区经济的腾飞,也对韦伯命题提出了实质性的挑战。以余英时和杜维明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尝试用“儒家伦理”替代新教伦理的各种假说,对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的观点进行了反驳。
韦伯在一战中进行的“诸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研究,将原本的“韦伯问题”扩展到了各大世界文明中。
原本的问题也被倒了过来:为何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其他文明,没有出现过类似西方近代的“合理资本主义”?在韦伯看来,合理主义作为欧洲近代资本主义的特质,不仅体现在经济制度中,也表现在科学、技术、法律、官僚体制,甚至艺术当中。
笔者认为,对韦伯问题的考察包含了“中西”和“古今”两种可能的坐标系统。如果只关注中西差异,将韦伯问题仅仅理解为一个“人有我无”或“人无我有”的问题,将会陷入历史细节的琐碎考证和无谓(不具有可比性的)比较中,而错失其关切的实质。
如果把韦伯问题放入古今框架中来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其实质:现代化的基本动力是什么?
或者说,对后进现代化国家和地区而言,“韦伯问题”在更深层次上,不再单纯旨在理解已经发生的历史过程,蕴含的乃是一个指向未来的规范性设问:怎样的现代性才是值得追求的?然而,后现代的文化多元主义以接近虚无的方式尝试回避这个问题。
在学理上对世界范围内多元现代化路径的承认,并不意味着单个民族或国家,可以同时采取多个现代化路径。即便存在新教伦理的“功能等价物”(例如儒家伦理),它是否就可以持续地成为合理化的内在动力?即便我们承认存在多元现代化的不同路径,依然无法回避“韦伯问题”的一个深层逻辑问题——如何在规范层面上区分“前现代”与“现代”?反之,若一味地强调文化和制度的“特殊道路论”,也势必会滑向虚无主义的无解境地。在此意义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可以构成对韦伯的补充,甚至也提出了对新教伦理命题的重大挑战,但依然无法回避“韦伯问题”。
在完成了“诸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研究之后,韦伯在整个项目的前言中写道:关于合理主义,存在截然不同的理解……例如,神秘主义的冥想,是种从其他生活领域看来非常不合理的行动,但却有神秘主义冥想的合理化,正如经济、技术、科学工作、教育、战争、司法和行政的合理化一样。
此外,这些领域每一个都可以从不同的终极视角和目标而加以合理化,从一者看来是“合理的”,在另一者看来是“不合理的”。因此,在截然不同的文化圈和不同的生活领域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合理化。
笔者认为,这段话道出了韦伯对现代性的一个基本判断:以往的绝对价值序列已经被打破,人们不再接受任何统摄一切的终极价值。换言之,任何“合理”都是局部的合理,并不存在整体的合理。这并非单个文明面临的困境,而几乎是现代性的宿命和诅咒。
韦伯在《宗教社会学文集》第一卷的“中间考察:宗教拒世的阶段与方向”中,提出现代人的六个基本“价值领域”:经济、政治、宗教、审美、性爱和知性。这些领域中的价值是无法彼此通约和还原的。韦伯在慕尼黑的演讲《以学术为业》将这种价值理论称为“诸神之争”。这样一种价值多神论意味着,不同价值领域之间不可调和,甚至处在相互的永恒冲突之中。即便是在个人的生活中,也可以时刻感受到各个价值领域之间的张力和撕扯。
韦伯的价值多神论似乎也为他的悲观主义提供了底色。韦伯在弗莱堡大学的就职演讲中,就曾经引用《神曲》中地狱之门门楣上的铭文说道:“就和平和人类幸福的梦想而言,在通向人类历史那未知将来的门楣上写着:‘入此门者,当放弃一切希望!’”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