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史学研究为人们提供了对历史的认知,那么对史学研究这一认知活动的知识论和方法论进行反思则是史学理论所扮演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史学理论展现了对历史学以哲学方式的观照,因此,也被称为历史哲学。然而,在历史学的学术发展史上,学界对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的意义和价值,往往有不同的认识。对于当代中国史学研究而言,要将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作为时代使命,那么,正视史学理论的学术功能,并提升中国史学理论的反思水平,则是不可偏废的功夫。围绕史学理论与史学实践的关系等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董立河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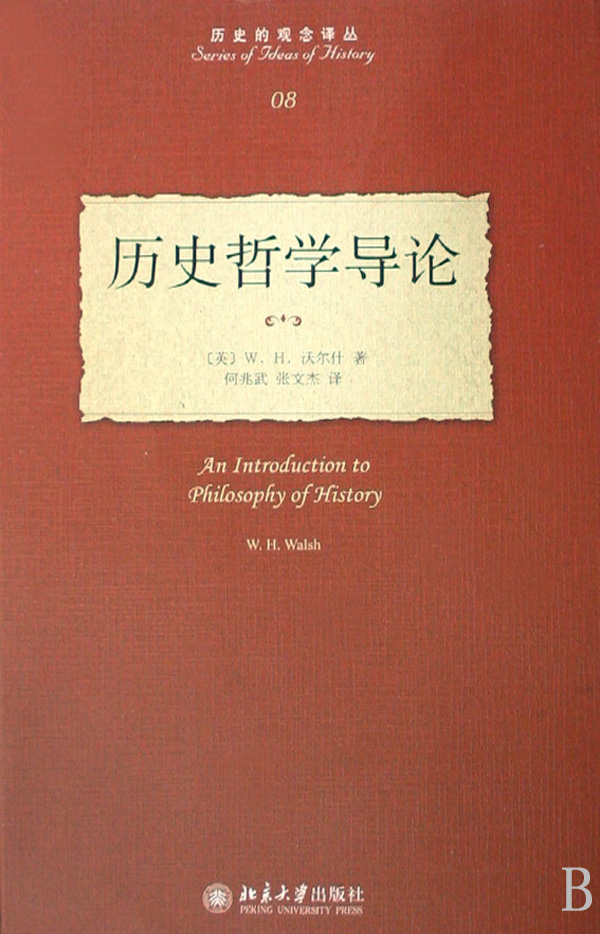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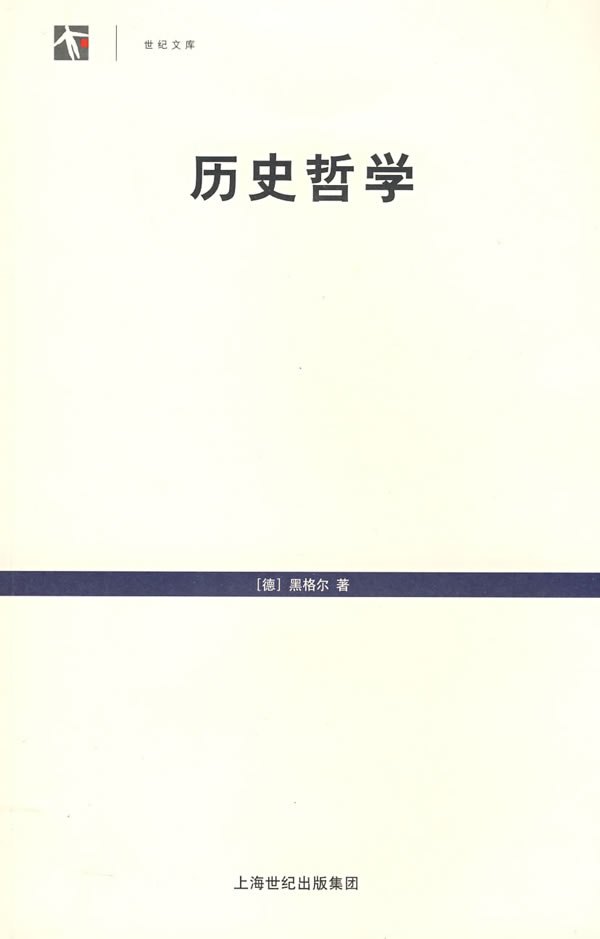
史学理论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谈到史学理论与历史学实践的关系时,曾使用“观看”这个颇具形象化的动词,并且将史学理论定性为一种哲学。历史学为何需要这种“哲学的观看”?董立河:在谈史学理论与史学实践的关系之前,有必要先追问一下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存在于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一切活动领域,不仅仅局限于学科领域。实践决定理论,而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列宁曾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不过,有意思的是,人们对于理论和实践的态度却有些纠结。对于理论和实践,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人们存在着一些认知误区。理论往往被看作是凌空蹈虚、不切实际的,而实践则被视为脚踏实地、稳妥务实的。在谈论这对矛盾范畴时,人们也就自然会夸大它们之间的对立性,却无意间轻视了二者之间的统一性。在西方古典时代,理论的声誉要好得多。我曾对西文中的“理论”一词作了初步的词源学考察。“理论”(theory)一词来源于希腊语动词theorein(名词形式为θεωρία,theoria),与“看”(look at)或“观看”(view)相关。在柏拉图看来,θεωρία作为一种神圣的“观照”,是人(哲人)的理性活动所能达到的至高至纯的境界。
人只有在这种境界中才能“看到”本真的存在,从而获得“真知”。这样看来,理论反倒是对现实最真实的捕捉。我国古代也存在类似的观念。《道德经》有言,“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在老子看来,万物竞相生长而终将复归根本的规律,也是需要“观”的。柏拉图还说,视觉是给我们带来最大福气的通道。亚里士多德也认为,眼睛是人类最偏爱的求知器官。如果人们没有见过日月星辰,就不会有关于宇宙的学说。眼界决定着思想的境界。能看多远,就会想多远。“思想”和“眼睛”之间存在某种关联性。当然,这里所说的眼睛,已不主要是指人的肉眼,而是“概念的眼睛”,是“心目”。视觉形象构成理论。反过来,理论也可以归结为视觉形象。“观看”并不都是理论,但理论都具有“观看”的维度。理论往往可以通过还原为视觉形象去加以确证,所谓“眼见为实”,也只有借助于视觉性的隐喻,才会被普通人更好地理解。比如,一提到万有引力定律,很多人头脑中都会闪现出苹果落地的画面。关于光的性质的理论,人们也往往会联想到颗粒和波浪。因此,理论与视觉存在密切的关联,是一种“看法”或“观点”。在德语中,“世界观”(Weltanschauung)作为一种有关世界的理论,其实是“观”(anschauen)“世界”(Welt)。
这与英语中的“世界观”(world view)是一致的。在中文语境中,我们习惯上所说的“三观”,也就是对世界、人生和价值的“观点”。另外,无论中外,“理论”一词以及与理论相关的词,也经常与视觉性的词语组合使用。比如,“理论观点”“理论视角”“理论视野”“理论眼光”“高见”“远见”(foresight)、“洞见”(insight)、“创见”“见解”“见识”等。语言表达透露出“理论”与视觉的内在关联。就史学理论而言,国内外学界有不同的界定。我把史学理论等同于历史哲学。在这里,“理论”“哲学”和“思想”是同等层次的概念,都可以理解为一种“观看”。我把史学理论分为两部分,一是历史理论,二是狭义的史学理论。前者是对于历史事件进程的概观,后者是对于历史思维过程的反思。先说“历史理论”。它有时被称作“历史观”,也就是“观历史”,是对历史本体的一种整体性的哲学把握。“历史理论”通常具有视觉特征。比如,一提到历史循环论、线性进步史观,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便是“圆”和“直线”的几何图形。唯物史观的主导概念“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则是一个有关大楼的视觉隐喻。作为对历史本体的一种“观点”,历史理论具有认知真实性的要求,也就是说,历史进程起码在某些人看来本就是周而复始的,或在某些人看来的确是不断进步的。
然而,历史理论最突出的特征在于其伦理的和审美的价值取向。历史理论不仅是经验描述,而且是先验规范。换言之,它不仅要传达过去究竟是什么样子,往往还指示历史应该是什么样子,因而具有未来向度。唯物史观既有经验的认知真理性,也有面向未来的价值理想性。历史理论既有客观性,也有主观性,不仅有规律和理性,也有价值和情感。换一种历史理论,也就是换一种观看过去的视角,同时也意味着一种不同的态度和心情。当然,人类需要理性而崇高的历史观。再说“狭义的史学理论”。它有时也被称作“史学观”,也就是“观史学”,是对历史学本质的一种哲学“透视”,聚焦于历史思维的“前提假设”。狭义的史学理论既是认识论也是方法论。狭义的史学理论是在19世纪晚期史学真正进入哲学的“问题视域”之后产生的。在此后近一个半世纪的时期内,围绕“历史学是什么”这一核心问题,形成了不同的狭义的史学理论“范式”。我们知道,“范式”这个词来自于科学哲学家库恩。他所说的“范式”的转变,其实就是一种看待科学发展的“视角”的转换。在某个史学理论范式中,史学家或者看到了历史学作为(自然)科学的一面,或者关注于其作为艺术的一面,从而形成了有关历史思维性质的不同的“前提假设”。
这些前提假设或学科理想一旦形成,它们就会多多少少规定着史家的研究视野。比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海登·怀特等史学理论家开始将人们的目光吸引到历史学家的语言上,特别是历史学的故事和修辞层面上,从而重新凸显了历史学的艺术面相。于是,在这一前提假设下,西方史学界涌现出了一批像《屠猫记》《马丁·盖尔归来》之类的文学性历史作品。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狭义的史学理论对于历史学实践具有根本性和构成性的作用。

历史学家与历史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报》:事实上,在历史学的学术史上,我们似乎一直能感受到对哲学进入历史学领地的“警惕”,历史哲学被认为是对历史学的“僭越”。您怎么看历史哲学的“身份”问题?董立河:在我看来,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是一回事,其实它就是哲学。历史理论也被称为“思辨的历史哲学”,而狭义的史学理论则被称作“史学哲学”。但是,对“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这两个术语,史学界的态度却有所不同。无论中外,人们大体认可前者,因为它被认为是历史学,而多少排斥后者,因为它被归于哲学。这背后便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学科身份或认同观念。自19世纪历史学科专业化以来,特别是从兰克史学被普遍接受以来,西方大部分经验派史学家一直都在努力将历史学同其他学科区别开来,以构建自身的学科身份。当代一些史学家不欢迎哲学家作为局外人对自己的学科指手画脚,担心好不容易构筑起来的学科认同遭到瓦解,从而发出类似“哲学请走开,我们是历史学家”的呼声。在他们看来,哲学扰乱而不是促进了他们的工作。当然,在跨学科趋势日益显著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史学家已经认识到,在史学和哲学之间设置学科壁垒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哲学和历史学之间,不应该是一种“多一点哲学就少一点史学”的零和关系,而应该是一种协作共生的相互促进关系。
许多伟大的著作,都是在作者浑然不觉学科边界的情况下,针对现实问题进行研究的结果。马克思、涂尔干、韦伯,他们同时是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后结构主义者福柯,正是以无论史哲的态度和方法,对社会历史问题提出了深刻而新颖的洞见。何兆武先生认为,考证出历史事实固然重要,但要达成对历史的真正理解则需要哲学的深度。刘家和先生通过回应黑格尔等哲学家的挑战,在中西史学比较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深刻的研究成果。历史学家之所以“警惕”历史哲学,其中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历史哲学家大都出身哲学,而缺乏历史学的从业经验。其实,历史学家和普通人的区别并不如人们想象得那么大。如同柯林武德所说,历史是所有人理解现在的方式,也是每个人处理问题的手段。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定程度的历史意识,都是历史的存在,这与是否为历史学家无关。贝克尔甚至说,从历史学作为对过去的记忆的角度看,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历史哲学与历史学家之间的距离也同样被人为夸大了。狭义的史学理论,也就是史学哲学,关注的是历史学家工作的前提假设。历史理论或思辨的历史哲学,作为历史学家整理杂乱历史经验的必要框架,则是另一种形式的前提假设。无论是思辨的历史哲学,还是史学哲学,各自有一个从自在(潜在)到自为(自觉)的转折点,前者大致是从奥古斯丁开始,后者要晚得多,大约肇始于19世纪晚期。
不过,即便在自在的阶段,左右着历史学家工作的那些前提假设,也始终是在场的,否则也就算不上前提假设了。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在书写历史的时候,头脑中一定闪现着有关“历史进程如何运行”,以及“好的历史书写应该是什么样”之类朴素的观念。因此,仿照贝克尔的说法,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我们也有理由说,历史学家都是他们自己的历史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报》:从历史本体与历史学的关系来看,您如何理解历史学的“科学性”?当我们强调科学性时,理论性是否一定要被拒之历史学的门外?董立河:在人们的观念中,历史学是一门经验性或实证性的学科。而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则多多少少具有先验性和超越性,呈现某种“自上而下”的外在性。这是经验派史家对史学理论保持“警惕”的另一个原因。就思辨的历史哲学来说,康德和黑格尔等这类伟大的思辨家,为了追求统一性和意义感,的确会有意无意地损害或扭曲“纯”经验的历史事实。然而,历史不仅需要用经验性范畴来予以描述,也需要用先验性范畴来加以规范。陈旭麓先生毫不避讳自己治史的“思辨”特色,其名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深受人们的喜爱。他用以解释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新陈代谢”理论,显然是来自生物学领域。
可以说,任何历史理论都具有某种先验性和理想性。而且,即便是看似平实直白的经验性概念,也很难避免先验性和普遍性。史学哲学的任务是反思历史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思维特征,也可以说是对历史学本质的一种“自上而下”的“俯视”。就目前来说,“史学哲学”有三种主要形态:“批判的历史哲学”“分析的历史哲学”和“后现代历史哲学”。后两种无疑都属于“自上而下的”历史学认识路径。“分析的历史哲学”的核心内容覆盖律解释模式,并不是由其代表人物亨普尔通过考察实际历史解释总结出来的,而是其科学解释理论向史学领域移植的产物;而“后现代历史哲学”的叙事理论和转义理论等,也并非主要来自历史研究本身,而是源自文学批评理论。“批判的历史哲学”的思想标识是历史主义,旨在论证历史学的自律性,因而的确是历史学园地里“土生土长”的一种史学哲学。然而,关于“历史学终究是艺术”的论断,则同样是从外部的哲学视角出发,审视和比较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的思维特征而得出的。如同我前面所提到的,这三种史学哲学所得出的历史学或科学或艺术的前提假设一旦确立,就会对历史学家的工作产生“自上而下”的规范和借鉴作用。总之,历史学的科学方法论“武库”中,除了要有经验的技艺工具,更要有先验的哲学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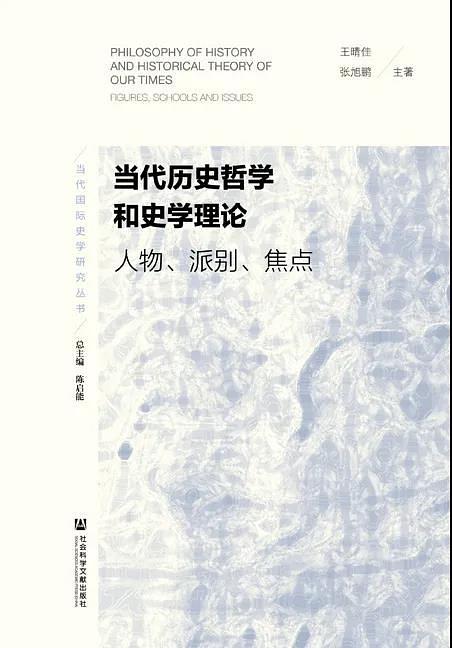
增强理论自觉《中国社会科学报》:今天学界以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为学术自觉。与时代使命相呼应,建设中国特色史学理论应有何为?董立河:任何一门学科,如果故步自封,因循守旧,就会出现知识生产力的停滞甚至递减。作为一门执着于经验事实的实证性学科,历史学更容易出现这种内卷化现象。历史学的创新,并非来源于同质知识的累积和叠加,而是来自于异质思想的碰撞和激荡。而哲学的普遍化对于历史学的个别化,往往能够达到意想不到的激发效果。纵观近代以来的西方史学史,几次重大的历史学实践的革新,都受到哲学观念直接或间接的影响。18世纪末,思辨的历史哲学对融贯统一性的诉求,激起了人们对散漫的编年史的不满。如柯林武德所言,普遍历史的观念打破了历史学中的狭隘,正如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最终打破了天文学中的狭隘。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后现代历史哲学”,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但对历史学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它崇尚多元和开放,鼓励史家重思历史,转换视角,历史学也因此焕发了生机和活力。新文化史、性别史和后殖民史的兴起和繁荣,与后现代主义的启发有很大关系。进入21世纪,西方史学理论家在深化后现代议题的同时,也在积极开拓新的视野。一部分学者的视线开始从抽象的语言转向生动的经验、记忆和情感,从而导致了“记忆的转向”,促成了大众史学和情感史的勃兴。另外,世界全球化趋势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史学本身的碎片化倾向,又引发了史学理论家对思辨的历史哲学和整体性观念的乡愁。当前全球史和大历史的盛行,以及普遍历史的复兴,都多少与之相契合。史学理论的任务及其价值在于,把史家头脑中自在的前提假设揭示出来,使之成为人们的自觉,以便更好地研究和书写历史。面对风云变幻的世界形势,致力于民族复兴的当代中国,既需要讲好自己本民族的故事,也要讲好与其他民族和谐共处融合发展的故事。为此,我们迫切需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为了提高在学理上的说服力,增强在国际史学界的话语权,我们的历史学必须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我们不仅要知道历史本体的所以然或道理,也要知道历史认识的所以然或道理。历史学“躯体”需要史学理论的“骨骼”和“灵魂”。构建真正令人信服的中国特色历史学离不开史学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