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今建构中国哲学话语的一个重要根由是为了摆脱近百年来西方话语对于中国哲学主体性的宰制,而福柯的“话语理论”就对话语宰制主体的问题做了理论上的揭示与批判。不过,与福柯批判现代性的后现代立场不同,中国学界大多基于中西对峙的民族立场而批判现代西方话语的西方性,这也成为近现代儒学话语建构的底色。然而,包括儒学话语在内的任何主体话语都不具有自明性,而是有着前主体的共同本源,即前主体性言说,其本源地生发着主体话语的实质内容,同时也引导着主体话语的时代更迭。因此不论中西,都需要以当下的现代性生活本身为共同渊源,建构与之相宜的主体话语。据此而言,传统儒学话语并不是落后于西方,而是落后于时代,故当今建构儒学话语的根本在于实现传统儒学的现代转化,即以儒家的思维方式言说现代主体价值。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在顺应时代的积极意义上持守儒学话语的独特性,才能在发展现代主体价值的普遍意义上有效地批判现代西方话语。
关键词:话语理论;现代主体;儒学话语;西方话语;
“建构中国哲学话语体系”是中国学界继讨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省察中国哲学的“失语”现象之后,对于如何确立中国哲学主体地位问题的新一轮思考。尽管目前国内哲学界已体现出充分的思想自觉,但尚未对中国哲学话语建构的基本思路和根本内容做出理论上的解释。而在这方面,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的话语理论已提供了一种颇具影响力的解释,因此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为此,笔者拟通过与福柯话语理论的对勘,尝试从当代儒学的视域,就中国哲学话语建构问题展开必要的分析。
一、批判现代西方话语的逻辑与旨趣
(一)批判的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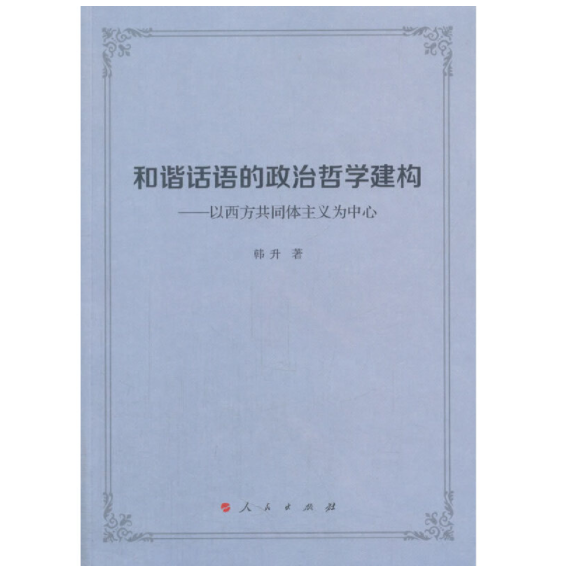
建构中国哲学话语的一个重要根由是为了摆脱近百年来西方话语对于中国哲学主体性的宰制,这虽然一直渗透在近现代中国哲学的研究与实践中,但国内学界并没有对西方话语与中国哲学主体性之间的逻辑关系问题提出专门的理论解释。而福柯的“话语理论”就话语宰制主体问题的揭示与批判,似乎可以为这一问题提供一种相应的学理支撑。
如福柯所说,我们要建构的“话语”不仅仅是一种说话的权利(speaking right),而是一种在特定历史时期,通过特定知识系统表达出来的一系列陈述(statement),其实质表征和确证的是当时社会的特定权力关系。当然,在福柯的分析中,话语本身也是在特定社会语境中,由特定的说话人、受话人、文本等要素相互影响和共同作用而成的,因此话语本身也是由某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决定的。但是他指出,“权力与知识就是在话语中相互连接起来的”【1】,这使得现实的话语往往在知识与权力合谋下以真理的面目示人,因此话语通常对社会观念和制度规范发挥着主导性和影响性的作用,进而成为一种稀少、有用、令人向往和占有的“公共财产”——话语权力(discourse power)。这就意味着,在“制度”“机构”“网络”中拥有“地位”的人,就是拥有“话语权”的人,而这种特定的权力主体在实质性地宰制着其他人。在这个意义上,“话语并不等于所说的事物,而是构成对象”。【2】如此一来,话语也就成为一种权力关系的表征。【3】这种话语权力已远远超出了传统的和狭义的权力范围,他强调,“我们必须首先把权力理解成多种多样的力量关系”【4】,“而不是将它看作一个仅仅行使压制职能的消极机构”【5】。
在他看来,话语权力总是以规训的方式驯服他人,就此塑造着人格,日常生活中的“言语惯例”“话语圈”和“信仰群体”等都是对人进行规训的话语。正如有学者所说,福柯认为“是话语建构了我们的生活世界,是话语建构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解释,同时也是话语就建构了我们主体自身”【6】。这套话语构建世界、话语宰制主体的一般逻辑,也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在诸多中国学者对于西方话语的批判中,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要抵制西方话语,就是因为近代以来,西方话语在建构中国人的生活世界,西方话语在建构中国人对世界的理解和解释,同时西方话语也在建构中国人的主体性,这会使我们的生活世界、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以及我们自身都失去中国之为中国的民族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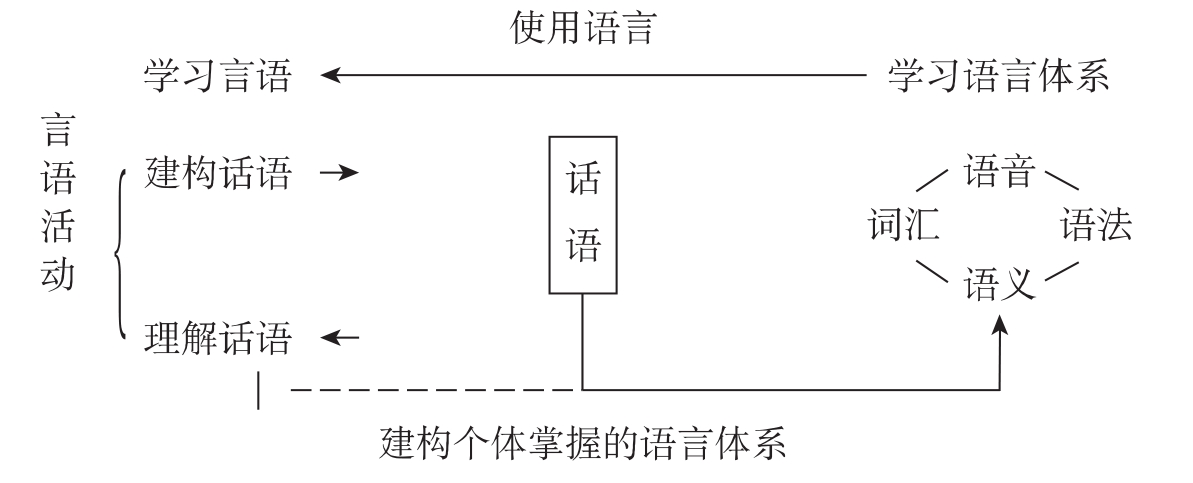
(二)批判的旨趣
当然,福柯的旨趣与中国学者不同。他对于现代西方话语的批判是一种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的立场,即解构现代话语中的一切普遍性的主体价值,进而提出以不确定的、个别性的自我取而代之。然而,正如理查德·罗蒂所批评的那样:“浪漫知识分子自我克服、自我创造的目标对知识分子个人而言是个好的模式(很多好的模式之一),但对社会而言却是个很坏的模式。”【7】同时,哈贝马斯也直言:“这些试图取消所有的标准,将审美判断等同于客观经验的表现。诸此许诺,都已证明自身是胡闹的实验。”【8】
而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对于现代西方话语的批判重心则在于西方性。因为有不少人认为:“我们所操的表面上似乎还是现代‘汉语’,而实际上讲的却是西方话语;我们不过是以汉语之形,而道西语之实。”【9】这里的“汉语之形”是指使用的语言符号,而“西语之实”是指言说的实质含义。因此中国学者并不像福柯那样否定一切主体性,而是要通过否定西方的主体性来重建中国的主体性。事实上,从晚清的西学东渐以来,儒家就开始了重建儒学话语的探索,其思想进路大致分为原教旨主义和现代主义两种:其中原教旨主义将中西截然对立,主张以传统儒学话语取而代之,而现代主义则在借鉴西学哲学的方法、语汇的基础上进行批判,其理论水平最高的现代新儒学虽然对德国古典哲学多有亲近,但根本还是以改变“花果飘零”的民族文化窘境、实现“灵根自植”为目的。例如:梁漱溟先生进行中西印文化比较的意图就是为了“重新拿出中国的态度,改造西方的态度,排斥印度的态度”【10】;而熊十力先生的全部工作,“就是面对西学的冲击,在儒学价值系统崩溃的时代,重建儒学的本体论,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11】但是,仅从儒家原教旨主义与儒家现代主义所言说的内容来看,前者通过重启传统儒学话语的言说,始终难以回应现代中国人的价值诉求,而后者立足“老内圣”来言说“新外王”的努力,则暴露出其自身就存在着传统儒学话语与现代性话语的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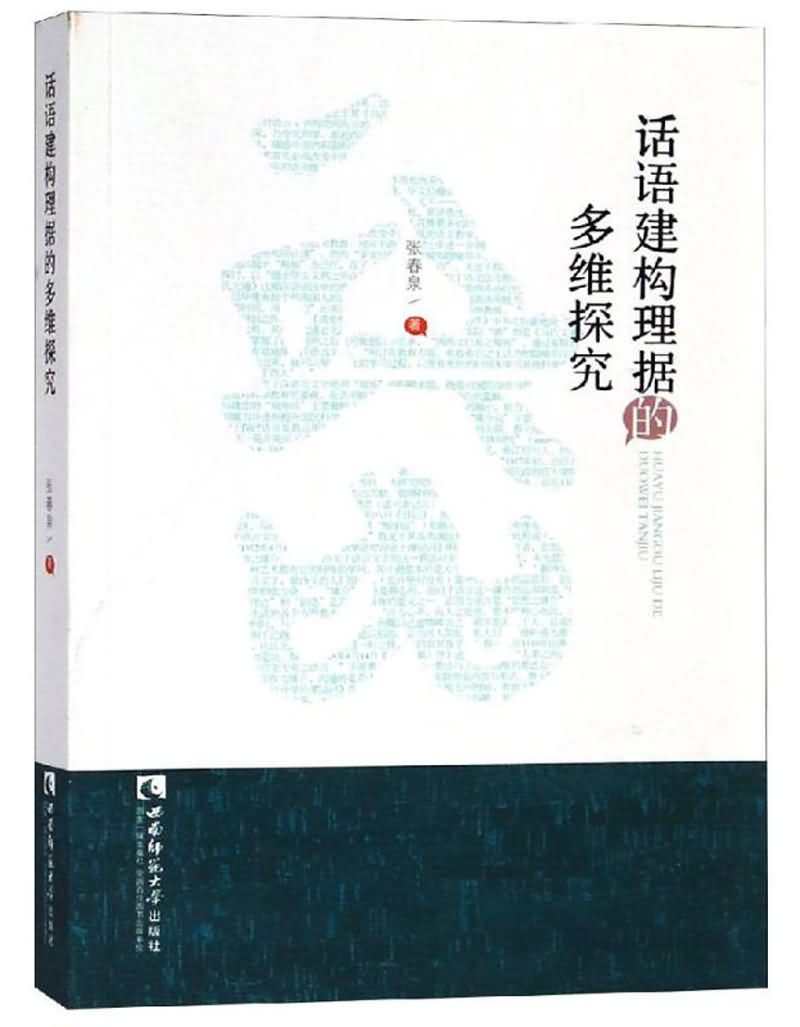
这意味着,上述进路都存在对传统儒学话语的固守,其背后是将传统儒学话语所言说的内容与中国哲学话语的民族特质互相等同,这种民族情结一直左右着儒学话语乃至中国话语的建构,如林毓生所说:“中国接受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主要是以中国的民族主义为基础的。”【12】事实上,这依然盛行在当代的儒学复兴过程中。因此有学者说:
中国现代思想领域的言说……其实都是在“中西文化优劣比较”的情绪支撑下进行的,这种情绪本质上是民族主义情结的产物。民族主义情结本身并无所谓好坏,但它如果试图代替严肃的运思,那就是对真正的哲学之思的遮蔽。【13】
哲学之思的特点在于:哲学所思正是其它所思之所不思。任何一种意识形式,作为一个思维过程,总有它的逻辑起点、话语背景或者语境,而这个起点恰恰是这个思维过程本身所不思的,是被作为不证自明的原则接受下来的观念前提。这个观念前提,其实就是现代语义学、语用学所谓的“预设”……然而哲学所思的正是这个观念前提、这个预设本身。【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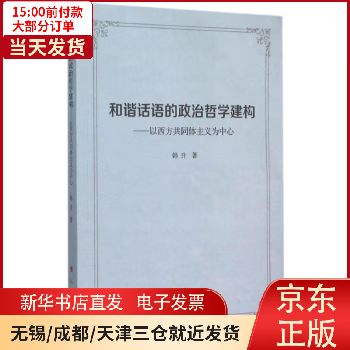
这就是说,我们需要对前述的话语权力关系的预设进行检讨。因为话语权力实际总是以“主—客”的存在为前提的,所谓由权力关系“生成知识,引起话语”,本身就意味着在话语形成之前已经预设了某种主体的存在,而话语所言说的内容实质就是以这种预设的主体为标准的,话语宰制主体的背后是一种主体对另一种主体的宰制,而近现代中国思想界所要反对的是,西方作为建构和掌控话语的主体对于中国作为被动接受话语的主体的宰制。然而,我们首先要意识到:要建构的中国哲学话语本身也是一种主体话语,这其中也是以某种主体的先行置入为基础的,那么,以我们置入的主体性为基准来批判现代西方话语,这其中的合理根据又是什么呢?我们如何才能避免各执一词的偏见呢?因此,作为一种哲学的思考,我们需要先行为主体话语所根据的主体本身奠基,即先行回答主体何以可能、主体话语何以可能的问题。唯其如此,才能确保我们建构儒学话语的合理性,以及批判西方话语的有效性。
事实上,福柯的话语理论就是要解构一切主体性的预设,其立足特定情境,或可揭示主体话语的渊源,但是在其“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谱系学”的分析中,作为话语基本单位的陈述,却是由一个个现成的主客因素相互关联而成的,因此他最终只是以一种碎片的、个别的、偶然的“自我”主体取代了以往哲学中普遍抽象的主体,其实只是一种主体性视域之下的否定性思考。这也提醒我们,当今建构儒学话语势必需要超越主体性的思想视域,即要超越以“中—西”两个既定主体为预设的儒家原教旨主义和儒家现代主义,同时要超越以个别“自我”为预设主体的后现代主义。
二、主体的本源与前主体性言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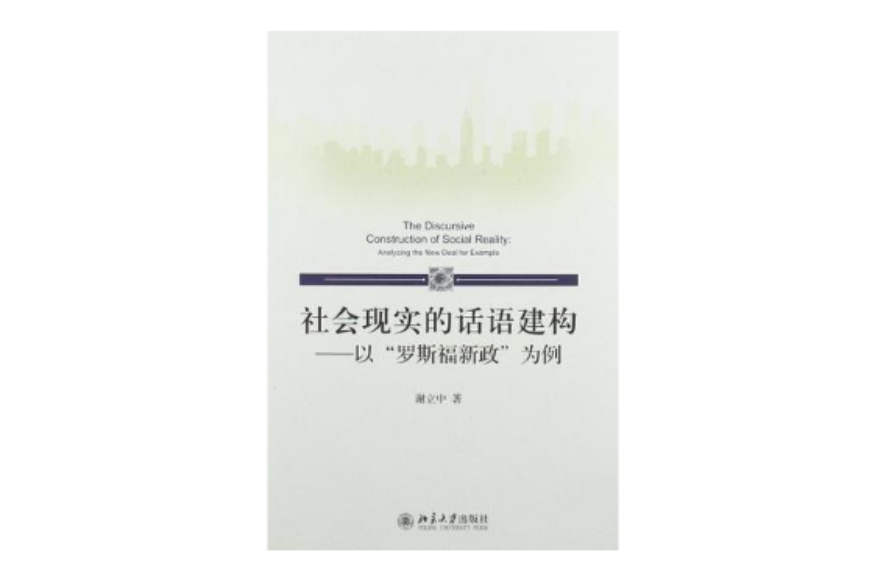
当代哲学的一个根本性突破就是开启了无预设的前主体性思想视域,这在暴露一切主体观念的非自明性的同时,也揭示出前主体性观念乃是一切主体观念得以可能的渊源。【15】从话语角度上讲,前主体性观念是为一切主体话语奠基的前主体性言说,或曰本源性言说。在这方面,海德格尔对“人言”(Spreche/Speeches)与“道言”(Sage/Language, 或译“道说”)的区分极具理论启发意义。
对此,当代儒家黄玉顺解释说:“‘人言’无论怎么说都只是一种形而下存在者的存在。而‘道言’有两种可能的理解:可以理解为形而上者的言说;但我们今天重新发现一个更古老的观念,如果说形而上者这样的存在者尚未存在,那么‘道言’就是‘道’、‘命’、‘诚’、‘活’,这一切都应该理解为动词,先行于任何名词性的实体性的东西。”【16】如果用海德格尔的话说,“道言”就是“存在”(Being)本身的近邻,它虽然需要经由人之口传达,但并不是言说某种主体诉求的“人言”,而是“大道”(Ereignis/Event)本身在说话,即所谓“大道之道言”(die Sage des Ereignis/the Language of Event),也就是“前存在者”“前主体性”的言说。
事实上,黄玉顺也将其创建的“生活儒学”理论划分为“无所指”和“有所指”的话语层级,恰与海德格尔“人言”与“道言”的区分相对应。其中“无所指”的“道言”作为一切主体话语之渊源的前主体性的本源言说,有别于“有所指”的“人言”,也即有别于主体性话语,是因为它所言说的内容没有所谓对象、主体等任何现成的存在者,故而“无所指”,因此,这并不是由种种具体的主客观因素而构成的一个陈述,更不是以概念符号系统进行表达的一种思想学说,而只是无言的言说即先于主客相分的本源情境在其自行涌现中的示意。【17】
这里所说的“本源情境”,并不是一个客观的“场所”,即不是一个与对象、主体等现成物并列的、构成陈述的要素,也不是衬托着陈述要素的、但其本身又疏离于要素之外的“背景”,而是一种未经自我选择的、浑沌一体的“无我之境”,即“作为始终非现成的、非专题的纯态势本身,境域就是既澄明有隐匿着的‘存在’本身”【18】。正因如此,“本源情境”先于一切存在者,也即先于一切主体性,且使一切主体性得以可能。这意味着一切主体性观念并不是人为的理性设定,而是由无前设、无中介的本源情境造就的。
相应地,一切主体性话语以前主体的本源言说为渊源才得以建构,即本源情境不断生发、涌现的“行”与“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