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伟,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现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代社会思潮等问题的研究。
摘 要:查尔斯·泰勒持有一种强健而多元的实在论思想即“多元强健实在论”,并以此来批判罗蒂等人的“压缩实在论”。泰勒努力从根本上跳出笛卡尔以来的“中介认识论”传统,并发展出一种不同以往的“接触理论”来取代“中介理论”。泰勒的实在论思想可谓立意高远、愿景宏大,但在其内部又隐含着疑难:“框架塑造”与“本然描述”之间的张力。能否化解疑难,关系到其实在论思想的成败,而化解的关键在于从“框架”的高度恰当地理解“塑造”与“具身性”——框架的塑造本是具身的塑造。
它可以同时容纳接受性与自发性、被动性与主动性,可以汇通因果性与可理解性。也正因如此,泰勒才坚持一种符合论的真理观,认为我们可以“如其所是”地描述独立的实在,从而与罗蒂的实用主义真理观产生了激烈的冲突。罗蒂洞见到“嵌入”与“符合”之间的张力,泰勒则借助于现象学的资源努力说明“嵌入”并不会导致“符合”的不可能。二者的思想交锋可谓精彩纷呈,却始终无法说服彼此,遑论达成一致,其根本原因是“框架”的差异。
关键词:多元强健实在论;框架;中介认识论;真理;具身性
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实在论思想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自我的根源》一书中,泰勒更加注重从道德之善的角度来理解实在,反对关于善的形式化、程序化的解读,提出了一种善的本体论,“坚持认为存在着诸如道德客观性这样的东西”(Abbey[ed.],p.108)。泰勒认为自我只有借助于善,才能得以“定位”与“定向”并获得自我认同,“我的认同是由提供框架的承诺和身份规定的”。(Taylor,1989,p.27)在《世俗时代》一书中,泰勒更加侧重从“框架”(frame)转型的角度来解读实在,指出人们对于实在的理解都是以特定的背景框架为前提的,它可以“控制人们的思考、论证、推论以及使得事物具有意义的方式”。(Taylor,2007,p.557)框架的内在化转型决定性地改变了人们的“实在观”,超越性框架(transcendent frame)使得超越的实在观得以可能,内在性框架(immanent frame)则使得内在性的实在观得以出现。在新出版的《重申实在论》一书中,泰勒与德雷福斯一道提出了“多元强健实在论”(pluralistic robust realism)。
它可以看作对泰勒实在论思想的全面总结。更为重要的是,“多元强健实在论”代表了实在论思想的最新版本,它批判了笛卡尔以来的“中介认识论”传统,反驳了罗蒂等人的“压缩实在论”(deflationary realism),同时也指出了一条不同于科学主义与主观主义(相对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一、泰勒实在论的疑难:“框架塑造”与“本然描述”
泰勒持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实在论立场,这种立场可以概括为多元强健实在论。“多元”(pluralistic)意味着追问实在方式的多样性,即原则上我们可以具有多种不同的描述或解释实在的方式,“可能具有多种语言,每一种都正确描述了实在的某个不同方面”(Dreyfus and Taylor,pp.153-154),而且我们很难将这些不同方式整合为统一的、单一的理论模式;“强健”(robust)则意味着实在独立于我们而存在,关于实在的真理也具有独立性,我们的认知必须依据实在而调整,“这些真理要求我们改正或调整我们的思维以便把握到它们”。(ibid., p.154)总之,多元强健实在论一方面坚持实在本身的独立性与本然性,另一方面又坚持通达实在的方式上的多元性。
泰勒的强健实在论实际上是针对着压缩实在论而提出的。压缩实在论一词最早由德雷福斯提出,来指明洛兹(J.Rouse)、马尔帕斯(J.Malpas)等人对于海德格尔实在思想的解读方式。在《重申实在论》中,泰勒与德雷福斯继续使用了这个概念,只不过语境发生了变化。此时,压缩实在论所标示的是罗蒂等人所持有的实在论思想。这种实在论主张一般实践对象甚至自然科学的对象,都无法脱离嵌入性的背景框架而显现,因此一种“本然”“自在”的对象是无法理解的。
罗蒂认为我们应该抛弃“就其本身而言”与“对我们而言”之间的区分,认为这样的区分是琐碎且无趣的,并以此来反对泰勒的观点。罗蒂说道:“令人遗憾的是,他(泰勒)坚持赞同威廉斯、斯特劳斯和其他笛卡尔崇拜者的意见,认为这个区分必不可少。”(罗蒂,2003年d,第74页)正如罗蒂所说,泰勒坚持了在“就其本身而言”与“对我们而言”之间的区分,坚持认为确实存在独立于我们的、并非对我们而言的本然的存在——实在的独立性是不可取消的,而且我们的思维也必须根据这种独立性而作出调整。与泰勒相反,罗蒂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取消了实在之独立性地位,认为外在的实在是无意义的,是否有意义取决于是否具有效用,“我们希望用较为有用的事物与较为无用的事物之间的区分,来取代实在与表象之间的区分”。(罗蒂,2003年a,第101页)
与罗蒂不同,泰勒持有一种强健实在论的立场,并以此来反对罗蒂意义上的压缩实在论,并认为由于“罗蒂愉快地接受了这种新的内-外区分”(Dreyfus and Taylor,p.131),所以罗蒂依旧处在中介认识论传统中,依旧是“认识论世界观的俘虏”。(泰勒,第258页)需要注意的是,泰勒对压缩实在论的批判是非常微妙的。事实上,从泰勒的框架理论出发,我们可以得出诸多同压缩实在论相似的结论。压缩实在论认为我们的认知、操作、实践等等都是嵌入性的,即这些活动都必然地在特定的背景之中展开并必然地被它所塑造。因此,我们无法通达物自身,无法获得关于物自身的认识。
即便是科学认识,也无法逃脱这种嵌入性,亦无法发现独立的实在。不难看出,压缩实在论的深层逻辑是:坚持在对象自身与对象的显现之间的区分,并认为我们所能认识的仅仅是对象的显现,所谓的对象自身是无意义的,我们无法“如其所是”地描述事物。泰勒也主张,“让我的行为成为可能的背景是复杂的” (Taylor,2004,p.21),我们的认识与实践活动是无法脱离框架的,对于框架的嵌入是无法避免的,不存在无框架的情况,“对我们来说,在没有框架的情况下生活显然是不可能的”。(Taylor,1989,p.27)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泰勒实际上同意压缩实在论的背景性嵌入的观点,“我们以这种方式深深的嵌入到社会中,随之也深深的嵌入到宇宙之中”。(Taylor,2004,p.55)可以说,泰勒与罗蒂在这一点上有明显的交集,那么泰勒的不同之处体现在哪里呢?
从表面看来,这种不同之处尤其体现为:泰勒坚持一种独立的实在,而罗蒂则认为独立实在是无意义的。但是,如此一来,泰勒实在论不就陷入到一种明显的矛盾之中了吗?一方面,泰勒坚持认为框架无法逃避、嵌入性无法避免,“人不可能脱离其身处其中的不可逃避的框架而存在”(Abbey[ed.],p.128);另一方面,泰勒又坚持认为存在着独立的实在。实在是独立的,这也就意味着它不依赖于我们的背景框架,它可以如其所是地存在,即脱离于框架而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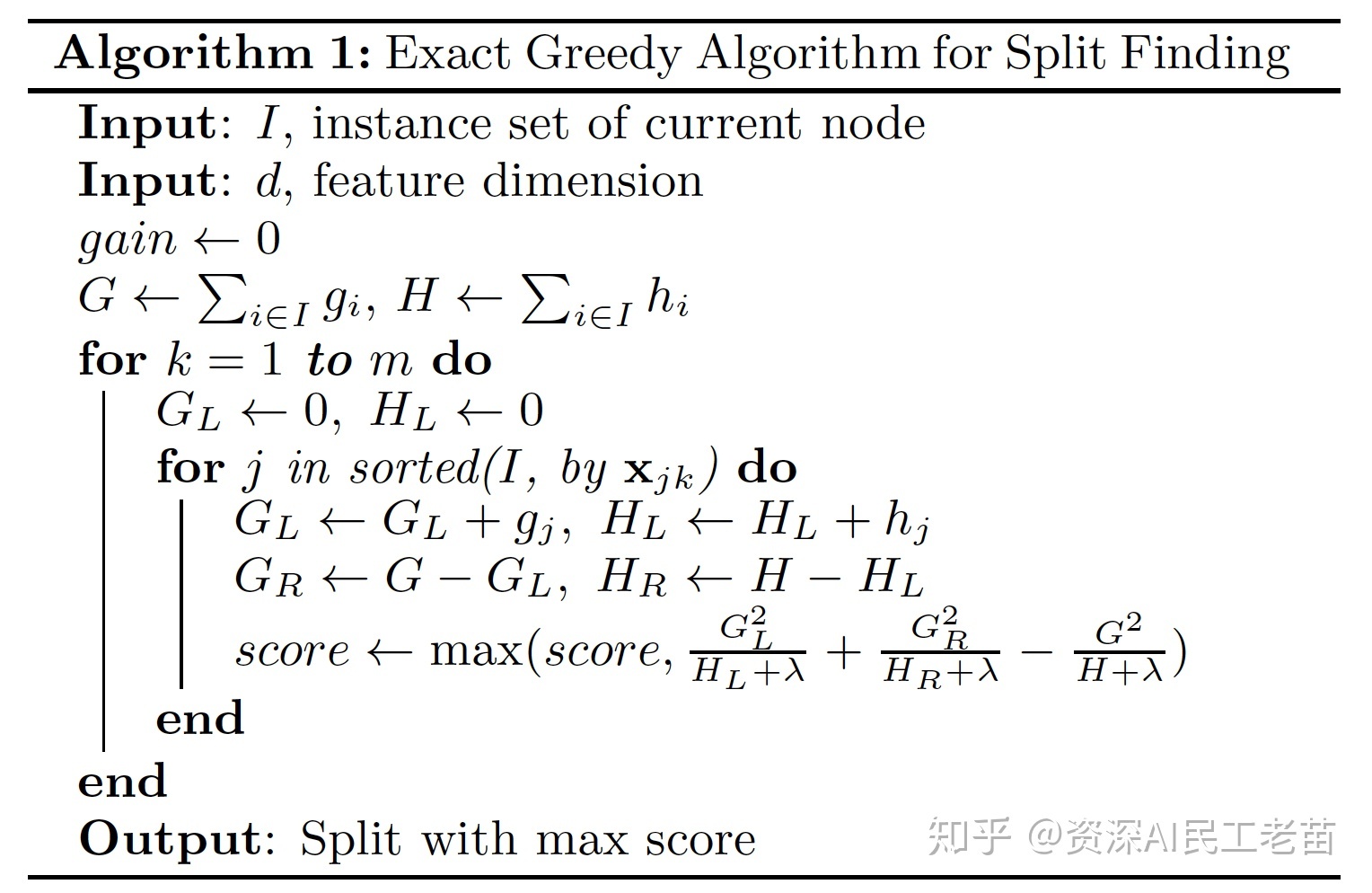
实在的独立性难道不与框架的嵌入性相矛盾吗?为了化解矛盾,我们可以采取如下的进路:首先,我们可以将实在的独立性限定在本体论的层面,仅就存在而言,事物才是独立于我们的,且事物的存在本身并不依赖于任何的背景框架;其次,在认识与操作的层面,就事物与我们之间的关系而言,事物必然地处在背景框架之中,换句话说,我们对于事物的认识、操作等等都已经被框架所“塑造”。也就是说,泰勒所坚持的是一种存在层面的独立性。但是,这样的解释仍旧没有穷尽强健实在论的全部意涵。除了坚持事物的独立存在之外,泰勒还坚持认为:在日常实践的层面,我们可以直接通达事物,即在日常实践中我们与事物是直接地接触的;在科学认识的层面,我们也可以“如其所是”地描述事物。
与泰勒不同,罗蒂基于反对“镜式哲学”的立场,对上述两点都持有怀疑态度。罗蒂认为“能否直接接触事物”的问题本身就是无意义的,原因在于“没有人,或者至少没有知识分子会相信:在我们内心深处有一个标准可以告诉我们是否与实在相接触,以及我们在何时与(大写的)真理相接触。在这个文化中,无论是牧师还是物理学家,或是诗人与什么政党,都不会被认为比别人更‘理性’、更‘科学’、更‘深刻’”。(罗蒂,2004年,第14页)罗蒂反对“大写的真理”,反对符合论的真理观,不认为科学认知更加符合于实在。
为了反驳罗蒂,泰勒面临着如下疑难:如果说事物自身独立存在而关于事物自身的认识与实践则被背景框架所塑造,那么我们如何可能坚持对于事物的“直接通达”?框架嵌入所带来的塑造效应,难道不已经意味着我们无法绕过框架而直接通达物自身,进而也无法如其所是地描述物自身了吗?如何化解“框架塑造”与“本然描述”之间的张力?
二、化解疑难的关键:“塑造”与“具身性”
对于上述疑难的化解依赖于对关键概念、不同领域与层面的现象学澄清。对于关键概念的澄清,涉及如何理解“塑造”;对于不同领域的澄清,涉及意义理解的领域与物理因果的领域;对于不同层面的澄清,涉及前概念的层面与概念的层面。
下面,我们来看看塑造意味着什么。我们在上面所谈论的塑造指的主要是:对于背景框架的嵌入所带来的在认识上、实践上难以避免的影响或者改变。但是,上面的这种理解仍旧是不全面的。实际上,我们首先嵌入的是身体,我们首先是身体性的存在。泰勒本人深受海德格尔与梅洛-庞蒂的现象学的影响,并将海德格尔的世界理论与梅洛-庞蒂的身体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明确主张“行动者的世界是由他的身体性存在所塑造的”。(Dreyfus and Taylor,p.133)这种意义上的塑造体现在不同的领域中,包括物理因果的领域与意义理解的领域。
我们首先着眼于因果领域中的塑造。这种塑造主要涉及:具身性对于知觉的塑造,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对于世界的塑造。例如,我们无法直接看到脑后的事物,这本身是由我们物质性身体结构以及光线反射所决定的,这些都可以还原为物理性的因果关系,而无需涉及任何的意义理解。这种意义上的塑造完全由物理性的因果法则决定,我们物理性身体基于因果法则塑造着我们的知觉,进而塑造着我们的世界。
但是,还有另外的一重更为关键的塑造,即意义理解领域中的塑造。这种塑造指的是:世界之“意义”是由我们的具身性背景所塑造的。世界之意义依赖于我们经验世界的方式,而经验的方式最终依赖于我们的具身性并被它所塑造。例如,我们将粉笔看作“近”的,这其实是一种特定的意义理解。我们将它认作“近”,这是基于我们的身体性结构的(我一伸手即可以拿到粉笔)。我关于粉笔之“近”的意义领会,有赖于我的身体结构(手臂的长短)。也就是说,粉笔之“近”的意义最终由我的具身性所塑造。
不难看出,有两种不同的塑造关系:一种涉及“因果性”条件,另一种则涉及“可理解性”条件。前者对应于物理因果的领域,而后者则对应于意义理解的领域。自然主义者所侧重的显然是因果性。胡塞尔等现象学家则更加侧重可理解性,认为科学观念最终起源于原初的知觉经验。罗蒂等人也更加侧重可理解性,取消了科学的对象和日常实践的对象之间的区分,认为科学对象并不具有更多的独立性,进而采取了“压缩实在论”的立场。罗蒂不但取消了独立性物自身的意义,而且不认可符合论的真理观。
泰勒则吸收了现象学的资源,反对自然主义,并自觉地与罗蒂区分开来。泰勒一方面非常注重意义领域中的实在,看重可理解性的条件,反对自然主义者将意义还原为因果性做法;另一方面,肯定了因果性在科学认识中的作用,坚持科学对象的独立性与符合论真理观的合理性。泰勒实际上探寻一条可以同时容纳乃至超越因果性与可理解性的第三条道路,这条新的道路“产生又超越于与宇宙的直接因果关联和与日常世界的基本的理解性关联”。(Dreyfus and Taylor,p.135)
泰勒第三条道路的关键在于“具身性”(embodiment),原因在于具身性可以同时容纳“因果性”和“可理解性”,并弥合二者之间的间隙。例如,我拿起一支粉笔的活动,本身就是一个同时涉及物理的因果条件和意义的可理解性条件的具身性活动。“拿起粉笔”一开始就需要我根据粉笔与身体之间的因果条件来调整身体。一方面,我首先需要调整我的视线以便看到粉笔,然后估计我与粉笔之间的距离,最后举起我的手臂并用手精准地捏住粉笔等等,所有这些步骤都依赖于物理性的因果法则。另一方面,我又必须能够将粉笔从周围事物中区分出来,进而可以将粉笔“认作”粉笔。“认作粉笔”是一种复杂的意义理解过程。
我必须将粉笔理解为能书写的工具,而不单单是石膏;我必须将粉笔区别于话筒,从而不至于拿起话筒等等。首先,我拿起粉笔的活动涉及“接受性”,即我受到物理因果条件的制约,我必须根据因果条件来调整我们的身体才能最终拿起粉笔,这本身已经意味着粉笔的独立存在;其次,拿起粉笔同时也涉及“自发性”,即我对粉笔有了基本的意义领会或认知,从而才可能拿起粉笔而非话筒;最后,我对于粉笔的意义理解,需要根据独立存在的粉笔来调整(“粉笔可以用来书写”,这依赖于构成粉笔的石膏的物理属性)。

总之,在“拿起粉笔”这样的看似简单的具身性活动中,已经包含了因果性与可理解性,而且它们已经“融会贯通”。在具身性活动中,接受性与自发性紧原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既是被动的又是主动的。基于因果性,我们可以合理地坚持事物的独立存在,即物自身的存在,原因在于因果性意味着被动的接受性,只有在事物自身独立存在的时候,这种被动的接受性才是可能的;基于可理解性,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我们对于事物的认识“符合”事物自身,原因在于我们的认识始终在根据事物的独立存在而不断地调整自身,这也是符合论真理观的合理性所在。
从具身性出发,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框架的塑造本身就是一种具身性的塑造。既然具身性可以同时容纳并汇通因果性与可理解性,那么以具身性为基础的塑造亦当如此。就此而言,塑造既是一种接受性、被动性的塑造,又是一种自发性、主动性的塑造。至此,我们可以初步回应在上面所遇到的疑难:我们虽然不可避免地嵌入到背景框架之中,从而使得我们的认识与实践必然被“塑造”,但我们依旧可以通达“事物自身”,依旧可以“如其所是”地描述事物,原因就在于这里的塑造是一种具身性的塑造,在具身性之中同时蕴含的“因果性”与“可理解性”。它们既可以让我们通达“事物自身”,又可以让我们“如其所是”地描述事物自身。从具身性的角度看,“框架塑造”与“本然描述”并不矛盾。
总而言之,具身性是我们与世界保持接触的关键,也是突破笛卡尔以来的认识论传统的关键。泰勒认为,笛卡尔式的认识论实际上是不具身的,“笛卡尔使得我们走得更远,我们作为具身能动者而具有与我们的生存相关的意义,他却要求我们从这样的意义中退出”。(Taylor,2007,p.285)虽然我们必然地嵌入到框架之中而无法超然地“独立自存”,但我们依旧可以嵌入到“更为合理”的框架之中。按照泰勒的框架理论,伴随着从前现代到现代性的转型,超越性逐渐式微,“世俗的现代性非常反对超越性”(O'Shea,p.240),人们所默认的框架本身也经历了从超越性框架到内在性框架的转型。
现代人嵌入于其中的框架,其实就是一种内在性框架,“现代人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内在框架之中”。(张容南,第51页)这种内在性框架塑造着我们的认知方式,使得我们处在“中介认识论”传统之中,“我们把我们的思想、观念或者情感考虑为‘内在于’我们之中,而把这些精神状态所关联的世界上的客体当成是‘外在的’”。(Taylor,1989,p.111)总之,中介认识论默认了“内-外”的二元区分,“将意识、我思或自我看成是一个封闭和自足的内在世界”(吴增定,第20页),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内在心灵如何认识外在世界”的问题。泰勒认为,破解笛卡尔以来的认识论疑难的关键,不在于“跨越”内外的鸿沟,而在于从根本上跳出中介认识论所预设的内外二分的“框架”,打破“中介图像”,从“中介理论”(mediational theory)过渡到“接触理论”(contact theory)。泰勒试图用一种全新的接触理论,来从根本上破除中介图像的牢笼,进而跳出“笛卡尔之手”。
这种接触理论之得以可能的关键就在于具身性,因为具身性从未以内外二分为前提,而是直接地使得我们与世界处在原初的“接触”之中,“我们与宇宙保持联系并不是因为我们具有一种脱嵌的、超人的、沉思的能力,而是多亏了投入的、主动的物质性身体,它能恰当地定向进而处理事物”。(Dreyfus and Taylor,p.137)也就是说,具有身体的我们,本来就已经直接地处身于周围事物之中,并直接地应对周围事物,“拥有一个身体,对一个生物来说就是介入一个确定的环境,参与某些计划和继续置身于其中”。(梅洛-庞蒂,2001年,第116页)一言以蔽之,自我处身于世界。
泰勒的可贵之处在于将海德格尔的“世界”与梅洛-庞蒂的“具身”融会贯通,打破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俘获我们的图象”,进而有力地批判了压缩实在论,并为自身的强健实在论作出了辩护。正如平卡德(Terry Pinkard)所说:“泰勒努力表明这种‘心灵之中’或‘仅仅行为上’的传统二分法,并未能穷尽我们的选择;这种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路线,依据一个行动主体是一个实践参与者,提供了另外一种意义理解的选择。”(Abbey[ed.],pp.193-194)
三、“如其所是”的科学真理:对符合论的辩护
借助于具身性所同时蕴含的“因果性”和“可理解性”,泰勒坚持认为存在着独立的实在,而且我们可以“如其所是”地描述这种实在。泰勒的强健实在论之所以是强健的,就在于它不单单在本体论上坚持独立的实在,而且在认识论上亦坚持“符合”实在的真实描述。泰勒所说的“如其所是”“本然”的描述,其实就是一种“符合”事物自身的真命题。命题之为真,就在于它符合独立的实在,因此符合论是无法从根本上取消的。科学命题就是一种符合独立实在的真命题,也正因如此,它才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日常信念。
面对泰勒的批判,压缩实在论者也会给出进一步的辩护,罗蒂说道:“没有任何人曾经怀疑宇宙中大部分事物在因果上独立于我们,我们所置疑的是他们在表达上独立于我们”。(罗蒂,2003年d,第66页)也就是说,其所否认的并非是事物在因果层面上的独立性,而是在表达层面上的独立性。罗蒂的核心主张是:包括科学对象在内的所有对象,都必须在嵌入性的背景之中才能得以理解和表达。这也就意味着,其实并未直接否认实在的独立性。而我们知道,泰勒正是从具身性之中的因果性出发,来论证实在的独立性的。
就此而言,罗蒂与泰勒的实在论思想,在因果性的层面上并不存在绝对的矛盾,它们的真正不同之处在于可理解性层面。罗蒂对符合论持怀疑态度,并不认可一种符合于事物自身的描述,“这就意味着抛弃通过探究命题是由‘世界’造就为真的还是由‘我们’造就为真的来对它们进行分类的企图……在我看来,如果我们抛弃这种区分以及这种成问题的问题,我们就无法解释我们所谓的‘符合’所意指的东西”。(罗蒂,2003年d,第67页)
罗蒂之所以质疑符合论,是因为至少在表达的层面、可理解的层面上,任何表述(不管是日常命题还是科学命题)都必然地嵌入到特定的背景之中,因而它无法“如其所是”地描述事物本身,进而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去区分“由‘世界’造就为真”与“由‘我们’造就为真”,没有必要去区分日常信念与科学真理了。泰勒则与之不同,他从强健实在论的立场出发,承认符合论的合理性,并且坚持认为科学研究的真理符合于独立实在,而且科学真理本身具有独立性。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罗蒂等压缩实在论者质疑符合论的关键在于“嵌入”。从原则上讲,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层面来理解嵌入性。首先,最初始的嵌入是身体性的嵌入,即我们首先具有一个身体;然后,此身体又嵌入到周围世界之中,不断地应对周围事物,同周围事物打交道,而这种打交道的过程即实践的过程;最后,我们还嵌入到我们的语言、文化、科学等观念系统之中,“自我只会存在于我所说的‘对话网络’中”(Taylor,1989,p.36),甚至我们的身份也依赖于的语言,“我们的认同本质性地依赖于我与他者的对话关系”。(Taylor,1994,p.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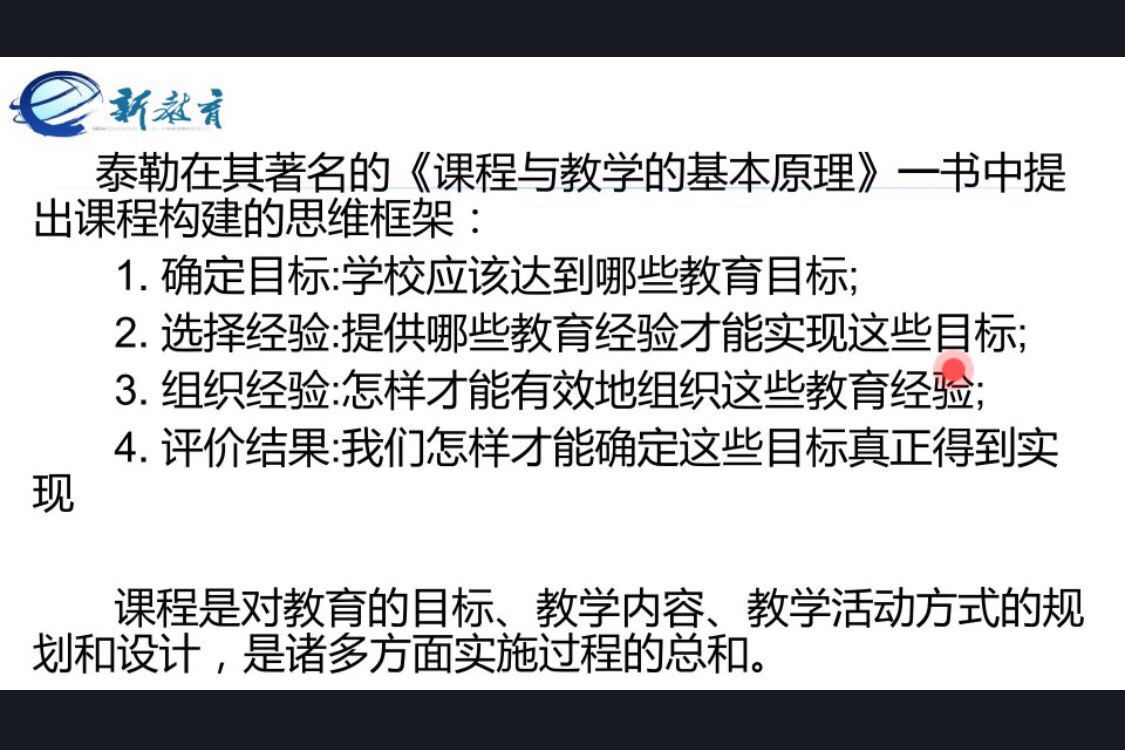
因此,当我们试图去描述对象的时候,我们必然是从上述的多重嵌入结构出发的,描述“依赖于我们从社会与文化当中获得的语言”(McKenzie,p.71);描述对象的方式,依赖于我们同对象打交道的方式,因此描述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我们的实践方式的塑造;描述虽然是观念的表达,但它依然最终依赖于我们的具身性,我们对对象的知觉首先是一种具身性的知觉。罗蒂也正是看到了这样的多重嵌入结构及其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塑造效应,才认为没有必要去坚持所谓的“如其所是”地“符合”事物自身的科学真理。他洞见到了在“嵌入”与“符合”之间的矛盾关系。
那么,“嵌入”与“符合”真的是相互矛盾的吗?泰勒的强健实在论能够给出有说服力的回应吗?在罗蒂看来,“嵌入于语言”实际上意味着“符合于实在”之无意义,“把运用语词看作对付环境的工具,而不是再现实在内在本质的尝试,也就是抛弃了人类的心灵是不是触及到了实在的问题”。(罗蒂,2003年a,第102页)泰勒反驳罗蒂并为符合论做出辩护,这并非易事。原因在于,泰勒从其自身的框架理论出发,也认定:我们无法从根本上脱离框架。泰勒与罗蒂实际上共享了嵌入性的前提。因此,泰勒要想反驳罗蒂,就必须指出:承认“嵌入”,并不会导致“符合”的不可能。他甚至还需要进一步从嵌入性出发为符合论做出辩护,这显然是泰勒所面临的另一个疑难。那么,泰勒将如何化解这一疑难呢?化解的关键在于“打通”前概念与概念,而这种“打通”的关键在于“在世”。
泰勒非常认同海德格尔所说的“此在具有在世界之中的本质性建构”(海德格尔,第64页)的“在世”理论,并将之与梅洛-庞蒂的“具身”理论结合起来,熟练地用“上手状态”(Zuhanden)和“在手状态”(Vorhanden)等概念来分析我们原初的处身方式。在泰勒看来,我们的在世意味着我们总是处在与周围事物的关联之中,总是与周围事物不断地打交道,总是对事物做出回应。正如梅洛-庞蒂所说的“一切知觉都在某一视阈并最终在‘世界’中发生”。(梅洛-庞蒂,2002年,第4页)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事物“仿佛具有一种本体的稳固性和深度,它们为我们活动划定了边界条件,这些事物具有后来在哲学上称之为‘本性’的东西,我们需要对之保持敬畏,并调整自己适应它们”。(Dreyfus and Taylor,p.138)也就是说,我们无法任意地同周围事物打交道,而是必须根据周围事物来调整我们自身。
而且,我们也会发现,事物向我们的展现是非完全的展现,事物总有尚未被发现的面相。在原初的在世中,我们会发现经验对象具有独立性,经验对象总是隐含着我们尚未经验到的更多的东西,我们必须根据它来调整我们的态度,等等。经验依赖于经验对象,而认识又进一步依赖于经验。也就是说,科学真理也最终依赖于这种处身性的在世方式。用发生现象学的术语来说,高阶的普遍性谓词最终起源于低阶的前谓词经验。
总之,通过借鉴“在世”现象学,泰勒发现:概念作为高阶的观念物,其实有着漫长的“发生史”,并最终可以追溯到我们的在世上面。在原初的在世中,我们更多地是以前反思、前概念的方式同事物打交道,“观念的确定性并没有奠定知觉的确定性,而是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之上”。(梅洛-庞蒂,2002年,第4页)例如,“踢足球”无需理论性的反思即可以直接进行。我们对于周围世界有着原初的背景理解,“在一般意义上,这个背景处于未被表达和未加以探究的状态”(Abbey[ed.],p.109),它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渗透进我们的意识深层,“这种背景理解是沉默的,前反思的,嵌入到所有的典型故事、想象和意识形态之中”。(McKenzie,p.113)概念性的反思活动本身已经预设了前概念的原初经验,二者虽然性质不同,但又存在着紧密的发生学上的关联。通过对在世的现象学考察,我们可以打通前概念与概念的界限,表明概念最终源于前概念的具身性经验,而且这种具身性经验同时也可以让我们认识到事物的独立性。
泰勒借助于现象学的资源努力表明:科学认识(作为概念构成物)实际上最终起源于并依赖于具有独立性的事物本身,进而它才可以符合于事物本身。即便如此,泰勒其实也无法说服罗蒂。在罗蒂看来,凡是表述总已经是概念性的、语言性的了,我们只能用我们所拥有的语言来描述事物。描述作为语言的描述,总以概念化为前提。宇宙自身并不会将自己概念化,概念显然来自于人。人通过概念来描述自然,这意味着在人与自然之间已经存在着概念的间隔,人不可能直接认识“宇宙本身”,对于“宇宙本身”的描述是无意义的。总而言之,在罗蒂看来,对于事物的描述已经是概念性的表达,它作为概念的表达已经嵌入到我们的语言体系之中,因而关于事物的表达也就无法直接通达到事物自身了。
泰勒对此的回应是:表达固然包含了概念化的嵌入,但是关于事物的表达依然可以符合事物自身。就像上面所说,泰勒可以借助于“在世”来说明概念依赖于经验而经验最终依赖于独立的事物自身,从而可以从发生现象学的角度说明概念与事物自身的发生学关联。但是,这仍然是不够的,因为概念与事物本身的这种发生学上的关系并不等同于“符合”关系。为此,泰勒借鉴了克里普克的严格指示词的理论。泰勒认为,至少在科学认知的层面,概念可以作为严格指示词而符合于事物自身。例如,我们可以用H2O来表达水分子,而且H2O可以完全地符合于水分子本身。泰勒将科学革命看作不断进步的更迭过程,伴随着科学更迭,我们可以更好地对事物进行预测与控制,而更好的预测与控制也反过来进一步说明了科学与宇宙本身的符合关系。
当然,罗蒂也可以提出反驳:预测、控制并不能够证明科学认识与事物相符合,它只不过说明我们可以更好地玩这种“游戏”,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生活、更便利地做事,即科学真理只是变得更“有用”而已,而非更加符合于独立的实在,科学真理不是自在的、先验的、本质性的真理,它并不享有更优先的地位。罗蒂说道:“造成关于DNA或‘大爆炸’之说的因果力量丛,与造成关于‘世俗化’与‘晚近资本主义’之说的因果力量,在种类上并无二致。”(罗蒂,2003年c,第28-29页)罗蒂认为追求普遍的、先验的宏大真理是徒劳的,我们应该抛弃大写的真理而满足于小写的真理(关于个别事态的真理),“考虑大写的真理,无助于我们去说某种(小写的)真的东西”(罗蒂,2004年,第3页),“真之为真”的最终依据,还是在于它对我们现实生活的效用。
泰勒也承认他或许永远无法说服罗蒂,“或许没有什么能让一个想要停留在康德式的内-外图像中的人相信这一点”。(Dreyfus and Taylor,p.146)二者分歧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他们所默认的框架的不同。泰勒对于认识论有着独特的理解方式,他洞见到了认识论中所隐含着的“结构”与“图像”,“我并不仅仅把‘认识论’当做流行的理论,而且也在结构的层面上,把它看作一种被部分地意识到的背景图像”。(Taylor,2007,p.557)泰勒认为罗蒂虽然也在批判笛卡尔以来的认识论传统,但仍旧处在这个传统之中,其压缩实在论依旧默认了笛卡尔以来的“内-外”二分的框架结构。在泰勒看来,压缩实在论的逻辑起点其实是内在性,而内在性已经是相对于外在性的内在性,因此它最终以内外二分为前提,即便它将事物本身排除在外或者斥之为冗余,也仍旧没有摆脱“内-外”的框架。
泰勒将罗蒂看作“认识论世界观中的俘虏”。(罗蒂,2003年d,第74页)当然,罗蒂本人并不认同这一点,因为他自己也反对“内部”与“外部”的简单二分,也认为对身、心作出如此严格的区分,乃是笛卡儿以后的事情。(参见罗蒂,2003年b,第41页)在罗蒂看来,他自己才是真正超越了笛卡尔认识论传统的人,泰勒反而在固守着这个传统。罗蒂将其“后哲学文化”(Post-Philosophical Culture)看作超越了笛卡尔传统认识论的文化,认为哲学家的作用在于反讽而不在于构建大写的真理,“对于这些反讽主义者而言,他们的成就是建立在他们与前人的关系之上的,而非他们与真理的关系之上”。(罗蒂,2003年c,第112-113页)
按照泰勒的框架理论,框架本身虽然隐而不显,但它默默地塑造着框架内部的具体观点,对于具体观点的彻底批判必然需要批判观点背后的框架本身,而不是仅仅批判这个观点或者与之相关的其他观点。但问题在于,如果被批判者仍旧停留在固有的框架之内,那么他是很难看到批判者的合理性的。泰勒的强健实在论与罗蒂的压缩实在论实际上预设了不同的框架类型,倘若二者都不认同对方的框架,那么他们也就很难达成一致了。罗蒂说道:“泰勒和我都为逃脱认识论而自豪。但是,我们都各自认为对方仍然在紊乱的绳索中间蹒跚而行,而未完全逃脱。”(罗蒂,2003年d,第73页)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让二者最终达成一致,或者让其中的一方说服另一方呢?就像我们在上面所说的,二者的分歧的根源在于框架本身,而不仅仅在于具体的观点,一种真正有效的批判是对框架本身的批判。
但是,我们是否可能直接去批判框架本身呢?批判具体观点是易的,而批判框架本身是难的。框架具有隐而不显的特性,它本身不易被发现。要想批判他人的框架,首先要求我们审视自身的框架。这样的自我审视,其实已经预设了自己可以“跳出”自己的框架。但是,这种“跳出”是可能的吗?实际上,按照泰勒的框架理论,我们永远都无法无框架地存在,所谓“跳出”只能是从一种框架“跳入”到另一种框架。“认识论的图像常常作为封闭世界结构而运作”(Taylor,2007,p.558),因此关键在于保持一种框架上的开放性,建立起一种“开放世界结构”而非“封闭世界结构”。基于开放性的视域,我们才能发现其他类型的框架的可能性乃至合理性,从而使得自己原则上可以“跳出”原先的框架并审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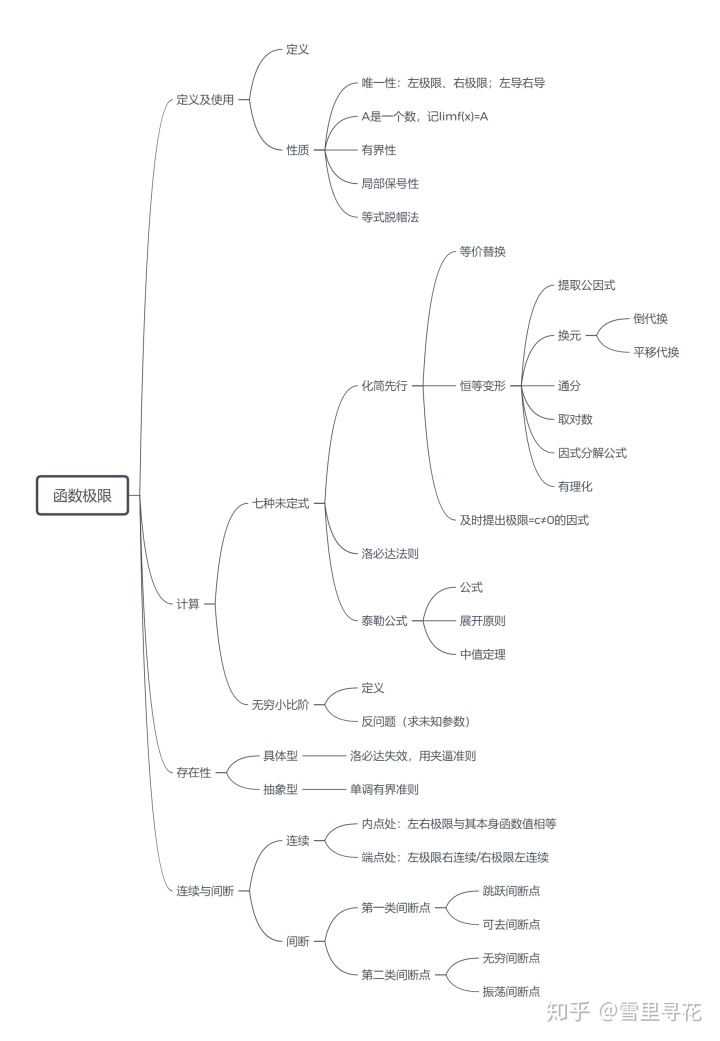
泰勒持有一种“强评估”(strong evaluation)理论,认为“人类是‘强评估者’”。(Abbey[ed.],p.128)强评估理论同框架理论紧密相关,框架作为特殊的意义背景为强评估提供了可能性的语境条件。在特定的框架下,我们才能够有意义地区分出更高的价值与更低的价值。同时,强评估理论亦同实在论紧密相关。在泰勒看来,框架本身就是一种广义的实在强评估理论的基础其实就是多元强健实在论。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我们能否对框架本身进行强评估?按照泰勒的强评估理论,我们总是可以进行高低、好坏的区分。照此逻辑,我们也可以对不同类型的框架进行价值上的评估,乃至区分出优劣。但是,当我们评估一个框架的时候,其实已经预设自身处在一种更高阶的框架之中。或者说,唯有从更高阶的框架出发,才能合理地评估更低阶的框架。
按照强评估理论,我们可以从原则上对不同类型的框架进行区分乃至分层,从而构建起框架的层级体系,乃至形成一种“框架本体论”。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更从容地基于高阶框架来评价乃至批判低阶框架,从更高的视角揭示出低阶框架内部观点的不合理性。上述种种,皆是我们自己的“设想”。泰勒虽然提出了框架理论,而且“这些框架或基本的预设以某种形式受到了本体论的启发”(Zemmin et al.[eds.],p.105),但并未建立起一种“框架本体论”。
总而言之,泰勒虽然未能说服罗蒂,但其实在论仍有诸多积极意义。泰勒的实在论充分借鉴了现象学的资源,“阐述了一种对我们存在于世的基本的前概念的解释”(Abbey[ed.],p.55),说明我们从一开始就处在同世界的直接接触之中,从而打破了笛卡尔以来的内在性禁锢,重新恢复了人与世界的贯通性,同时也表明科学真理可以符合于独立实在。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直接接触的框架,这种框架完全不同于笛卡尔以来的中介框架,超越了传统的“内-外”分殊,重新恢复了人与世界的整体性关联。提出一种新的框架类型,这才是泰勒实在论的最大的贡献——帮助我们挣脱传统的中介图像,以新的方式看到新的可能。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2006年:《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罗蒂,2003年a:《后形而上学希望》,黄勇编,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年b:《哲学和自然之镜》,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
2003年c:《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商务印书馆。
2003年d:《真理与进步》,杨玉成译,华夏出版社。
2004年:《后哲学文化》,黄勇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3]梅洛-庞蒂,2001年:《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
2002年:《知觉的首要地位及其哲学结论》,王东亮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4]泰勒,1990年:《认识论传统中的罗蒂》,载马拉科维斯基编《解读罗蒂》,布莱克威尔出版社。
[5]吴增定,2020年:《现象学中的内在与超越——列维纳斯对胡塞尔意向性学说的批评》,载《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6]张容南,2016年:《查尔斯·泰勒对世俗时代精神状况的剖析与反思》,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7]Abbey, R.(ed.), 2004, Charles Taylo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Dreyfus, H.and Taylor,C., 2015, Retrieving real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9]McKenzie,G.,2017,Interpreting Charles Taylor's Social Theory on Religion and Secularization:A Comparative Study, Switzerland: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10]Meijer, M.and Taylor, C ., 2019,“Fellow Travellers on Different Paths: A Conversation with Charles Taylor”,in Philosophy & Social Criticism 46(8).
[11]O'Shea, A., 2010,Selfhood and Sacrifice: René Girard and Charles Taylor on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New York and London: 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12]Smith, J. K. A., 2014, How (Not) to Be Secular: Reading Charles Taylor, Michigan/Cambridge: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3]Taylor,C., 1989,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in A.Gutmann(ed.), Multiculturalism: 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A Secular Age,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4]Zemmin,F.,Jager,C.and Vanheeswijck,G.(eds.),2016, Working with A Secular Age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harles Taylor's Master Narrative, Berlin/Bosto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