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教育学,其源头是上一个世纪之交中外人士共同作用下的教育学“中国化”过程。国内有研究者梳理、分析了早期传教士的教育话语转型,创新性地提出了包括“教士一类、魏源一流、龚自珍一品、容宏一列、留日生一脉”的“五路十代”中国教育学的拓荒者。中国教育学已伴随着共和国走过了七十年,不同时期的教育学具有不同品性。
原文 :《新中国教育学研究对象的思与辨》
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 杨小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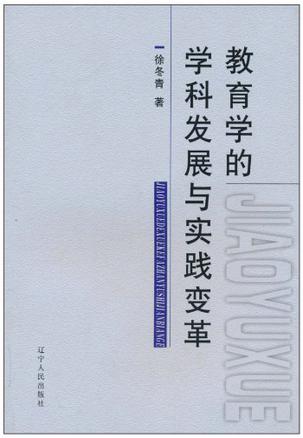
图片 |网络
七十年回溯:何来“问题”,何种方法?
新中国成立至五十年代,教育学移植苏联教材,以育师为己任。这个时期我国各条战线都向苏联学习,教育界尤其是师范院校大量引进凯洛夫等学者主编或撰写的教育学教材,成为新中国最早一批未来中小学教师心目中的教育学经典,加上苏联教育学、心理学教授的“亲传”,一些苏氏色彩明显的术语如“综合课五环节”“班主任”等代代相传。由于此时的主流是高校课程形态的教育学,主要任务是培养中小学师资,所以其研究方法基本谈不上有何种特征。
遭遇教育大革命和“文革”,作为理论形态的教育学几近消失。随后,中国教育学界开始批判凯洛夫教育学,开始意识到苏联教育学学习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开始关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并有学者提出要探讨教育学的中国化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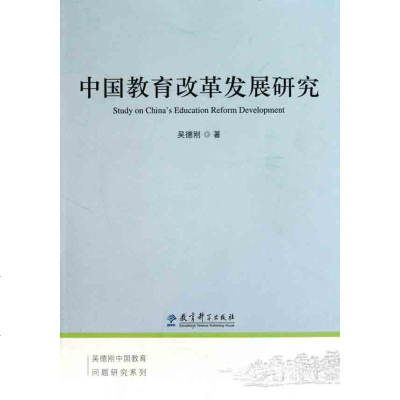
改革开放以来,学科意识觉醒,问题进入教育学的“对象”视野。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前,国内教育学研究鲜有深入的反思、追问与批判,直到1978年以后反思才真正开始。八十年代末,《教育研究》等杂志发表了系列反思性文章,并有相关书籍问世,尽管存在“谈成果多、析问题少”等现象,但反思、批判的学术氛围已初步形成。日本学者村井实曾对教育学的对象进行了较全面和系统的分析,得出了教育学的对象是“教育问题”的结论。我国学者在新编教育学教材的过程中,吸收了这一研究成果,从过去普遍持有的“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现象和规律”,发展到“教育学就是研究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揭示教育规律的科学”。八十至九十年代,我国中小学教材教法改革掀起高潮,实验、访谈、问卷、测量等实证的研究方法逐渐被应用其中,但还较少纳入规范化、系统化的教育研究方法体系之中,教育学的学科建设更是基本处于游离状态。
世纪之交的教育学研究开始以自身为对象,教育学从“单数”走向“复数”。九十年代中期,对教育学研究的反思开始达到高潮。“元教育学”以教育学自身为研究对象,力图为反思提供依据,试图为研究者提供可透视整个教育学研究的理念、方式和手段,并把间断性的反思整合为必要的学术研究机制。元教育学研究既是对教育学研究自身状况、发展等的省思,又强调这种反思的深刻性、完整性,关注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考察教育科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有关教育知识的学科经历了由一门“教育学”到多门教育学科的发展过程。由于自身的特性,教育学难以成为经验科学意义上的“单数”科学,但它要站在“众人”的肩膀上,把许多学科集于一身,从而综合成自身的体系,即成为一种“复数”教育科学。这不仅是可能的,更是必要的。
科学及学科的发展总是与社会发展同步共振。进入新世纪以来,教育改革和教育学的发展不仅欣逢教育现代化、治理现代化等多方面政策机遇,更有大数据、人工智能、学习科学等高科技、多学科的强力支撑,相信“复数”的教育科学将在应对挑战中不断地走向繁荣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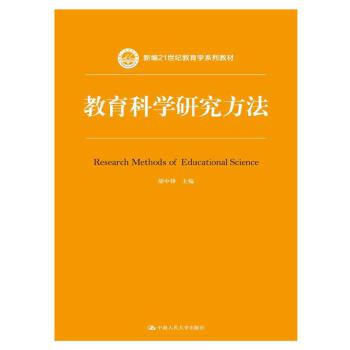
问题之功用:凸显对象,引领研究
现象、规律,还是问题?我国学界大多将教育学的研究对象认定为“教育现象及其规律”,这是值得商榷的。一位教师手执一卷,对课堂上一群学生侃侃而谈,教育学把这样一种现象看成是“教育现象”,这种认定只是出于这门学科对教育问题的关注,或以教育的观点看待这种现象;同样,出于对“社会问题”、“心理问题”或“文化问题”的关注,别的学科的研究者也可把它视为其他现象。这些不同的“问题”属于同一客观现象的不同的“问题领域”。显然,这一现象被视为问题,是出于研究者的主观意图,即主体对客体关注的立场和视角。至于“规律”,是教育学研究最终要认识的对象,但是像教育这一关涉人的活动,有没有自然现象那样的规律存在都还是问题,至多只能说是获得了“规律性认识”。
不妨说,教育现象或教育存在只有转换为教育问题,才能成为教育学研究的对象。正是问题才将内隐于教育事实/教育存在/教育现象中潜在的、间接的“实质对象”凸显出来,并引领研究者研究的全过程,即所谓“问题导向”。问题导向的教育学研究,有助于突破那种没有问题意识、迷恋体系建构的所谓“体系本位”的研究方式,增强教育学研究的知识创新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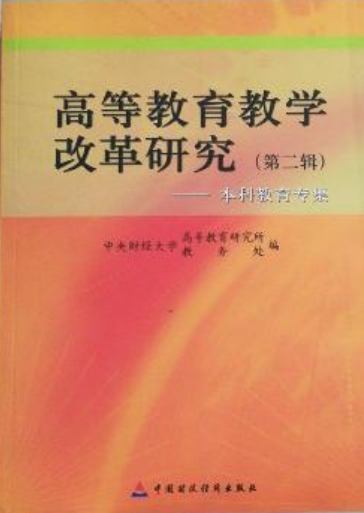
教育问题,还是教育学问题?有研究者认为教育现象、教育活动、教育问题都不是教育学的研究对象,这其实是在强调“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不同于“教育研究的对象”。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只有“抽象的教育系统”才是它的研究对象。这是因为,教育学是关于教育系统的知识体系,教育学研究方法论则是发现该知识体系的方法体系。尽管人们在讨论教育学研究对象时常常并不严格区分“教育的研究”和“教育学的研究”,但区分二者仍是有意义的。教育的研究的对象范围十分巨大,既包括“形成教育事实”,也包括“形成教育理论”;教育学无疑是一种系统的理论形态,其研究对象用“教育学对象”来限定,是一种必要的精确。
“单数”教育科学的问题,还是“复数”教育科学的问题?从用词上说,“教育科学”这一概念经历了由单数到复数的变化。“单数教育科学”主要指的是按经验科学的模式而形成的教育学,以区别于赫尔巴特以前的思辨教育学。“复数教育科学”的产生源于人们对教育学的理论基础的思考。从赫尔巴特开始,伦理学、心理学、生物学、生理学、社会学、统计学等学科,二战后还有经济学、政治学及技术学等都跨入了教育学研究的行列。“单数教育科学”中蕴含的观念是:力图将教育学变为经验科学,希冀它能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并驾齐驱;“复数教育科学”中蕴含的观念是:教育科学是大量人文、社会学科甚至包括某些自然学科应用于教育领域而形成的,它以教育现象或教育问题为对象,在方法上博采众家,其发展以这些学科的发展为前提。这需要进一步追问:教育理论是以怎样的理论形态而存在——经验科学理论抑或实用理论?后者应是可能正确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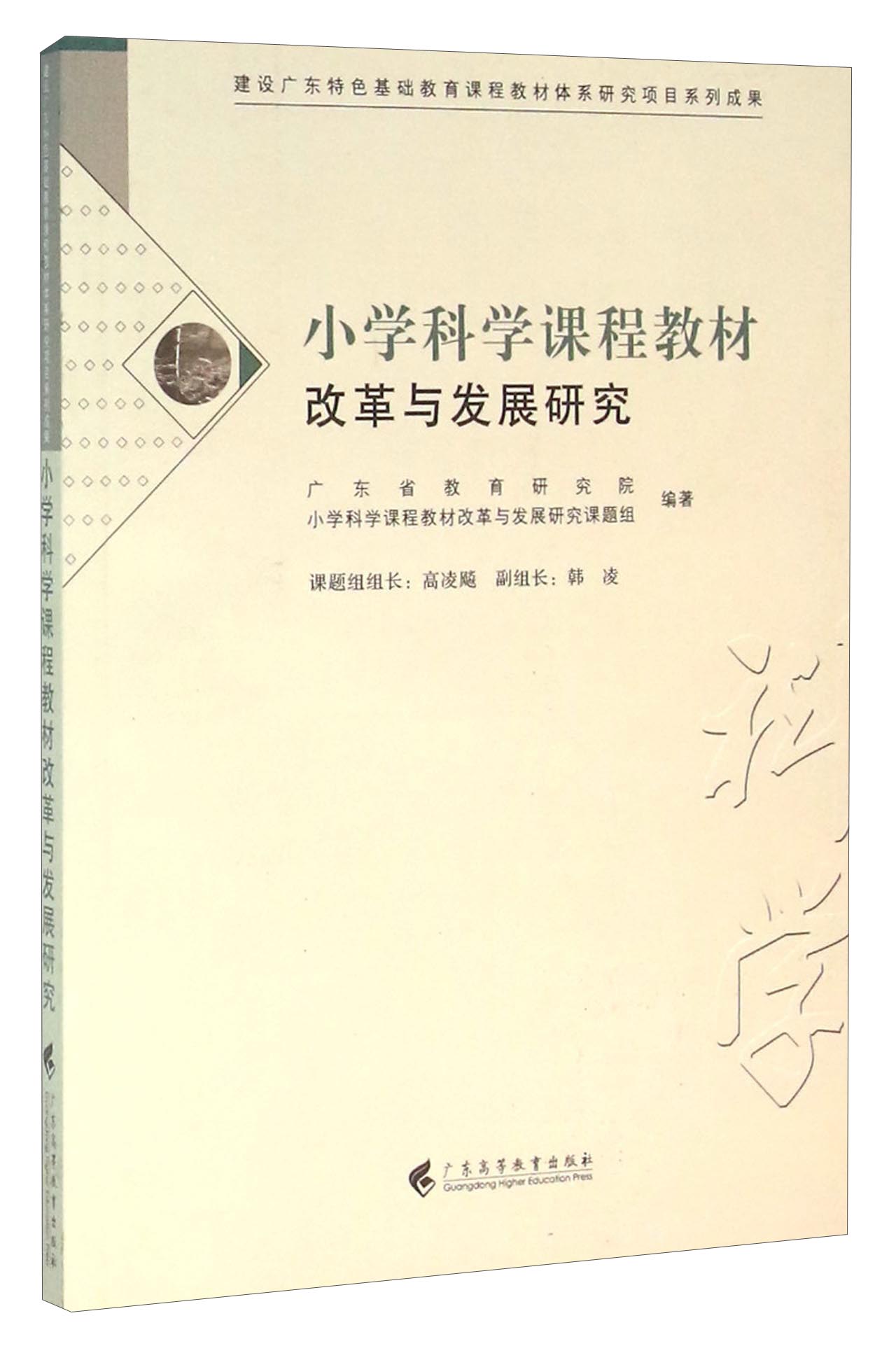
方法之反思:用创之妙,存乎一心
如果说,研究者与教育问题构成一种基本的主客体关系的话,那么研究方法的运用与创造则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重要中介。无论处于哪个时期,无论问题是否清晰,总有合适的方法出现在正确的时候。
在移植改造中更新方法。新中国成立至“文革”之前,我国教育领域就开展了一些教育教学改革实验,如集中识字和分散识字实验,中学数学自学辅导实验,以学制为龙头的多项改革实验,“三班两教室”办学模式,等等。尽管这时候的教育学还以高校教材为主,来自一线的实验成果还一时难以与之挂钩,但为改革开放以后教育教学改革实验的再兴起,埋下了难能可贵的“种子”。
在变革实践中创新方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兴起的第二次教育改革实验热潮中,多种识字与阅读教学实验争芳斗艳,自学辅导、尝试指导等数学教学改革实验此起彼伏,“读读、议议、练练、讲讲”等教学法创新层出不穷,还有不同分段、不同年限的学制改革试验也引人注目,这些本土原创研究创新了大量有效方法,如“经验筛选法”、“整体改革实验”等,加上大量移植、改造和吸收国外教育教学理论主张与实验成果,逐渐形成了风格各异的教学模式及数量众多的教育改革成果与典型经验,为“复数教育科学”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素材和理论元素。
在合作开发中提炼方法。近十余年来,大学与中小学、职业学校、特殊学校等的合作探索越来越普遍,新的成果与经验也不断涌现出来,如“名师名校长工作室”、“教师工作坊”、“前移后续”教师专业研修机制等。我们拟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通过多重比较和多级编码的方式,从与中小学教育改革实验区/实验校长期合作的成果与经验积累中,提炼出被我们命名的“协商式行动研究”范式的核心概念、基本命题、主要流程与机制等要素和架构,以更多的类似产出,反哺教育科学的研究与发展,凝练出有“中国教育学”独特品性的方法群及方法论体系。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课题《我国教育2030年发展目标及推进战略研究》(VGA170001)阶段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