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唯物主义哲学理论的缺陷
唯物主义在哲学上是一种世界观,而道德观念上的唯物主义则为享乐主义。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则为这样的一种观点:真实世界是唯一地由物质性的事物所构成的。这两种不同的概念的唯物主义在逻辑上是彼此对立的。不论何时,我们必须避免将唯物主义与实在论同那种认为知识或至少科学是用以描述实在的认识论学说相混淆。在某种意义上,逻辑的就是纯粹形式的,但人们并不是真正地知晓纯粹形式的本质,而是说从这一事实出发,任何认识都是一种表达,一种陈述。一切知识只是凭借其形式而成为知识,知识通过它的形式来陈述所知的实况,但形式本身是不能再被描述的,形式的本质只在于知识,其余一切都是非本质的,都是表达的偶然材料。这就使传统的“认识论”的问题得到解决。思考表达和陈述的本质,即每一种可能的“语言”的本质,代替了研究人类的认识能力。只要存在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在理论上指出它的解决的办法是与指出问题的意义相一致的。 \left[ 1 \right]
唯物主义的哲学的发展经过了六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古希腊和古印度的原子论为中心的古代唯物论。第二阶段是17世纪古代原子论的复兴。第三阶段是18世纪的唯物论。第四阶段是19世纪中叶的“科学”唯物主义,它兴盛于德国和英国,与自然科学中的不同分支的发展密不可分。第五阶段是辩证且历史的唯物主义,它伴随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不断地巩固。第六阶段即当前的阶段,是学术的且超党派的,但在其他方面又有不同。本章重点批判第五阶段的辩证且历史的“唯物主义”,它在逻辑上是互相矛盾的且也是落后的。
科学哲学中实在论取向的立场坐标
19世纪“科学的”唯物论者在哲学上是幼稚的,但却具有将哲学理论与自然科学相联系的能力,不仅科学家福格特、摩莱肖特和克佐而比属于这类,还包括延德尔和赫胥黎以及达尔文。由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所阐明的辩证唯物主义是物力论和突现论的,它自我声称是科学的,但它同时又被认为是一种意识形态。比较新的即学术的唯物论者是以多种形式出现的,从物理主义者如诺伊拉特、蒯因和斯马特到突现的唯物论者如塞缪尔·亚历山大和R.塞拉斯,通常认为,他们与当代科学的关系是较为疏远的。
唯物主义哲学因几条罪状而一直受到攻击。首先是同巫术般的宗教的世界观相冲突(因此被人与实证主义相提并论),其次则是因为自称是唯物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是苏东国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体系中的一部分而受到诅咒。第三则是因为被认为未能解决甚至是回避了一些哲学的主要问题。
在此,我们将应对来自各个方面的攻击,即认为唯物主义哲学完全是不必要的、不正规的、无意义的、以下的问题被认为是唯物主义哲学所不愿意甚至不能解决的问题:
必须承认,大多数唯物论者并未对上述的关键问题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他们或者没有正视其中一些问题,或者在面临这些问题时,提供了一些过于简单的回答,比如那些认为时空点是与物质同样真实的,认为精神是不存在的,以及认为数学对象即为纸上的符号的观点。特别是,看来并无关于意识、数学或价值和道德的完全成熟的唯物主义哲学。
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看似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但在文化消费领域,二者的疆界便被废除——自由资本主义的豪华奢侈品不断地被精英阶级——特别是上层阶级女性给买走,自由主义不断地许诺一个光明的未来的到来;具有反抗性质的商品或文化被不断地加工,流行于社会底层阶级,共产主义的文本则化身为弥赛亚,许诺末日审判之后的地上天国的到来。二者运作模式一致,差异仅来自受众群体,二者共同成为资本主义文化符号生产运作的一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所有的文化都是同一个文化。正如奈格里所说反抗变得只有在睡梦中才有可能,只有在睡梦中,我们才能去真正梦想其它的东西。因为只要你醒着,只要你的意识还被资本主义体系所影响着,你就很难想象得到处在资本主义体系把控之外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建构一种新的现实,新的本性——如果本性这个词还可以用的话,以此来抵抗异化和丢失的自我。因此,传统的唯物主义哲学或者说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的许诺在大众的视野中就堕落为另一种形式的消费主义,去除它的影响进而思考真正的问题是极为困难的。
大多数唯物主义哲学家很少使用更为精确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很少考虑以一种更为令人信服的方式来论证他们的观点,此外,唯物主义者总是忙于对付那些无知和恶意的攻击而忘却了建立更为全面的哲学体系并进而使之与现代逻辑学、数学、科学技术相一致的任务。其发展的结果为传统的唯物主义哲学彻底地与恶魔会面,变为一种具有强烈攻击性的宗教般的信仰。
自19世纪以来,唯物主义就没有任何进步。这部分地源于它无视现代逻辑学并强烈地排斥向对立的哲学学习。这些繁杂的唯物主义并非只是又一种本体论,它是科学和技术的本体论。特别地,还是某些科学突破诸如原子物理学和核物理学、进化论生物学、遗传化学理论、生命起源的科学研究、思维生理学以及古人类学和编史工作方面的最新进展的背后的本体论的动力。
对此,在这方面具有突破性进展的M.邦格则认为哲学研究应当系统地、精确地、科学地进行而不能采用文学的描述方式。这一信念的论点是,鉴于分析和争论可以摧毁一个哲学理论,因此如果能证明它同科学相一致并有助于科学研究的进展而不是起阻碍作用,那么理论的建构将会是成功的。
M.邦格认为在哲学和意识形态之间通常所存在的前者从属于后者的关系应当被颠倒,一种意识形态若不是只同由于对真理的自由探索而获得进展的科学和哲学相一致,它就不能为即是真实的又是有效的。某些“科学的意识形态”仅仅只是关于现实以及对现实认识方式的本体论、认识论和道德原则的某种组合。我们不应因唯物主义与某些意识形态的关系的程度的变动,而产生接受或拒斥唯物主义的行为。 \left[ 2 \right]
与M.邦格的相关引用指数的统计(来源:Google Scholar)二、对辩证且历史的“唯物主义”的批判——综合观点
这里先引用M.邦格对辩证法批判有关的段落,我们会在引用的段落其中批判M.邦格反对者的观点。
著名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
我们采用如下的辩证法的原理 \left[ 3 \right] \left[ 4\right]\left[ 5\right]\left[ 6\right]\left[ 7\right]\left[ 8\right]\left[ 9\right]\left[ 10\right]\left[ 11\right]\left[ 12\right] :
1.任何事物都有一对立面。
2.任何客体本质上都是矛盾的,即由相互对立的成分和方面所构成。
3.每一种变化都是所涉及的系统内部或不同的系统之间的对立面的张力或斗争的结果。
4.发展呈螺旋状,它的每一层都包含其此的上一层,但同时也是对它的否定。
5.每一量的变化都归结于某种质的变化,而每一新的质都有其新的量变方式。
辩证法的论点(1)在两方面是含糊的,“客体”的含糊性和“对立”的含糊性,它可以被分为两大命题即对于每一事物都有一反事物;对于具体客体的每一性质都有一个反性质。
假设辩证的本体论所涉及的具体的客体以及环境和事件能够以某种方式还原为事物以及性质;那么只要对反事物和反性质不作出精确定义,其上述两大命题仍然是模糊的,对于“反事物”(或“一事物的辩证对立面”)至少可以给予下述4种解释:
Ⅰ.一个给定事物的反事物是该事物不存在的事物(比如说不存在白的黑),但某些事物的不存在的事物不能与该事物相对立,更不能与之结合成为第三种对象,那么此定义即为不充分的,一个具体事物的辩证对立面不能是无。
Ⅱ.一个给定事物的反事物是该事物的环境,即在事物的整体中该事物的补充物,那么这个定义即为不合格的,相互补充的事物并不一定有对立面或斗争——我们无法做出一定存在这样的推论,事物的整体可为协调且统一的——太阳系与除其之外的宇宙即为如此。
Ⅲ.一个给定事物的反事物的存在即为与给定事物的结合会在某一方面或某一程度上破坏他的“存在”——毒药破坏人体结构,若采取此定义,那么就无法保证任一给定事物的反事物的存在,并且在即使有反面事物的情况下,它们也并非是唯一的——伽马射线暴破坏人体结构。这一定义并非是合适的。

Ⅳ.给定事物的反事物的存在为与该事物的结合会产生第三种事物的“存在”,它以某种方式既包含又取代这两者,似乎正反质子对就如同这样构成一对辩证的对立面,但它们可湮灭为光子,后者并不是原来的实体的扬弃,而是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事物。此外的伪证可为聚合,这为一种综合,但却是相同的实体而非相反的实体的综合。
上述关于反事物的四种描述都不符合辩证法的要求,则存在两种可能的情况:一为命题“对于每一事物都有一反事物”为无意义,二为我们应当给出第五种合理的关于“反事物”的定义。若前者为真,则辩证法初显漏洞,若是后者,则应由辩证法来作出一种新的定义,或者承认:原理(1)与反事物和事物无关。若求助于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则可得知辩证的对立面涉及(现实的或潜在的)品质或属性而不涉及事物。
论点“对于具体客体的每一性质都有一个反性质”除非给“反性质”这一术语规定含义,不 然这一句子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将考虑以下4种情况:
Ⅰ.一种给定性质的反性质是不具有这种性质的性质,因此,若一个谓词P代表一种给定的肯定型的性质,那么它的否定非P就将表示相应的反性质。但是,一种性质和不具有该性质并不能结合起来产生第三种特性,即前两者的综合,因为一种给定特性的缺乏并不是一种事物所实际具有的特性。否定P(或断言某一客体满足谓词非P)是一种没有实体对应物的严格概念上的操作。把P和非P合并起来则将产生矛盾或者并不存在的性质,即无论概念的客体还是物质的客体均不具有的性质。因此,我们必须反对把反P和非P相等同的说法。
Ⅱ.一种给定性质的反性质是在所有性质的集合中该性质的互补性质。 这个定义也是不妥当的,因为个别性质与性质的集合并非处于同祥的地位。固此不能与之对立,更不必说构成一个作为这两者的综合的第三种性质了。
Ⅲ.一种给定性质的反性质是能定能限制、平衡或抵销这种性质的性质,但质量这一性质就不具有所说意义上的对立面,因为并不存在反质量或负的质量(若存在,则违反了广义相对论的规则) \left[ 13 \right] \left[ 14 \right] 。这种反性质既不是普遍的、也不是唯一的、或者说并不是每一种物质都有一种反性质,而且当一种性质具有反性质时,它也有可能并不是唯一的。
Ⅳ.—种给定性质的反性质是当与它的性质相结合时会产生第三种性质且第三种性质包括前两者及不为空的性质。相同粒子的单纯增加(没有任何对立的东西)产生出有质量的物体。再如,这种过程可能会达到一个坍缩点——一种不包含辩证的对立面的质的飞跃。这种解释虽然是有意义的,但井没有证实“反”这一前缀的合理性,也没有产生任何普遍法则。
由此结论:在我们所考虑的关于“反性质”的4种似乎可能的解释中,第三种与第四种是有明确意义的,但它们都不足以使人在最普遍的意义上去肯定“对于具体客体的每一性质都有一个反性质”而仅仅能够肯定一种非常弱的论点:
Ⅰ.对于某些性质有另一或一些性质(所谓“反性质")会同前者相抵消或相中和。
这仍然是肤浅的且偏离辩证本体论原意的,但即使提出类似于"反性质"的第五种更为合适的定义,仍然会面临困难;关于每一种性质都有一种反性质与之相对应的假定,在一种拒绝对谓词(某种确定类型的概念)和具体事物的性质作出明确区分的唯心主义本体论中是可能的,并且,由于概念(谓词)非“P”与概念P是一样合理的对于一个柏拉图主义者和一个黑格尔的信徒来说,否定的性质和肯定的性质是一样真实的。辩证唯心主义者只要设法为反性质的概念提供一个适当的解释,他就能够接受对于论点“对于具体客体的每一性质都有一个反性质”。然而,对于持唯物主义立场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来说即不会如此,事实上,对于一个非唯心主义者来说,虽有否定的谓词,它们不能代表任何具体客体的性质,如果谓词P表示一种确定的性质、那么它的否定“非P”并不代表一种相反的性质而只表示不具有P所描述的那种性质。若“Pa”为命题“事物a具有性质P”的缩写,那么“非Pa”则为命题“事物a不具有性P”的缩写。既然不具有某种性质不能说成是这种性质的辩证的对立面,由此可以得到,否定的谓词不能得到反性质,否定是一种不具有实体对应物的概念上的操作:它和陈述及其否定有关而与具体的对立面的斗争无关。 \left[ 15 \right]\left[ 16 \right]
同样,谓词的析取并不表示析取的或可供选择的性质。析取与否定一样是概念上的而非本体的 \left[ 17 \right] 对形式逻辑是辩证法的极限情况的论点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它对于“所有知识都是对现实的描绘”断言也同样有致命的后果。事实上,考虑一个确定类型的谓词的集合和一个共同的指称物,关于哺乳动物的一元谓词的集合,这一谓词的集合是一种布尔代数;另一方面,相同个体性质的相应集合则仅是一个半群,其中的毗连被解释为性质的合取,断言谓词的结构反映了性质的结构是与唯心主义本体论一致的,与自然主义、特别是唯物主义则是不相容的,后者无须用到否定的性质。因而,辩证的唯心主义尽管看起来难以置信,却是可能的,辩证的唯物主义则是难以置信且同认识的反映论不相容的。
论点即每一客体都是一个对立面的统一体,通常被认为构成了辩证法的基本点。但是,除非使“对立面”这一术语精确化,否则这个语句几乎没有任何意义。正如我们在前两节中已经看到的,这并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任务,而且,不管怎么说,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们一直没有完成的任务。
著名科学哲学家M.邦格近照
M.邦格认为,如果把对立面或实体的矛盾解释成性质之间的关系,即反作用或相互抵消的关 系,对于具体客体的每一性质都有一个反性质是有意义的。因此,我们采用下述定义:性质(或关系)P1称为与性质(或关系)P2对立,当且仅当P1趋向于抑制,P2反之亦然。如果在这种意义下理解対立面、那么人们就可以断言存在着为内在的实在矛盾所支配的系统。但这与断言“所有系统都是矛盾的”有很大的差距。根据现代物理学,电子和光子并无内在的矛盾。而这还是一样,因为如果每一事物都是由两个矛盾的部分所构成,那么每一这样的部分也将类似地构成,从而陷入无穷的回归。
如果某些事物在某些方面同另一些相对立,即有些系统具有在某些方面互相对立的成分或性质,可得一个非常弱的论点:
Ⅰ.某些系统具有某些方面彼此对立的成分。
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主要论点就只限于复杂事物而且还只限于它们的某些方面。关于简单的事物(如果它们存在的话)则并没有作出什么结论。对于任一系统的所有方面或全部性质也没有作出任何断言。被极度弱化的辩证法基本论点“某些系统具有某些方面彼此对立的成分”则失去了普遍性,它并非是一个关于变化的彻底的理论的一部分,另外,它所给出的把系统分解为两极的提议在本体论上也并没有构成进步。在对立面中思考是古代思想 \left[ 18 \right] 及希腊古典思想 \left[ 19 \right] 的特征。
在对立中思考包含着一种对实在世界的极为武断地过度简单化,一个系统可以被称为两极系统,如果它是由这样的部分构成的,它们可以处于两种状态中的一种,且两种状态都是相互排斥或相互矛盾的,数字电子计算机中采用的一个开关电路或许就可被看作为两极系统。但是,辩证法只说明了过程的最后结果而忽略了中间状态或过程,也就是说过分地简单化问题。如果不考虑这些过渡犾态,那么系统的运转就可用通常的布尔代数来描述。但是,假定我们考虑到过渡状态,那么状态空间就需要第三个值并将获得更加丰富的结构,即一个三值的卢卡西维茨代数 \left[ 20 \right] 。而且,即使是三值的设计对于计算机的设计者和使用者来说,也是一种过分的简单化,把稳定状态的整个连续统归并为开放或封闭的两极化范畴以及把过程的整个连续统归并为一种状态,都是一种初步且粗糙的近似。 电学的网络理论提供了一个更为真实的说明,电动力学则提供了更深刻的描述、这两者都假设了无穷多种稳定的和过渡的状态。在这种真实的说明中,没有两极化的痕迹。两极化存在于我们关于实在的思维中,而不在世界本身之中; 并且两极化是早期的知识而非科学知识的标志。
事实上存在着不是由实在的矛盾所导致的变化。粒子或电磁波在自由空间中的运动并非由实在矛盾而驱动。氢原子不能被说成是互相对立的,2个氢原子构成1个氢分子也不是互相冲突的;恰恰相反,可以说它们是互相合作的。即可得到一个非常弱的的论点:
Ⅰ.某些变化是由不同事物或同一事物的不同成分在某些方面的对立而引起的。
这是一种非常肤浅的论点,即使是化学动力学,都比它更为确切、深刻、丰富。
对于矛盾是变化的动力这一辩证原理的文字表述与认识的反映论也是不相容的、实际上,如果每一陈述都反映某个实在的东西,那么每一矛盾的命题就必定反映某种实在的矛盾,后者又是某种变化的源泉。然而,由于矛盾是虚构的,它就不能反映任何真实的东西;从而要么就没有变化,要么认识的反映论必须与辩证法分道扬镰。
辩证法对于自然界来说是人为的,但一当人们使用辩证法时,就将冲突作为变化的唯一源泉从而完全排斥了另一方面——合作,甚至在辩证唯物主义者内部中,他们也是鼓励群体的自我分裂的,将其称为“通向进步的必经之路”。由此,这些分裂的群体也就印证了辩证法与协同论一样都极大地妨碍对社会的认识。
按照唯物主义者的观点,知识自身是没有发展的,只是因为并没有单独存在的知识,真正有的是人脑和研究团体及知识应用者的认识的发展。因此,如果我们希望发现认识发展的真实的动力,我们就必须注意置身于社会中的现实的认识个体(个人或团体)的认识活动,而不是由这些活动产生的脱离现实的产物,合作在认知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那么知识的发展就不符合关于变化的辩证“法则”。
对于辩证法原理“发展呈螺旋状,它的每一层都包含其此的上一层,但同时也是对它的否定”,由于辩证的否定尚不明晰,扬弃的概念并非如某些辩证者所说的,既是“保存”又是“死亡” ,这两者在根本上就是冲突的,若按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看,对资本主义的否定的共产主义社会既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又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或者说辩证法的扬弃保存了事物的一部分,丢弃了事物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那么这种辩证法只是一种混淆概念的诡辩术,我们在这里得到的结论与波普尔在《辩证法是什么?》中得到的结论相同;而且这种辩证法与以科学实在论为本体论的唯物主义理论毫无关系。
辩证法论者或许会将突变论作为自己反驳对辩证法的攻击的有力工具,“我们的模型把所有形态发生都归因于矛盾,归因于两个或更多的吸引子之间的斗争” \left[ 21 \right] 赫拉克利特式的突变理论是虚构的,斗争的对象并不是物质的而是几何学的。生物学和社会学中的突变模型是描述式而不是预言性的,突变论充斥着任意性,没有强制限定的发展规律,也并非是辩证法当中所说的“螺旋式”的发展。
辩证法不是一种对事物的解释具有普遍性的学说,它并不是对所有事物、所有性质和所有变化都是正确的。它能得到例证证明,也可以得到反证。 \left[ 22 \right] 辩证法没有解释物理客体和概念客体两者的普遍性的理论,思维的产物遵循概念的法则,与支配着自然界的法则不同,它是人造的。思维产物是我们大脑创造性活动的虚构物,它们还以自已的不适用于物理客体的法则为特征,实在的客体是以物理的法则为特征的。两者无相同之处。
M.邦格经过一系列的批判,认为辩证法是含糊和不确切的,有损智力的,古典的且极为简单化的。辩证法并不具备对所有物理、概念客体的普遍性。每一实在事物均处于流动状态之中以及在任何过程中必定会出现(或丧失)新的性质——是为所有经过加工的本体论所共有的。另外,可以用一种精确的方法表述它们,并使之与其他普遍的本体论假设相联系以构成一种与科学协调的、首尾一致的假设-演绎系统 \left[ 23 \right]\left[ 24 \right] ,这种新本体论是动力论的而不是辩证的。由于辩证法是以含糊的、隐喻的术语加以表述的,它就很难与事实相对照,即很难对它的真理性进行检验。然而某些人批判他,说:“形式逻辑认为P=P,辩证逻辑认为P=P也等于-P······形式逻辑是静止孤立的思维,辩证逻辑是全面、变化的思维”以此来捍卫辩证法在思维层面的“特别地位”,M.邦格其实早已反驳这种观点,这种对M.邦格的批判实际上是建立在对M.邦格对辩证法的批判所不理解的基础上的,M.邦格说:
辩证法论者声称逻辑学是辩证法的特殊情况,即是对于缓慢运动的一种近似,它在变化极度缓慢、以致粗略的近似叫以忽略这种变化的情况下是成立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实际上, 一条规律的陈述如果说是另一规律的特姝情况,两者所涉及的必定是同样的事物。但对于逻辑规律和本体论的假设来说并不是这种情况。相反,经典电动力学的规律是量子电动力学规律的一种极限情况(对于大量光子而言):这两种规律是可以互相比较的,因为两者都是关于辐射的。就谓词演算或任何别的逻 辑理论与物理学或本体论的法则的关系来说则不是这种情况: 前者描述的是概念和命题所发生的情况,后者所涉及的则是物理系统的描述。思维的产物(不同于思考它们的过程)不是物理客体。因此形式逻辑就不可能是辩证的本体论的一种特殊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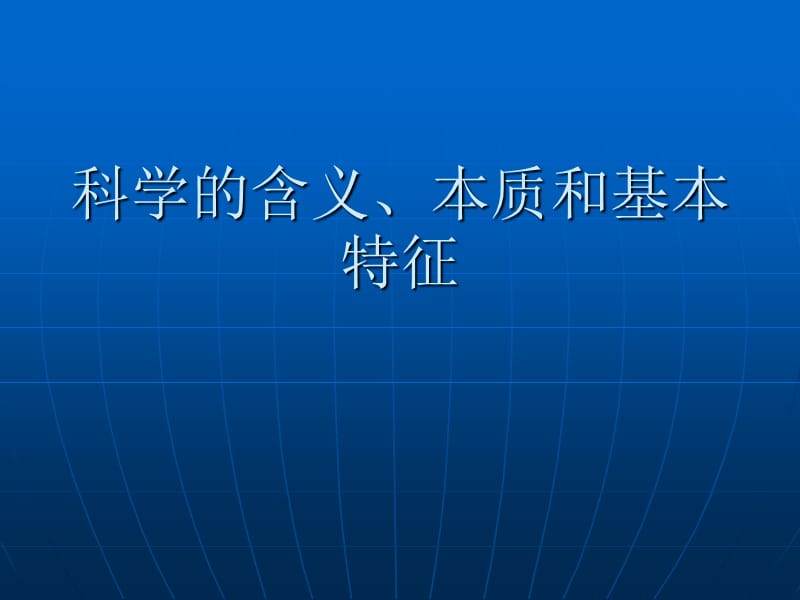
逻辑和任何一种具有说服力的非逻辑的理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还原关系,而是一种预设的关系。逻辑学是根据所存其他令人信服的理论预设的。这种关系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无论是在数学、自然科学或在本体论中、在对任何实质性的理论进行使之秩序化的再构造时,都必须具体说明所使用的语言以及这 —理论所容许或使用的推理规则。
逻辑自身,即逻辑理论的体系,是独立于经验且不受经验影响的论题。它是一种先天的结构,而其作用正如数学之对于物理学或社会学的作用一样。既然任何实质性的理论T都预设丁逻辑理论L,T就包含或承担L。T被说成是实质性的理论,因为它描述了某些非逻辑的对象,而L对于确切的指称物则是中性的。 实际上在L中出现的概念和命题可以指称任何事物,从而也就没有任何特殊的指称。相反,如果T是如此之贫乏,以致它的所有实质性假设均被除去的话,所剩下的就至多是一个并无任何确切指称物的框架,此时,T或许可以被说成是关于某个未经详细说明的抽象集合中的个体。但辩证法恰恰不是被设想成这样。
形式逻辑涉及一切事物但并不描述也不代表它自己的基本概念——“非”、“和”、“所有”、“蕴含”及其他相关的概念——以外的任何东西。这些逻辑学的特殊概念涉及或适用于命题,而不是物理客体。实际上,例如逻辑的联结词“或者”就可看成将一组命题映射成另一命题的函项( V:X\times X\rightarrow P ,其中P是命题的集合)另一方面,本体论的相互作用的概念不能被看成应用于命题的概念„ 实际上“相互作用”涉及到具体的客体:精确地说,相互作用是使一对具体的客体成为语如“A和B相互作用”这样的命题的谓词( I:C\times C\rightarrow P ,其中C是具体客体的集合)如果我们承认一 个谓词的指称域等于所有在它的定义域中出现的集合的并 \left[ 25 \right] ,于是我们得到:
R(V)=P\tag{1} R(I)=C\tag{2}
并且,由于命题与具体的或物理的客体是相交的,因此,这两个谓词除去它们的一般形式以外就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而这种形式是一种数学的性质,以逻辑学为一方,物理学为另一方,它们并不涉及同样的客体。因此,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可能是另一个的特殊情况。事物是在此之外、位于外部世界中,思维的产物并非物理的或物质的存在,它们仅是概念的存在,即作为概念的群体的成员而存在。我们构思出了某种概念并假托它们因此而获得了—种独立的存在,即它们已不再依赖于它们心理学上的起源和历史的发展,我们并不赋予概念以一种独立的或自主的存在。唯有活着的思想者才成为一种具体的或物理的存在,他们的大脑过程也是如此。我们仅仅是假装或假托他们所思想的事物能够从其思维过程中想象地分离出来。这种做法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赋予思维以诸如具有—种意义或一种真值这样的非物理的性质。
认为由于形式逻辑对于论述变化是无能为力的,从而需要—种为变化自己所有的逻辑学——辩证逻辑或某种类型的时态逻辑——这种观点是古代哲学的一种遗物。当我们未能理解某一种变化时,我们将把失败的原因归之于某些具体或实际的理论而不是逻辑,逻辑是在建设、检验及批判科学理论中使用的工具,逻辑是先验的。
M.邦格在进行一系列的对形式逻辑的探讨后,发现若不赋予思维客体之独立存在,会为这些“庸俗”唯物论者带来“方法论的二元论”的困惑,若赋予,则可以导致“本体论的二元论”的困惑。M.邦格从思维独立的性质的角度考察概念客体和物理客体的性质与关系,陷入歧途的“庸俗”辨证法无法理清精神的含义,进而在这些问题上表述模糊,极为严重地阻碍了相关领域的科研发展。
M.邦格认为心理物理二元论致命弱点是其理论使精神状态和事件同任何可能处于这种状态或经历这种变化的事物分离开来,这种构想状态和事件的方法同科学的本质格格不入:实际上在各门科学中状态都是物质实体的状态,而事件则是这种状态的变化。
在此,我认为简要的对M.邦格对唯物主义的新观点的概述是必要的,它与批判旧理论的同时是互相补充的,此外,也是对批判的深化和外延。M.邦格如此定义关于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性质:
Ⅰ.对象 x 是一种物质客体或实体,当且仅当,对于每一个参照系y,若 Sy(x) 是关于 x 的状态空间,那么 Sy(x)至少包含两个元素;不然的话, x就是一种非物质的客体或非实体。公式则表述为:\mu x=dt(y)\tag{1}
若 Sy(x) 是关于 x 的状态空间,则有:
\left| Sy(x) \right|\geq2\tag{2}
Ⅱ.物质 (M) 是所有物质客体 (x) 的集合:
M=dt \left\{ X|\mu x\right\}\tag{3}
这是一个集合, M 是谓语 \mu 的外延, \mu 读作“是物质的”; 如果我们想坚持唯物主义的话 ,我们就不能说物质存在(自然上的概念除外),与此相反,我们仅仅假设个别的物质客体的存在。
Ⅲ.— 个客体 x 是实在的, 当且仅当 ,或者 (a) 至少存许另一客体 y ,在x不存在的情况下,它的状态会有所不同, 或者(b)x 的每一成分都改变着它的另外一些成分。
Ⅳ.实在是由真实客体所构成的集合。
根据以上性质,我们得出重要的假设“当且仅当它是物质的,一个客体才是实在的” (更简要地,所有且仅有物质的客体是实在的)。
我们引用卡尔·波普尔和南希·卡特赖特的观点来继续反驳各式各样的诘难:
阿达马在1898年发表的一篇有趣的论文中讨论了一个简单的力学问题:质点以恒定的速度沿无限弯曲表面的测地线的运动。测地线指最短线,这里的弯曲表面是一种特殊类型,具有变化的负曲率,还假定没有不连续的情况。阿达马假定初始位置绝对精确地给定,他容许运动的初始方向在角度α内变化。他证明会有若干轨迹类型,特别是有:(1)轨道或者闭合的轨迹,包括那些渐近闭合的曲线,始于其上的点在运动中将永远与初始点保持有限的距离。(2)通向无穷的轨线,足够长的时间后,在其上运动的点与初始点的距离将会超出任何给定的值。
我们考虑两个不同的闭合轨迹,它们是由邻近的、不同的初始方向演化出来的,初始方向之间的夹角为α。阿达马证明,即使我们让角度α如我们愿意的任意小,从此α角内(也就是说从我们可以选择的任何两个不同的闭合轨道内)仍然能够找到那样的初始点,其轨迹会通向无穷。
但是这意味着,对轨迹初始方向的测量,无论如何精确(某种绝对的数学精确性),都不能确定一个质点是在一条轨道上运动还是在最终通向了无穷的一条轨线上运动。当然,初始位置绝对精确地给定这样的假设,更是不现实的。换言之,这意味着,我们没法确定质点会以第一种方式运动还是以第二种方式运动,前者指质点运动中距起始点不超过某有限值,后者指质点会稳定地增加它与起始点的距离,最终跑向无穷。 \left[ 26 \right]
上述两段说的是初始条件的分形特征。我们可以把初始条件换成[0,9]线段更简明地描述一遍。设A和B是线段[0,9]中任意两个初始点。假定由A出发,在动力学规则的作用下,它最后演化出的轨迹是闭合的轨道,而由B出发最后得到的是发散的通向无穷的轨迹。这说明A和B是不同类的初始点。下一步是在A的附近找一个与A同类的点A1,假定A1大于A,A和A1形成一个小区间[A,A1],现在我们就专门考察这个小区间,它就相当于上述的α角。阿达马的证明相当于,我们在[A,A1]中总是可以找到与A和A1不同类的点,由那样的点出发,经动力学规则的作用最终得到发散的轨迹。那么是不是这个区间[A,A1]太大了呢?也许是,但是,无论把它变得如何小,我们仍然能够找到不同类的点!比如说我们再在A的更小的邻域内找到同类点A2,现在考虑更小的区间[A,A2],在此内部,仍然会发现"敌人",即不同类的初始点。即使我们考虑[A,A3,]、[A,A4]、[A,An]等,也无济于事。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简化的、示意性的描述,实际情况比这要复杂。
波普尔由此得到他所需要的结论:
因此,我们以前讨论的"科学"决定论的强版本被阿达马的结果反驳了。因为,如阿达马指出的(此处加了第三个脚注),任何精度的初始条件都不可能使我们预测一个(多体的)行星体系在拉普拉斯的意义上是否稳定。这是因为这样的事实,决定了轨道的数学上完全精确的初始状态,和决定了通向无穷的测地线的另外的初始状态,对于任何物理测量,是无法区分的。阿达马以此拒斥了拉普拉斯(关于天体系统稳定性)的结果,此结果很可能是拉普拉斯"科学"决定论观念的一个主要思想来源。 \left[ 27 \right]
波普尔第三个脚注的内容是:“参见阿达马1898年论文第71页(第59节)。阿达马说,他的结果暗示,太阳系稳定性的问题,'似乎不再有任何意义'。我不同意。证明一个预测问题不能基于任何一种理论以及对初始条件的任何精确测量来进行计算,并不能使问题本身成为无意义的。毋宁说,它证明此问题是不可解的。不可解的问题并不是无意义的问题。对其不可解性的发现也是对问题本身的一种阐明,有如对其解的发现一般。” \left[ 28 \right]
波普尔确认,阿达马的结果否定了强决定论,但对弱决定论并不构成损害:“然而,如我所见,阿达马并没有拒斥我上面所定义的较弱的'科学'决定论的教条。” \left[ 29 \right] 理由是,对于确定性系统,对于任意给定的时间,假定一定的对初始条件的测量精度,质点的状态一定程度上仍然是可预测的。这取决于预测任务所要求的时间有多长,以及对于预测所要求的精度。这种理解完全正确,但是表达得仍然不够明确。对于任一非线性动力学系统,即使其中可以出现高度不稳定的浑沌行为,只要预测任务设定的预测时间跨度非常小,比如以离散系统为例,已经n=0阶段的初始条件和动力学规则,由此预测n=1,n=2,n=3等等阶段系统的状态,通常是完全可行的,甚至可以以非常高的精度做到。在这些邻近区域内,这个系统仍然可视为完全决定论的,说它是弱决定论也可以,甚至说成强决定论也是可以的。数学上,动力系统就是确定性系统,英文是一个词,也叫决定论系统。问题的关键不在这。深刻的问题在于:"谁能根据什么划分出可行的预测与不可行的预测?"对于上述离散系统而言,谁能明确说出当n大于k时以后的结果不再有意义?这样的判断是不可能根据方程(数学模型)本身先验地判定的,一个数学模型可以对应无穷多种可能的现实物理过程(如logistic方程既可以描写虫口演化,也可以描写经济过程,即使描写虫口问题,其中的中"虫口"也可以作多种解释,实际上大量"物种"都可以包括在内),其中的物理量可作多种解释,时间的单位原则上也是可以任意约定的。但是,对于任何这样的系统,原则上都存在一个临界时间 T=\frac{M}{(λ-L)} 。其中 \lambda 为李雅普诺夫指数, L 为利普希兹常数。在 T 之内,预测是可接受的,在 T 之外预测是不可接受的。但T究竟取多大的值,除了与系统本身的性质(如李雅普诺夫指数和利普希兹常数)有关外还与常数 M 的取值有关,而M是与物理要求有关的。
波普尔在这一节的最后一句话为:“我们不能预测的是,系统在所有时间瞬间(all instants of time)的行为。”这是一句十分有启发性的描述,波普尔在此话后加了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长的脚注:“在这一阐述中,'对于所有的'和'对于任意给定的"之间的区别,与哥德尔发现的事实有某种类似性:虽然我们能够对任意给定的算术命题构造一个形式化理论,在其中此命题是可判定的,但是我们不能构造一种形式化理论,使得所有的算术命题是可判定的。记住这种类似性,我们就可以说,阿达马的问题(此问题问,其初始条件以任意有穷精度给定的一个多体系统,是否会处于某种特定的状态)是一个物理上不可判定的(Physically Undecidable)问题。”福特(J.Ford)和斯美尔(S.Smale)讨论过浑沌系统的不可判定问题,也认为与哥德尔定理的关,但都未给出具体的刻画。另外,1987年C.Agne's和M.Rasetti合写一论文“不可判定性与浑沌”,用算法复杂性的概念讨论了乌拉姆映射,结论是“不可判定性是导致浑沌的深层机制”。如果这个结论站得住脚的话,波普尔则又有了一个先见之明。如果注意波普尔1950年论非决定论的文章,波普尔设法把非决定论与逻辑学的新进展以及算法信息论的一贯套路,还是非常清晰的。这再一次印证,波普尔是个不轻易放弃自己观点的人。
波普尔说:“从历史的观点看,非决定论物理学的涌现是完全可理解的。长期以来,物理学家信仰决定论的形而上学。因为逻辑境状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从原子的力学模型中导出有统计学效应的光谱,其各种尝试的失败必定产生决定论的危机。今天我们清楚地看到,这种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不可能从原子的非统计的(力学)模型中导出统计定律。决定论的大厦坍塌了,主要是因为概率陈述被表述成为形式上单称的陈述。在决定论的废墟上,非决定论崛起了,得到了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的支持。但是,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它之崛起同样误解了形式上单称概率陈述(Formally Singular Probability Statements)的含义。 \left[ 30 \right]虽然我不认为量子力学是物理学的最终结论,但我却恰好相信它的非决定论在根本上是正确的。我认为,甚至经典物理学原则上也是非决定论的。 \left[ 31 \right] ”实际上,波普尔的见解远远领先于他提出此观点时的科学界,20世纪80年代初在经典力学的框架内大批关于浑沌、分形等非线性科学的研究成就的涌现,才使人们意识到经典力学也是非决定论的。然而波普尔得出此结论时,还没有非线性动力学的大规模研究。郝柏林说:"对于同一个自然界,物理学中有决定性和概率性两种描述。在牛顿创立古典力学之后250年间,直至20世纪20年代为止,决定论长期处主导地位,基于概率论的统计描述,原则上只能视为不得已情况下采用的辅助手段而已。 \left[ 32 \right] "
在反驳“科学”决定论时,波普尔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它为“Accountability”,译为“可测算性”。可测算性是与“科学”决定论相一致的一种要求。波普尔说:“换言之,我们的理论必须能够测算预测中的不精确性:给定预测中我们所要求的精确度,用此理论就能够使我们计算出来,在为我们足以提供所要求之精确度的预测时,初始条件(应当具有)的精确度。我称这项要求为‘可测算原则’(Principle of Accountability)。必须把这一条原则体现在‘科学’决定论的定义中。”此叙述有两个要点。第一,可测算性是从后向前推的一种要求,其方向与预测过程正好相反。即如果要达到什么样的预测精度,初始条件应当如何。能够明确地给出此种条件,则可视为满足了可测算性原则。“科学”决定论如果成立,则必须满足此原则。实际问题中,某些预测任务是“可测算的”,即满足可测算原则,而有些预测任务不是可测算的。只要没有解决牛顿动力学中一般的n体问题的真正希望,就毫无理由相信牛顿动力学是可测算的,即使是弱意义上的“可测算性”。 而且,当我们继续考虑强意义上的可测算性时,我们发现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牛顿动力学是不可测算的。 \left[ 33 \right] “因此,任何令人满意的'科学'决定论之定义,都必须基于可测算性原则,即我们能够根据我们的预测任务(当然,还要加上我们的理论),计算出所要求的初始条件的精确度。
” \left[ 34 \right] 正是在这一句之后,波普尔加了一个脚注:“迪昂提出了类似的原则,但是那是在不同的语境中(不是讨论决定论),并且有着不同的着眼点。”波普尔提到的迪昂的话是指这样一段极为重要的论述:要对物理学家有用,还必须证明,当第一个命题只是近似地为真时,第二个命题依然近似地精确。甚至这还不够。必须界定这两个近似的范围;当测量数据的方法的精确程度已知时,必须固定在结果中能够导致的误差的限度;当我们希望获悉在确定的近似度内的结果时,必须确定能够被认可的数据的概差(Probably Error)。 \left[ 35 \right] 迪昂当时讨论的主要是数学推理与物理学过程对照时可能出现的问题,他发现有些数学推理结果是无法"翻译"为物理结论的。可翻译的条件是什么?迪昂确实指出了,这就是与波普尔提出的可测算性相类似的一种条件。这种条件,在今天非线性动力学已经比较发达的时候,可以用某种“稳定性条件”来更明白地表述。也就是说,迪昂、波普尔讲的科学预测中要求的条件,相当于非线性动力学中讲的结构稳定性和运动稳定性的结合。前者对应于安德罗诺夫和庞特里亚金的结构稳定性、鲁棒性,后者大致对应于李雅普诺夫稳定性。在动力学中,这些稳定性都有明确的数学定义和物理含义。
至此,波普尔利用非线性动力学的进展已经系统地证明:在相当多的情形之下,经典力学无法满足可测算性原则;“科学”决定论是一种幻想;首先是经典物理学而非量子力学瓦解了决定论的信条;引用自然科学和数学的结果为任何一种决定论辩护,均是有问题的。
这也就是波普尔批判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决定论的关键根基所在,“科学”决定论的神话的破产促使一切依赖于其为基础的理论土崩瓦解,化为它原本的“纯信仰”的模样。形而上学决定论只断言世界上的事件都是确定性的、不可改变的,或者说预先决定好了的,但不声称有任何人知道它们或者可以用某种手段做出预测。这种形而上学决定论是不可检验的。实际上它是一种非常“弱”的断言,一种相信弥赛亚终会到来的神话传说,既被宗教决定论所蕴涵也被“科学”决定论所蕴涵,它是各种决定论的共同点,也是构成它们所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历史唯物主义就如同这“科学”决定论般小心翼翼又突出狂言地“预言”未来世界的模样,并建立了一个假想的模型,并将实在的客体强制绑定于其理论上,然而却随着人类对世界的不断认知而解体崩溃。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样依赖于所谓现实例子来试图建构它们理论本身的合理性,我们经常在各种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中看到用实际例子说明其理论的情况;更加精确地说,“最佳说明推理(Inference to Bset Explanation)”成为建构其性质的方式,“最佳说明推理”基本思想是:如果一个假说能足够好地说明各种现象,那么我们就能推断该假说是正确的。莱普林(Jarret Leplin)认为批判最佳说明推理的主要四种思路的论证代表为蒯因(W.V.Quine)、范·弗拉森(Bas Van Fraassen)、劳丹(Larry Laudan)、法恩(Arthur Fine)。
蒯因认为,对于任何一个说明的理论,都能建构出与之相冲突的另一个理论,该理论同样能满足所有的相关证据。这就是经验等价性论题(EE),由于从它可推断出非充分决定性论题(UD),没有一个重要的证据能排除所有其他竞争理论,而支持任何一个理论。因此,理论的选择最多只能是实用的选择,而且,理论信念的正确与否在原则上得不到保证。蒯因自己把EE看成是基于勒文海姆-斯克伦定理(Löwenheim-Skolem Theorem)和把科学限定为广延语言的一种逻辑观点。
范·弗拉森则用说明的实用主义分析来拒绝假说推理;理论可以提供说明,但需要有确定兴趣和意图的语境。语境的相对性使得说明关系的不对称性并不是基本的,不是被理论所规定的。于是,语境是在实用的意义上加以确定的。一个语境的变化能够把说明项和被说明项的地位颠倒过来,因此不存在“什么是说明”的基本事实。一个理论的说明成就,不可能成为证明理论信念正确与否的根据,因为可能断言,这些成就只不过是在实用意义上作出的选择,而不是提供证据的理由。
劳丹的思路是一种历史论证;劳丹认为我们从曾经同样受到有效支持的就理论的失败,可以推断出任何一个理论,不管它如何有效地受到证据的支持,都有可能是错误的。更一般地说,与当先的科学相冲突的理论在达到一个有效的测量范围内且能够获得任何一种形式的经验成功,并将这种成功印证为是相信一个理论的正当理由。他断定,接受理论的标准没有能力支撑实在论。也就是说,理论都是具有生命周期的,现时的成功并不能保证超越时间的真理性。劳丹论证说,说明的优点不可能证明理论信念的正确性,因为具有这些优点的理论,会被以后的发展所推翻,从历史的观点看,说明的成功不等于它的真理性的标志。
法恩的论证则把在最佳说明推理意义上为实在论辩护的企图,理解为是一个恶性循环。法恩区分出在科学内部进行推理的第一个层次和关于科学的哲学推理的第二个层次,在第一个层次上,根据相关的经验证据,提出和评价关于特殊的物理学理论和假说,在第二个层次上,提出和评价关于科学结论的认识论地位(Epistemic Status)的一般理论。实在论和工具主义是在第二个层次上的哲学理论。在每一个层次上运用的推理都可以得到评价,实在论是属于元科学的论题并且对通常用于辩护或拒绝的推理的评价是元哲学的。
法恩认为,通过概述历史论证就会发现过去常为接受特定的物理学理论提供依据的假说推理在第一个层次上是可以的,我们不应该把对物理学的信任建立在关于特殊观察和实验的说明策略的基础之上。假说推理作为一种推理模式在第一个层次上是可疑的,也就是说它得出的结论没有得到充分的证实,在第二个层次上去运用它则会得到关于在第一个层次上的结论的认识论地位是不可靠的。因此,法恩抱怨说,典型的实在论论证,以这种循环方式强调实在论说明的优势;实在论说明的一切更多的是以循环论证来论处而不是涉及它的可信度。 \left[ 36 \right]
然而本章重点讲述南希·卡特赖特的理论,由于国外早已展开对她的理论的研究,而在国内,对她却无人问津,因此基础的介绍是必要的。
南希·卡特赖特(Nancy Cartwright)教授被认为是当前学术界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哲学家之一,她是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哲学教授,英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麦克阿瑟基金获得者。
卡特赖特出生于1943年,并于1966年毕业于匹兹堡大学数学系,获金带学士。她于1971年在伊利诺斯大学完成博士论文《关于量子力学中的混合概念的哲学分析》,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斯克姆斯(BrianSkyrms)也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主要研究方向是逻辑学、科学和经济学哲学,他是还在世的美国国家科学院(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院士中的仅有两位哲学家中的一位。
从1971到1973年,卡特赖特执教于马里兰大学哲学系,任助理教授。1973年,卡特赖特前往斯坦福大学哲学系,开始她学术生涯的最重要的一个时期。在那里,她和她的第一任丈夫哈金(Ian Hacking)、杜普雷(John Dupre)、加里森(Peter Galison)等人一起被称为科学哲学的“斯坦福学派”。“斯坦福学派”持有一种实验主义,或者可以说是反理论主义的视角,他们并不把数理物理学太当真,而是强调实验的实践活动和现实物理学的不均一性。哈金、加里森等人更是认为近来影响颇大的新实验主义的代表人物。卡特赖特于1991年离开了斯坦福大学并前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于哲学、逻辑和科学方法系。
1983年,卡特赖特的出版了她的第一部著作《物理定律是如何说谎的》,在书中卡特赖特倡导一种介于科学实在论和经验主义的反实在论之间的中间立场—实体实在论,又称实验实在论。卡特赖特把实在论只限定在理论实体的范围之内,而避开对理论定律的实在论解释。卡特赖特认为物理学的理论实体和它们之间的因果联系是真实的,但是那些被认为来描述其行为特征的定律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她认为:“基础定律(Fundamental Law)的巨大说明力并不能论证它们的真实。实际上我们用以说明的方式只能论证它们的错误。因为我们总是通过其余情况均同条件定律、原因组合的方式、改进基础定律的近似来说明。”本书的思路一反常态,实现了从关于物理学抽象观点至现实物理学的具体细节的伟大转型,此书聚焦于科学如何运作,并发出了非常必要、令人警醒且印象深刻的警告。
1989年,卡特赖特出版了她的第二部著作《自然的能力及其测量》。在书中,卡特赖特着手构造一种以真实能力(Capacity)为基础的反休谟经验论。本书的内容简单地说来就是先颠覆休谟对因果关系的解释,然后引入能力概念,把基础定律理解为关于能力的描述。在卡特赖特兰看来,引入能力概念不是为了提供因果性研究所需的模化力,相反,能力是真实的,它是构造世界大厦的最基本的砖头,关于能力的知识是科学的最为基本的知识。从前被认为处于科学说明核心位置的定律不再是说明的源头,它们是被说明的对象。物理学的基础定律也不再是关于休漠主义的规则的定律,它们是关于能力或与能力有关的陈述。
1999年,卡特赖特出版了《斑杂的世界——科学边界的研究》。在书中,卡特赖特发展了一种以能力为基础的多元经验论,提出要反对一元论的基础主义(Anti-Funamentalism)。卡特赖特说,在《物理定律是如何说谎的》中,她错判了敌人,她要反对的不是实在论,而是基础主义。基础定律或许是真实的,但是它们绝不是普遍的,因为它们只在模型中或类似于模型的地方为真,这一点可以从科学实践中观察到。因此,科学知识不是统一的,不具有金字塔般的逻辑结构,相反,科学知识是以拼凑的方式组合在一起。相应地,我们的世界不是一个有着良好秩序、系统的世界,它正如我们的日常感觉经验,是一个斑驳、杂乱的世界。
查尔默斯(A. F. Chalmers)在有着广泛影响的《科学究竟是什么》第三版(1998)的序言中写到为什么要对前一版进行大范围重写时说:“在过去的10年或20年中,科学哲学有了如此重大的发展,以致任何一本入门性的教科书都需要对此予以说明······最近的研究,尤其是南希·卡特赖特的研究,把有关科学中出现的定律的本质问题提到了显著的地位,因此,在新的这一版专门开辟出新的一章讨论这一话题,以便与有关科学的实在论解释和反实在论解释的争论齐头并进。
卡特赖特确实是后实证主义时代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哲学家之一,她所倡导的关注于科学真实特征的研究、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中间立场的寻求、定律本质的讨论以及反基础主义等都为科学哲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正如吉宾斯(Peter Gibbins)所说的那样:“卡特赖特的成就不是说她所讲的每个议题都是正确的,而是说她的工作可以来定义接下来几年的研究领域,这对于任何一位哲学家来说,我们已不能再要求更多的了。”哲学家法恩(Arthur Fine)等人也认为,我们可以质疑她的哲学观点,“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卡特赖特总是在制造新的哲学,而我们的学科正以她的方式发展着”。
让我们回到话题,该论证形式的拥护者可能在怎么样算是足够好或者需要说明多少种现象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但他们都认为,解释力虽有真理并非一致却引导我们通向真理。最有力的论证在迪昂的《物理学理论的目的与结构》并由此范·弗拉森(Bas Van Fraassen)在他的《科学的形象》(The Scientific Image)中用一种特别指出的方式对其质疑地重新表述为:说明的关系倾向于保证“如果X说明了Y,并且Y是正确的,那么X也应该是正确的”,这种质疑当且仅当因果说明的情况下有答案,假定我们描述了导致某现象发生的具体因果过程,那种说明也只有在被描述过程实际发生时才能成功。从我们认为因果说明是可接受的这一点上讲,我们必须相信所描述的原因。
卡特赖特试图对科学知识进行重构的动力来自于迪昂(Pierre Duhem)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定律的说明和表征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说明的角度来说,定律可以分为基础定律和现象学定律(Phenomenological Law)。传统的观点认为基础定律不仅具有表征功能,而且还有说明功能。现象学定律则只有表征功能,它需要基础定律来说明。实在论者的观点认为,通过最佳说明推理,基础定律被认为是普遍真实的,而现象学定律可以从基础定律演绎得到因此也为真。与这种观点联系在一起的是覆盖律(Covering Law)的说明模型。卡特赖特追随迪昂的看法,认为现象学定律的真实可以通过归纳得到,但是,我们并不能通过最佳说明推理的方式来论证基础定律的真实。卡特赖特其实并不反对基础定律的真实性,她反的是用以说明基础定律真实的最佳说明推理方式。在她看来,基础定律的巨大说明力并不能论证基础定律的普遍真实,如果我们一定要坚持说明力和真实性有内在联系的话,那么基础定律的说明力只能论证它们是错误的定律。也就是说,在定律的说明和表征之间存在一种紧张关系,用卡特赖特的话来说,就是在定律的“说明力”和“真实性”之间存在一种交换的关系真实的定律不能用于说明而用于说明的定律通常是错误的定律。
卡特赖特引例道,考虑克鲁克斯(William Crookes)1853年发明的辐射计,它是一个小风车,其叶片一侧为黑色,另一侧为白色,装入抽空的玻璃球中。当光照到辐射计时,叶片旋转。最初人们认为是光的压力使得叶片旋转,不久就发现光的压力并没有那么大。于是认为,旋转归因于抽空的玻璃中残留气体分子的运动。克鲁克斯已经尽力在他的辐射计中排开气体分子,创造真空环境,显然,如果我们接受这个被认可的说明,那么我们则可以推断到其真空是不完全的,该说明需要球中有分子存在。
关于分子的运动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假说,第一种假说是叶片被反弹挑起的分子的压力所推动,在黑色一侧反弹挑起的分子比白色一侧的分子具有更大的能量。但在1879年,麦克斯韦运用气体的动理学理论说明,气体中的力在各个方向都是相同的,因此不能推动叶片。然而,气体稍微加热会产生切向应力,这使得气体沿表面滑动。当气体沿着边缘流动时,它推动着叶片随之运动。在麦克斯韦的传记中,埃弗雷特非常赞同麦克斯韦的观点,认为要比已经广泛接受的另外一种观点更具优越性。 \left[ 37 \right] 他对麦克斯韦因果理论的信任也反映在他的本体论观点中。埃弗雷特的反对者认为,切向应力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埃弗雷特相信,如果制造一个足够大的辐射计,他就能测量叶片边缘气体的流动。
人们能够拒绝理论定律而不拒绝理论实体。在麦克斯韦支持者和辐射计切向应力的例子中,范·弗拉森的问题得到了回答:我们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因果说明,因此有很好的理由去“相信”问题中的实体、过程和属性。
因果推理为我们相信理论实体提供了“很好”的依据,我们也可以从结果的精细结构上准确地反推出原因必须具有的导致结果发生的“特征”。卡特赖特认为没有导致最佳说明的推理,只有导致最可能原因的推理(Inference to Most Likely Cause)
范·弗拉森问:“得出原因的推理,归根到底不就是‘只能’得出描述事物一般特性的命题为真的推理吗?” \left[ 38 \right] 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当接受因果说明后,我们所研究的这个命题就是高度详细的因果原则和具体的现象学定律,而不是基本理论的抽象方程,特别是在目前的状况下。
麦克斯韦说,叶片是被边缘滑动的气体所拖动,而不是被光压力或者叶片表面气体的法向力所推动。
麦克斯韦运用了一个现象学定律——在这里也是一个因果原则:
(气体沿叶片表面滑动的)速度和相应的切向应力受叶片表面温度的不定稳定性所影响,这种不稳定性产生一种力,使得气体沿叶片表面从较冷的地方滑向较热的地方。 \left[ 39 \right]
现象学定律“当热流稳定时,这些力(作用在各个方向上所有的力)是平衡的。 \left[ 40 \right] ”对叶片不是被与表面垂直压力所推动的观点至关重要。
麦克斯韦在得出关于叶片转动的因果说明中,使用了玻尔兹曼方程(Boltzmann's Equation) \frac{df_{1}}{dt}+\xi_{1}\frac{df_{1}}{dx}+\eta_{1}\frac{df_{1}}{dy}+\zeta_{1}\frac{df_{1}}{dz}+X\frac{df_{1}}{d\xi_{1}}+Y\frac{df_{1}}{d\eta_{1}}+\int\int\int d\xi_{2}d\eta_{2}d\zeta_{2}\int bdb\int d\phi V(f_{1}f_{2}-f_{1}^{'}f_{2}^{'})=0\tag{1}
和一般连续性方程(Equation of Continu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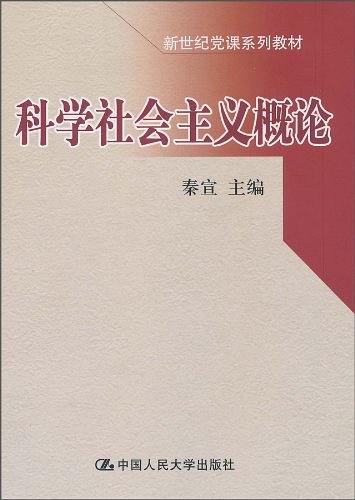
\frac{\partial}{\partial t}[Q\rho]+\frac{d}{dx}[Q(u+\xi-U)]+\frac{d}{dy}[Q(v+\eta-V)]+\frac{d}{dz}[Q(w+\zeta-W)]=\rho \frac{\delta}{\delta t}Q\tag{2}
这些是一般、抽象的方程式,它们不针对任何特定环境下的发生的任何特定情况。在行为陈诉中,一般性的应用更广,但特定性的应用更真实。
卡特赖特认为,解释力不是真理的保障。在因果说明中,真理对于说明的成功是必要的,但它仅仅是低水平因果原则和具体现象学定律的真理。有两种说明模型“能”显示抽象定律真实性,但这两者都有严重的缺陷。物理学的说明涉及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第一种即为在说明对象时陈述其原因并尽可能详细地阐述现象所产生的原因,第二种即为使现象符合尽可能复杂或有力的理论框架。因果说明使用阐述具体情况下发生事件的非常特殊的现象学定律,而理论定律则是描述非特殊情况的完全抽象的公式。标准的覆盖律说明(Covering-Law Account)试图使两种说明合二为一。但卡特赖特认为,定律在两种情况下的功能不同,它们对真理的陈述也不同。这种区别是超越哲学的,在科学实践中也能发现这一点。因果说明则不同,不同的假说若其中一个被采纳,其它的假说就必然被拒绝。理论处理则不然,无论对错都要给出因果说明。统一定律的存在必须依靠足够的将不同学科的知识进行连接的桥介规律(Bridge Laws),然而卡特赖特怀疑统一定律的存在,并相信没有足够的桥介规律使得统一定律存在。
卡特赖特引例范戴克(Milton Van Dyke)的《流动力学中的摄动方法》(Perturbation Methods in Fluid Mechanics)中的引言:
这个基本的非线性,使得在流体力学的任何分支中都缺乏精确解······即使一个常微分方程必须进行数值积分时,也需要宽容地认为是“精确的”。莱特希尔(Lighthill)给出了无黏性可压缩流体的解的可算详尽的列表。 \left[ 41 \right]
范戴克列出了7个例子,然后继续写道:
另外,自施利希廷(Schlichting)依赖,人们能够为不可压缩黏性流体构造一个局部列表。 \left[ 42 \right]
第二个列表又给出了7个例子。但是,即使是这14个例子仍然无法为基本理论和实际环境之间提高一个严格的纽带。范戴克总结道:
这些自相似的流是典型的,它们包含理想化的几何结构,远不同于有实际重要性的多数形式。为了进一步处理,通常情况下必须近似。 \left[ 43 \right]
实在论哲学家认为近似的处理方法在原则上毫无问题,偏离“真正的解答”的怨言仅仅是为此详细作答是不必要的。近似处理方法的广泛使用,使得它自身的存在就是对抽象理论的普遍性的全盘否定,为了最终达到对现象的精确描述,推导步骤远离了“启用定律、修正定律和改进定律的严格结果”,这种近似的处理方法将定律应用于实在,证明了定律的谬误而非正确。
卡特赖特支持一种影像的说法,这种影像即为“仅仅有某个事物的形态或者外观而不拥有其实质或者固有属性的东西”。在影像说法中,说明一个现象就是构建一个使现象拟合于理论的模型。理论的基本定律对于模型中的客体是正确的,而且它们被用于导出这些客体如何行动的特定描述。但是模型中的客体仅仅有“事物的形态或者外观”,在一种很强的意义上,没有“实质或固有属性”。
覆盖律说法认为,原则上每一种现象都有一个“正确的”说明,影响说法否定这一点。说明性模型的成功取决于导出定律(Derived Laws)是否能很好地近似于现象学定律和对于模型客体都是正确的特定的因果原则,已经有更多的现象学定律,而且它们能够以更好的、不同的方式近似。没有任何单个说明是正确的。更进一步地说,理论说明是冗余的。这是物理学说明的一个特有特征。演绎-律则(Deductive-Nomological,简称D-N)说明对这一特征不以为然。
卡特赖特的“影像”说法坚定地认为:一般情况下,有准备的描述和未准备的描述不能相提并论,仅仅是有准备的描述才能服从基本定律。关于基本定律真实性的论点则坚持基本定律不支配是在中的客体,它们只支配模型中的客体。
接下来,我们将叙述有关量子力学中的指数式衰变定律的推导,默茨巴赫(Eugen Merzbacher)概括说:“事实就是,我们在放射性过程中有如此多经验支持的指数式衰变定律,不是量子力学的严格结果,而是稍微精密的近似结果。” \left[ 44 \right]
指数式衰变定律是一个简单的、概率论上绝妙的定律,但它却不能在量子力学中被精确地推导,该指数定理只能通过作一些重要的近似才能导出。严格解与近似解之间的差别对于许多现实的时间周期而言是不可观测的。数据和任何简单化的合理标准一起代表了指数定律的真理,但是这种定律不能严格地被导出。
有两种指数式衰变的标准处理方法:斯科普夫-维格纳方法(Weisskopf-Wigner Treatment) \left[ 45 \right] 和马尔科夫方法(Markov Treatment)。我们先看马尔科夫方法,我们思考一个与储存器(Reservoir)系统是一个激发的原子核储存器电磁场,主方程变成泡利变率方程(Pauil Rate Equation),它是再次激发时对指数定理的模拟:
泡利方程:
\frac{\partial S_{j}}{\partial t}=-\Gamma_{j} S_{j}+\sum_{k\ne j}^{}{\omega_{jk}S_{k}}\\
(其中, S_{j} 是第 j 种状态的占有概率, \Gamma_{j} 是寿命的倒数, \omega_{jk} 是从 k 态到 j 态的跃迁概率)
开始于对复合体系——系统和储存器——状态 x 的标准二阶微扰(Second-Order Perturbation)扩展,在相互作用绘景中形如:
\chi(t)=\chi(t_{0})+\frac{1}{iℏ}\int_{0}^{t}[V(t^{'}-t_{0},\chi(t_{0})]dt^{'}+(\frac{1}{iℏ})^{2}\int_{0}^{t}dt^{'}\int_{0}^{t^{'}}dt^{''}[V(t^{'}-t_{0}),[V(t^{''}-t_{0}),\chi(t_{0})]]\\
系统和存储器在t时的状态通过这个方程右边的积分取决于它全部的过去的一切记录。马尔科夫的近似观点为导出系统状态的一个偏微分方程并使得这种状态在某个时间点的改变仅依赖于其时间点的事实而非它过去的一切记录。由于存储器的相关性只对我们所观察的该系统周期相比的一个短周期有意义,将只包含储存器相关性的时间积分扩展到无穷大;由于对系统考虑的时间周期小于其寿命,令 t-t_{0}\rightarrow0 ,得出带有所期待特征的主方程。
我们注意到,就比现在更早先的时刻,主方程的r.h.s不再包含时间积分S(t')[S是单独的系统状态]所以将来实际上被现在所决定。我们已经假设,储存器相关性时可在某一时间标度上为零,在这个时间标度中,系统失去了有限能量······人们有时引用马尔科夫近似作粗粒平均(Coarse-Grained Averaging)。 \left[ 46 \right]
马尔科夫近似导致了主方程,原子与电磁场相互作用,主方程特殊化后成为泡利方程,泡利方程预言原子的指数式衰变。没有马尔科夫近似,衰变至多是近指数式衰变。
韦斯科普夫-维格纳方法使用精确的薛定谔方程来处理振幅,但要假设只在激发态和退激发态之间存在着显著耦合:
\frac{dc_{e}}{dt}=\sum_{f}^{}{}g^{2}_{ef}\int_{0}^{t}dt^{'}exp[i(\omega_{eg}-\omega_{f})(t-t^{'})]c_{e}(t^{'})\\
[其中 \omega_{eg} 是 \frac{(E_{e}-E_{g})}{iℏ} , E_{g} 是退激发态的能量, \omega_{f} 是场中第 f 种模的频率, g_{ef} 是激发态与第 f 种模之间的耦合常量, c_{e} 是激发态中的振幅,没有出现光子。]
第一级近似表面,用于退激发原子的场模形成了一个近连续统,因此遍于 f 的和将被一个积分所代替,即:
\frac{dc_{e}}{dt}=\int_{-\infty}^{+ \infty}-g^{2}(\omega)D(\omega)d\omega\int_{a}^{t}dt^{'}exp[i(\omega_{eg}-\omega)(t-t^{'})]c_{e}(t^{'})\\
选择随着 \omega 满变的项作 \omega 积分,给出一个含 t 的 \delta 函数:

\begin{align}\frac{dc_{e}}{dt}&=g^{2}(\omega_{eg})D(\omega_{eg})\int_{0}^{t}dt^{'}c_{e}(t^{'})\times\int_{-\infty}^{+\infty}exp[i(\omega_{eg}-\omega)(t-t^{'})]d\omega\\&=g^{2}(\omega_{eg})D(\omega_{eg})π\int_{0}^{t}dt^{'}c_{e}(t^{'})\delta(t-t^{'})\end{align}\\
或者设 \gamma=2πg^{2}(\omega_{eg})D(\omega_{eg})\\
\frac{dc_{e}}{dt}=-\frac{\gamma}{2}c_{e}(t)\\
最后: c_{e}(t)=exp(\frac{-\gamma}{2t})\\
但是,这种推导就错失了兰姆移位(Lamb Shift)——1947年发现的能级小位移(Displacement)。它将以相反的顺序作积分。在这个例子中,与指数级的快速振荡相对照, c_{e}(t) 本身是慢变的,因此它能从 t^{'} 积分中分解出来,积分的上限被扩展到无穷大。 t^{'} 极限的扩展与基本原理类似于马尔科夫近似。
我们得到: \begin{align}\frac{dc_{e}}{dt}&=\int_{-\infty}^{+\infty}g^{2}(\omega)D(\omega)c_{e}(t)exp[i(\omega_{eg}-\omega)t]d\omega\times\int_{0}^{+\infty}exp[-i(\omega_{eg}-\omega)t^{'}]dt^{'}\\&=\int_{-\infty}^{+\infty}g^{2}(\omega)D(\omega)c_{e}(t)exp[i(\omega_{eg}-\omega)t]d\omega\times\ \left\{ π\delta(\omega_{eg}-\omega)+iP(\frac{1}{\omega_{eg}-\omega})\right\}\end{align}
或者设 \gamma=2πg^{2}(\omega_{eg})D(\omega_{eg})\\
并且 \Delta\omega\equiv\int_{-\infty}^{+\infty}\frac{g^{2}(\omega)D(\omega)}{\omega_{eg}-\omega}d\omega\\
(P(x)=x的主部)\\
\frac{dc_{e}}{dt}=-(\frac{\gamma}{2}+i\Delta\omega)c_{e}(t)\\
这里的 \Delta\omega 是兰姆移位。第二种方法如今通常被称为“韦斯科普夫-维格纳”方法,除谱线增宽 \gamma 之外还得到兰姆移位。
求解拉普拉斯变换(Laplace Transform),变为:
c_{e}(o)\equiv\int_{0}^{+\infty}exp(-ot)c_{e}(t)dt=\frac{1}{o+i\sum_{f}^{}{(\frac{g^{2}_{ef}}{\omega_{eg}-\omega_{f}+io})}}\\
那么
c_{e}(t)=\frac{1}{2πi}\int_{\in-i\infty}^{\in+i\infty}exp(ot)c_{e}(o)do\\
解方程方法即被积函数必须定义在第一和第二个黎曼片(Riemann Sheets)上。该方法可在戈德伯格(Goldberger)和沃森(Watson)的一本有关碰撞理论的书籍上找到,因内容过多,本文不作详细阐述(本文提供该书籍的下载) \left[ 47 \right] 。
一个简单的极 \Delta\varepsilon 使得
\frac{i}{ℏ\Delta\varepsilon}\equiv\frac {\gamma}{2}+i\Delta\omega=\lim_{o \rightarrow 0^{+}}{\sum_{f}^{}{\frac{g_{ef}}{\omega_{eg}-\omega_{f}+io}}}\\
给出指数:
c_{e}(t)=exp[-(\frac{\gamma}{2}+i\Delta\omega)t]\\
至此,卡特赖特并不认为这是一个严格解,在这一系列的推导中,正如扭歪了黎曼片上的等值线一样,没有考虑的其他极彼此交叉;也忽略了围绕最终的等值线本身的积分。戈德伯格和沃森计算这个最重的积分贡献了与 \frac{ℏ^{\frac{3}{2}}}{t^{\frac{3}{2}}E_{e}} 成正比的一项。卡特赖特批判性地说,他们指望着其他极只添加可忽略的影响,以至于精确解十分接近于我们所寻求的指数定律。近似永远是近似,如果我们要导出一个纯粹的指数定律,我们最好将我们的近似作为对初始薛定谔方程的改进,而不是偏离真理。
特别注意的是,卡特赖特选取了一个经典的例子来作为他阐述观点“正确的近似程序不被事实所决定”而举例的两个例子前的铺垫。卡特赖特指出20世纪70年代的大量衰变定律的实验检验被詹尼斯(E.T.Jaynes)的新经典理论所推动,但反过来,实验检验却只关心衰变率依赖于初始状态的占有水平。温特(Rolf Winter) \left[ 48 \right]一直在测试 ^{56}Mn 的衰变直到34个半衰期;巴特(D.K.Butt)和威尔逊(A.R.Wilson)也实验了氡的 \alpha 衰变接近40个半衰期 \left[ 49 \right] 。但是,正如温特所谈到的:“对于 ^{56}Mn 的放射性衰变而言,非指数效应在大概200个半衰期之前不会发生”在这个例子中,和用所有平常的放射性衰变物质一样,在指数范围结束之前很长时间内应该怪查不到什么东西。”派斯(A.Pais)评价说:“使这种偏差起作用的实验条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被发现。 \left[ 50 \right] ”差异出现之前的时间太长了。
卡特赖特说,相同的程序被相同的事实陈述证明是正确的,但因为我们使用的时间不同而得出不同结果:相同的近似运用于推导过程中的不同点得出两个不同的不相容的预言,卡特赖特认为这在整个物理学中都是典型的推导,她用两个相关联的现象加以阐述这一事实:单个二能级原子激发态的兰姆移位和原子基态下的兰姆移位。
总之,卡特赖特在一系列的讨论后得出结论,基本定律是无法决定何种现象学定律为真,基本定律在实践说明上的成功就证明了这种论据,在应用物理学和工程学的各领域有大量的现象学定律,它们对现实情况中的事物给出了高度精确、详细的描述。在一个说明性处理中,这些只能通过一系列近似和修正从基本定律中导出。修正几乎总是改进了基本定律的规定;而且甚至在基本定律保持其初始形式的地方,推导的步骤经常也不被事实所规定。这给D-N模型、一般-特殊说明以及更好的基本定律观点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当描述现实世界时,现象学定律赢了。自然界不会可以准备情况去符合我们所渴望的那种数学理论。我们既要构建理论又要构建它们所适用的对象,但是一般不会马上直接得到所有事实。基本定律不支配实在。基本定律所支配的仅仅是实在的表象(Appearance of Reality)。
基于所谓“历史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同样面临这样的困惑,自从马克思去世后,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争论不停,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被理解为多种多样的历史哲学思想,进而分裂了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产生出了各色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知名的就有罗莎·卢森堡、弗拉基米尔·列宁、卡尔·考茨基、爱德华·伯恩斯坦等一系列人物。那么,真相如何?是否存在一个明晰的历史定律?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决定论的时代已经过去,科学实在论被不断地质疑,最佳说明推理和D-N模型的正确性遭到越来越多的反对声音,因果律与关联规律的分野模糊不清,关于概率的辛普森悖论而来的质疑与休谟主义的不断反击重塑了整个理论。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及其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将在下一部分中详细阐述,同时也引入新的来自科学哲学的观点去看待这些被批判的理论并且还将深入探讨卡特赖特的理论,批判之后就是理论的重新建构——范式转换。
待续。
注释:
文件下载:
Download The File "On Stresses in Rarified Gases Arising from Inequalities of Temperature"
Download The File "Collision The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