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
现象族群(包括化学的、电子的、量子的)被开发并加以利用以后,就自然而然地引起了技术的聚集。比如,与电以及电现象有关的设备和方法(例如,电容器、感应器、晶体管、运算放大器)会自然而然地聚集到电学中来。它们和电的介质结合之后,彼此就可以方便地“对话”。光以及与光传播相关的元素(例如,激光、光纤、光学放大器、光学传感器等)聚集成光电子学。它们互相传递光量子和光能单位,以服务于不同的操作。这样的聚集构成了我在第2章所谈到的复数技术。现在我还想就这个问题再展开谈一下。我认为每一个“集群”都形成了一种语言,在这种语言中,一些具体的技术(设备和方法)聚集在一起,构成那个技术进行表达时所用的语言。
为什么个体技术要聚集成群?原因之一是它们是分享了现象的族群。但这不是唯一的理由,技术聚集在一起还因为它们分享了共同的目标:斜拉桥的钢索需要锚固设施,锚固设施需要重型螺栓,这样一来,钢索、锚、重型螺栓就自然集成在一起了。那些分享共同物理强度和规模特征的要素,大梁、桁梁、柱子、钢梁、水泥板等聚集在一起,它们在强度、尺度和应用范围上是匹配的,它们因此成为了结构工程的构件(building blocks)。就这样,要素积聚成群,进而为形成可用的次级构件服务。基因工程方法,即DNA纯化、DNA扩大、放射性标记术、排序、通过限制性内切酶进行切割、克隆基因片段以及表达基因筛检,组成了一个天然的装满模块的工具箱,特定的程序就从这个工具箱中产生出来。
有时候,要素聚集的原因是它们可以分享同一个理论。例如,用来概括和分析数据并实施统计性测试的统计软件包,拥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前提,即抽样在总体上应是正态分布的,因而统计软件包工作的基础是共享了所操作数据在这个性质上的假设。描绘一个技术集群的通常是某种共性的外在形式,即某些可以使共同工作成为可能的、共有的、自然的能力。
我称这种集群、这种技术体为域。一个域可能是任意一个由不同要素构成的,从中可以产生设备和方法的集群,以及产生这些设备和方法所必需的实践、知识、组合规则及思维方式等的集合。1
THE
NATURE
OF TECHNOLOGY
技术思想前沿
某种具有共性的外在形式,或者是可以使共同工作成为可能而共同固有的能力,可以定义为一个技术集群,对于这种集群或技术体,我们称之为域。
对我们来说,如果想弄清楚技术是如何形成和进化的,关键是要保持个体技术和域之间的清晰界限。但是有时候,这个界限看起来是模糊的,比如雷达(个体系统)和雷达技术(工程实践)听上去非常相像,但其实不然。
一项技术(个体技术)是要完成一项工作,达成一个目标的,而且这个目标经常非常特殊。而一个域(复数的技术)则不需要完成工作;它仅仅是以一个工具箱的方式存在,你可以从中选取有用的元器件或一系列的应用规范。一项技术界定一个产品或一种工艺。一个域不界定任何产品,它表现为技术的星座—— 一组互相支撑的装置。当这组互相支撑的装置由生产它们的公司来表现时,它就界定了一个产业。一项技术是被发明的,它是由某个人集结组装的;一个域(例如,无线电工程)则不是被发明出来的,而是从它的个体的组件开始一点一点展现而成的。一项技术(例如,一台电脑)只向占有它的人展示某种潜力;一个域(例如,数字技术)则将潜力赋予了整个经济,并及时地将其转化为财富和政治权力。
技术和域还有另外一个不同之处。技术所占据的是模块、次级模块和零部件这样的层级关系,而域所占据的则是次级域、次次级域。电子学包含电子模拟技术和数字电子技术两个次级域,而次级域又包含着次次级域,比如固态半导体元件,在次次级域中又包含了砷化镓和硅器件这样的次次次级域。
对上述差异的总体表述是:个体技术对于技术体来说就如同程序对于程序语言一样。
域定
工程中的设计是从选择一个域开始的,也就是说,是从选择一组适合建构一个装置的元器件开始的。当建筑师设计一个新的办公大楼时,从视觉和结构上考虑,他们可能选择玻璃–钢架的组合而不是花岗岩,他们会在含有不同特性材质的“调色板”中进行选择,我们将这种“调色板”也称为域,而将这个选择过程称为“域定”(domaining)。域定过程常常是自动的、下意识的。一位航海雷达的设计者会在电子元器件中毫不犹豫地“域定”主控振荡器,可能仅仅是因为眼下没有更适合的域了。
但有时选择也很费思量,比如,一位设计者如果要集成计算机操作系统,那么他就需要在Linux系统和Windows系统之间进行选择。当然,任何规模较大的技术通常都需要几个域的同时加入,比如,一座发电站是从建筑施工、水利、重型电机和电子等不同的域中选取集成而来的。
在艺术领域,域的选定在很大程度上关乎风格。作曲家会让一个主题穿梭于管弦乐中不同的域——或管乐部分或弦乐部分,以此来获得感受和对比。在技术领域上,域的选定不取决于情绪或感受,而取决于它所能完成的集成的便利程度和效率,以及它和其他集成形成链接的容易程度以及成本。技术中的域定通常是很实际的。
THE
NATURE
OF TECHNOLOGY
技术思想前沿
工程设计是从选择一个域开始的,也就是要选择一组适合建构一个装置的元器件,这个选择过程,我们称之为“域定”。
针对给定目的的“域”的选择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在数字化技术出现之前,飞机设计师们是在机械和液压技术的范围内选择控制机翼和稳定器表面系统的。他们用推杆、拉杆、电缆、滑轮和其他机械链接将飞行员的操纵杆和那个用来移动飞行操纵面的液压机械舵联结起来。20世纪70年代,他们开始以数字化的方式在一种新式的、被称作电传操纵(fly-by-wire)的新技术体当中重新域定飞机的控制系统。新系统捕捉到飞行员的行动和飞机目前的运动状态,然后以信号的形式通过电线发送到计算机中进行处理,最后计算机再次通过电线将必要的调整信号传输到用来控制飞机操纵面的快速液压传动装置上。
电传操纵的飞机控制系统2要比之前使用的机械轻得多,且可靠性更高,反应也更快,新的控制系统能够在毫秒之间对变化作出反应,而且它们是“智能的”。通过计算机控制的电传操纵比人更精确,甚至可以纠正飞行员的不佳决定。
事实上,新的域使得新一代“内在不稳定”(inherently unstable,用技术术语讲就是“放宽静稳定”)的军用飞机设计成为可能。这种设计赋予军用飞机一种优势。就像控制一架不稳定的双轮自行车要比控制一台三轮车更容易一样,控制一架内部不稳定的飞机要比控制内部稳定的飞机更容易。新的控制系统使飞机平稳的方法和骑车的人通过反向运动来抵消不稳定性以保持自行车平稳的方法是一样的。人类飞行员无法如此迅速地作出反应,因而在早期的手动技术中,内在不稳定飞机是无法飞行的。
THE
NATURE
OF TECHNOLOGY
技术思想前沿
重新域定(redomained),是指以一套不同的内容来表达既定的目的。重新域定不仅提供了一套新的、更有效的实现目的的方法,还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这意味着技术的颠覆性改变。
因此,我们可以说飞机控制系统经历了一场“创新”,并且他们真的做到了。但是我们应该更准确地说,飞机控制系统是以不同的方式被域定了,或者说是被重新域定了。这种区分很重要。历史上的创新常常是在已有的技术上进行的改进,例如,一种更好的建造圆屋顶的方法,或者一种更有效率的蒸汽机。但是显著的改进实际上是“重新域定”,即以一套不同的内容来表达既定的目的,就像动力供给的方式从水车技术发展为蒸汽技术那样。
重新域定之所以强大,不仅仅在于它们提供了一套新的、更有效的实现目的的方法,更在于它们提供了新的可能性。20世纪30年代,人们可以用由水泥制造的、15英尺或更高的巨大的声反射镜去监察跨越海峡飞往英格兰的飞机。它需要搜集来自20英里远的声音,然后交由具有超敏感听力的人进行处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雷达被用来实现同样的目的。雷达的有效范围更大。我们可以说,飞行侦查任务采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引发创造)了雷达技术,但是我更愿意说是这项技术利用了一种新的、更强大的域,即无线电工程。这个域横扫了整个世界,其组件后来又被发掘出许多用途。
域内发生的某些变化是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式。
当一个新的域出现的时候,它可能并不能直接显现明显的重要性。比如,最初无线电仅限于电报通讯,即从船和岸之间用无线电方式发送信息。但是,新域的出现不仅在于它能做什么,更在于它能带来的新的潜在性。这种潜在性会激发当时技术专家的灵感。1821年,查尔斯 ·巴贝奇(Charles Babbage) 3和他的朋友,天文学家约翰·赫歇耳(John Herschel)正在为天文学会准备一张数学表。两人之前比较了同样一张表,然后分头计算。巴贝奇因为错误频出而绝望地说:“我真希望上帝能够用蒸汽来进行这些计算。”巴贝奇的话在今天听起来很奇怪。后来,他设计了一个计算设备,但不是用蒸汽,而是用手柄和杠杆驱动的。这里应该注意到的是,他诉求的不是新的设备,而是新的域!让我们向那个时代的奇迹之域致敬吧,在19世纪20年代,蒸汽定义的是一个关于可能性的新世界。
实际上,域不仅定义可能性,而且可以定义一个时期的风格。回想一下,在维多利亚晚期,科幻小说中对宇宙飞船航行的憧憬,就可以明白我在说什么。我这里想到的是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的《从地球到月球》中的场景 4,其中折射了19世纪60年代的法国映像。如果你看到这本书中描绘的航天器以及它的着陆装置,就能体会到,那些辨别出它们所属时代的因素,不是其外形或设计(这是航天器独有的),而是因为它们所选用的组件是18世纪中叶才可能出现的技术。这些技术包括铸铁的太空船、用火炮抛送太空船,整个冒险发生在砖和熟铁的建筑结构当中。这样的技术组件和使用方式不仅反映,而且定义了一个时代的风格。
时代创造着技术,技术同时也创造着时代。技术的历史不仅是单个发明和技术(印刷机、蒸汽机、贝塞麦炼钢工艺、无线电、计算机)的编年史,它也是在目的集成过程中确定的新时代(整段时期)的编年史。
当你步入一个被精心设计的博物馆,你就可以看到,或者应该说可以感受到这一点。博物馆通常会有一个或者几个特殊的房间用来回顾这些历史上的特殊时刻。洛斯阿拉莫斯历史博物馆就用这样的展览来展现人工制品和战争技术。你可以看到化学用曲颈瓶、计算尺、曼哈顿计划的身份证、身着宪兵警察制服的假人、汽油配给的卡片、旧卡车和吉普车的场景等,所有这些都与当时完成任务的典型的手段,也就是技术有关。而这些技术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能定义它们所描述的时代。洛斯阿拉莫斯展览本身是小规模的,只有两个或三个房间,但进入它,就相当于进入了那个时代。
域不仅定义时代,它们也定义时代的边界。想象一下,如果用巴贝奇时代的域来描绘一幅地震数据地质图会怎样。它可能需要巴贝奇亲自设计设备,组装一台地震波分析仪,并依据爆炸回声进行地图的渲染。这个机器将是一个奇迹,它也许会带有一个犄角形的听筒,一个辅助的铜齿轮和杠杆,以及转盘和着墨的绘图笔。这个设备工作起来缓慢、复杂,而且它将专门用来进行地震勘测。巴贝奇时代的这些域(机器、铁路、早期工业化学)的触角很短,因此所能提供的可能性很有限。今天,我们拥有的域则可以提供更广泛的可能性。实际上,一个域的有效性一半来自于它的范围,即它能开启的可能性,另一半则来自于它能否为不同目的进行反复的、相似的组合。这有点像过去的排字工人都会在手边事先准备好一些常用字的组合(法国18世纪的印刷工人称它们为“clichés”),以便使用起来更加方便、高效。
设计就如同语言表达
一个新的设备或方法是由一个域中适用的零部件,或者也可以说是适当的词汇聚集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一个域构成了一种语言,当某个域在产生一件新的技术产品时,就是这个域在以某种语言进行表达。这使得技术在整体上如同多种语言的集合,因为每一项新技术都可能从多个域中汲取元素。这也意味着技术中的主要活动,即工程设计,变成了一种写作方式,一种(或几种)语言的表达。
THE
NATURE
OF TECHNOLOGY
技术思想前沿
一个域就相当于一种语言,当某个域在产生一件新的艺术品时,就相当于这个域在以某种语言进行表达。语言的组织必须依据语言规则,设计的建构也要根据域允许的组合规则进行,这种规则就是语法。
我们并不熟悉这种看待设计的方式,但是它值得我们考虑一下。语言中有清晰和不清晰的表达方式、恰当和不恰当的语言选择之分,设计亦是如此;语言可以简明扼要,设计亦是如此;语言有不同程度的复合句式,设计亦是如此;用语言表达一个理念可以只用一个简单句,也可以用一整本书,并辅之以若干支撑材料来呈现一个主题,设计亦是如此。语言中任何目的的表达都可以有很多选择。类似地,技术为达到任何目的也可以选择多种组合。如同语言的组织必须依据语言规则一样,设计的建构也要根据域允许的组合规则来进行。
我将这种规则称为语法。可以将语法想象成一个域的“化学”规则,即确定什么可以被允许进行组合的一组原则。这里用的“语法”就是我们常用的那个意思。亨利 ·詹姆斯(Henry James)曾谈及“绘画语法” 5;生物化学家埃尔文·查戈夫(Erwin Chargaff)1949年在论及他在DNA化学方面的发现时就曾说过:“在眼前模糊黑暗的轮廓中,我开始看到了生物学的语法。” 6詹姆斯和查戈夫所指的语法,并不是绘画或分子生物学的特性,而是指绘画元素或生物元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结合并形成结构的方式。
一个域的语法决定它的元素如何被组装在一起,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它们会结合在一起。它决定什么东西在“起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就有了电子学、水力学以及基因工程学的语法,对应更精细的域,还会有次级语法和次次级语法。
这样的语法是从何而来的呢?7当然,毫无疑问,它最终一定是来源于自然。电子学的语法背后是电子运动的物理学以及电现象的规律。DNA操作的语法背后是核苷酸和与DNA一起工作的酶的内在特性。语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对“特定域中自然是如何工作的”这个问题的理解。这种理解不仅是来自于理论 8,也来自于经验积累:工作温度和压力参数、机器配置和工具的选用、过程计时、材料强度、集成件间的安全距离——无数的知识碎片组成了各种技艺的“烹饪术”。
有时这种知识可以还原为拇指法则[1](rules of thumb)。飞机设计界早就从多年的经验中知道:“成功的喷气飞机的引擎推力重量与加载的飞机之间的比重永远都大约介于0.2~0.3。”但更多时候,知识通常不能转化成这样的法则。在这方面,技术和艺术实际上没什么不同。正如巴黎蓝绶带烹饪(Cordon Bleu) [2]不能简化为一套书面原理,专业电子设计也不能。不论烹饪还是工程的语法,都不仅作为规则存在,还必须作为一套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潜经验(unspoken practices)存在,因为实践知识(practical knowing)可能没办法用语言进行充分的表达。语法由文化经验和应用技巧构成。如此一来,语法就不仅存在于使用者的头脑中,不仅出现在课本中,还存在于它们共享的文化中。它们出现时可能被当作规则,但是最终则会成为一种概念化的技术、一种思维的方式。
事实上,正如口语表达的清晰度不仅取决于语法一样(它依赖于词汇的深层含义及其文化相关性),技术的清晰表达也不会仅仅依赖于语法。技术的清晰表达需要相关域的深层知识,包括:所使用组件的词汇的流利程度;对标准模块、以前的设计、标准材料、相关技术的熟悉度;一种关于什么是自然的,什么会被该领域的文化所接受的“洞悉”(knowingness);直观知识、横向沟通、感觉、曾经使用的经验、想象力、品位——所有这些都是有价值的。
技术专家詹姆斯·纽科姆(James Newcomb)在谈到提供节能服务时说:“做好这种业务需要数以千计的个体技术知识,以及为特定目的吸收和优化组合这些技术的能力,同时要考虑到交互影响、控制系统、过程影响、能源经济和节约需求的差别。这要求大师级的厨艺,而不是杂货店采购员的水准。” 9
好的设计事实上就像一首好诗。这不是指诗的崇高感,而是指从众多的可能性中为每个部分作出完全正确的选择。每个部分必须紧密配合,各部分的运行一定要准确,必须符合与其余部分的互动规则。一个好的设计10的美感在于适切性,在于为所获得的东西付出最少的努力。它源于一种感觉:恰如其分,增一分则多,减一分则少。技术中的美不一定非得需要原创性,技术语法不论在形式上,还是短语的选用上,都大量借鉴了其他语言。如此看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设计所依赖的往往是对“clichés”的组合和操纵。尽管如此,一个美的设计总是包含一些意想不到的组合,并以其适切性震撼人心。
技术就像写作、演讲或高级烹饪,存在不同程度的流畅性、表达能力和自我表现。一个建筑界的新手,就像一个学习外语的新手一样,即使有时不太适合,也会一遍又一遍地一直使用同样的组合,或者说同样的短语。一个熟练的建筑师深谙域的艺术,他会摒弃纯粹的语法规则,而诉诸直觉知识,使它们组合、搭配在一起。一位真正的大师会挑战极限,他会在域中赋诗,会在其所使用的惯用组合中留下自己的“签名”。
技术大师实际上非常难得,因为技术的语法不像语言的语法,它变化迅速。技术语法最初是原始的,只能被模糊地感知;当组成它们的基础知识发展时,它们得以深化;当发现了新的匹配良好的组合,或者发现了设计在日常使用中遇到的困难时,它们就进化了。这个过程永无终结。结果就是,即便是此中的专家,也不能完全跟上它们在“域”中组合的原则。
在一个域中投入巨大的成本会让设计师较少考虑从所有可用的域中选择组合。保罗·克利(Paul Klee)认为,艺术家会自觉去适应自己调色盘上所能配出的东西:“画家……不会让画去迎合世界。他自己会去迎合画作。” 11技术也是这样,设计师总是从他们了解的域中着手建构技术。
参与的世界
如前文所述,一个域或者一个技术体提供一种表达的语言、一套内容和实践的词汇表,设计师可以从中作出选择。计算技术(或数字技术)是一个集合,是一个巨大的词汇表,包括硬件、软件、传输网络、协议、语言、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算法,以及所有和它们相关的组件和实践。所以,我们可以把计算技术,或者任何与之相关的域看作是一个仓库,它们随时准备服务于某种特殊用途。
我们可以将这个仓库假设为装有元素或功能的工具箱。但是我更愿意设想它是一个王国,那是一个可以在其中建功立业的世界,一个为了能在其中完成某个任务而呈现的世界。
一个域便是一个想象的王国。在那里,设计者可以在思维中想象自己能做什么。那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域世界。电子设计师知道他们可以扩大信号、转换频率、减少噪音、调节载波信息、设置定时回路,还可以利用许许多多其他可靠的操作。他们依据电子世界实现内容的可能性去思考。此外,如果他们是专家,他们应该非常熟悉这个世界,因此他们几乎可以自动地组合操作并预见结果。那个发明了微波激射器(激光器前身)的物理学家查尔斯·汤斯(Charles Townes), 曾经在波和原子共振相关的操作和设备上花费了许多年时间来研究以下内容,包括:场下离子分离、共鸣室、敏感高频接收器和检测器、微波光谱。然后他将这些功能应用到他的发明中去。专家们沉浸在域的世界里,就如我们写信的时候沉浸在文字中一样,他们的精神沉浸其中。他们着眼于目的性,然后在头脑中进行每一步操作,这很像一个作曲家构思出一个主题,但是却要回过头来诉诸乐器去表达它。
一个域也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在那里,有设计者和用户都可以接触并完成的真实的任务,在那里,常规的操作是可能的,使用过程也总是相同的。一些目标(行动或者业务流程)也以实体形态进入世界当中。想象一下,图像处理专家通过扫描使图像进入“数码世界”,或者是用数码技术摄制图像。一旦有对象被从一个操作传递到另一个,就会继续下去,完成转换,有时还会与这个领域内其他的活动和对象结合起来。在数码世界里,影像变成了数值、数据,因此它可以接受数字化操作,包括颜色校正、锐化、去饱和度、变形成广角效果、增加背景等。当操作结束后,对象再次以这种加工过的形式,被应用到现实世界中。作为被操作过的数据,加工过的影像被翻译成真实世界的视觉图像,又一次展现在计算机屏幕上,被储存起来或被打印出来。
无论是域还是它的世界,这种操作过程构成了域的真正的有用性。我们可以认为某些东西“下到”了一个具体环境,在那里成为对象,被进行各种操作,然后再令它回到“上面或外面”并被使用。现场交响乐可以通过麦克风设备被带到“下面”的电子世界进行加工(电子化操作,例如电子记录),然后再带回到“上面或外面”,重新进入物理世界,以声音的形式被“演奏”出来。
对于域世界来说,每个域的所能都是独特的。某些域世界提供了特别丰富的可能性。数码世界可以对任何简化成数字符号的东西进行操作,不管是建筑设计还是摄影图片,或是飞机的操控系统。它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运算操作或运算次序,以及逻辑步骤的系统。而这些操作的速度可以非常迅速,数字电路中的变换是会以超快的变换速率进行的。
另一些域世界则很有限,在所能方面会有所限制,但是它们可以更有效。在18世纪后期,运河提供了一个域世界,在那里用载货驳船更便宜,也更容易运输大宗商品,如煤炭、粮食、木材、石灰石,甚至牲畜等。这样,大宗货物的运输就通过进入运河世界完成了。准确地说,这意味着货物已经离开了道路和陆地域,而进入了驳船、船夫、船闸和纤道构成的水的世界。当然,在那里,东西的移动是缓慢的。但尽管如此,由于它的移动是流动性的,因此与陆地比较,这种移动更容易。在这个域中的货物可以流向不同方向,向后或横着停泊在水中突起的陆地上。一些货物被卸下来,腾出空间,再装上另外一些货物,到达目的地后,运输还可以继续进入公路或马车运输的域,而那里曾是运输业开始的地方。
已经成为历史的“运河域世界”实际上功能很单一,它其实只提供一种功能:运送物料。甚至这个功能也只能在开挖运河的地方才能实现。但是它在成本–收益方面是成功的。在河道运输之前,陆地运输只能依赖笨拙的牛车蹒跚在颠簸的土路上,而19世纪早期河道运输方式在英格兰推广以后,煤的运输成本就下降了85%。
一个域的力量所在通常是那些最容易完成的部分。只要你能将某事还原为数字式描述,从而进行数学操作,计算就可以行之有效地进行下面的工作。只要你能将货物装载到驳船上,并用它来运送货物,运河世界就能开始运作。电子学(非数字类)的有效性取决于运动的显现要依赖于电子的运动。域们各善其事。当然,从原理上讲,你可以在不同的域世界中完成同样的任务,但是功效可能会不一样。应用数字域可以很容易列出顾客名单,但是如果你非要用电子域去完成它新设计团队linux内核设计的艺术:图解linux操作系统架,你可能需要用不同的电压代表不同的字母,然后按照感应电压和输出的振幅顺序来安排电路,这当然可行,但很笨拙。你甚至可以用运河域世界来分列顾客名单:比如每艘驳船可以作为一位顾客的标记,然后驳船被向前拖动就如同字母缓慢显现。这也是可行的,但是它肯定不是运河世界最有效的应用方向。
如我所说,不同的域世界提供各自擅长的,互不相同的可能性。每个世界提供各自最容易完成的一套操作。所以这是很自然的,一个对象或业务活动,要进入一个以上的世界,各尽其能地完成整体工作。光学数据传输提供了一个光子的世界,通过光纤网络发送信息。这里的主力是光子(或光量子)包。这些信息很容易被携带,并且以接近真空中的光速迅速移动。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光子不像电子那样可以携带电荷,因而它们是中性的,不易操作,而且由于部分光缆中的光总是被吸收,因此信息每隔数英里就会衰减。所以这些信息必须不断“重复”或放大,才能得以继续传输,这意味着光子流必须被适当地还原和调整。
在早期,光子世界并没有成为传递信息的直接手段。信息经常退出光子世界,转而进入电子世界,因为信息在那里更容易被重新调整、放大和切换。但是电子世界太慢了,它必须依赖电子的移动,而那需要对电磁场作出反应,因而不能瞬时完成。这就像每隔几英里,信息就要被带下高速公路,到一个便道进行电子操作,然后再把它重新放回高速公路一样。系统本身是可行的,但是持续的离开和再进入光子世界提高了成本而且降低了速度。直到适用的光子放大器(即掺铒光纤放大器,EDFA)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诞生后,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
常规经验是,当任何一项活动离开一个世界并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时候,其成本就会累积增加。在海上运输货运集装箱并不昂贵,但将货物从铁路运输域转移到船上使货运进入“集装箱世界”,这就需要铁路端点、码头、集装箱装卸起重机和装卸业务等繁琐而昂贵的技术。这种“过渡技术”通常是一个域中最棘手的部分。过渡技术会产生延迟和瓶颈,并提高成本,但它们又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们不仅使域有效,而且控制什么可以进入或离开它的世界。我们可以这样看待域:它包含着一些核心操作,比如蒸汽驱动的、便宜的海运集装箱运输,还包括处于域的边缘,围绕这些中心操作的缓慢的、笨拙的技术。与其相对应的域世界允许其在活动开始时进入,在活动结束后再离开,比如说甲板和龙门吊。总体上讲,它们是昂贵的。
我此前曾说过,域反映着它们创造的那个世界的力量,但是它们也同时反映着它的局限。将设计域定在数字技术中的建筑师可以让设计思路的变化瞬间呈现出来,并且可以同时将材料成本计算出来。但是数字域会有它自身微妙的偏见,只有真实世界可量化的部分能够进入数字世界,并在那里获得成功。因此,数字建筑设计可以轻而易举地产生拱形,或者以流畅的数学曲线呈现倾斜,但是正如建筑设计评论家保罗·葛贝格(Paul Goldberger)所说,数字化设计对“魅力、闲适、留白都缺乏耐心”。 12数字世界可以计量表面形状,却无法计量时尚。或者我应该说,时尚目前还不能被量化。如果它能够被量化了,即如果你可以通过显示器上的移动滑块控制你想要的魅力程度,那么现有的域就需要扩展了——不过到目前为止,这还是不可能的。一个世界的“不能”,便是这个世界的局限所在了。
我将在第8章重新谈论域或曰复数的技术,去探究它们是怎样产生以及怎样随着时间发展的。现在我们只需认识到,当我们将技术理论化,我们必须看到技术的中间层(技术体)是在不同于单体技术的规则之下运行的。这些技术体或者域,决定着某个特定的时代的可能性,它们引发一个时代的标志性工业,它们是工程师可以有所成就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什么是静止的,待完成的东西随着域的演进及其基本现象边界的扩展而不断变化着。这暗示着创新不是发明以及对其的应用(例如,计算机、运河、DNA或者芯片的发明和应用),而是在新的可能世界中,将旧任务(例如,会计、运输或者医疗诊断)不断地进行重新表达(re-expressing)或者再域定(re-domaining)的过程。
[1]拇指法则,即一种经验性、直觉性的简单原则。——编者注
[2]指法国顶级的厨艺水平。——编者注
到
目前为止,我们探究了技术的本质,它的工作原理以及它最深层的含义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形成了一套关于技术的逻辑和框架,用以说明技术在世界中是如何被建构和操作的。在本书的以后章节,我将继续应用这个逻辑去探索技术是如何形成并进化的。
我们现在已经不再将技术看作是作为整体的一块铁板了,而将其看成是具有内部解剖结构的事物。事实上,一旦我们接受技术是建构的产物,即由零部件或组件组合而成,我们就不得不这样看待它们了。这样一个内部视角能否使我们从与以往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技术这个问题呢?
我认为会,这种不同至少会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技术在其生命周期当中如何进行自我修正。如果我们从技术外部将技术看作是一个整体的对象,那么个体技术,如计算机、基因测序、蒸汽机似乎是相对固定的。它们的生命周期可能表现为从一个版本到下一个版本的变化。如计算机从阿塔纳索夫–贝瑞计算机(Atanasoff-Berry machine)到埃克特和莫齐利的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Eckert and Mauchly ’s ENIAC),再到电子数据计算机(EDVAC),这些技术可能会以这种方式非连续性地进行改变。但是当我们从内部来看技术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某一技术的内部组件一直都在变化,比如替换零部件、改进材料、改变建构方法、对技术所基于的现象有了更好的理解,或者随着母域(parent domain)的发展,有了新的元素可以利用等。所以,技术并非是总体上很静态、只是偶尔发生变化的事物。正好相反,技术是一种非常易变的东西,它是动态的、活的,会随时间发展而不断进行构成和发生变化。
第二个不同之处是我们如何看待技术的可能性(我现在是在“集合”的意义上谈技术)。从外部看技术,每项技术看起来都是在完成某个目标:如果想测量,我们有测量的方法;如果想导航,我们有全球定位系统。我们可以应用测量方法完成某个具体任务,应用GPS完成另外一个具体的任务。但是这么看技术,在“理解技术是什么”时是有局限的。因为技术不仅是为了提供某种特定功能而存在,它实际上还提供了一个组合或编程的词汇表,这个词汇表的存在使技术可以提供无穷无尽的新颖方法,去实现无穷无尽的新颖目的。
如果这样看技术的话,结果就会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可以设想一下未来某天,计算机技术已经消失了,考古学家们挖掘出了一个20世纪80年代的破旧的苹果电脑,于是他们急忙回到实验室,插上电源,这个珍贵的盒子就闪烁着开启了,那么他们应该立刻就能发现几种能够执行的功能:用于文字处理的MacWrite程序,用于影像制作的MacPaint程序,或者一个旧版的电子制表软件。这里的每个功能都是可用的,可以很好地执行特定的任务,因而调查者可以在很长时间内使用这个机器去执行每个任务。
但是实际上,这个苹果机还可以提供更多用途。在苹果机的内部,蕴藏着它的工具箱,这是一套内部的命令和函数,它们可以使一般的目的被程序化执行。这些命令可以以某种方式被组合起来,从而创建以前没有的新命令和函数(功能)。这些新命令自身可以被命名,并且被用作未来组合的新组件。只要从故纸堆里对苹果机的相关知识进行充分研究,研究者们就可能学会如何进入其内部命令系统。他们会搞清楚如何提取命令,并把它们重新组合,去完成新的任务,或者将它们作为新的程序命令的组件。在这个时刻,会出现一个质的飞跃,研究者们会发现他们可以操控苹果机了,他们可以用一小部分基础命令进行编辑,这些基础命令再以新的方式进行新的无限的组合,从而简单命令可以被建构为许多复杂命令。
这时的机器就不再只是那个提供几种独立功能的机器了,它现在可以提供的是一种语言表达。到此,一个可能的新世界已经被开启了。
技术通过改变内部组件的结构进行适应,以及通过新组合产生新结构,这两个主题将是本书接下来不断重复的主题。但是别忘了,我们的主题是:技术进化是如何通过组合现存技术来产生新技术,以及如何通过现存技术去驯服可能形成新技术的现象的。我想要探究的是:这个过程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对此我会在第9章更加详细地加以论述。
现在让我们沿着这个思路继续下去,我们需要留意技术写作中的两个反复出现的问题。一个是达尔文机制应用于技术进化中的程度,即在什么程度上,技术的新“物种”会从某种旧技术中通过变异而产生出来并且被选择?另一个是,在什么程度上,托马斯 ·库恩的观点会被应用到技术中?库恩认为,业已公认的科学范式会随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完善,直到遭遇所谓的“异常”,进而发生更新换代的情形。那么这个观点也适用于技术吗?
我们还需留意的议题是:创新。“创新”是技术中另一个棘手的词。通常在实践或尝试新点子时,如果出现了一些进步或提高,不管它多么微小,创新都有可能会被唤醒。熊彼特使用这个词(对我来说,有些费解)来说明发明被商业化的过程,而我则会在它的一般含义上,也就是“新颖性”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这种新颖性会表现为几种形式:给定技术中的新的解决方式、新技术自身、新的技术体,或者在技术集合中加入新元素等。在后面的章节中,因为“创新”这个概念太分散、太模糊、不利于更有效地说明问题,所以我选择去探究新颖性或创新的每个具体类型。
一个好问题可能是成功的开始,为此我们需要一个关键的、足可以引领我们本章和下一章探讨的问题来开始进一步的探究。进化的发生源于新技术的不断形成,它们通过将已有技术作为组件来形成(forming)新面貌的方式,表明它们是脱胎于此的。那么,这种“形成”到底是怎样发生的?新技术的产生机制是什么?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是,它是通过某种根本性创新(radical innovation)过程(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称之为发明过程)来实现的,简单来讲,确实可以这样认为。但是别忘了,新组件的元素也来自于日常性的标准工程。根本性创新与日常标准工程放在一起,初看起来会令人感到有些讶异,因此我想挖掘一下这个过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首先让我澄清一下什么是我所说的“日常标准工程”。
标准工程
工程师们的日常工作到底是什么?总的来说,他们设计并且建造人工物。他们也开发方法、建立测试设备并进行研究,以找出材料被运用以及解决方案在实践中得以履行的方法。他们在专业的研究所或实验室中深化对操作对象的理解;他们调查失败原因、寻找修复的对策;他们管理法律事务并提供建议,对顾问委员会提供咨询与服务;他们对相关问题,也即那些好似需要反复讨论、思考及担忧的问题进行审慎的斟酌。
THE
NATURE
OF TECHNOLOGY
技术思想前沿
标准工程是执行一个新项目时,在已知可接受的原则下聚集方法和设备的过程,是对已有技术的新的计划、试制和集成过程。
工程师们为所有这些活动奔忙。但是我想集中讨论的是标准工程1,即执行一个新项目时,在已知可接受的原则下聚集方法和设备的过程。有时这个过程被称作“设计和建造(construction)”,有时则被称为“设计和制造(manufacture)”。但无论怎样称呼,它们都是对已有技术的新的计划、试制和集成过程。它不是指斜拉桥或者飞行器的“发明”,而是指设计和建造一个新版的斜拉桥,比如日本的多多罗大桥或者新版的空中客车。方便起见,我将这种活动简称为“设计”。
几乎所有的设计项目都是在规划和建造某个已知技术的新版本。这就像几乎所有的科学活动实际上都是将已知的概念和方法应用于新问题一样。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标准工程是简单的。我们可以按照困难程度列出一个谱系:从应用惯例和标准组件的传统项目,到那些需要实践或实验的项目,再到那些拥有真正难以突破的界限并需要应对一些特殊挑战的项目。在后面的例子中,我会着重讨论这个谱系中更具挑战性的一端。
标准工程或曰设计项目,到底应该包括什么?其基本任务是需要找到一个形式(form),或者说一套已建构好的程序集(architected assemblies)来实现目的。这意味着要用一些可用的概念框架和目的进行匹配,然后再进行现实的集成。这是一个过程,而且经常是一个冗长的过程。教科书里通常会讲到三个阶段:先从一个总体概念出发,然后细化出可以完成这个概念的集成件,最后实行制造或建造(这个过程中会伴随一些必要的反馈)。这里我们可以再次借用递归性来描述标准工程这种沿层级演进的过程,即从总体概念层次到单个集成件,再到次级集成件,再到它们各自的零部件,接下来每一个部分的构成也是上述过程的重复性进行。
事情大致来讲就是这样,但仅仅是大致来讲。设计过程在沿着层级向下演进的同时,也会从需求特点或者需求物(desiderata)向外演进。目的本身决定总体概念的样式,总体概念又决定着需要什么样的核心集成件,核心集成件决定需要何种次级集成件来支撑它们,次级集成件又决定它们所需的组件。20世纪60年代末,波音747的总工程师约瑟夫 ·萨特(Joseph Sutter)的一段描述正可以说明这个过程 2:我们想要设计一种搭载350名乘客的飞机。我们设想建造一个宽阔的单甲板。由于在载客区会有9~10人并肩而坐,因此机身的长度也就被大致确定了。我们试图优化机翼使其达到我们需要的吊装能力、飞行里程以及燃油效率。而机翼跨度首先要满足空气动力学的要求,还要达到初始巡航高度的要求,以及保持合理的降落速度以便飞行员有足够的时间着陆。
注意一下这里的顺序,需求作为飞机的主要目的开始显现——要搭载350名乘客,然后向外扩展构成集成件,每个集成件的需求决定了下一步要做什么,每个层次的集成件又需要互相匹配和相互支撑。
可以设想,这个过程有时可以进行得如同预先计划好的一样完美。有些项目确实如此。但是在难度谱系中具有挑战性的那一端,就不一定那样利落清晰了。通常整体概念不一定是一个,有可能存在好几个整体概念,而且有一些概念还是直到实验阶段或者甚至细节设计阶段才发现是不可行的。即使一个概念被选中了,它也必须被转译成集成件或者工作组件,而其中许多组件都需要特别设计。设计者不可能总是事先就预测出它们的实际性能。先前的版本也可能表现出某些未预料到的小毛病:可能不如期望的那样好,可能根本不运作,或者可能耗用了更多的质量、能量和成本。为了获取更好的解决方案或者原材料,必须对其进行修改。在一个集成过程中,不可预知的低效率必须通过调整其他部分得以提高。可以说,一项设计就是一系列折中的过程。
要使过程进行下去,除了需要大量的支持者之外,还要对理念、集成件和单元组件进行测试和平衡,并克服不断被揭示出来的困难。3只要一个核心集成件不好用,就有可能需要重新开始整个计划。如果项目特别复杂(例如,登月计划)则可能需要分步骤进行不同版本的实验,每种技术都分别建构在之前技术的基础之上。
一个项目一旦进入到一个未知领域,许多小问题的出现就变得不可避免了。比如,1965年的波音747还处于构思阶段,那时,它的巨大的重量要求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的动力系统来支撑。这不仅要求更大的涡轮风扇,而且要求更高的涵道比(从风扇吹出的风与从发动机流出的燃气之比要从以往的1:1达到几乎6:1)。为此,普拉特(Pratt)和惠特尼(Whitney)打算重新设计JT9D引擎。一个巨大的涡轮风扇被安装在压缩机前面,其直径为8英尺,能提供77%的推力。新的动力装置使性能实现了一个飞跃式的进步,但是它的创新性特征又引发了另外一系列困难。它的变容量定子(用来帮助控制通过压缩机叶片的气流)本来是由可移动的链接控制的,但是这些改进会产生周期性的卡停(解决的办法是自由使用WD–40),而要使这个装置产生更高的压缩温度,则又需要一个更好的涡轮机冷却手段。
最糟糕的问题是将发动机安装在机翼上选择何种方式。当发动机高速运转时,它会被向前推动并产生“弯曲”,引起外壳产生轻微的椭圆化变形。“根本原因在于引擎太大、太重,导致它起飞时会弯曲。”JT9D项目副经理罗伯特 ·罗萨蒂(Robert Rosati)解释道。发动机高速运转造成的挠度并不大,大约是0.04英寸,但这却足以引起高压压缩机叶片的底部与外壳之间的摩擦。这类问题并不危险,一定量的摩擦也是可以接受的。不可接受的是由此带来的效率和可靠性上的损失。普拉特和惠特尼尝试了几种修正的方法,如加固外壳、使用抗磨损椭圆形封条,但都没有成功。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安装一个反向的Y型锚固件,这在本质上是一种转移推力、减少弯曲的手段。挠度因此减小到80%,足以应付上述问题,但是这个小挫折使整个747的研发进程受到了拖延与阻碍。对于这样顶尖级的项目,类似的挫折并不常见。
在开发747的年代,实现新的设计需要手动完成庞大的计算量,手绘大量的明细图以及手工制作许多实体模型。现在,计算机接替了这些工作。计算机可以在瞬间将设计理念转换成明细图和部件要求,可以创造虚拟模型,有时甚至可以指导零部件的制造。但是即使有计算机辅助,这个过程也必须要有人的参与。这是因为过程进行中需要决策,而决策是不能依赖机器的。设计者必须对概念、结构、材料、强度、比例和容量的适合程度作出评价和判断。而像这样在一个项目的许多层级都要做恰当匹配就一定需要人的协调。
但是对于规模较大的项目来说,协调通常是很困难的。大规模项目的组件可能是由不同团队甚至不同公司设计的,这样一来,他们之间就需要进行平衡。一个团队的解决方案对于另一个团队来说可能反而是障碍,因此需要充分讨论来加以协调。从这个角度看,标准工程成了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一切都变得不那么清晰理性了。历史学家托马斯·休斯(Thomas Hughes)强调,一项新项目成功与否,它是否能形成可见的设计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围绕其周围的利益关系网:工程团队、融资系统、投资者以及其他参与者,他们从项目中获得或失去的包括权力、安全、威望等东西。因此, 设计与发展是与人高度相关的组织和行动过程。
解决问题的工程
此前我说过,工程师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有时候几乎是他们全部的时间去解决问题。为什么非得如此呢?教师教学、法官断案,那么工程师为什么不专司工程?为什么他们要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去解决问题?
在我们看来,运气不好可能是一种解释,例如747遭遇到的那个不可预见的挫折。无法满足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也是一个原因。技术挫折或人的原因当然很重要,但是它们并不是最主要的,工程之所以和解决问题紧密相连,有着更系统的原因。
正如我所定义的,标准工程与已知技术有关。这使得每个设计实际上都是已知技术的新版本或新案例(JT9D就是喷气式发动机的一个新版本)。但是一个新案例或一项新设计只有在技术的某个方面需要变得不同的时候才会被需要(如果不进行新设计的话,设计中已完成的部分将被迫放弃,建构过程也将停止)。新的设计可能是需要达到一个新的功效水平(例如,JT9D);或者是需要一个不同的物理环境;或者有了更好的零件和材料的选择;还有可能是市场发生了变化,因而需要某个技术的新版本。总之,无论哪种情形,一个新设计只有在必须的情况下才会被实施。
这意味着一个新项目总会抛出一些新问题。完整的回应(即完成的项目)通常就是一种解决方案,也就是需要在具体的理念指导下对集成件进行恰当地组合以完成这个给定的任务。我们可以说,一个完整的设计就是对特定工程问题的特定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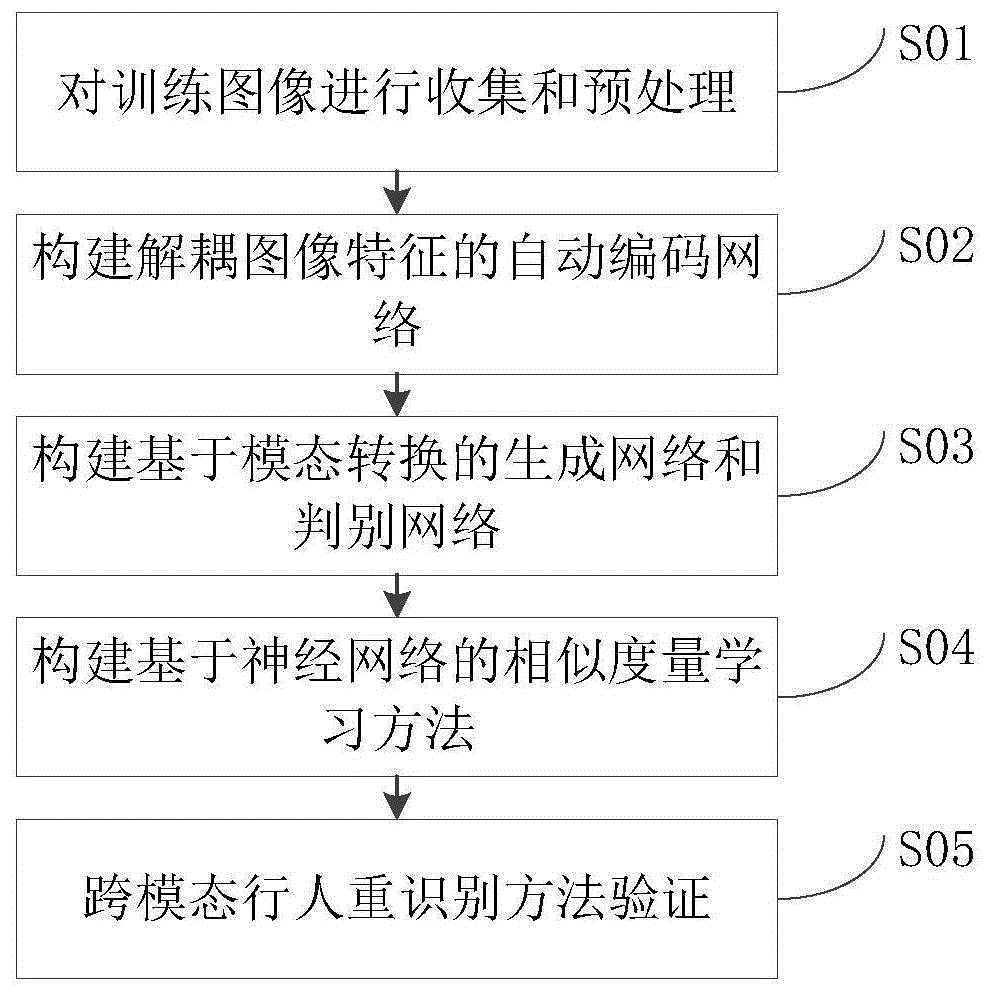
想要全面解决问题,就一定会遇上许多新情况,因为每个层级上的集成件的选择都需要重新考虑,并重新做出相互和谐的设计。某些集成件或模块当然可以单独进行修改,但是总的来说,当一个现存技术正在建构成一个新的版本的时候,每个层级,每个层级的每个模块都需要重新加以考虑。如果它不能和其他部分或预期的希望相匹配的话,必然要被重新设计。而这里的每一项设计又都会抛出它们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更准确地说,一个完整的设计是针对一系列问题的一系列解决。
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每个解决结果都能令人满意。不良的解决结果可能引起持续不断的问题。波音737就曾因方向舵失灵(专业术语叫“异常”)问题而备受困扰,这个问题曾引起过一次坠毁。工程师们用了很长时间去理解和解决这个问题。设计问题在技术的一个生命周期中常常不能够被彻底地解决,从莱特兄弟的飞行器到现代F–35喷气式战斗机,为飞机提供合适的控制系统一直都是一个难题。由计算机控制的自动驾驶现在成为一种解决办法,但是这种解决方法本身还处于完善当中,需要和应用它的新机型共同进步。
组合与解决方案
所有这些都解释了为什么在难度谱系更具挑战性的那端,工程的主要任务是解决问题,以及为什么工程师会不断地遇到问题。
但是这里又有了一个新问题。如果工程是关于问题的,那么是什么构成了一个或一套针对问题的解决方案呢?我曾经说过,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能完成一项给定任务的恰适组合。工程中的任何创造都是一次为达成特定目标的建构,这是一个将众多元素组合起来的过程。所以我们可以这样重新发问:一个解决方案是如何被建构的?这种建构又是如何与组合关联起来的?
实际上,对我们来说,这才是议题的核心。这本书通篇思考的是作为组合的技术——假使设计也能成为一个组合的过程,组合是如何在设计中发挥作用的呢?当然,工程师会选择适宜的组件并把它们放置在一起,他们组合它们,让它们共同工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开始就明确地知道如何组装所有的东西,知道他们将组合出什么。工程师只是简单地将自己投身于完成某个目标、满足某些技术条件或人,以及解决那些连带问题的过程之中。其中,精神劳动的部分包括了选择,即选定哪些部分共同组合成一个组件。组合不是工程创造过程的目的,而是选择的结果,是为了产生技术的一个新实例而完成要素聚集的结果。这样看来,组合实际上是工程的一项副产品。
这类似于思想表达的过程。现代心理学和哲学都告诉我们,思维在一开始都不会产生于语言之中。我们从无意识层面拔升出我们的理念——思想,然后用词语的组合去表达它们。思维存在了,它的语言表达随后才会到来。
如果会说几种语言,你就能明白,或者应该说能感受到这点。假设你的公司正在莫斯科做生意,和你一起谈判的人都只会说俄语,或者只会说英语。你想要说点什么,于是你用俄语说了。片刻后,你又用英语表达了同样的想法。这个“想法”某种程度上是独立于你如何将它说出来的。你有了一种想说什么的意向,然后经由某种潜意识的过程找到话语进行表达,其结果是你最终呈现出什么样的说话方式:它可能简短而自然,比如在一场对话中;也可能显得冗长,类似你在准备一个演讲时需要将内容一点一点拼接起来。无论哪种,它都是一个与某个目的相联系的想法或概念的组合,然后需要用句子、短语,或只用基本的单词进行表达。你在创造这种组合时并非刻意为之,但实际上你确实在“组合”。
这个过程和技术是一样的。设计师先对某事产生意向(intends something),为了表达这个意向而去挑选一个工具箱或语言,为了将这个存在于“想象”(mind’s eye)中的意向呈现出来而去预想出概念和功能 4,然后找出合适的组件去组合,从而最终达成那个想法。预想常常会同时产生,或者也可能会在修正之后出现。我们会在第6章更详细地探讨这样的创造过程是如何进行的,但是现在,我们要关注的是它和语言的关系,先有意向,然后是完成的方法——组件的恰当组合。所以, 设计即表达。
这暗示着工程及其寓所是一个创造性的领域。工程通常被认为比那些更重视设计的领域,如建筑或音乐,更缺少创造性。当然,可以说工程是日常性的,但是我们也可以说建筑同样是日常性的。因为从原则上看,工程中的设计,与建筑、时尚或者音乐中的设计,以及所有我们能想到的创造性的方式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它们都是某种组合、某种表达。
与其他创造性领域相比,工程创造性被低估的一个原因是,与建筑和音乐不同,公众没有被训练如何去欣赏一个具体的、制作精良的技术。计算机科学家霍尔(C.A.R. Hoare)在1960年创造了快速排序法 5,这是一种真正优美的创造,但是他不能到卡耐基大厅去表演快速排序从而赢得欢呼和掌声。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技术工作大部分都隐藏起来了,它们倾向于深藏不露,罩在某个罩子下面,藏在某个程序里,或者躲在某个工业流程中。谁能看见一位手机设计师是如何解决一个具体问题的?总之,这些工作对外行来说完全是不可见的。
创造偶尔还是可以被看见的。20世纪的前10年,瑞士工程师罗伯特 ·马亚尔(Robert Maillart)创造了一系列桥 6,作为通用技术,它们根本不新鲜,但是却和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或者密斯 ·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的创造一样具有创新性。在桥梁被用繁复的雕饰和厚重的石墙建成的年代,马亚尔的大桥显得优雅轻盈。直至今天,他的作品也显得非常现代。土木工程师大卫 ·比林顿(David Billington)在描述马亚尔1933年位于瑞士伯尔尼附近的Schwandbach大桥时,曾说它是“有史以来最美丽的两三座混凝土大桥之一”。它看起来与其说是要跨越沟壑还不如说是漂浮在那里,它那样纤细,却有着无可比拟的创新性。
作为建筑,Schwandbach大桥并没有采用什么新形式:它依然是由固定在拱上的竖向构件来支撑桥面。这是马亚尔时代广为接受的结构形式,它根本没用什么新材料,也没用什么新的结构构件——钢筋混凝土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被应用了。马亚尔完成他如此优雅的表达时,所用的却几乎都是最普通的技术手段。经过大量的几何学分析之后——尽管他不是天才的数学家,他明白了需要大大加强桥面的刚度,这有利于把重力荷载(假如桥的一端有一辆卡车)均匀地分散在大桥的结构上。设想一个桥的实体模型,其支撑拱是一条金属带,其两端被牢牢地固定在桥墩上,但是中间部分是弯曲的。现在将桥面,一个平板,置于拱的顶部,两端也固定在桥墩上,由固定在拱上的竖向构件来支撑。在桥面的一端施加荷载会使这端向下,而另一端则会翘起。如果桥面是软的,这个重力荷载就只能作用在施力端,而这是他们不希望看到的。但如果桥面是坚硬的,桥面的硬度将使反作用力作用在未加载端,从而产生一个向上的推力,这样一来,荷载将被更均匀地分散在整个结构上。
正是这个“解决方案”使得桥拱和桥面的重量可以很轻,而同时也有足够的强度——而且其中又蕴藏着优雅。而重量轻也使得建桥时可以使用很迷你的脚手架。马亚尔还学会了熟练地运用新型的钢筋混凝土,从而把自己从厚重的砖石建筑中解放出来。他摒弃了几乎所有的装饰,这也是他的建筑直到现在看起来还很现代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形式既有效又经济,而且具有创新性。但是它成功的原因却远不止这些。零部件和材料组合在一起,在整体上呈现了一种流动与和谐。这里完成的当然是一个技术产品,但毋宁说,它更是一件艺术品。
我并不想将标准工程及其主要的实践者们浪漫化。你在马亚尔的大桥中所发现的技巧并不来自于“天才”,而是来自于知识和技能的经年累月的积累,这正是马亚尔拥有并为之着迷的东西。并不是所有的标准技术的例子都和马亚尔的一样。大多数的项目依然坚持为标准问题提供标准的解决方案。需要的尺寸或规格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是重新计算和设计不外乎还是依据一些必要的标准模板。即使最具日常性的项目也是针对一个问题或一组问题的一个或一组解决方案,同时一定也具有创造性。
这里有了一个结论。设计就是关于解决方案的选择。因此,设计与选择有关。如果一项技术的所有部分都被诸如重量、绩效和成本严格限定的话,选择看起来就可能很严格。但是限定经常使得问题的解决更加复杂,继而需要调集更多的部件来完成。关于一个复杂表达的选择的工作量,即解决方案和解决方案的解决方案(次级解决方案),它的数量是巨大的。技术的任何新版本都可能成为后来大量不同建构方式的潜在要素。
实践中的建构方式比理论上的要少,因为工程师倾向于重复使用以前曾经用过的解决方案——短语和表达,并且他们倾向于使用可获得的现成的组件。所以,由同一从业者完成的新项目通常少有新奇的解决方案。但是由许多不同设计者同时参与的项目则会产生许多新颖的解决方式,它们会出现在诸如实现目标的概念设定方面,在域的选择上,在组件的组合过程中,在材料、建构方式以及生产技法方面。所有这些创新聚集起来,推动现存技术及其领域的进步。不同解决方案或次解决方案的经验以这种方式被牢固地聚集在一起,促使技术随着时间而变化和进步,其结果就是创新。
经济史学家内森·罗森伯格在谈到微小进步的聚集现象时说:“改进是通过不为人注意的设计和工程活动而获得的,但是它们构成了巨变的基本内容,并且在经济生活中为消费者带来了福利。” 7从这个意义上说,标准工程对创新贡献良多。
标准工程就是一个认识过程。
未来的技术构件
标准工程还有其他功能。它为技术的进化作出了贡献。读者根据我前文所述内容可能已经预想到这一点了。大多数时候,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都是具体的,而且不是作为一个整体加入到技术的指令系统中的。但是一些解决方案会被偶然地多次重复使用,从而使其本身变成了目标,继而在未来的技术建构中成为新的元素。
如果你看过任何一本工程手册,你就会发现许多标准问题的解决方案。比如《机械和机械设备图集》8就给出了“耦合旋转轴的19种方法”,以及“15种不同的凸轮机构”。另外一个电子类的手册,则图解了5种振荡电器:阿姆斯特朗振荡器、科耳皮兹振荡器、克拉普振荡器、哈脱来振荡器、瓦卡振荡器。这类手册提供了标准解决方案来解决那些重复性的问题,也可以为特定的用途进行修改。有时候这些解决方案是以适当的发明的形式出现的,最后成为了解决未解问题的正式答案。但是它们更多时候是因实践者找到了新的方式,即找到了一种新的、巧妙的组合现存组件或方法的方式,来解决一个标准问题。如果设计结果特别有用,就会被其他技术采用。通常它会先在共同体内部进行推广,之后再成为通用模式,这时它就变成了一个新的技术构件。
这个过程很像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所讨论的模因(meme,即文化基因) 9,的运作方式。模因,正如道金斯最初设想的那样,是类似信念、流行语、时装等文化表达的单元,它们在社会中被模仿、重复和传播。成功的解决方案和理念就是以这种方式在工程中起作用的。它们在从业者中也是这样被模仿、重复和传播的。它们是组合的后备元素。
THE
NATURE
OF TECHNOLOGY
技术思想前沿
一个解决方案如果被使用的次数足够多,它就成为了一个模块,并因作为适用于标准用途的模块而具有包容性,它自己也成为了一项技术。
事实上,如果被使用的次数足够多,一个解决方案,一个成功的组合就成为了一个模块。它会获得自己的名分,并因作为适用于标准用途的模块而具有包容性,同时它自己也成为一项技术。当一个新的术语可以概述某些复杂的想法的集合,并且成为词汇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的时候,就会有与之并行的相应的语言产生出来。“水门”或者“慕尼黑”就是源于对一系列特定的、复杂的政府过失或谈判过程的概述而建构起来的。现在,“某某门”和“慕尼黑”已经固化为独立的名词,用来表示政府过失或政治绥靖。它们已经成为语言中的构成模块,被加入到构成英语的整体元素中了。
这种机械主义的解决方案能产生建构达尔文主义的模块吗?正如我所描述的,它听起来很达尔文主义。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多样的,其中较好的会被选择并自我传播。但是我们需要注意:解决方案并不是像生物进化那样一步一步地变化而来的,它们是快速聚集起来的组合,并且以解决问题为目的。
准确来讲,解决工程问题的过程产生了新的解决方案——某种新颖的组合,但按照达尔文的说法,它不是渐变的,而是以突变方式到来的。较好的方案会被选择,并依照达尔文方式通过工程实践进行传播。最后,一些解决方案将成为建构新技术的元素。产生技术构件的最基本的机制是组合。达尔文机制在随后的选择过程中起作用,其结果是只有某些解决方案能够存活下去。
顺便说一句,这种选择并不意味着技术中最好或最适合的解决方案总会存活下来。当针对工程中给定问题的几种解决方式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认为这种竞争是为了应用——为了能被工程设计者所采用。随着解决方案越来越得到普及,它也越来越显眼,从而更可能被其他的设计者所采用和改进。小的偶然事件,例如谁在什么时间和谁提到过某个解决方案,谁的方法在贸易杂志上被提到过,谁推销过某个解决方案等,都有可能推动某个解决方案,使其领先一步。因此它会被其他设计者更进一步的采用,进而在它的域的实践中被“锁定”(lock in)。在过程中获得主导地位的解决方案肯定是有其优点的,但是不一定非得是竞争中最好的。它可能是非常偶然地在竞争中占据优势的。
一波流行引发另一波流行,然后被锁定,这是一个偶然的过程。这一点我已经在前面集中描述过了,所以不再赘述。可以肯定地说,流行的技术(或解决方案)更趋向于获得进一步的优势,继而被锁定,所以在技术“选择”中,存在一个正反馈过程。
你可以在核电站的核反应堆设计案例中看到这种正反馈。这里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冷却材料的选择:用什么将热量从反应堆的核心部分传输到涡轮机?另一个问题是慢化剂(moderator)的选择:用什么控制中子的能量水平?在核电技术发展的早期,对此曾经有很多建议——‘啤酒’,一位工程师说道,这是目前唯一还没试过的慢化剂。有3种方案曾经被广泛地开发:轻水(H 2O),同时用于冷却和慢化;重水(D2O),同时用于冷却和慢化;用气体(通常是氦气或者二氧化碳)进行冷却,用石墨进行慢化。
不同国家、不同公司都经历过这些方案开发过程。加拿大倾向于使用重水方案,因为它有水力发电那一套技术用来进行重水制取;英国曾试验过气体–石墨方案,但都没有成功。美国则同时使用了几种方案。最后,美国海军在海曼 ·里奇欧文(Hyman Rickover)上将的领导下,开发了核潜水项目。 10尽管钠可能更有效,并且体积也更小,但是钠在水中会爆炸,暴露在空气中则会燃烧。由于担忧潜艇内的钠泄漏,里奇欧文最终为他的潜水艇选择了轻水冷却。此外,工程师更熟悉压缩水,因而没有对液态钠系统进行更多的尝试。
1949年,苏联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美国的一个反应就是想通过他们拥有的核反应堆来彰显其核优势,所以美国原子能委员会(U.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在里奇欧文的建议下,在宾夕法尼亚的海港将本来打算用于航空母舰的反应堆重新设计成供陆地使用。新的反应堆和以前用于海上的反应堆一样,也采用轻水慢化。后来,西屋电气和通用电气开发出来的反应堆也都是采用轻水模式。史学家马克·赫兹加德(Mark Hertsgaard)对此评论道:“这为轻水模式奠定了里程碑式的开端,其他方案无法与之匹敌,从而使该产业将它的商业前景实际上置于某些专家认为的经济和技术上都较弱的一种设计之上。”
到了1986年,世界范围内(前苏联除外)的101个反应堆中,有81个都建立在轻水基础上。轻水解决方案占据了主导地位。 11它虽然始于小的偶然事件,但将继续占据未来设计的主导地位。最终流行起来的技术是被从几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中选择出来的。但是,正如后来的研究指出的那样,它不一定是最好的。
在我研究“标准工程”之前,我不曾奢望它能对技术创新和进化有多么大的贡献,但是正如你从本章看到的,我现在改变看法了。标准工程中的每一个项目都会使一系列问题显现出来,每一个解决的结果都是一套对应的解决方案。可用的解决方案被建构并在实践者中传播,其中一些可能变成技术名词,进而变成未来技术的建构元素或模块。标准工程对创新和进化都贡献良多。
在第6章,我将转到另一个话题:新技术(不是指已有技术的翻版)是如何诞生的。换句话说,就是发明是如何形成的。在这之前我需要澄清一点,许多目的系统(贸易公约、侵权行为法、工会、货币系统)都是全新的,它们没有所谓的“前身”,但是它们也不总是被刻意发明出来的,如此说来,它们存在于标准工程和发明之间。那么我们需要如何对待这样一个范畴呢?
我们注意到,上述目的系统是一个缓慢的随着时间呈现的过程,这和标准工程中解决方案的产生很相似。工会实际上不是被“发明”出来的,它们是从中世纪的雇佣工互助联合会,即共谋兄弟会的形式中衍生出来的。从早期的记录中你甚至可以目睹它们的形成过程:
剪羊毛的人“常常在城里所有同业市场之间转悠,他们会借此进行一些密谋,比如命令所有同业中人停止工作,或者不为自己的主人服务,直到主人和奴仆之间或市场之间达成某种共识”。 12
我们看到了工会的一种新形式的形成过程(其内核则来自14世纪)。几百年来,始于社会实践的工会经历着成长、夯实、发展,并且应环境的要求呈现出不同的形式。
这类偶然形成的事情并不罕见,在此无须赘述。考虑到我们的主张,我们只需注意到,新的目的性系统(作为解决经济或社会问题的实践或者惯例)可以在不经意中产生,而且如果确实能起作用,它们将继续成为更广泛的系统的组件。在本书中,我们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严格意义上的主动创造新技术,即发明这件事情上,所以让我们继续追问它们是如何形成的吧。
达
尔文生物进化论最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新物种是如何产生的?” 1类似地,我们理论的核心问题是:根本性的新技术是如何产生的?当然我说过,不能简单地用达尔文进化论来解释技术。比如,我们不能说喷气式发动机是由此前的发动机经过自然选择获得的微小变化的积累而产生的,也不是简单地将现有的技术碎片在头脑中或现实中囫囵地加以组合就能产生的。正如熊彼特所说:“无论你如何重组邮政马车,你永远不能因此而得到铁路。” 2这并不是否认组合原理,而是强调了创新会涉及更多的秩序性,而不仅仅是纯粹的随机偶然性的结果。
那么,新技术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
我们实际上也可以这么问:发明是如何发生的?奇怪的是,尽管这个问题很重要,但是在关于技术的现代思考中却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最后一个将发明理论化的尝试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但是接下来的数十年间,这个主题却被搁置了。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创造行为”的核心部分被认为是没办法进行评估的。因此,发明在技术中占据的位置就像是心理学中的“心理”或“意识”,人们愿意谈论它,但是并不想真正解释它是什么,教科书常提到它,但也仅是一带而过,以避免对诸如“它是如何运作的”这样的问题作出解释。
我们确实知道一些关于新技术是如何诞生的故事。我们知道(大多数是从社会学研究中获得的)新技术是由社会需求形塑而成的;它们主要来自于标准域以外的经验;它们更经常地在鼓励冒险精神的环境中产生;它们更容易在伴随知识交换的过程中产生;它们经常会在网络中得到促进。没错,这些解释都对,但是它们在解释“一项新技术是怎样形成的”这个问题上,除了指出“种子发芽是由于有合适的土壤”之外,并没有给出更多的洞见。
因此,对于技术产生的最核心部分,在历经几十年才能形成的经济结构的核心部分,以及我们所成就的人类福祉的基础部分,却依然是一团谜雾。
构成经济的装置、方法和产品到底来自于哪里?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过程?这是我们的问题。
什么样的技术才算新技术
首先我们需要弄清楚,什么样的技术能被看成是一项发明呢?什么样的技术才符合根本性新技术(那些在深层意义上与以往不同的技术)的定义呢?我在这里将根本性的新技术定义为:针对现有目的而采用一个新的或不同的原理来实现的技术。原理就是做某件事情的操作方法,使某事运作的基本方式。
THE
NATURE
OF TECHNOLOGY
技术思想前沿
新技术是针对现有目的而采用一个新的或不同的原理来实现的技术。新技术是在概念当中或实际形态当中,将特定的需求与可开发的现象链接起来的过程。
对于我们通常认为的发明,这样的界定对吗?20世纪70年代,计算机打印是通过行式打印机来实现的,其实质就是带有固定字母的电子打字机。随着激光打印机的发现,计算机打印开始通过引导激光在硒鼓上“打印”文本来实现了。在20世纪20年代,飞机动力是通过活塞式螺旋桨推动的,随着喷气式发动机的发明,飞机动力改由汽油涡轮发动机产生反推力来实现了。这采用的是不同的原理。20世纪40年代,数字计算是通过机电方式实现的,随着计算机时代的到来,数字计算通过电子中继电路得以完成。在这些案例中,新技术的形成(激光打印机、涡轮喷气发动机、计算机)都是源于一个新的或不同的基本原理。
原理中的某个变化使发明,即根本性的新技术产生的过程,从标准工程中分离出来。如此一来,我们可以分辨其中关键的差异仅仅是改进还是真正的原创。我们说,波音747是波音707的改进,而不是一项发明。它是对一项现存技术的发展而不是全盘应用新的原理。我们说,瓦特蒸汽机是纽可门蒸汽机的改进,因为它只是提供了分离式冷凝器这个新的组件,但是没有应用新原理。(当然,在商业上,有时候改进比纯原始性发明更重要。)这样看来,判断一个技术是否是真正的发明,我们仅需要通过判定对当前的目的起作用的是否是一个新的、不同以往的根本性原理即可。而这样一来,却可能导致出现一个判定的灰色地带,马亚尔的加筋甲板(stiffened deck)是一个改进的组件,还是一个新的原理?它两者兼有。依据根本原理新颖性的程度可以产生一个连续统一体,而它存在于标准工程和根本的新颖性之间。
我们依然没有找到一个关于新技术如何形成的准确理论,但是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有效的标准来衡量什么算是合格的“新”,我们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入探讨。
一项新技术是怎样产生的呢?
我们现在思考的基点是新技术(发明)应该应用新原理。我说过,原理就是应用某种现象、概念或理念。所以当我们说技术建构在新原理之上,实际上是说它建构在新的或不同的一个或几个现象之上。这强烈地暗示了新技术是从何而来的。新技术是在概念或实际形态当中,将特定的需求与可开发的现象链接起来的过程。我们可以说,发明是将需求和一些现象链接起来,并能令人满意地满足那个需求的过程。(当然与标准工程比起来,这个原理或这个现象的应用对于那个目的来说一定是新的。)
我发现勾勒出这个链条很有用。链条的一端是“需求”或“目的”;另一端是能达成需求或目的的基本“现象”。在两个端点之间是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即新的原理或现象被用来实现目的的过程。但是如何使新原理恰当地起作用,也是个颇具挑战性的过程,这需要它们继续寻找各自的解决手段。整个过程通常是以系统或集成的方式使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的过程,我们可以将其想象为解决问题的链条上的一系列环节。
这个比喻还远没结束。每一个环节反过来又都有其自身的任务,并可能因此需要接受属于它的挑战。它可能因此又需要它自己的次级链接,或者次次级解决方案。是的,不用感到惊讶,链接过程也是递归性的。它包含链接——解决——进一步的次链接——进一步的解决,并且它们可能又需要它们自己的解决方案或者发明。我们可以将发明看作集成这些链条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会持续下去,直到每个问题和次问题都能找到现实的解决方式,直到链条完整为止。
在实际中,链接过程会相当不同。一些发明可能是单兵作战,另一些则是团队行动;一些拥有巨资资助,另一些则依靠微小资金的努力;一些需要经过经年累月的试错,并显然产生了一系列不能完全实现目标的中间版本,另一些则好似无中生有般突然呈现。
THE
NATURE
OF TECHNOLOGY
技术思想前沿
发明有两大模式:
• 肇始于链条的一端,源于一个给定的目的或需求,然后发现一个可以实现的原理。
• 发轫于链条的另一端,从一个现象或效应开始,然后逐步嵌入一些如何使用它的原理。
但是无论发明过程多么变化多端,最终我们都可以将它们归为两大模式。它可能肇始于链条的一端,源于一个给定的目的或需求,然后发现一个可以实现的原理。或者,它也可以发轫于链条的另一端,从一个通常是新发现的现象或效应开始,然后逐步嵌入一些如何使用它的原理。无论哪种模式,其过程都要等到将原理转译成工作元件之后才算完成。
两种模式会在很大程度上相互重叠,所以没有必要将两种过程都详细地加以描述。我将主要探究始于可见需求的那一类模式的过程,然后我再简短地补充一下始于现象的另一种模式。
找到一个基本原理
让我们假设发明起始于一个目的,为此要找到一个实现某种需求的解决办法。这个需求可能来自于某种经济机会新设计团队linux内核设计的艺术:图解linux操作系统架,一种关乎潜在市场利润的可能性,或者来自经济环境的变化、社会挑战、军事需求。
需求通常并不来自于外部刺激,而是源于技术自身。20世纪20年代,飞机设计者们认识到他们可以使飞机在高纬度稀薄的空气中获得更高的速度。但是在这样高的纬度上,往复式发动机甚至是压缩空气超动力发动机都无法得到足够的氧气,而导致螺旋桨缺少必要的“咬力”(bite)。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一个不同于活塞–螺旋桨(piston-propeller)的原理。
这种需求产生的方式很具典型意义。它们出现时常常只有极少数实践者知晓,同时可行的解决方案也还未出现。假设这时已经有了解决方案,那么标准技术就足以应付。但现在不行,因而如何定义问题本身就变成了挑战。那些接受挑战的人会遇到类似需要满足某个需求或需要克服某种限制的情况。他们很快会将挑战简化为需求——一个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喷气式发动机的发起者(originators,由于发明者inventor这个词常常蕴含“古怪而孤独地进行工作的人”之意,所以我不打算使用它)弗兰克 ·惠特尔和汉斯·冯·奥海因都意识到此前的活塞–螺旋桨原理的局限,因而需要寻找不同的原理。但是他们将这种需要重新表达为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一个需要满足的要求。惠特尔为此选择去寻找某种动力设备,要轻巧且高效,可以适应高纬度的稀薄空气,如果有可能,甚至可以不要螺旋桨。冯 ·奥海因则去寻找“稳定的奇热动力学流动过程” 3,意思是“当空气进到这个系统时,在遇到对马赫数敏感(mach-number-sensitive)的发动机元件之前会减速”。至此,需求已经变成一个被详尽描述的问题。
现在需要继续去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案。思想者(我暂且将发起者设定为一个人,而通常的情况都是几个人同时工作)开始专注在问题上,开始调查、搜索能够通过进一步发展来满足必要条件的可能性。这种搜索通常是概念性的、宽泛的、执着的。牛顿的一段很有名的关于他的引力轨道理论的评论是:顿悟来自于“连续不断的思考”。这种连续的思考允许潜意识工作,有可能从过往的经历中回想起某个现象或概念,而且它提供了一个潜意识的警觉,当一个可供选择的原理或界定问题的不同方式出现时,叩门声就会轻轻地响起。
这个阶段所追求的并不是完整的设计,正如我前面说过的,这时需要寻找一个基本的概念,即关于何种效应或效应组合作用时正好会解决问题的理念,以及关于达成这个理念所需要的工具手段的设想。
每个经过认真思考得出的备选原理又会带来自己独有的困难,这些困难将抛出新的次一级的概念性问题。因此“新障碍”等于是对待解问题进行了缩小或再定义。一旦思想者认识到一小部分问题可以被解决,其他大部分的解决方案就会跟进,或者至少会比较容易地落实到位。这是个在不同层级之间来回跳跃的过程,一会儿需要测试原理在某个层级上的可行性,一会儿需要解决它们在较低层级上产生的问题。
上文提到的整个过程如同预先策划登山线路一样。抵达顶峰相当于解决问题,预想一个基本原则如同设定一个从某个确定地点出发的比较可靠的整体(或至少大部分)的攀登线路。山上是障碍重重,充满了未知的冰瀑、裂谷、峭壁、雪崩和坠石。每一个新的原理(或者说攀爬的总体规划)都会遇到需要克服的困难。
此时,递归性又一次上演了,因为每一个障碍都变成了自身的次级问题,并需要各自的解决方案(次级原理或者次级技术)。直到完成了从出发地到山顶的可行的攀登规划之后,才意味着获得了整体的解决方案。
当然,我们可能曾经领略过这座山的某处风景,也就是说,某个次级技术是我们知道的,那么其解决方案就可能被采用。如此一来,整个过程更像将已知部分连缀在一起,而不是作为先锋去寻找一条完全陌生之路。这个过程也是递归性的,整个事件内部是级联关系,它形成了一个前进的计划,或者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技术的预想过程。
这些候选路径,这些原理,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它们来自几个方面。有时候原理是借用的,它们本来满足的是别的目的,或使用的是另外的域。惠特尔在1928年曾考虑了几种可能性 4:火箭推进力、转动式喷嘴的反作用力、使用螺旋的涡轮推力(涡轮螺旋桨飞机)、活塞引擎推动的管道排风机(reaction jet),以及所有这些问题引发的次级问题。这里的每一种可能性都借用了本来服务于其他技术目的的原理。
THE
NATURE
OF TECHNOLOGY
技术思想前沿
原理从何而来?有时候原理是借用的;有时候原理来自于以前概念的组合;有时候原理来自于对过去的回顾;有时候原理是和现存功能性结合在一起出现的。原理来自于已有的其他设备、方法、理论或功能之中,它们从来都不是无中生有的。
有时候,新原理来自于以前概念的组合。1940年,英国战争期间需要找到传输雷达微波的有效方式。物理学家约翰 ·兰德尔(John Randall)和亨瑞 ·布特(Henry Boot)一下子想到磁电管的原理 5—— 一种被用来服务雷达目的而产生微波,利用磁场控制电流的圆柱状电子管。为此他们将电磁管的高能量输出和电子速调管利用共振腔扩大微波的优点组合了起来。
有时候,原理来自于对过去的回顾,或者从同事的谈论中偶然获得,或者由理论而来。实际上,兰德尔曾经偶然在书店看到了赫兹(Hertz)的《电波》( Electric Waves)的英译本。这本书使他想到了圆柱谐振腔——基本上就是赫兹在他的书中所分析的三维的线圈共鸣箱。
有时候,原理(一种概念上的解决)是和现存的功能性结合在一起出现的,每一次出现解决一个次生问题。1929年,欧内斯特 ·劳伦斯(Ernest Lawrence)找到了使带电粒子加速以实现高能粒子对撞技术的方法,即粒子可以被电场加速。但问题是,当时人们还不知道如何获得产生高强度电场的极高电压。直到有天晚上,劳伦斯在大学图书馆浏览学术期刊时,发现了挪威工程师罗尔夫 ·威德罗(Rolf Wideroe)写的一篇文章。罗尔夫 ·威德罗的想法是用低电压交流电使粒子反复振荡进行加速,这样就回避了高电压问题。他建议通过一系列首尾相连的管子来传输粒子,管子和管子之间有小的缝隙。管子的安排要恰到好处,即粒子一定要在交流电的峰值通过缝隙的时候同时到达。但是这意味着当粒子运动越快,管子的长度就需要越长。劳伦斯看到了这个方案的精妙之处,但是他算了一下,如果想达到他要的能量,管子就要伸到实验室的窗户外面去了。(按照现在的观点,管子的长度需要达到2英里。)威德罗的想法在劳伦斯看来不具可行性。
但是就像当时任何一位物理学家一样,劳伦斯知道,磁场可以引起带电粒子在回路中运动。我问我自己:“是否可能用两个电极管一刻不停地输送阳离子(粒子),通过某种合适的磁场排布,让它们在电极管中来回运动。” 6换句话说,可以通过只使用两根管子,将它们弯成两个半圆,中间有缝隙,然后使用磁场驱使粒子在这个环形回路中来回运动。接着他让威德罗的恰到好处的交流电通过缝隙,这样粒子就在每次通过缝隙时被加速了。当它们不停地旋转运动时,就可以被加速、盘旋,最后被高能释放。
这个原理最终演变成了回旋加速器。它的实现过程是:将问题从如何获得高电压转变为如何使用威德罗提出的低电压交流的次级原理,然后再利用劳伦斯的方法,用磁场来大大降低空间需求的次次级原理。此处获得的原理是在已存在的碎片(现存的功能)的基础上建构而产生的。
在所有这些案例中,原理都是来自于已有的其他设备、方法、理论或功能之中,它们从来都不是无中生有。7在发明的创造核心,呈现的是“挪用”(appropriation)的特征,是某种半意识形态的精神借鉴。
有时候,原理来得很迅速,只需花费很少的心力。但是更多时候,整个问题都藏在思想背后,被一些困难所困扰,并没有现成的原理摆在眼前,而且这种状况可以持续数月甚至数年。
解决方案有时候会突然出现,就像查尔斯·汤恩斯(Charles Townes)在讲述他发明量子放大器的过程时说的那样:“灵感倏然而至”。惠特尔也曾写道:
我在惠特灵时,突然间我的脑海中出现了这样一个念头,去找一个替换活塞发动机的涡轮机(用来驱动的压缩机)。这种变化意味着压缩机要有一个比我对活塞发动机的期望高得多的压力比。简言之,我又回到了燃气轮机上,但这一次是推进喷气式飞机,而不是推进压缩机。当想法初现时看起来怪怪的,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那个概念,而突然间它显得那样明显而且简单。计算结果使我确信这远远超出我的预期。8
灵感的显现就如同一个疏通堵塞的过程,经常是一下子就通畅了。要么是总原理找到了可以与之匹配的次级原理,要么是一个次级原理为主原理的应用扫清了障碍。这是一个连通的时刻。它在问题与能够解决问题的原理之间完成了链接。
使人感到惊奇的是,对于发现者来说,这个洞见是如此完整,让人觉得在潜意识中各部分已经被组合完好了一样。而且它一来,大家就“知道”它是对的——那是一种对其解决问题所具备的正当性、优雅性、非凡的简洁性的觉察。因为它总是从一个人的潜意识中涌现出来,所以洞察力通常来自个体,而不是团队。它一般不会在活动中或狂想时出现,却常常在静寂中到来。
灵感力的到来并不是过程的结尾,而只是一个标志。概念依然必须被转译为可行的技术原型。就像作曲家虽然在头脑中已有了主题,但是依然需要通过演奏来将之一起表达出来一样,原创者必须将工作组件组装起来,才能完成他的概念的表达。
概念的物化
概念物化的进程很可能早已开启了。一些设备或方法的概念通常在经验中已经被建构起来,某些基本概念也可能早已经在实践中被试验过了。所以发明过程的第二步和第一步通常是有重叠的。将概念完全实现,意味着详尽的细节建构;关键组件必须被制造出来、作出平衡并进行建构;要选择恰当的测量工具;要进行理论计算。这些建构需要背后的鼓励和资金支持。竞争在这个阶段是有帮助的。事实上,如果各竞争团队觊觎的是同一个原理,那么接下来的竞争一定非常激烈。
将理念变为现实的过程会带来许多挑战,这些挑战或许曾经在头脑中被很多次地预想过,而如今必须在真实世界中面对它们了:在提出解决方案的过程中,有时会经历失败,如零部件可能不适用,也许需要重新进行设计,也许必须要进行实验等。发明的第二步主要是寻找次级问题(subproblems)的解决方案,其中会包含许多标准工程的特征。
这一步所面对的挑战可能是巨大的。20世纪60年代晚期,施乐(Xerox)公司的盖瑞 ·斯塔克伟泽(Gary Starkweather)曾经探索一种不会受制于缓慢的逐行打印机(本质上的一种大型打字机)的限制,而能够直接打印数字化字节(例如,由计算机制造的图像或文本)的方法。最初,他曾经想到过用激光将图像“打印”到硒鼓上这一核心理念。但是在将概念付诸实际操作时,他遇到了几个困难,其中有两个关键性的难题亟须得到根本的解决:为了使打印过程可以商业化,必须将扫描文稿的时间控制在几秒钟之内,也就是说,为了得到高分辨率的扫描结果,需要激光束能够以每秒50万次的速率通过开关的通断得到调制,从而使黑点或白点留在硒鼓鼓面上。但在当时,以这样的速率调整激光是不可能的。同时,对于这个任务来说,激光和镜头上的所有模块(module)都太重了,这将带来过大的惯性,从而导致在以每秒数千次速率的扫描过程中出现持续反复的物理振荡。要完成既定的技术目标,这两个问题都必须得到解决。
斯塔克伟泽通过应用由一个压电单元驱动的偏振滤波器,开发出一个非常快的快门装置,从而解决了开关高速通断的问题。9通过利用一个旋转多楞面镜,可以使激光束移动,而激光模块却可以保持不动,这样就解决了惯性问题。当多棱镜转动的时候,每一面都可以扫描硒鼓上的一窄行,这很像灯塔发出的光束横扫过地面时的情形。但是这个解决方法随即带来了它自己的次生问题。斯塔克伟泽经计算发现,棱镜相邻的镜面的紧密度公差(tight tolerance)必须是准确的6弧秒,否则相邻的扫描行就不能很好地相互弥补,从而出现扭曲。但是,加工到那种精细的程度在成本上是不可行的。一款精心设计的柱透镜(斯塔克伟泽是主修光学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可以确保相邻行不至非常紧密,这样即使镜面轻微错开也不要紧。
当你听完斯塔克伟泽的故事后,印象最深的应该是他所面临的选择。每个次生问题都可能有几种解决方案。斯塔克伟泽选择解决方案、检验它们的可行性,并努力从中组成和谐的整体。当需要找到次生或次次生问题的源头时,他就向下拓展这一梯式递归进路,如果这些问题得到解决或被放弃了,他就再向上回溯。这个过程几乎总是很漫长,只有当获得了必要的知识,并且次生技术带来的挑战已被成功地克服后,才能向前迈一大步。前进的方向总是沿着运行恰切的版本向前延伸的。
最早的导航装置是一个很具说明性的例子。尽管它最初看起来并不完善,然而它诞生的那一刻却弥足珍贵。所有关于其起源的叙述都会记下那粗糙的集成闪烁出生命火花的时刻。在这一刻,原理得到了自证。成功了,一个里程碑过去了,让我们为那些时刻而欢呼。“1954年4月初的一天,我和我的学生们正在进行一场研讨会,吉姆 ·戈登(Jim Gordon)突然闯进来”,汤恩斯(在谈论微波激射器的发明时)回忆道,“他翘课是为了完成一个实验。他高呼他成功了!我们立刻停止了讨论,和他一起奔向实验室去看振荡的证据,然后就开始庆祝他的成功了。”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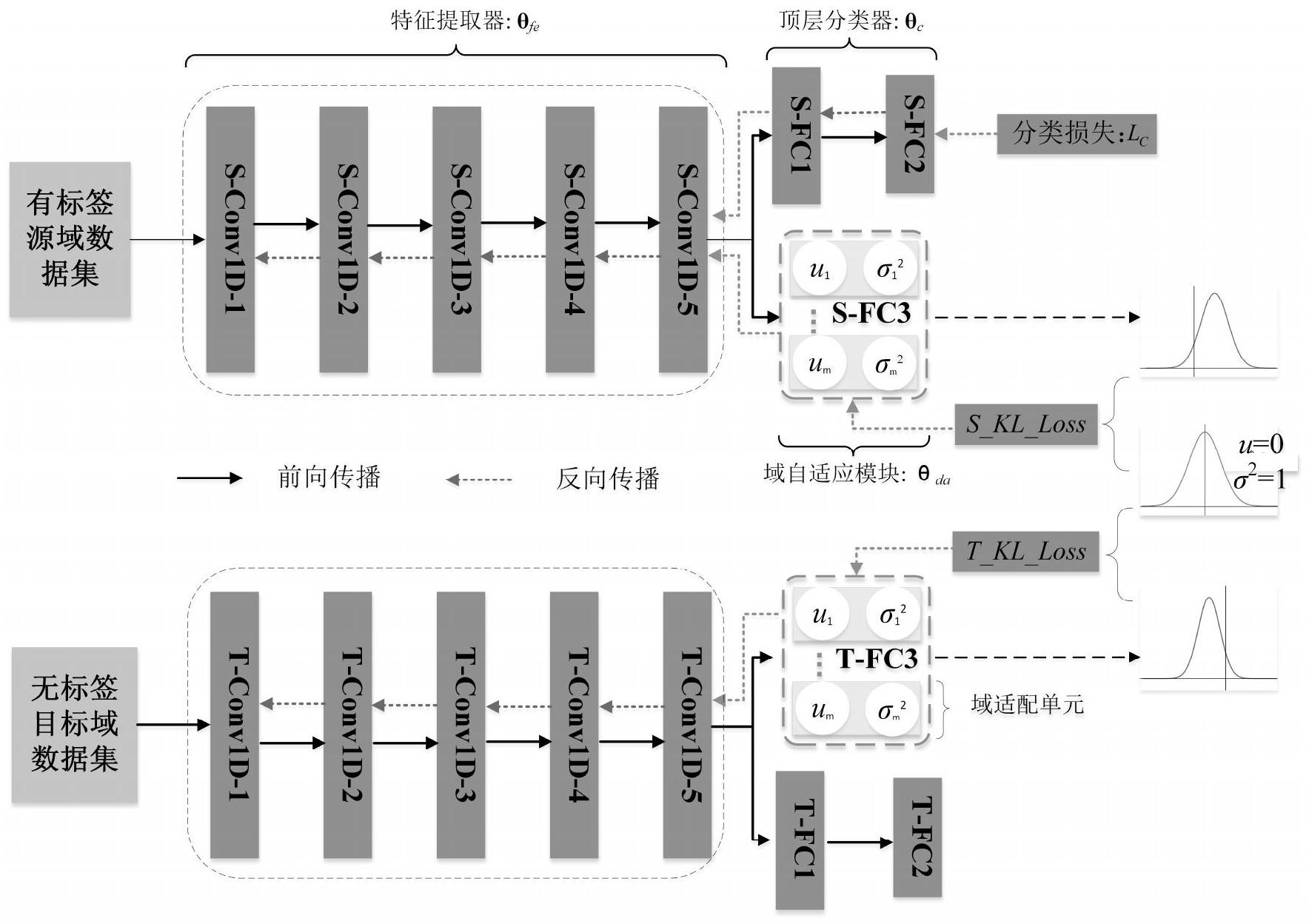
最初的呈现可能真的很微弱,但是随着进一步的努力、自组织性的修复以及随后呈现的更棒的建构,巩固的工作状态就浮现出来。这时,一个新的基本原理就进入到一种基本可靠的状态了,即它具备了物理形态。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它考验着赞助者和主管们的耐心。在这段时间里,最为必要的人类品质就是意志力,一种要赋予原理以生命,使其成为有效实体的意志力。到目前为止,一个新装置或方法又成为进一步开发并进行商业应用的候选者了,如果足够幸运,它就有可能作为某种创新进入经济领域。
发明,作为一个过程,现在完成了。
基于现象的发明
我们简单地谈两句发明的另一个过程——始于现象的发明过程。这个过程也是现象和目的的链接过程,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过程开始于现象一端。通常,当人们注意到了一个现象或拥有了关于该现象的理论时,就意味着有了一个如何使用它的理念、一个原理。和始于需求动机的过程一样,接下来的过程也同样是建构出支撑组件来将原理转译成现实的技术。
始于现象的发明过程似乎应该简单些了。一个现象可能直接就暗示了一个可应用的原理,而且通常的确如此。但是有时这种暗示也是不清晰的,比如1928年亚历山大 ·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那个著名的发现就是如此。“他当时注意到一个现象,即一种霉菌(后来被证明是青霉菌的孢子)中的某种物质可以抑制葡萄球菌的生长,他随即意识到这可以用来治疗感染。这一存在于现象和应用之间的联系在回顾时很清晰,但实际上还有许多人,比如物理学家约翰 ·廷德尔(John Tyndall)在1876年,安德烈 ·格拉提(Andre Gratia)在20世纪20年代都曾经先于弗莱明注意到了这个反应,但他们却都没有预见到它的医疗用途。弗莱明“看到”这个原理是因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经是医生,对于战地感染造成的伤亡曾感到震惊,因此他更容易发现一个看似无用而实际上意义重大的现象。
即使应用原理清晰可见,技术实践的转译工作也并非轻而易举。通常的情况是,如果效应(effect)是新颖的,就不易被理解,同时相应的技术工具可能还未被开发。例如,将青霉菌现象转化成可用的治疗方法首先意味着对青霉菌中的活性成分进行隔离和纯化;接着需要弄清楚它的化学结构;然后需要经过临床试验检验其疗效;最后还要进行生产方式的开发。这一整套步骤完成下来,已经远远超出了弗莱明的能力范围,它需要集结高度专业化的生物化学专家们来共同完成。最终这一计划是由牛津邓恩病理学院(Oxford’s Dunn School of Pathology)的霍华德 ·弗洛里(Howard Florey)和恩斯特 ·柴恩(Ernst Chain)领导的生化学家团队来执行的。13年之后,弗莱明的发现才转化成实际可行的技术产物——盘尼西林。
我曾经说过,发明或者始于需求,或者始于现象,但是读者可能会反对说,有许多发明并不是这样的。莱特兄弟确实不是从需求或现象出发的。自力推动飞行器的愿望以及实现它的两个基本原理(通过轻体内燃机推动、通过固定式机翼飞行)在许多年前就存在了。事实上,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基本技术原理和对应的需求经常一起被发现,而能将其变为现实的次生原理和元器件则可能要等到数十年后才会被人们发现。莱特兄弟所要做的是解决阻碍原理被转译成可行技术的四个关键的次生问题。通过认真地实验和无数次尝试,他们终于解决了飞机控制及其稳定性的问题,发现了机翼对飞机上升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建造了轻体推动系统,开发出了高效推进器。他们1903年的那次动力飞行不能作为对一次“发明”过程的完整解释,它只不过是前人踩踏出的漫长小路上的一个标志而已。
莱特兄弟的案例并没有形成其他不同的发明模式,它只是我描述的两种模式的一个变种。基本原理有时会自然呈现,有时会突然出现。困难之处在于如何使原理正确地发挥作用,这可能需要漫长的努力。
什么是发明的核心
关于发明我已经说得够多了。发明的核心在于发现合适的可行性解决方案,即“ 看见”合适的工作原理。剩下的,夸张点讲,就是标准工程了。有时候原理显而易见并容易借鉴,它会自然而然地呈现。但大多数情况下,它需要进行深思熟虑地心理联想,那好似一个在头脑中进行的链接过程。
那么这种心理链接过程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呢?12
回到劳伦斯案例。我们注意到,开始时他并没有想到后来那个最终解决方案,即将一个电磁铁与一个产生于在两个D型容器之间的振荡射频电场组合起来。他思考的是如何将可采取的行动和可利用的效应(功能)组合起来,并达成解决方案。换句话说,他是将问题和解决方式联系起来,并且想象当某些组合构成后会发生什么。
劳伦斯的洞察力固然是深邃的,但这只是因为他所利用的不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功能。从原理上看,劳伦斯的问题和我们日常面对的问题其实并没什么不同。当我的车还在修理店里而我却想去上班时,我可能会想:我可以先坐地铁,之后换乘出租车,或者我可以搭朋友的车,又或者我可以在家工作,只要我能在我的小窝里腾出块地方就行。我在我的日常功能储备库中搜寻,选出一些加以组合,并考虑每种解决方案所带来的次生问题。当我们看到这种方式应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时,会感到这种推理并不神秘。其实在发明中,它也没什么不同。可能它发生的领域是我们不熟悉的,但是那一定是发起者所熟悉的。发明的核心是心理联想。
我在谈论劳伦斯那类的心理联想时用到了功能性。发起者进入功能库中去想象,如果某些功能组合起来会发生什么。但有时联想直接来自于原理自身。原理经常跨界工作。例如,哪里有波(声波、洋流、地震波、无线电波、光波、X射线、粒子),哪里就有干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波能产生叠加)、频谱、共鸣系统(以其固有频率振荡)、折射(当进入一个新介质时,波会改变方向),以及多普勒效应(如果波源相对于我们运动,频率会有可被感知的变化)。所有这些都会提供一个可以利用的概念——原理,它们反过来也可以从传统“域”中借用过来,并应用到新“域”当中。发起者想到需求功能:如何才能测量运动?如何才能在一个特定的频率中制造一个稳定的振荡?然后他会从某些已知的领域开始联想,并借用其中的原理。兰德尔借用了赫兹的感应线圈原理,并且设想它在三维模式中如同圆柱谐振腔一样工作。当发起者需要一个特定功能的时候,他们可以回过头联想他们知道的、在某一领域内产生过相应功能的原理。这一机制的核心称为原理转换(principle transfer),它是“发现”的一种类比,这是另一种心理联想的形式。
我说发明的核心是心理联想,但并没打算排除想象。恰恰相反,发起者必须具备足够的想象力去理解问题,这是第一位重要的,然后才是预见它如何被解决、有多少种解决方式、必要的组分及结构是怎样的,以及如何解决随机出现的那些还不可见的次生问题。但是这类想象绝不神秘。发起者的共同之处既不是“天赋”,也不是某种特殊的能力。实际上,我不相信有天赋这类东西,我只相信对巨大的功能和原理库的占有能力。发起者通常很熟悉他们即将应用的原理、现象的相关实践或理论内容,惠特尔的父亲是一位机械师和发明家,因而惠特尔从小就对涡轮机很熟悉。
然而,发起者不仅要掌握某种功能性,并在他们伟大的创造中一劳永逸地用一次,还要更频繁地面对冗长的功能集结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无休止的、如同钢琴五指练习般的针对微小问题的试验过程。在和功能性打交道的这个阶段,经常可以看出发起者试图利用某种现象的蛛丝马迹。在查理·汤恩斯的伟大发现完成的5年前,他就曾在他的备忘录中提到微波无线电 “已经可以利用如此短的波长,以至于已经和对分子共振有丰富研究的量子力学理论和光谱分析技术有了部分重叠,这可能会对无线电工程有巨大帮助”。而他正是用分子共振来发明微波激射器的。 13
我们可以看到功能性的专业知识聚集过程,通常这个过程在发起者眼中都是理所当然的。生化学家凯利·穆利斯(Kary Mullis)认为他的聚合酶链反应计划(从单一DNA样品复制出含有大量DNA拷贝的DNA链)非常简单。“它太简单了……所涉及的每个步骤都已经完成了。” 14但是穆利斯的“简单” 解决方案是 “通过往复促成与带有特殊DNA顺序的独立各股相杂交的两条引物的交互延伸来放大DNA”。这就意味着首先要找到一段DNA原本,然后标出待复制片段的首尾,接着将DNA双螺旋分离成两条单链。一旦原本被加入,双链就可以使用一种被称为聚合酶的酶开始复制,连接互补成分形成两个新的双螺旋。重复这个过程使得新的双螺旋以2、4、8、16的倍数无限地进行复制。穆利斯口中的 “简单”,只是对像穆利斯这样的对DNA功能非常熟悉,操作也非常有经验的人来说,才是简单的。
因果性金字塔
我在本章已经描述了作为微观过程的发明,即一个人(或几个人)提出一种新的做事方法。但是它一定是发生在某个情境中的,换句话说,新技术一定衍生于此前已经存在的组分或功能之上。这样的观察可以使我们如同透过广角镜一样看到更全面的发明过程:新技术实际上是由先前作出铺垫的一系列设备、发明和理解的堆积而形成的山峰。
事实上,我们可以假定任何新设备或新方法都是一座通向顶峰的因果性金字塔。那是一座应用共同原理的技术金字塔,一座包含所有对此新技术有所贡献的先驱技术的金字塔,一座包含那些使新技术成为可能的支撑原理或组分的金字塔,一座包含使这些新技术成为可能的、但是曾经一度是新现象的金字塔,一座包含用于新技术中的仪器、技术以及制造过程的金字塔,一座包括先前工艺及其理解的金字塔,一座包含用来描述现象的语法以及所用原理的金字塔,一座包含在这些层级上人们之间互动的金字塔。
在这座因果性金字塔中,特别重要的是随时间增长的知识的积累,既包括科学形态也包括技术形态的知识。正如历史学家乔尔·莫基尔和埃德温·雷顿(Edwin Layton)指出的,这种知识不仅存在于工程实践自身当中,而且也存在于工科院校、学术团体、国家科学院、工程院以及公开发行的出版物当中。 知识构成了新技术呈现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基础部分。
这一更为宽泛的视角15与我们前面的论述并不矛盾。这个因果性金字塔对发明的宏观过程的支撑,非常像战争中后勤系统对部队的支撑。事实上,可以用历史因果性的解释来替换我这种个人用法。这就像解释滑铁卢战役时,其军事作战兵力、文化、培训和设备,其先前的成就,以及他们的补给线都可能成为解释战争胜利的原因,但我们往往将赢得战争的原因更聚焦于在实际战斗中发生军事冲突的紧急时刻所作的决策和采取的行动等方面。
说新技术拥有因果性历史并不表示它们的出现是可以预先确定的。发明取决于奇思怪想和发现新现象的时机,还取决于新需求的出现,以及对此作出回应的人的洞察力。同时,由于所有发明都会受到因果金字塔支撑,这也意味着当必要性和需求的碎片都一一铺垫到位之时,一项发明就将显露。
这种时机呈现过程中粗略的“就绪状态”使得一项新技术很少拥有唯一的发起者。几位颇具代表性的发明家可能会几乎同时想到同样一个原理并准备付诸实施。众多的努力以及关键部件的加入使得我们实际上很难从“第一”这个意义上来讨论“发明”。更多时候,我们可能看到部分原理以与从前相关的方式出现或者只是以往形式 16的重新体现,我们无法很好地领会它们,但实际上它们有共同的出身。我们总能看到一个系列产品的原初版本是由不同的工人互相借鉴着开发出来的,只是随着新的次级技术的出现,设备和方法才从最初的粗糙状态逐渐变得精致起来。以计算机为例,它实际上并不很像“发明”。我们可以说克劳德 ·申农(Claude Shannon) “看见”了利用电子传递线路进行算术运算的基本原理,然后原理的实践转译版本被建立起来,之后通过互相借鉴,加上组件的连续改进,最终完成了计算机的发明。因此,计算机的发明不是一蹴而就的。
如同上述情形展现的那样,设定一项所谓的“发明”是困难的。现代关于技术的有些论述已经谈到这一点。计算机先锋迈克尔 ·威廉姆斯(Michael Williams)就认为:
与人类发明相关的活动中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第一”。如果你加上足够的形容词来描述,你总是可以声称你找到了你认为的第一。例如ENIAC(Electronic Numerical Integrator and Calculator,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经常宣称自己是“第一台电子、通用、规模化、数字计算机”。但是,在你有一个正确的陈述之前,你一定要加上所有这些形容词。如果离开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那么,像阿塔纳索夫–贝瑞计算机(ABC),“巨人”(colossus,美国海军水下声呐探测潜艇警报系统的代号),楚泽(Zuse)的Z3计算机(德国康拉德 ·楚泽开发的第一台采用二进制和布尔逻辑的可编程计算机),以及许多其他设备(甚至一些根本没有建造的机器,如巴贝奇的分析机)都将成为“第一”的候选人。 17
威廉姆斯是对的。事实上,由于同样的原理会被许多人想到,以及将原理付诸实施的行动的多样性,这通常使得将“第一名”的殊荣完全给予某一个人或某一组人都显得缺乏说服力。如果一定要把“第一个”发明的荣誉归功于谁,那么一定是那个第一个拥有清晰原理的人或团队。他们看到了原理的潜力,努力使其获得市场的接纳,并最终令其获得充分的使用。但通常会有好几个这样的人或团队几乎同时存在。
其实即使是一个单一的发起人,由于人际互动和信息网络18的存在,也已经大大扩展了我描述的那个发明过程。这些交流会使发起人沉浸到相关问题和先前所进行的尝试当中,并提供原理在其他域中应用的建议以及相关的设备和技术诀窍,从而有助于将概念转变成物理实在。
科学与数学中的发明
我所描述的关于发明的逻辑结构能否被拓展到科学和数学的起源上呢?我的回答是:如果加上一些必要的变化的话,是可以的。理由是,不论科学理论还是数学理论,其目的与技术一样,都是要使其系统化。它们的结构来自于那个完成给定目的的组件系统,因此,技术的逻辑同样可以应用在它们之上。
让我用一个读者耳熟能详的科学例子来阐明这一观点。在达尔文完成贝格尔号航行后大约一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寻找一个关于物种进化的理论,来解释诸如他在加拉帕戈斯群岛观察到的不同种类的雀类是如何形成的问题。从他的阅读和经验当中,他将一组事实和观点放在一起,这可以帮助他找到一个支撑原理:进化的时间尺度与地质时间是相符合的;个体应该是物种形成的中心元;性状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遗传;变异可以使物种适应缓慢变化的环境;在个体生命过程中获得的习性,可能会以某种方式促成可遗传的变化;动物饲养员可以选择他们想要的对遗传有利的特质。事实上,“我很快就认识到选择是人们成功获得动植物育种的基石。但是选择是如何被应用于生活在自然状态中的生物身上的,对我来说还是个谜”。达尔文纠结于这些不同的候选组件将如何共同建构起一个关于物种进化的解释。
在1838年,达尔文写道:“我为了消遣,碰巧阅读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并为去理解书中随处可见的生存斗争的论述做好了思想准备。这种准备来自于我对动植物生活习性的长期观察。醍醐灌顶般地,我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有利于生存的变异将会被保存下来,而不利的将被摧毁。结果就会形成新的物种。这时,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有效的理论。”
用我的话来讲,达尔文并没有从马尔萨斯那里得来理论,他只是借用了一个次级原理:对稀缺资源的持续的竞争选择了群体中最具适应性的个体。然后他应用这个次级原理,使得他的两个主要原理之一成为可能:那些有利的适应会被选择,并被积累下来,从而产生新的物种。但对于另一个主要原理,即变异产生了一系列特征,在此基础上选择才得以进行,他还不能归纳出更好的解释,所以不得不将其作为一个前提。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将部分组合起来形成解释功能,使他找到了一个令他得以展开工作的理论。经过15个星期的艰苦思考,他完成了他的基本原理。而余下的工作,即运用所有的支持片段进行从基本原理到完整理论的细节转译,并最终使自己达到满意的过程,则用了大约20年。
科学理论化的起源说到底也和技术一样是一种链接,一种对一个可观察的给定问题与一个对此有模糊暗示的原理之间的链接。科学最后需要用一套完整的原理再现这一切。
数学中的起源又是怎样的呢?它也是一种链接。但这次需要被证明成为某些概念形式或原理的东西(通常是一个定理)共同构成一个证明过程。设想一个定理是一轮精心建构的逻辑论证,如果它是在已被接受的逻辑规则之下建立的,那么它就是有效的。这些规则来自其他有效的数学内容,主要包括其他定理、定义以及那些构成数学有效组件的辅助定理。
一般来说,数学家“看到”或模糊地感到一个或两个主要原理,即一种概念性的想法,然后以可证明的途径提供某种整体的解决方案来进行证明,这些用于证明的方案必须来自其他公认的次级原理或定理,最后再去除每个部分有争议的部分。安德鲁 ·怀尔斯(Andrew Wiles)对费马大定理的证明就是使用了日本数学家谷山纪章和志村五郎的模块化和椭圆方程作为基本原理来链接他需要的两个主要结构的。
为了证明这个猜想并链接构成争论的各部分,怀尔斯采用了很多次级原理(subprinciples)。“你翻到一个页面,就会看到那里有德利涅(Deligne)的一些基本原理的简短概观”, 数学家肯尼斯 ·里贝特(Kenneth Ribet)说,“然后你翻到另一页,多少有点巧合,你会看到赫勒高曲(Hellegouarch) 的原理——所有这些都会被召来参与并在下一个念头出现之前被短暂地利用。” 19这个整体是一种原理(概念性理念)的级联(concatenation),它们共同建构以达成目的。而每个原理构成或原理又都源于一些更早期的级联。和技术一样,每个链接都提供了一些通用的功能,一些构成争论的关键部分,它们被用于整体结构之中。
科学与数学中的原创和技术中的原创没有根本性的不同,我们不必对此感到惊讶。这种对应的存在不是因为科学、数学和技术是一样的,而在于三者都是目的性系统。广泛来说,也可视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因此需要遵循同样的逻辑。三者的构成都始于形式或原理:对于技术,是源于概念性的方法;对于科学,是源于解释性的结构;对于数学,则源于真理与基本的公理结构。因此,技术、科学和数学的产生都是通过类似的试探启发过程——基本上是通过存在于问题和能满足它的形式之间的一个链接来完成的。
发明与新的构件
我们现在有了关于“新技术是如何产生的”这个关键问题的答案了。其机制当然不是达尔文主义的。技术中的新物种并不是产生于微小变化的积累。它们产生于一个过程,一个人类的漫长过程;一个将需要和能满足需要的某个原理(某个效应的一般性应用)链接起来的过程。这个链接从需求自身出发,延伸到能够被驾驭的某个基本现象,再通过配套解决方案以及次级解决方案最终使需求得以满足,并且使其界定出了一个递归性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断进行类似的重复,直到每个次级问题消解到可以进行物理性解决的程度。最后,问题一定会被那些已经存在的片段、成分,或者那些由现存部分创造出来的片段所解决。发明是从已有之物中产生出来的。
我们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发明是如此不同了,因为每个个别的案例可以分别源于需求驱动或者现象驱动;发起者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很多人;发明原理可能很难被想象,也可能自然地就流露出来了;把原理转译为物理组件可能很简单,也可能只有当关键的次生问题被解决之后才能进行下去。但是无论它们经历了什么,最终所有的发明共享同样的机制:所有发明都是目的与完成目的的原理之间的链接,并且所有发明都必须将原理转译成工作元件。
那么在关于新技术如何从技术集合中建构出来的问题,上述论述又能告诉我们什么呢?将本章论述和第5章结合起来,我们可以说,新技术的产生有三个可能的途径:作为标准工程的解决(阿姆斯特朗振荡器),自发的发明(货币制度),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发明,即在全新的原理之下,全新的根本性解决(喷气式飞机发动机)。无论哪种情况,发明都是产生于那些提供了制造新元素必要功能的已有技术(现存的元素)的组合。
至此,我们依然没有完成对个体技术的解释,一项新的技术并不会就此停滞,它是会发展变化的,或者我们可以说它存在一种狭义上的“进化”过程,会呈现出一个改进的面貌,因而会建起一个家谱。如同发明自身一样,这种发展自有其独具特征性的阶段。那么技术的发展及其背后又隐藏着什么呢?
通
常来讲,一项新技术的最初版本都是粗糙的。在新技术发展初期,只要它能发挥基本效用就足够了,此时,它可能只是由现有构件或者其他技术中的零部件粗略地拼凑而成。劳伦斯最初的回旋加速器就曾用了一把餐椅、一个衣帽架、玻璃窗、封蜡,还有些黄铜当配件。诞生初期的技术只能以手边可用的组件作为基础,然后再作适当调整,并适当地扩展应用范围以尽量有效地服务于不同的目的。接下来,推动者会不断把玩这个新结构,并开始制造新配件。为此,他们需要试验更好的材料、发展理论、解决问题,当然过程中会常常碰壁。总之,这是个通过逐步的、试验性的努力取得进步和发展的过程。
THE
NATURE
OF TECHNOLOGY
技术思想前沿
技术的两种发展机制:
内部替换(internal replacement)和结构深化(structural deepening)。内部替换是指用更好的部件(子技术)更换某一形成阻碍的部件。结构深化是指寻找更好的部件、材料,或者加入新组件。
一项技术就这样开始走上一段发展和进化的旅程。1实际上,这段旅程可能早就开始了。在将基本概念转译成物理形式的过程中,人们就已经在试验不同的零部件了,并一直致力于寻求改善,因此,在技术的创始和发展之间,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
无论技术发展是怎样开始的,一旦上路了,技术的不同版本就会随即出现。其中一些版本出自技术的发起者,一些则来自侵入这一新领域的其他发展者,还有一些可能来自实验室或者一些寻求发展新技术的小公司。之所以这样,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行动者可能会有各自界定概念的视角;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新技术开始适应不同的目的或市场时,会发生相应的演变,这也会使技术慢慢呈现出不同的版本。2例如,雷达在实现了“探测飞行物”这个基本目的后,其功能就被分别拓展到探测潜艇、空中和海上导航,以及空中交通管制等许多分支领域去了。
不同的视角和应用分支为解决问题提供了不同的方案。我们可以说,是技术本身引起了解决方案的变化,是它自己表明或暗示了需要什么样的解决方案。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发者可以获得更大的空间去选择解决方案,这时达尔文理论中的变异和选择就真的在技术中开始发挥作用了。3通过选择更好的方案来解决其内部设计问题,技术的不同版本将逐步得到改善。
但设计师们也通过自己的深入思考来改进技术,对此达尔文理论是无法帮助我们弄明白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也无法对技术发展之谜给出解释。在技术逐渐成熟的过程中,它们总是倾向于变得更复杂,实际上是变得非常复杂。F–35C喷气式战斗机比莱特兄弟的飞行器要复杂多。如果硬说它是莱特兄弟飞行器的变异和选择的结果,那对我们的想象力将是巨大的挑战。这里应该有什么东西是超越单纯的变异和选择而起作用的,让我们回到技术发展过程中重新审视一番,看看到底是什么在起作用吧。
内部替换
当一项技术涉及了商业或军事的议题,它的功能性就将可能受到“促逼”(pushed):它被逼迫着给予更多功能。为了赢得竞争,投资人会寻找更好的组件、更优化的结构,不断进行组件间的调整和平衡。如果竞争非常激烈,甚至技术的边边角角都会被要求完成得尽善尽美。
但是一旦系统中的某些部件遇到了限制,那么技术(或者更准确地说,技术的基本原理)就可能无法再继续向前了。尽管开发商们希望集成电路可以排布得更密集、容纳更多器件,但是在该项技术发展的过程中,总会遇到限制出现的那一刻,比如光刻法最终会受限于光的波长。在雷达发展的早期,人们不断尝试以更高的频率发射信号,以便能够更准确地识别目标。但是在如此高频的情况下,信号发射源将无法维持稳定的功率。一项技术在遭遇局限性后只能就此停步。
限制性障碍令技术投资者大为恼火。4为了进一步发展,遭遇到的每个瓶颈都必须得到认真对待。5令人沮丧的是,限制是不可避免的。假设一个设计没能接近操作的极限,它的效率就不是最充分的,它会继续被要求表现得更充分。
通常,开发人员可以通过更换形成阻碍的零部件(一个次生技术)来克服局限。这种置换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采取更好的设计或更深思熟虑的解决方案,或者天才地盗用竞争对手的思路等。另一种方法是,用不同的材料,比如强度更大或熔点更高的材料进行替代。喷气发动机在开发的数十年间,就一直在不断改用更强、更耐热的合金零部件。事实上,开发者经常寻找的并不是更好的部件,而是这个部件恰好能提供的一个现象。因而,开发者在寻找化学性质相似的材料时最在意的是,哪一种材料在被利用时会出现更有效的现象。的确可以这样说,大多数的材料科学是通过理解材料性能来寻求现象的改善的。
当然,一部分组件的改进需要其他组件也进行适应性的调整。这个过程需要对整个技术再次进行平衡,甚至可能需要重新考量技术的整体结构。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期间,木结构飞机被替换成了金属框架,那使得整个飞机设计都必须重新加以考量。
关于通过内部替换进行改进的过程看起来好像已经很完整了,但是按照我们的递归原理,这个过程也应该是递归性的。技术的改进过程应该伴随着构成次级组件以及次次级组件的零部件的置换过程,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将作为客观对象(object,其实更像一种有机体)的技术的发展视为一个在所有层级上的所有组件都同时发生改进的过程。
除此之外,一项技术的发展不仅需要那些内部的、直接的努力,还需要目标技术以外的“外部”改善。这是因为许多技术组件都来自于其他技术。几十年以来,航空仪表和控制原理都不断得益于其“外部”的电子领域的发展。技术的发展依托于其构成组件所需的外部发展。
结构深化
“内部替换”部分地解释了技术为什么会随着发展而变得越加复杂。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替换构件平均来讲要比它们所取代的部件复杂。但那不是重点,真正起作用的另有原因。我将其称为结构深化(structural deepening)6。
开发人员可以围绕着技术障碍去寻找更好的部件或更好的材料。他们也可以通过加入新的零部件或是添加进一步的零件系统去消除障碍。这时,解决障碍的方法不是调换旧零件,旧零件实际上已经被保留下来了。在极限圈定的范围内,会有其他零件或集成件被添加进来,以辅助已有的旧零件完成工作。因此,当喷气式发动机被要求在更高的温度下运行而导致涡轮叶片开始在极限温度软化时,开发者采取了在叶片旁边添加通风系统冷却叶片,或者在叶片内部添加循环冷却系统的方法。当早期雷达系统接收的回声信号与发射信号因同步而被淹没时,开发人员加入了一组零件(双工器),这可以使发射器有零点几秒的短时关闭,这样回声就可以被清晰地接收到了。
为了突破局限而不断加入次级系统,技术因此发展得越来越精致。技术结构就是这样不断被“加深”或者不断地被设计得更为复杂的。
技术从而变成了重重叠叠的复合体。
驱动技术复杂化的动因不仅在于为完成目标功能而被迫去克服技术限制的尝试。一项技术不仅需要自身运行良好,还需要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也可以应付自如。也就是说,它应该可以安全可靠地应对一系列任务。而在这个过程中,极限无处不在。所以我们可以说,为了克服各种极限,一个技术还需要主动增加次级系统或次级模块以完成如下目的:(1)加强基本性能。(2)对改变或异常进行监视并作出反应。(3)去适应更广泛的任务范围。(4)增强安全性和可靠性。
这一观点不仅限于技术的统筹层级。由于它的次级系统或集成模块本身也是技术,也需要发展,需要被促逼着加强技术总体的性能,所以,通过递归性过程,主动改进过程也会发生。设计者会寻求打破极限的方法,根据上面(1)–(4)的原理加入次级系统从而加强性能、对环境的改变作出反应、适应更广泛的任务范围、增强可靠性。新加入的集成块或子系统反过来也会被促逼着趋近它们自己的操作极限。设计者将进一步加入次次级系统(sub-subsystem)来打破这些极限。这个过程持续进行着,集成模块围绕提高主模块的工作性能工作,其他次级模块又围绕着集成模块工作,还有其他模块再围绕着这些次级模块工作。性能在系统的所有层级上被提高,技术结构的所有级别都将变得更为复杂。
我们可以从燃气涡轮飞机发动机这个例子来看这个递归性的结构深化过程。弗兰克·惠特尔的发动机原型是用独体压缩机来供应压缩空气进行燃料燃烧的。这是一个径向流动(radial-flow)压缩机:它吸入空气,然后通过快速“旋转”进行压缩。惠特尔熟悉这种压缩方式,之所以选择这种技术,是因为它是达到目的的最简单的设计。但是随着对更好性能的需求,设计师被要求采用更好的组件,即轴流式压缩机来替换径向流动压缩机。它是一个巨大的风扇,其空气流动方向平行于传动轴。但在单轴压缩机阶段,增加压力供应比的极限也只能达到大约1.2:1。为了达到更优越的性能,设计师同时使用几个压缩机,并最终将它们按顺序排列组装在一起。但是这个压缩系统的操作需要既能适应高纬度的稀薄空气,又能适应低纬度的高密度空气,并且还要适应不同风速的操作环境,因而设计师增添了导叶(guide-vane)系统来控制吸入的空气。系统因而被精致化了。反过来,导叶系统现在又需要一个可控集成块来感知环境条件,从而对叶片进行相应的调整。这是进一步的精致化。但是现在输出的高压空气会以意想不到的冲击波回冲到压缩机中,这又成了另一个主要的障碍。所以压缩机又需要安装防喘振放压阀这一次级系统对此加以控制,并且要对该系统进行更进一步的精致化。防喘振系统又需要更灵敏的传感、控制系统。此外,还要有更多的精致化过程。
以这样的方式,一项技术(例如,压缩机)在性能和使用范围上得到了极大改善,但这是要付出代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只能背负着越来越多的老旧的子系统和次级子系统才能正常运转,它要不断处理各种异常情况、被迫扩大应用范围、为防止或应付失败而进一步提供大量冗余设计。
在喷气发动机的案例中,当技术被促逼时,也会发生为提高性能而主动进行改进的情况。例如,为了提供空战条件下要求的额外的推动力,特意添加了补燃室这个集成件;为了防止发动机起火,特意加入了复杂的烟火警探测系统;为了防止通风口结冰,特意加入了除冰组件。此外,专门的燃油系统、润滑系统、可变尾喷系统、启动系统也都是因此被加入进来的。所有这些反过来又需要控制、传感、仪表测量系统及其子系统。如此一来,飞机性能确实被提高了,现代飞机的发动机动力比惠特尔最初的喷气发动机要至少高30~50倍,但它们也更复杂了,惠特尔1936年的发动机包括一个移动的涡轮增压机以及几百个零件,而它的现代版已包括22 000个零部件了。
通过结构深化来改进技术的过程是缓慢的,飞机涡轮增压汽油发动机的改进前后共用了几十年。原因在于,改进过程中不仅要识别新的集成模块及其问题,还必须对它们加以实验、论证,以及对即将涵盖它们的新系统进行重新平衡和优化,而这些都需要时间。
经济因素也在这个过程中帮助控制改进的时机。如果竞争激烈,改进就会加速,如果缺乏竞争,改进就会慢下来。开发人员即使意识到明显的技术进步,也不一定会予以采用。不论竞争压力是否出现,任何时候发生的技术改进都会被认真进行选择,某个技术上可行的新改进必须是在经济上进行考量,认为值得进行整体的重新设计后,才可能被采用。
就这样,随着新的改进被选择性地采用,技术一点一点向前蹒跚发展。如果遇到某个限制性的阻碍,发展会缓慢下来,致使整个过程显得时断时续。总之,技术的发展深深依赖于结构的深化。
结构深化对技术进步的作用往往是巨大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不断加入系统、子系统而获得更高的性能之后,新技术也会遭遇硬壳化(encrust)。硬壳化对于一个方法和设备可能不算什么,一旦开发成本、费用已完成分摊,导致的结果可能仅仅是材料或空间使用成本的提高或权重的增加。但对于所谓“非技术性的”目的系统,负担则可能相当沉重,如军事组织、法律制度、高校管理以及文字处理系统都需要通过不断加入子系统或子零件来赢得性能上的改进。只需设想一下税法的复杂性逐步增加的过程就可见一斑,而它只不过是法律制度体系中的一个小分支。这些以复杂性和官僚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改进”成本是无法分摊的,即使环境已经不再需要它们了,它们还将继续存在并且很难消除。
锁定与适应性延伸
我所描述的内部替换和结构深化这两种发展机制,将作用于技术的整个生命周期。起初,一项新技术被小心翼翼地、试验性地开发出来。后来,当它能够服务于某一特定目的时,它就迅速发展起来,并成为标准工程的一部分。当然,同时,达尔文机制开始起作用,它从许多内部的改进中去选择(通常是通过设计师对前辈的借鉴)更好的解决方案。
THE
NATURE
OF TECHNOLOGY
技术思想前沿
在新旧原理更替的过程中,旧原理往往已经被锁定了,有4个原因导致旧原理通常会存在较长的时间:
•经过精致、繁复的过程之后,已经成熟的旧原理会表现得比它的新对手好。
•采用新原理可能意味着改变周围的结构和组织,因为成本过高,所以可能不会被实现。
•从业者不认可这个新原理带来的愿景或承诺。
•新原理将使旧知识过时,它在潜在的新原理与安全的旧原理之间制造了一种认知失调以及情感上的不匹配。
当调换部件和结构深化都不能再为提高性能做什么的时候,技术就成熟了。这时候,如果想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则需要一个全新的原理。但新原理不能说出现就出现,即使出现了,它想要取代旧原理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旧设计、旧原理往往已经被锁定了。
这是为什么呢?一个原因在于,经历如此精致、繁复的过程之后,已经成熟的旧技术会表现得比它的新对手好。新对手们可能潜力无限,但此时它们还处在婴儿期,因而无法马上追赶上那些老道的旧技术。它们的成熟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旧技术存在的时间通常比预料的长。
还有一个理由使得旧原理存在的时间要比应然的长,在经济领域即是如此。即使新的原理发展得很好,表现也比旧原理好,但是采用它可能意味着改变周围的结构和组织。由于这样做成本过高,因而可能不会被实现。在1955年,经济学家马文 ·弗兰克尔(Marvin Frankel)很想知道为什么兰开夏郡(Lancashire)的棉纺厂没有像他们的美国同行那样采用更先进、更高效的机器。 7他发现,如果在英国设置新机器,的确会更有效率。但是这些新机器很重,如果安装它们,那么安置旧机器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砖结构就会被拆除。就这样,“外部”的组件或经营锁定了内部机械,导致兰开夏郡的棉纺厂没有改变。
还有一个原因是心理上的。旧原理可以持续下去是因为从业者不认可这个新原理带来的愿景或承诺。首创不仅仅是一种新的做事方式,而且也是一种新的看待事物的方法。
还有新的威胁:新原理将使旧知识过时。事实上,有些新原理已经被推广过了或业已存在,但是它们被从业者所摒弃。有时候并不是因为人们缺乏想象力,而是因为它在潜在的新原理与安全的旧原理之间制造了一种认知失调以及情感上的不匹配。社会学家黛安·沃恩(Diane Vaughan)谈到过这种心理失调:
(当我们作为人类去处理情况时,我们会使用)一个由一套假设、期望和经验构成的综合的参照系。所有感知都建立在这个框架的基础上。这个框架会变成自确定性的,因为,只要我们能够,我们总是倾向于将感知置于经验、事件之上,创造符合它的变故和关系。我们对那些不符合这种参考框架的事物往往采取忽视、误解或否认的态度。结果是,我们通常能找到我们所要寻找的东西。这个参照系是不易被改变或铲除的,因为,我们看世界的方式与我们在和这个世界的关系中如何看待或者定义我们自身是密切相连的。因此,在我们与这个参考框架保持一致的过程中,是有自己的既得利益的,否则我们自己的身份识别就将遭遇危险。8
它和新原理的关系也是如此。新的和已被接受的解决方式之间的距离越大,对传统方式的锁定就越牢固。因此,迟滞现象(hysteresis)是存在的,即对变化的一种延迟反应。新技术被非常成功的旧技术所阻碍,技术上的转换既不容易也不顺畅。
这种对旧有的成功原理的锁定所引起的现象,我称之为自适应延伸(adaptive stretch)。 9当一个新的情况出现或要求在其他领域应用时,人们更容易想到用旧技术或旧有的基本原理加以解决,并且会通过“拉伸”它来涵盖新的环境。
THE
NATURE
OF TECHNOLOGY
技术思想前沿
自适应延伸:对旧有的成功原理的锁定所引起的现象称之为自适应延伸(adaptive stretch)。
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将旧技术的标准组件重新配置以应用于新用途,或增加更多的集成模块来完成新的目标。20世纪30年代,喷气发动机的高速高海拔飞行本来可以提前好几年实现,但是设计者当时还不熟悉燃气涡轮机的原理。于是,当军用飞机被迫在空气稀薄的更高的高度飞行时,他们适应性地延伸了当时的技术:飞机活塞发动机。这迫使活塞发动机要打破极限 10:这些极限不仅包括高海拔氧气稀少,还包括能够将氧气以足够快的速度泵入汽缸的极限,它受氧气在四冲程发动机系统中燃烧和处理的速率所限。增压器和其他系统的深化被加入进来,用以进行高压快速泵入空气。活塞螺旋桨推进器的活塞部分被独具匠心地精致化了,它被延伸了。较难延伸的是螺旋桨推进器。如果长时间在空气稀薄的高空飞行,螺旋桨推进器就会无法咬合。如果它被促逼着进行更高层次的改进,它就可能走向超音速。如果它被扩大了,拥有了更大的直径,螺旋桨尖部的运动会更快,同样也会走向超音速。一个根本性的极限已经达到了。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在发展的某种程度上,旧原理变得很难再进行扩展延伸。这时新原理就有了向前发展的立足点。当然旧原理还会在附近徘徊,但是它已经变成为某个特定目标服务了,而新原理已开始了精致化过程。
我在本章和第6章所描述的新原理的起源、结构深化、锁定以及适应性延伸等现象组成了一个自然周期。一个新的原理出现、开始发展、陷入局限、其结构不断被精致化。环境结构和专业熟悉度被锁定在原理及基础技术当中。新的目的和变化的环境出现时,它们通过延伸锁定技术进行适应,从而产生了进一步的精致化。最后,已被高度精致化的旧原理已经超出了它能承受的极限,因此将让位于新的原理。新的基本原理可能更简单,但在适当的时候,它会自己变得精致化。
这个周期循环往复,有时简单性会切入到精致化的过程中。精致化和简单性就这样来回交替,直到精致化进程随时间的推移而到达它的边缘。
这可能会使我的读者受到震撼,因为我正在描述的整个循环与托马斯·库恩就科学理论发展所提出的周期描述非常相似。库恩所说的周期肇始于一个新原理(他称之为范式)取代旧原理的新理论模型。新范式之后被应用于许多样本,从而被接受,并进一步在库恩所谓的常规科学中被精致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不适合那个基本范式的例子(异常)逐渐树立。范式会通过伸展来适应这些,但是当异常进一步建立起来,范式就会越来越勉强。当且仅当一个更新的、更令人满意的解释,即一个新范式出现后,旧范式就崩溃了。
如果想要展现这种对应性,我可以用库恩的术语重述一遍技术周期性的循环。但是用我在本章使用的术语来重述库恩理论将更有趣。我们可以说一个理论通过面临新的事实和被迫进行新的应用而被促逼着。它的组件可能需要被替换,可能需要更准确的定义,很多已有的构件可能需要重构。当遇到限制(用库恩的话说就是异常)的时候,许多方面就会发生特殊情况:这时真正在工作区附近徘徊的系统就会进行精致化,从而应对这种可感知的限制。这个理论建立的基础是通过加入次级理论来处理困难和特殊的情况。例如达尔文的理论就必须加入次级论述来解释为什么有些物种会展现利他性。
理论的发展就是进行精致化的过程,它加入附录、完善定义、添加补编以及特殊结构,其目的在于将所有特例纳入考虑范围。如果特例不太符合理论,理论就会延伸,它就会加入相当于“本轮”的东西。最终当面临足够的变异时,它的“功效性”就降低了,此时就要寻找一个新的原理或范式。当现存范式无法再被延伸时,新的结构就开始形成。库恩的循环开始往复。
我重申这种一致性并不意味着科学和技术是一样的。它只意味着,由于科学的理论体系是目的性的,因此它们遵循同样的逻辑。科学也会发展,碰到局限性,进行精致化,并在适当的时候寻求替换。无论是科学还是技术,其发展变化的逻辑是相似的。
本章我们一直在探索技术发展的过程。但我们要注意,它适用于技术所有的部分。新的技术被促逼着陷入局限,并通过优化零部件和深化结构来获得提高。这个过程也同样适用于所有的零部件。发展是非常典型的内部过程。整个技术和它的所有部件并行着。
责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