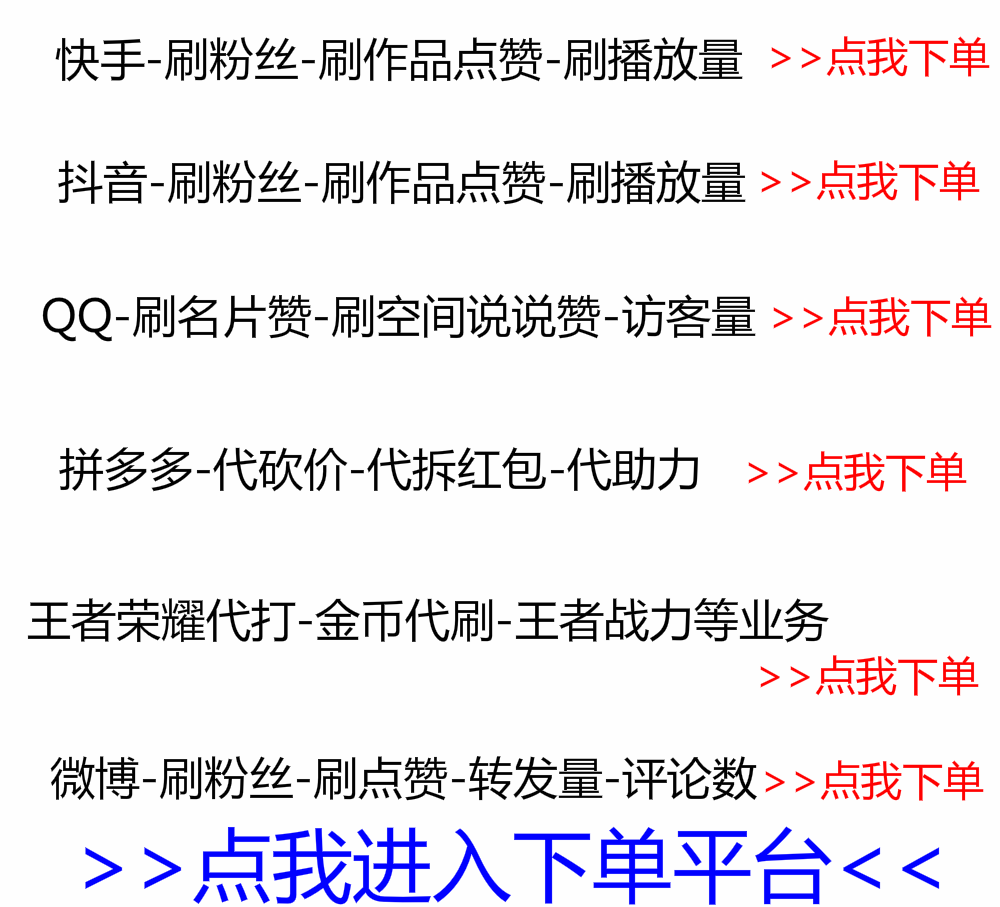天城五金厂、冲压机和杀马特
三炮的工作是给产品打包装。每天工作11个小时,除了上公厕,一刻不能离开工位。他有点懊悔退学,“打工比念书辛苦得多”。
更难忍的是无趣和焦躁。人成为机器的一部分,人类的肢体是它们延长的终端。每天,三炮的手重复着同一套动作,每过一小会儿,他就困得不行,头几乎要砸到桌上。
他开始学吸烟解闷。只有借助上公厕的5分钟,抽上一支烟,他才觉得自己获得了片刻的逃出。
蓝城去了父亲打工的厂,后来父亲在广州办了个小作坊——天城五金厂。蓝城带着从前的同班同学大姐姐,投向了这个日后蒙上神奇光晕的地方。
但在现实中的龙城五金厂,工作琐碎得几乎让人忘了自身的存在。车间生产门锁,比农村的卧室大不了多少。大姐姐是冲压机操作员,每天重复三个动作上千次——左手将材料装入磨具,右手调整,最后脚踏用两根脚趾踏板,几吨重的铣床哗地压出来,一个金属制品初步成形。
因为工作太无聊,蓝城在车间摆了个扬声器,放DJ舞曲快手买粉丝,他将音量开到最大,一边操作机器,一边摇动身体。
一天,意外险些发生——大姐姐差点没从机器里取出右手,一个趾甲砰地断成两半。
小马林也差点因打盹出事。他在另一家鞋厂操作机器,将标志印在产品包装上。有一次他没把产品放起来,把自个的手搁起来了,幸好是个大型机器,否则几根中指早已没了。
几年后拍《叛逆少年》,三炮没怎样想就设计出了冲压机操作员酱爆上场的标志性动作——三根竖起的拇指。在他对鞋厂的记忆中,断指相当普遍,身边有同学缺了好几根手指。
“很多人以为是很high的觉得,很酷,其实在厂里待过的人一眼才能看下来,我想抒发的是右手被机器压断了。仔细看镜头,酱爆拿手机是用三根右手去夹的。”在直播间,三炮不停对粉丝指出,“在厂里下班的同事们一定要当心啊!”
在鞋厂的焦躁气氛中,蓝城看到了好多“杀马特”。他们十分在意外表,“想让他人认为自己是最奇特的”。这些年轻人穿着颜色艳丽的外套,留着斜刘海和爆燃头,脚上是尖衬衫,却做着“很脏很脏的工作”。
大家打招呼永远是同一句话:“你是那个厂的?”比较鞋厂的大小、操作的机器、伙食有没有肉,成了这种打工青年虚荣心的膨化剂。
下了班,三炮认识了老乡的蓝城、小马林,一起玩摩托车快手买粉丝,在大坝歪斜头、飙车。
他们都自恃“爱车如命”。摩托车是加装过的:卸了车头,这样玩翘头更轻便;加装了排气管,跑起来声音更响。塘红到广州600公里,为了把摩托车从老家弄过来,他们连夜骑了15个小时,期间还被警员擒获罚金。
镇上的杀马特们更浮夸,除了改装排气管,还在摩托车上缠着五颜六色的彩灯,连车轮的轴上都缠着。虽然车很酷炫,但毕竟她们车技通常,三炮挺厌恶。《叛逆少年》中那辆缠满彩灯、贴着5块牌照、装着8根排气管的鬼火摩托车,就是为了讽刺她们而设计的。
玩车久了,三炮开始渴求拍下和同学玩车的日常。买一部拍视频疗效不错的苹果手机,是他打工时最大的愿望。
刚来广州一年多时,他曾因买手机受骗过。那时他还是个孤僻的“厂仔”,花300元在街边买了部“来路不明的苹果4S手机”。回寝室后,他才发觉手机开不了机。折腾了一周,他不肯舍弃,将手机置于水里泡,用厂里的电容笔测试屏幕,用螺丝刀旋紧后盖,直到他见到了一块黄褐色的铁板,他才彻底悔悟——对方给他调包成了模型机。
最终,即便厌烦了鞋厂,经常辞工的三炮入不敷出,他还是还钱买了部真正的苹果5S。他没想到,手机改变了他的命运。
塘红乡F8合照
酱爆上场时作出三指冲天的精典手势
大姐姐从广州打工归来

疼叔的妈妈搬去山上,每日放羊养殖
三炮家的红色小楼在塘红乡车别庄愈发醒目
拥有600万粉丝的三炮,是靠“土”和“叛逆”走红网路的。在涌动着乡村非主流风的配乐中,他和同伴戴着艳丽的杀马特假发在村头尬舞,骑着加装过的家用摩托车在大路上翘车头,把柴房当KTV自嗨,在发廊用瓦刀染眉毛……
这些都是《叛逆少年》中的场景。一年多前,三炮开始在快手上发布这个用手机拍出的系列爆笑短片,很快,这个中学没结业、曾在广州打工的农村青年,成了快手广东第二大网红。
在广东上林县塘红乡,他家贴着墙纸的小楼快成了旅游景点。每到周日,总有十几岁的农村少年结伴骑着摩托车寻过来。有的希望三炮收自己为徒,有的追星般偷窥几张相片后悄悄走掉。一个云南少年骑了50多天自行车过来,只为瞧上一眼。
如今,和三炮一样舍弃打工、返乡拍段子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的。”正如这个在快手上被重拍了无数次的段子所预示的,三炮和他在农村的追随者们都在渴望一种新的人生自由——不打工。
留守青年
6月的三天早上,三炮家的后院里,上万只蚕悠闲卧在层层叠叠的桑寄生上,许久不见动弹。院外鸟鸣不已。
塘红乡车别庄仅存的3个留在故乡的年轻人——《叛逆少年》里的三炮、表哥和疼叔,正在熟睡,网络的世界昼夜颠倒。
在现实中,他们是堂兄弟,一起长大,一起外出打工,如今一起在老家拍段子。有人戏称她们是“留守青年”。但和祖辈共同生活的她们,更像活在另一个平行时空里。
三炮的母亲已经出门采玄参。儿子走红的网路世界,似乎与她们无关。街上每隔两天有集市,兜售簸箕之类的农具,买卖者几乎都是中老年人。
下午三四点,阳光不再这么耀眼,车别庄忽然闹腾上去。
玩快手的年轻人醒了。公路上传来机车轰鸣声,同样留守塘红乡的蓝城、大表姐、小马林、大卫和阿蓝相继到来。在一片片白色裸砖房子中,三炮家的红色小楼愈发醒目,它是少数墙面贴了磁砖、所有楼层都装了木门的房屋。方圆几十里,这是年轻人最密集的地方。
大家惊呼笔名,几乎全是95后,清一色穿网购的T恤衫,脚下是黏着泥的皮鞋。
客厅台式机35英寸的曲面屏亮了,大表姐坐在笔记本前的椅子上,身体跟随音乐节拍摇动,不时打着响指。
拍段子是三天中最重要的工作。想出恶搞的梗最难,灵感可能源自任何地方。听到一段魔性的音乐,想起影片中某段精典台词,或是扫视旁边快要虚脱的红色28杠单车、扔在院中一角的大红色编织袋……一个关于打工或回乡的段子就此诞生。
三炮坐在小板凳上思索了一会儿,决定拍一个模仿《流星花园》F4卖萌的段子。他和弟弟、小马林戴上剪短的斜刘海假发,大表姐套上暗红色大衣,踩上7块钱一双的红色塑胶拖鞋。他们要饰演刚从广州打工归来、在村里风光无限的年轻人。
4个人拖着帆布拉杆箱,手插内裤口袋,一边顺着村口道路徜徉,一边面无表情地望向跟拍的手机镜头。大姐姐从外套口袋缓缓拿出一把塑胶小梳,向上捋了捋毛发,漫不经心地将木梳朝脑后一抛,留给镜头一个不羁的白眼。
在村口来回走了近10遍,三炮终于认为“那种感觉到了”。拍完后,头发蓬乱的他坐在家旁边垃圾堆旁的铁管上,低头用手机自带的软件剪辑视频。几年里,他用这个软件摆弄出了上千个作品。
和其他人一样,初中没结业的三炮说不出这个只有英文名的软件叫哪些,只晓得它的图标是一颗星星。
这个不到一分钟的段子最终在快手上收获了超过400万播放量,20万个赞。
有人称三炮是“快手周星驰”。对他拍的《叛逆少年》系列,有网友评价“笑得不能自理”“大片即视感”“演技比一些小鲜肉很多了”“拍摄和剪辑相当专业”。
“都是本色主演。”三炮笑了笑。这帮农村青年未曾接受过任何专业的演出训练。在拍段子之前,他们在广州操作冲压机、做磨具、打包装、炸鸡块、修车……

四五年前,他们未曾想过,有三天,他们会成为网红。
自由之路
在《叛逆少年》中,几乎每位角色都个性鲜明。
三炮是穿着衣服的初中生,呆傻直率,总被人欺侮;表哥是个护弟狂魔,老实中带点傲娇知性;大姐姐是个非主流狂躁青年,经常深陷悲伤追忆中;酱爆痞里痞气,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阿妈打电话;小马林是车神,骑摩托车会翘头,每次上场都引起男生惊叫;疼叔则是当初叱吒塘红的老车神,如今退隐江湖,走村串户卖腐竹。
从广州打工归来的大姐姐,带来了令人羡慕的“贵族气息”——他留着暗红杀马特短发,穿着用胸针拢住裆部的外套,身上挂着泛光的铁链,在村里坚持说普通话。他还用力将两个哥哥往时尚的路上推,带她们喝“不加奶的珍珠奶茶”,去乡里的野狼沙龙做眉毛。
一天,大表姐抡起着铁链,教两个儿子“吸引异性的街舞”,蹲在树林中暗中观察的酱爆闪了下来。
他喊着周星驰影片中的精典台词登场:“在捏个moment,我酱爆感觉到,我要爆呃!”
“你是那个厂的?”音乐骤停,身上满是水泥的大姐姐丢弃铁链。
“天城五金厂,3号车间,580吨冲压机,操作员,酱爆呃!”身穿带毛领的天蓝色大衣、留着白色杀马特短发的酱爆缓缓仰起头,竖起大拇指、食指和小拇指。
“酱爆?!”三炮和弟弟同时瞪大了眼。
天色渐暗,山间树林流淌着黑黢黢的影。酱爆用三只中指伸入衣服口袋,夹出手机,搁在地上作舞台灯光。他走进大姐姐,冷冷地说,“如果我没有猜错,你的口袋里还有半斤水泥。”
大姐姐咬了咬舌头,狠狠地将口袋中的水泥一把把砸向地面,一场斗舞在灰尘飞扬中开始。
莫名的台词、夸张的演出、怀旧的配乐,让这段农村尬舞极具奇幻现实色调。很多人不知道,这段雷人剧情并非完全虚构。
有一次直播,三炮作出酱爆三根手指冲天的精典手势,问她们,“这是哪些意思?”
屏幕上弹出一条条“摇滚”“耍酷”等回答。三炮不断摇头。
这个手势始于真实的打工经历。
初二,三炮退学了,他“也想出去打工”。
那些沾满了城市气息、衣着时髦,说话参杂着普通话、给村里小孩买糖的打工者,对小山村的少年来说闪着奇特的光芒。村里奶奶种田一年的收入赶不上她们打工一个月。读高中时,三炮家还是土房屋,有一次他洗脚时,整面墙“哐地”倒了出来。那时,他吃得最多的是猪油拌饭,很少看到肉。
出去打工意味着,有钱,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初中时,三炮迷上网路,QQ空间背景是一片黑,签名是无头无尾的诗句,夹着符号拼凑的“火星文”。他的眉毛快到膝盖,斜刘海几乎盖住半边脸,自以为相当“飘逸”。但他最艳羡姐姐的短发,后面不是塌下来的,而是向下飞起的爆炸头,三炮仍然想弄个一样的,却苦于没钱烫头发。
蓝城是酱爆的扮演者,他比三炮高一届,少年时他迷上了音乐。在网咖一边打游戏,一边戴着大音箱听歌,当尖锐战栗的电音、语速飞快的饶舌从麦克风中传出,他顿时觉得电压击遍腰部。
塘红乡没有KTV,蓝城和几个朋友请病假跑去市区。几十公里的路,坑坑洼洼,他们骑着摩托车硬挺挺地驶过。唱歌的钱,是前一周吃方便面攒下来的。他喜欢点周杰伦的歌。唱完歌,几个女孩挤在小酒店30块一晚的卧室里,第二天赶回中学。
初中三年,无心学习的三炮没买过一支笔,实在要写字就找同桌借。平时上课,他总趴在桌上午睡。
初二下学期,三炮离开了中学,退学手续都没办。疼叔算是个循规蹈矩的中学生,他起初想上小学,但高考分数还不到总分一半。家里供不起他读中学,只好舍弃。在他的班上,仅仅二人升入了城区的普通高中。
大多数人选择休学去广州打工。临近高考时,老师会苦口婆心地给中学生打电话,劝她们回去出席高考。大卫回去拿了个中学毕业证,毕竟有些鞋厂急聘要求提升了。
真正进厂后,三炮才发觉,靠打工通往自由,只是一个农村少年的幻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