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论

自二战结束以来,输出法治一直是美国、英国和欧洲外交政策强烈关注的重点。德国和日本的战后宪法则追随着这种西方式宪法民主概念和法治概念。冷战结束导致许多前东方板块的共产主义国家实施西方类型的民主宪法和法治概念。同样地,在1979年,邓小平指引着中国实行“向西方开放的政策”,这使中国开始努力实施法治。最近,乔治·布什总统荒谬地以军事手段在阿富汗和伊朗传播“民主”和“法治”,以之作为对抗恐怖主义传播的预防措施。在所有这些场合,只有“法治一直被真正地看作现代国家的灵魂”,只有关注法治才是有意义的。
然而,法治在美国和全世界都面临着严峻挑战。在美国,法律的不确定性和法律理论与法律实践之间的本体论断裂提出两种困惑,这些困惑向当代规范法律理论的解决方式提出了挑战。虽然法学家们(从极端激进的解构主义者到当代法律规范主义者)对法律的不确定性达到了何种程度,迄今仍然意见不一,他们却一致认同法律具有不确定性。之所以说法律具有不确定性,是因为对一些棘手案件或疑难案件,明显地,与之相关的制定法、普通法、合同法或宪法规定都不能解决其中的争端。因此,法律的不确定性提出这样一种严重的忧虑,即:由于法律必须依赖于个人的政治信念、伦理信念或宗教信念,因而在那些疑难案件中作出的司法判决是不合法的。

尽管广泛认同法律是不确定的,当代法律理论却不能提出一种规范的法律理论来解释在这些棘手案件中法律何以能是合理合法的。譬如,法律实证主义者,像哈特(H.L.A. Hart),认识到了法律的不确定性或者法律的“开放结构”,但却坚持认为法官具有判决疑难案件的“判断力”,可是他并没有具体地说明他们应当如何运用这种判断力。批判的法律研究学派、女性主义法律理论和批判的种族理论否认非政治的法律合法性的可能性,并集中力量解构与阶级、性别和种族有关的那些潜在的政治偏见。最终,某些法律理论家则不成功地试图否认法律的不确定性。譬如,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仍然固守着他的所谓“正确答案说”——除了极端罕见或奇异的案件以外,在疑难案件中存在着“正确答案”——尽管一直以来人们认为他的法律解释理论使得整个法律体系成为不确定的。
在《法律困境》[1]一书中,史蒂文·史密斯(Steven D. Smith)确定了第二种重要的对当代规范法律理论的挑战。他令人信服地论证说,法律实践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前提与当代法律理论的前提是不一致的。法律实践是以经典的或宗教的本体论为前提的,而当代法律理论通常是以科学的本体论(例如,科学的唯物主义)为前提的。史密斯的结论是,法律实践与法律理论之间的这种“本体论的断裂”表明了“某种形而上学的困境”,这“将要求我们‘严肃地对待形而上学’”。史密斯的论证表明法律理论家们不能再无视形而上学前提或本体论前提的问题了,但是他承认他“对这个问题的可能答案是什么也不知道”。下面将要重点论述这一困境,并要表明其预兆并不像史密斯所说的那样可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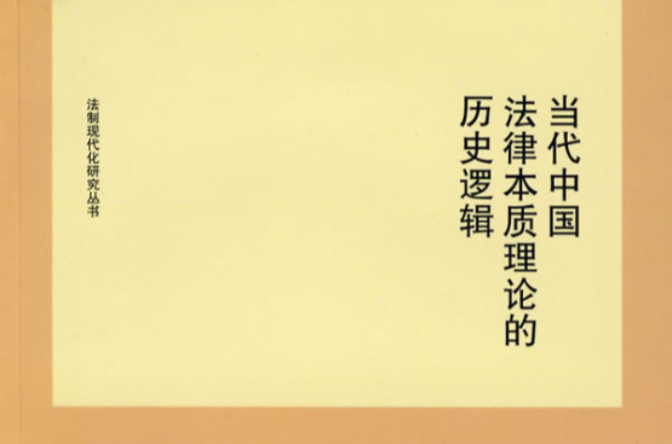
在国外推进法治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即法治的西方前提或假设是否与其他文化的前提相协调。有名望的文化人类学家克里弗德·吉茨(Clifford Geertz)论证说,法律“不是一组有限制的规范、规则、原则或价值观……而是对现实进行想象的不同方式的一部分”。他进一步警告说:“法律的比较研究不能是一件把具体差异归结于抽象的共同性的事情。”相反,法律是“本地的知识;本地的不只是指地点、时间、阶级和各种各样的问题,而是指口音——与本国对可能发生之事的想象相关的各种特征”。正如下面所要讨论的那样,拉里·卡塔·贝克(Larry Catá Backer)、布朗·塔马那哈(Brian Tamanaha)和唐纳德·克拉克(Donald Clarke)在他们的批判主义理论中已经认识到,在中国严格地实施美国的法治观念,而不考虑文化差异,这是行不通的。
此外,规范理论能使法治在文化方面更为敏感,并能强调法律的不确定性和本体论断裂。如果没有这种规范理论,法治在美国是极度危险的,输出到国外甚至会更成问题。继续谈论法治还有意义吗?法律的不确定性和本体论断裂意味着法律最主要是由本地的社会【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