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复见天地之心”阐释中的未发已发问题
——兼论“静中存养”工夫的优先地位
作者简介:
李健芸,1994年出生于贵州省安顺市。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哲学与科学系讲师。2016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博雅学院,2016至202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宋明理学,尤其是朱子哲学,兼及阳明哲学的研究,对于先秦哲学和魏晋玄学亦有一定涉猎。博士学位论文《与朱子哲学的展开》被评为2022年北京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在《哲学动态》、《中国哲学史》等刊物发表论文数篇。
本文原载于《哲学动态》2021年第5期
摘要:在朱子将“复见天地之心”与“未发”“已发”概念关联起来的阐释中,存在由已发之用的生气流行显示未发之体的天地生物之心的结构。朱子又从这个结构中区分了“由纯粹蕴蓄而尚未显露的生气显示天地之心”和“由显露几微的生气端倪显示天地之心”两种对“复见天地之心”的解释。朱子实则更加看重前者。与此相关,在心体流行的层面,“复见天地之心”则可以相应解释为“由心灵活动在未发阶段的静中知觉不昧显示天地之心”,在此状态下心灵活动保持自身为完全纯粹的醒觉。心体层面的静中纯粹醒觉和生气层面的纯粹蕴蓄的生气都以其纯粹性而能够最直接地显示自身不会孤立显示的天地之心。这正是朱子在生生流行统体之内确立“以静为本”的思路,也是进而确立“静中存养”工夫的优先地位的思路,后者正是朱子在中和新悟中对延平教诲的重新理解。
关键词:天地之心;未发已发;中和新说;静中存养
一、问题的缘起
对于《周易·复卦·彖传》中的“复其见天地之心乎”一语的阐释在宋代道学话语的形成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1],成长于道学传统中的朱子自然很早就开始注意“复见天地之心”的问题。朱子在其父朱松离世之后从学武夷三先生,于屏山先生刘子翚处得“不远复”之教。[2]此后,更在从学延平时期,主动向延平提出了自己对“复见天地之心”的理解,据《延平答问》记载:
问:“太极动而生阳”,先生尝曰:“此只是理,做已发看不得。”熹疑既言“动而生阳”,即与《复卦》一阳生而“见天地之心”何异。窃恐“动而生阳”,即天地之喜怒哀乐发处,于此即见天地之心;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即人物之喜怒哀乐发处,于此即见人物之心。如此做两节看,不知得否?[3]
在此,朱子明确把周敦颐《太极图说》“太极动而生阳”和《复卦》的“复见天地之心”对应为天地之已发,以此区别于人物之已发。延平在回信中认为“太极动而生阳”说的是“至理之源”,而“未发已发”则是“就人身上推寻”,所以二者不可混淆:“盖就天地之本源与人物上推来,不得不异。此所以于‘动而生阳’,难以为喜怒哀乐已发言之。”[4]简言之,延平认为不能用言说人的“未发已发”的概念把握言说“天地之本源”的“动而生阳”和“复见天地之心”。虽然朱子的后续思考并未留下记载,不过朱子在这里的表达中有一处细节却值得注意,即朱子并未直接引用《复卦》本文“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而是用了“一阳生而‘见天地之心’”这个表达。可见,在朱子看来,“复见天地之心”指的就是由“一阳生”可以见出“天地之心”。在这个表达中包含了朱子的两层源初的洞见:其一、“见天地之心”的表达包含了“由……见……”的结构,朱子也正是据此结构而将已发的概念引入到他的解释当中;其二、在这个结构中所由以见出天地之心的就是“生”这个事实。这两层源初的洞见在朱子思想成熟之后的意义将会随着下文的展开而得到阐明。
从这段早期的问答可见,延平并不同意将“未发已发”的问题和“复见天地之心”的问题混在一起讨论。但是,朱子在标志了其思想成熟的“己丑之悟”当中却有如下表达:
方其存也,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是则静中之动,复之所以“见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纷纠而品节不差,是则动中之静,艮之所以“不获其身,不见其人”也。(《答张钦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二)
这封《答张钦夫》(诸说例蒙印可)研究者皆系之于乾道五年己丑,且通常认为这是朱子在连写了《已发未发说》和《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表达自己的中和新说之后,再次致信张栻阐明自己的新的思想。[5]这些都是学界之所共识。本来,这是一篇久已被讨论了的文献,但是论者大多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其中论“中和”的部分,而笔者认为这篇书信中仍有其他值得关注的部分。显然,朱子在这篇书信中明确以“复见天地之心”对应心体流行在未发之时[6]的“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的状态,这个状态指向了心的“静中之动”。这里引入“复见天地之心”对应“未发”、“静中之动”的解释,未见于《已发未发说》和《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应当是朱子对这个问题的最完整的思考的表达。对此表达的阐释将在后文展开,但是由此表达可见:朱子并未放弃将“复见天地之心”和“未发已发”的问题关联起来的思考,但是不同于《延平答问》当中的关联,朱子在此就人心的流行活动的层面而言,将“复见天地之心”对应到了未发之时“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的状态,并且,朱子也没有明言在“复见天地之心”中的“一阳生”与此处静中“知觉不昧”的状态的关系。
但是,朱子试图将“复见天地之心”与“未发已发”关联起来的思考似乎并未由所谓“己丑之悟”得到最终确定。这其中的问题在于,“见天地之心”的结构总是“由……见……”的结构,即由一个已经显示者指示出、一同显示出一个不会孤立显示者,而这个结构就很容易引向由“已发”显示“未发”的解释。在《朱子语类》当中有如下一段话:
但其静而复,乃未发之体;动而通焉,则已发之用。一阳来复,其始生甚微,固若静矣。然其实动之机,其势日长,而万物莫不资始焉。此天命流行之初,造化发育之始,天地生生不已之心于是而可见也。端蒙。(《朱子语类》卷七十一)
程端蒙的记载是在淳熙六年己亥以后所闻,也就是说已经距离乾道五年己丑至少十年以上。朱子在此明确以“未发之体”和“已发之用”的表达区分天地之心的未发和已发,而“复见天地之心”在此指的就是由已经显示出来的非常细微的“始生”之“一阳”显示出“未发之体”,即天地生生不已之心。诚然,此处以“体用”关系讨论的“未发已发”关系,并不同于“己丑之悟”中以“思虑未萌”和“事至物来”区分的心的活动过程的“未发”和“已发”两个阶段。但是至少说明朱子对“复见天地之心”和“未发已发”的思考仍有不同的说法。而且,即便是到了朱子晚年仍然如此。据《朱子语类》记载:
曰:“十月阳气收敛,一时关闭得尽。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尝息,但无端倪可见。惟一阳动,则生意始发露出,乃始可见端绪也。言动之头绪于此处起,于此处方见得天地之心也。”因问:“在人则喜怒哀乐未发时,而所谓中节之体已各完具,但未发则寂然而已,不可见也。特因事感动,而恻隐、羞恶之端始觉因事发露出来,非因动而渐有此也。”曰:“是。”铢。(《朱子语类》卷七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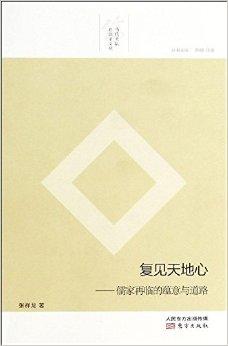
存养是静工夫。静时是中,以其无过不及,无所偏倚也……其静时,思虑未萌,知觉不昧,乃《复》所谓“见天地之心”,静中之动也。祖道。(《朱子语类》卷六十二)
董铢的记载是在庆元二年以后所闻,曾祖道的记载是在庆元三年所闻。在董铢的记载中,“复见天地之心”指的是由发露而出的始生端绪见出天地之心,这体现在人心而言,就是在“因事感动”的情况下,由恻隐等已经发露的端绪见出未发时的“中节之体”。显然,这里指的是朱子哲学中的“情”与“性”的关系。[7]但曾祖道的记载却几乎就是《答张钦夫》(诸说例蒙印可)中的表达的重复。可见,朱子直至庆元年间也仍然坚持他在“己丑之悟”中以“思虑未萌知觉不昧”对应“复见天地之心”的思想。
难道朱子用“复见天地之心”同时指向两种完全不同的“未发已发”的结构?即便如此,既然朱子都用“复见天地之心”这个表达,那么其间难道没有一致之处?抑或需要对朱子的用法另做一番思考?笔者认为,缠绕在“复见天地之心”和“未发已发”的关系当中的不同表达,有待进一步澄清其中的准确意义,且依循这番澄清,覆藏于“己丑之悟”和其中的“静中存养”的思想也会得到更深的发明。因此,本文将由以下三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阐明朱子关于“复见天地之心”与“未发已发”关系的解释;第二、由这种解释回观《答张钦夫》(诸说例蒙印可)中的表达并予以进一步的澄清;第三、由此发覆朱子在心体流行未发时节确立“静中存养”工夫的更深的意义。
二、何由以见:生气敛藏抑或生气端倪
上文已经分析,朱子在《延平答问》中流露出的对“复见天地之心”的源初的洞见中就包含了由“一阳生”而见出天地之心的意思,这个洞见意味着在朱子看来,能够显示出自身不孤立显示的天地之心的事实在于“生”,这一点后来被朱子提炼为“天地以生物为心”这个表达,并由此与张栻、吴翌、何镐等人展开了所谓“仁说”之辩。[8]其实,在“己丑之悟”以前朱子就明确提出“天地以生物为心”的说法:
“复见天地心”之说,熹则以为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故阳极于外而复生于内,圣人以为于此可以见天地之心焉。盖其复者气也,其所以复者,则有自来矣。(《答张敬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二)
这封书信作于乾道三年夏间。在此,朱子认为“天地之心”指的就是且仅仅就是“生物之心”。如同陈来所言:“在朱子的讲法中,天地惟以生物为心,更加突出‘生’的地位。”[9]而且,天地惟以“生物”为心恰恰就是天地之心对万物的主宰地位的体现,因为万物之“生”皆根源于天地之心,无天地之心则无万物之“生”。[10]并且,天地之心生物不息,这个过程没有丝毫片刻的间断可言。朱子在此以“其复者”和“其所以复者”区分了新生的气和这个气由之而得以生成的根源,后者即天地之心。不过,朱子在写完《仁说》(乾道八年)之后对他此处用以解释天地之心的“所以”二字做过辨析:
“复非天地心,复则见天地心”,此语与“所以阴阳者道”之意不同,但以《易传》观之,则可见矣……至于复之得名,则以此阳之复生而已……岂得遂指此名以为天地之心乎?但于其复而见此一阳之萌于下,则是因其复而见天地之心耳。(《答吴晦叔》,《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二)
这里并非意味着朱子对稍早几年“所以复者”的思想做出根本调整,而只是对之前用的“所以”这个表达略作了澄清,指出“复则见天地心”与程颐“所以阴阳”的意义不同。其实,在上文引用的给张栻的书信中,朱子说的是“其所以复者则有自来”,于此可见,朱子本就强调的是天地之心作为所生之物的来源、根源之意,因而上文的“所以”强调的是“所自来”,而程颐“所以阴阳”的“所以”则是强调阴阳之所以循环无端的根据,两者的意义本就不同,但毕竟用“所以”还是会引起误解,故而朱子也不再使用“所以复者”的表达指称天地之心。此外,这封书信还通过区分“复非天地心,复则见天地心”明显突出了“见”字所标明的结构,即上文分析《延平答问》时指出的“由……见……”的结构。通过上述分析可见,至少直到乾道八年,朱子在解释“复见天地之心”的本文的意义时,仍然坚持他在《延平答问》时期所获得的源初的洞见:由所生之物——在《复卦》本文中即一阳始生——见出、显示出生物的来源、根源,即天地生物之心。同时,天地之心生物不息,没有片刻的间断,因而时时刻刻都有新的生气在生成。
在本文第一部分的分析中已经表明,朱子在不同的时期都在两种意义上把“复见天地之心”和“未发已发”关联起来:其一、就未发之体和已发之用的关系而言,“复见天地之心”指的是由“已发之用”显示“未发之体”;其二、就心体流行过程中的未发和已发两个阶段而言,“复见天地之心”对应未发阶段中的“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但是,就第二种意义上的对应来看,“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如何体现出“复见天地之心”中的“由……见……”的结构呢?对此需要进一步分析“由……见……”结构中这个所由以见出天地之心的所生之物。由上文“所复者气也”的表述来看,由所生之气见天地生物之心是一种理解“由……见天地之心”的方式。在《朱子语类》中载有朱子与弟子之间关于何种所生之气的状态符合“复见天地之心”的理解的讨论,据笔者详细考察之后认为,朱子对此问题可以分为两种说法,为了行文的简洁,以下仅选择部分条目摘录(为了表明朱子在不同时期都存在下述两种说法,括号内加注弟子记录的年限),兹先录第一组如下:
冬,终也;终,藏也。生气到此都终藏了,然那生底气早是在里面发动了,可以见生气之不息也,所以说“复,见天地之心”也。胡泳。(庆元四年所闻,《朱子语类》卷五十三)

一元之气,亨通发散,品物流形。天地之心尽发见在品物上,但丛杂难看;及到利贞时,万物悉已收敛,那时只有个天地之心,丹青著见,故云“利贞者性情也”,正与“《复》其见天地之心”相似。僩。(庆元四年以后所闻,《朱子语类》卷七十一)
天地之心,别无可做,“大德曰生”,只是生物而已。谓如一树……到冬时,疑若树无生意矣,不知却自收敛在下,每实各具生理,更见生生不穷之意……《通书》曰:“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通即发用,复即本体也。㽦。人杰录少异。(淳熙十五年所闻,《朱子语类》卷六十九)
由上可见,朱子在这些说法当中将“复见天地之心”的“复”解释为周敦颐《通书》“利贞诚之复”的“复”,对应冬季万物寂静,生意敛藏,但此时已经蕴蓄了新的尚未显露而即将显露而出的生气。由于天地之心生物不息,故而不存在没有生气生出来的时刻,但存在生气生出来却尚未显露的时刻,这正对应隆冬时节所蕴蓄的细微的始生之气。所以会有“那生底气早是在里面发动了”、“却自收敛在下”等语言,指的就是在生意敛藏至于极致之中已经蕴蓄了新的始生之气。这样,由以见出天地之心的生气就以蕴蓄于生意敛藏之中的尚未显露而即将显露的存在状态而得到了把握。此外,在朱子看来,之所以需要由生意敛藏之中蕴蓄的尚未显露的生气见出天地之心,不是因为只有这时才能见出天地之心,天地之心生物不息,没有片刻间断,生物繁盛丛杂之时也都能展现出天地之心,只是不如生气蕴蓄之时容易看出。在朱子看来,生物丛杂之时天地之心本身就容易被具体的丛杂的所生之物所掩蔽,所谓“但丛杂难看”指的就是“看者”(也即人)易于滑入对具体的繁盛的所生之物的“看”,所看到的总是落入具体的某种生物,而“难看”所生之物的来源即天地之心自身,而恰恰在天地寂静之中仍然蕴蓄的细微的新生之气之中,最易见出与之一同显示出来的天地生物之心。
但是,朱子对由以见出天地之心的所生之物的状态还有另一种说法:
十月万物收敛,寂无踪迹,到一阳动处,生物之心始可见。淳。(绍熙元年、庆元五年所闻,《朱子语类》卷六十二)
十月阳气收敛,一时关闭得尽。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尝息,但无端倪可见。惟一阳动,则生意始发露出,乃始可见端绪也。铢。(庆元二年以后所闻,《朱子语类》卷七十一)
圣人说“《复》其见天地之心”,到这里微茫发动了,最可以见生气之不息也,只如此看便见。(未载何人所录,《朱子语类》卷七十一)
在这几条语录中,朱子首先承认天地之心生物不息,但是只在有端绪显露出来的时候才能见出,与之相区别的便是“万物收敛”、“阳气收敛”之时无端倪可见。可见,有别于第一组记载中以“利贞诚之复”解释“复”字之义,这一组记载是以“复现”之义解释“复”字,即阳气重新显露端倪。显然,这里能够显示出天地之心的就是微微显露出来的生气。相较之下,前引第一组记载中朱子恰恰认为正是在万物收敛之中蕴蓄的尚未显露而即将显露的生气最易显示出天地之心。两组记载的差别在于:通过生气的何种状态最易见出天地之心。前者认为通过生意敛藏之中蕴蓄的尚未显露的生气最易见出,与之相对的则是生物丛杂之时难以看出天地之心;后者则认为通过微微显露的始生之气最易见出天地之心,与之相对的恰是万物收敛之时“无端倪可见”。
可以说,在上述两组表达中,一者指的是生气流行尚未显露的阶段,而另一者则指的是生气流行显露几微的阶段。但是,当朱子的弟子就“复”的两种用法请教朱子时,朱子认为二者虽有差别但根本指向则是一致的:

“伊川与濂溪说‘复’字亦差不同。”用之云:“濂溪说得‘复’字就归处说,伊川就动处说。”曰:“然。濂溪就《坤》上说,就回来处说。如云‘利贞者诚之复’……伊川却正就动处说。如‘元亨利贞’,濂溪就‘利贞’上说‘复’字,伊川就‘元’字头说‘复’字。以《周易》卦爻之义推之,则伊川之说为正。然濂溪、伊川之说,道理只一般,非有所异,只是所指地头不同。以《复卦》言之,下面一画便是动处。”僩。(《朱子语类》卷七十一)
此条为沈僩所录,又载刘用之之语,当为庆元五年所闻,可以算作朱子最后的说法。在此,朱子区分的周敦颐和程颐的两种说法恰好对应上文摘录的两种说法。在朱子看来,就《复卦》的本文来说,程颐的解释贴合本文,但就“道理”而言,两说没有根本区别。这里的“道理只一般”当然是指两说对“复见天地之心”所包含的道理的揭示根本一致。实际上,这其中的道理已由上文阐明,无论是生意敛藏之中蕴蓄的尚未显露的生气,还是微茫显露的生气的端倪,都可以由之显示出自身并不孤立显示而是与其所生之物一同显示的天地生物之心。由于天地之心生物不息,不存在没有生气生出来的时候,故而就天地之心及其运作而言,不可用心体流行过程中的未发已发两个阶段把握天地之心,因为心体流行的两个阶段是就思虑是否发动从而指向具体事物而言,但天地惟以“生物”为心,天地之心不曾止息地生出生气,不可能区分出生出生气之前的阶段和生出生气之后的阶段,毕竟根本没有前一个“阶段”可言。但是,就天地之心生出的生气流行而言就可以套用心体流行的过程分出两个阶段,即生气尚未显露和生气已经显露两个阶段。这样,就天地之心本身的层面谈论“未发已发”就仅仅只有一种说法,就是本文第一部分所引记载中区分的未发之体和已发之用。生气流行的两个阶段都属于天地之心的已发之用,由之可以显示出未发之体。但是,这里存在的问题在于:既然朱子明确承认程颐的说法贴合《复卦》本文,那么,何以朱子还要不厌其烦地阐释“复见天地之心”的第一种意义呢?首先,如朱子自己所说,这当然是因为在“道理”上这样说是合乎道理的,这一点上文已经阐明。但是,除了这个原因,笔者认为,这也与朱子在“己丑之悟”中确立的心体流行的思想和与之相关的“静中存养”工夫的优先意义有关。下文将试图对此给出详细阐明。
三、“知觉不昧”与“静中存养”
如果将上文对“复见天地之心”的阐释再次引入到对《答张钦夫》(诸说例蒙印可)的解释,那么,这封书信中“方其存也,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是则静中之动,复之所以见天地之心也”这句话的内涵就能获得清晰的理解。以下试做疏解。首先,由上文已经阐明的“复见天地之心”的意义可知,生气流行的两种状态——尚未显露和显露几微——都可以显示作为生气流行的根源的天地生物之心。那么,对应于这句话可知,这里将“复见天地之心”引入心体流行的未发阶段所表达的意义在于,“复见天地之心”所包含的“由……见……”的结构同样适用于心体流行的过程,因而这里完整的意思应当是:由“思虑未萌知觉不昧”可以见出天地之心。并且,“思虑未萌知觉不昧”正是“静中之动”的一种表现,即在心灵活动尚未产生关于某个具体对象的具体思虑之前,心灵活动自身未曾间断,而是始终处于活动醒觉的状态,而这种活动醒觉的状态具备随时展开为朝向某个具体对象的具体思虑的可能,这就好比在生意敛藏之中蕴蓄的尚未显露而有待显露的生气一样。进一步而言,如同上文已经言明,朱子在《延平答问》时期就已经认为由“生”这个事实可以显示天地之心,而至少在乾道三年给张栻的书信中就已经明确提出“天地以生物为心”这一表达并进行了阐明,那么,这里由静中知觉不昧显示出的天地之心当然就是天地生物之心。
但是,这种显示不同于由生气显示作为生气根源的天地之心,因为“心”不等同于“生气”,而是如同朱子在随后的《仁说》当中提出的“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七),即由人心之活动不息、静中醒觉、至静之中蕴蓄的随时展开为具体思虑活动的可能性,显示出作为人心之根源的天地生物之心。不过,既然是由一者显示另一者,自然二者之间有不同,二者的差别就在于,人心之活动不息恰恰就是天地之心的具有主宰意义的“生”的作用所生成的结果。这种生物不息、活动不息的状态正是朱子关于“仁”的展现的整体概观。故而朱子在这封书信中,紧随此处疏解的这句话之后,就有“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贯彻而无一息之不仁也”这样的总结,又在随后正式的《仁说》当中深化了这种思想。当然,这种状态并不等同于“仁”,而是“仁”所展现出来状态。经由上述分疏可知,朱子在“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的表达中所揭示出的心灵状态,不仅与佛者溺于虚无寂灭的静坐工夫划清了界限,也不同于日常所说的意识的流转不住,而是对天地生物之心的展现、对“仁”所展现出的周流不息的状态的展现,这也同时就是对人心当中具有价值内涵的心之仁德的确立。
但是,此处仍然存在如下问题:正如生气蕴蓄和生气显露都可以显示天地之心,同样,静中知觉不昧和动中思虑萌发都能作为心体流行的状态而显示作为心体流行之根源的天地之心,但上文引述的朱子《答张钦夫》中却单以静中知觉不昧对应“复见天地之心”,这是为何?从这封书信的上下文来看,朱子分别引入《复》之“见天地之心”和《艮》之“不获其身不见其人”对应心灵活动的两种状态,前者对应心在未发时节,“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是则静中之动”,而后者则对应心在已发之际,“事物纷纠而品节不差,是则动中之静”。对于后者的解释可以很容易得到澄清。依朱子,《艮》卦的大义在于“各止其所”,朱子云:“‘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易》中只是说‘艮其止,止其所’。人之四肢百骸皆能动作,惟背不能动,止于背,是止得其当止之所。明道答横渠《定性书》举其语,是此意。”(《朱子语类》卷七十三)这样,朱子以《艮》对应心在已发之际能够做到“品节不差”,指的就是心在应事接物的过程中能够达到自身的安定状态,并进而实现对事事物物极致恰好的安顿,让事物得其所止。但是,无论心在静时动时,其实都显示了“天地之心”,那么何以朱子在此必定要以《复》之“见天地之心”匹配静中知觉不昧的心灵状态呢?表面看起来,朱子只不过是把心灵活动在未发和已发阶段的两种状态贴切地对应到了经典中的原文,看起来只是一种修辞上的表达。
然而,如果联系到朱子为天地之心赋予的主宰地位和朱子为“静中存养”工夫赋予的优先地位,那么,这里的关联就不仅是修辞上的关联。为了继续澄清这个问题,下文将通过阐明“静中存养”工夫所具有的优先意义,从而阐明何以“复见天地之心”和静中知觉不昧之间具有必然的关联。已有的研究已经表明,朱子在从学延平时期就接受过延平静中体验未发气象的教诲,并认为这是道南一脉相传指诀,但朱子自己却未能对此有深刻体会。他在延平离世之后给何镐的信中说:“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然当时亲炙之时贪听讲论,又方窃好章句训诂之习,不得尽心于此,至今若存若亡,无一的实见处,辜负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尝不愧汗沾衣也。”(《答何叔京》,《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但是,在“己丑之悟”之后,朱子自认为已经对延平静中工夫的要义有所体会,他在给林用中的书信中,在简述了自己的中和新悟之后就言及延平的教诲:“旧闻李先生论此最详,后来所见不同,遂不复致思。今乃知其为人深切,然恨已不能尽记其曲折矣。”(《答林择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三)可见,在“己丑之悟”之后,朱子自认为已经了解了延平当时的教诲“为人深切”。
在写于乾道八年的《中和旧说序》中,朱子更是确信自己领会了延平关于未发工夫的指点:“独恨不得奉而质诸李氏之门,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远矣。”(《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可见,从延平离世开始,“静中体验未发气象”就成了朱子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持续缠绕在朱子的思想中,直到“己丑之悟”朱子才确信对“未发”的含义以及相应的静中工夫有了恰当的理解。从上引《答何叔京》中“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的概括可知,在朱子的理解中,李侗的静中工夫相较于处事应物而言更具优先意义。可见,至少直到“己丑之悟”,就朱子自己的思想处境而言,李侗教诲中的静中工夫对于朱子本人产生了巨大影响,与之相应,静中工夫也就占据更优先的地位。不仅如此,更直接的证据表明,朱子在其成熟的思想表达中同样强调了“静中存养”工夫的优先地位。他在《已发未发说》中就说:“以事言之,则有动有静。以心言之,则周流贯彻,其工夫初无间断也,但以静为本尔。”(《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七)在上文分析过的给张栻的书信中也对这个问题做出回应:“来教又谓熹言以静为本,不若遂言以敬为本,此固然也。
然‘敬’字工夫通贯动静,而必以静为本,故熹向来辄有是语。今若遂易为‘敬’,虽若完全,然却不见敬之所施有先有后,则亦未得为谛当也。”(《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二)可见,朱子虽然承认“敬”的工夫贯通动静,但在这个看似完全的“敬”的工夫当中还必须分别先后,故而必须要说“以静为本”。关于“以静为本”,朱子在乾道七年给胡广仲的书信中给出解释:“必曰主静云者,盖以其相资之势言之,则动有资于静而静无资于动。如乾不专一,则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则不能发散。”(《答胡广仲》,《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二)从这封书信可以看出,朱子所以必须确立“静中存养”工夫的优先地位,理由在于“动有资于静,而静无资于动”。如果就上文讨论的心体流行的动静两种状态而言,可以说,动中状态要得到恰当合宜的展开(事物纷纠、品节不差),就必须经由静中状态的存养工夫才得以可能。这其实就是朱子在中和新说中强调的“本领工夫”:“但平日庄敬涵养之功至,而无人欲之私以乱之,则其未发也,镜明水止,而其发也,无不中节矣。此是日用本领工夫。”(《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四)但是,朱子所谓的“静中存养”并非无所事事,而是在尚未应事接物、产生具体思虑的时候,始终维持此心活动不息、知觉不昧的醒觉状态,而这种状态朱子又以“主宰”称之:
殊不知未感物时,若无主宰,则亦不能安其静,只此便自昏了天性,不待交物之引然后差也。(《答林择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三)
未发时着理义不得……只一个主宰严肃,便有涵养工夫。㽦。(《朱子语类》卷六十二)
虽是耳无闻,目无见,然须是常有个主宰执持底在这里,始得。不是一向放倒,又不是一向空寂了。贺孙。(《朱子语类》卷九十六)
下面说《复卦》,便是说静中有动,不是如瞌睡底静,中间常自有个主宰执持。贺孙。(《朱子语类》卷九十六)
可见,静中维持此心常活、知觉不昧的醒觉状态,根本上是一种涵养此心自做主宰的工夫,由此才能称为“本领工夫”。综合以上所引材料可以给出如下分析,心体流行周流不息、无间动静,但是,理想的心灵状态要求静中知觉不昧、动中品节不差,而后者以前者为本。这是因为,动中品节不差的思虑活动总已经处在了具体的关于某物的知觉当中,也就是说,它不再是纯粹的、整体性的、尚未进入分别状态的心灵活动,而静中维持醒觉的心灵活动,由于它尚未滑入有所限定的关于某物的思虑当中,故而它是整体性的纯粹的自身显示,这种特殊的心灵状态维持自身为纯粹的醒觉的姿态,以便在不为任何思虑、外物所扰动的情况下,随时在事至物来时迅疾感应而投入到具体的关于某物的思虑活动,由于它排除任何扰动而保持纯粹的醒觉,故而它自做主宰,又能以主宰的状态进入具体的思虑活动,使得具体活动能够排除干扰而实现当然之则。由此分疏,一种特殊的且具有优先意义的心灵状态就被揭示了出来,这种特殊的心灵状态虽然不是常人在日常状态就能直接达到,但却可以通过与之相应的具有优先意义的“静中存养”工夫而达到,在这种特殊的心灵状态中,心灵处于尚未进入有所限定的关于某物的思虑当中,而整体性地自身显示为、自身保持为纯粹的无所扰动的醒觉的状态,这种状态既是此心自做主宰,又主宰了心灵的其他活动,而“静中存养”工夫所存养出来的就是这种特殊的心灵状态。
这样,这种特殊的心灵状态与“复见天地之心”的特殊的关联就可以得到澄清。这种特殊的关联在于:在诸多心灵状态中,唯有这种特殊的心灵状态——这种尚未进入具体思虑活动的整体性自身显示的纯粹的醒觉——最直接地显示作为其根源的天地之心。为了对此做更充分的说明,可以先回顾上文的分析。在朱子看来,生物丛杂繁盛之时,反倒不易看出天地之心,而在生意收敛之中蕴蓄的尚未显露的生气之中,更易看出天地之心。这正是因为:在生物丛杂之中,生气总是已经具体化为了某物的生气,而作为生气根源的天地之心自身反倒容易被掩蔽起来,只有在尚未作为某物的生气显露的纯粹蕴蓄着的生气中,才最直接地显示了天地生物之心。但是这个“直接性”并不是指作为未发之体的天地之心能够孤立显示自身,而是指天地之心虽然总是随同其已发之用而显示自身,不过就其诸多已发之用当中仍然可以区分出最特殊的一种,即尚未显露的纯粹蕴蓄着的生气,而这种生气的活动状态因其尚未落入作为某物的生气,故而最直接地显示了生物之源的天地之心。与此结构相应,在心体流行的诸多状态中有一种最特殊的状态,即上文阐明的那种尚未进入具体的关于某物的思虑活动的纯粹醒觉状态,这种状态因其活动的纯粹性而最直接地显示了天地之心,直接地显示了作为心灵能够活动起来的根源的天地生物之心,没有天地之心的“生”的必然趋势,就没有能够醒觉、能够活动的心体。这样,静中知觉不昧和“复见天地之心”之间的必然的关联就得到了阐明。简言之,唯有经由静中纯粹醒觉这种特殊的心灵状态的自身显示才能最直接地显示天地之心,唯有“复见天地之心”这句直接道说天地之心的经文才能言明静中纯粹醒觉这种具有优先意义的心灵状态。借此也就一并阐明了本文第二部分遗留的问题,即何以朱子在承认由显露端倪的生气见出天地之心这种解释是贴合本文的解释的情况下,还要屡言另一种解释。一言以蔽之,理由就在于后者才是朱子更为看重的解释,唯有由至静之中纯粹蕴蓄的生气才能在不掺杂任何具体生物之气的状态中最直接地显示出天地生物之心,而这也更为符合朱子力图确立的“静中存养”工夫的优先意义这一思想旨趣。
四、余论
综上,朱子关于“复见天地之心”和“未发已发”关系的思考已经得到了阐明。在朱子看来,天地之心就是天地以生物为心,而“见”字则意味着“由……见……”的结构。就天地之心自身及其作用而言,这个结构指向由已发之用见未发之体的关联。天地之心自身不会孤立显示,而是由其已发之用的显示而一起得到显示,即随同其所生之物、随同生气流行一起得到显示。虽然朱子承认,就《复卦》本文而言,这句话的意思应当是由生气流行中的隐隐已经显露的生气的端倪显示天地之心,但是朱子实则更看重另一种解释,即由生气流行中尚未显露的纯粹蕴蓄的生气显示天地之心,这种特殊的生气流行的状态以其尚显露为某物的生气而保持纯粹性,就其纯粹性而言最直接地、最纯粹地显示了天地之心。与此相应,心体流行的诸多状态中同样有一种特殊的状态,即尚未落入有所限定的关于某物的思虑活动而维持为纯粹的醒觉,这种纯粹的醒觉同样以其纯粹性而在心灵活动的层面最直接地显示天地之心,也因此而具有在诸多心灵状态中的优先地位,这种状态既表明心灵自做主宰,又能够作为主宰进入具体的与物交涉的思虑活动。“静中存养”工夫存养出来的就是这种特殊的心灵状态,这种工夫所以具有优先地位,也正是由此而得到说明。
这样,本文事实上也就同时引向了朱子思想历程中一个关键问题:己丑中和之悟到底意味着什么?其间的意义非常复杂,可以放在各种关联语境下得到理解,学界也早已对此问题做了丰富的研究。就朱子本人在“中和新说”的表述来看,此说的意义就在于确立了他所谓的“本领工夫”。[11]但是,就本文的视角而言,这个本领工夫不是朱子自己通过某种主观的偶然的体会而体验到的,而是通过道理上的追寻而确立的。这个追寻过程就是要在诸多心灵状态中找寻到一种优先的状态,也即从各种已经落入有所限定的关于某物的思虑活动当中回退到尚未落入具体思虑活动的纯粹的醒觉,但是这两者都是心灵活动的某种状态,前者并非由后者派生出来的,只不过后者的优先地位在于,只有保持了后者前者的品节不差才是有可能的。这也就是朱子要从已发察识追溯未发涵养的意义所在。因而,朱子的“以静为本”不同于王弼“以无为本”。[12]在朱子这里,“以静为本”的意义只有在首先确立流行统体活动不息的前提下才能成立,也就是说,“以静为本”不是以静为流行统体之本,而是在流行统体之中的以静为本。这一点无论对于心体流行还是生气流行都适用。进一步,“以静为本”还直接显示了天地生物之心,而这才是朱子的落脚所在,即由此进入“仁”的思考。
换言之,静中纯粹的醒觉恰恰纯粹地显示出了作为生生不息的根源的天地生物之心。另一方面,在朱子确立“静中存养”工夫的优先地位的过程中,不得不说李侗的影响始终在发生作用,李侗静中体验未发气象的道南指诀一直是朱子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但是,朱子“静中存养”工夫却不是对李侗的简单的重复。从本文在开头引述的《延平答问》的记载来看,朱子认为由“生”这一事实可以显示天地之心,已经暗含了在后来正式提出的“天地以生物为心”这一表述中所包含的洞见。因此,纵然朱子自认为他的“静中存养”工夫是对李侗的指点的重新体会,但是客观来看,不得不说其实是李侗的指点与朱子本人的源初洞见之间的差异才是推动朱子达成上述思考的一项重要缘由,这个差异就是:如何在朱子自己早就确认的生生不息的流行统体之中安顿以静为本的优先地位。正是中和新说的确立才使得这个困难得到一定程度的安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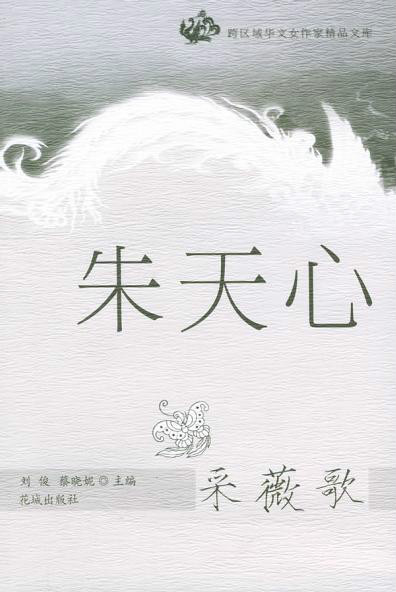
注 释
———
1.陈来在《仁学本体论》中就指出:“北宋前期对《周易》的思想诠释是儒学的共同关注,也因此,天地之心的思想对宋儒影响甚大,宋儒对天地之心的运用也最为广泛。”参见陈来:《仁学本体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第230页。
2.朱子为刘子翚所作的墓表中记载了刘子翚曾语朱子云:“所谓‘不远复’者,则吾之三字符也。”(《屏山先生刘公墓表》,《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
3.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328-329页。
4.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3册,第329页。
5.相关考证参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第60-61页、第68页;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176-177页;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406-409页;顾宏义:《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第3236-3241页。
6.虽然学界对朱子在“中和新说”当中的“未发”“已发”概念的内涵尚存争议,但就朱子《已发未发说》、《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和本文此处引述的《答张钦夫》(诸说例蒙印可)来看,陈来先生所分析的朱子“未发”“已发”的两种用法中的第一种用法应是确凿无疑。陈来先生认为朱子在“中和新说”中首先的用法是以“未发”“已发”指“心理活动的不同阶段或状态”,“心体流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或两种状态。思虑未萌时心的状态为未发,思虑萌发时心的状态为已发,也就是说心有已发时,有未发时。”参见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175页。本文对朱子“中和新说”当中用来描述心灵活动的“未发”“已发”概念的理解遵循陈来先生的上述结论,不再另行说明。
7.如同陈来先生已经指明:朱子也在“性体情用”的意义上使用“未发”“已发”概念,即以性为情之未发,情为性之已发。参见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179页。
8.详细讨论可以参见陈来:《朱熹的与宋代道学话语的演变》,收入陈来主编:《早期道学话语的形成与演变》,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第182-228页。
9.陈来:《仁学本体论》,第316页。
10.此义赵金刚、唐文明论之甚详。赵金刚综合朱子众多表述得出推论:“天地之心也就是天地之理……理对于气的主宰,就是生物的不停息,‘生’是主宰的根本含义。”参见赵金刚:《主宰谓之帝——朱子哲学中“理”的主宰作用》,《哲学动态》2016年第3期,第65页。唐文明认为:“‘天地以生物为心’的表述更有可能被理解为一种实在的描述,从而隐约透露出天地生物的主宰之义。”参见唐文明:《朱子论天地以生物为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159页。
11.例如,陈来认为,朱子的中和新说“不是通过未发工夫获得内心体验,而是把主静之功作为主体修养的手段,以为穷理致知奠定基础。从追求未发体验的直觉主义转为主敬穷理的理性主义,才是朱熹早期学术思想演进的真正线索”。(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193页。)王健认为,朱子确立“静中存养”工夫的优先地位是要确立在“存养”中“所应保持的对天理良知的敬畏……他的深意在于突显天理良知作为价值理念相对于人类实践活动的绝对性”。(王健:《在现实真实与价值真实之间——朱熹思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248页。)牟宗三则全然不能理解朱子以“静中存养”为先的工夫旨趣,认为朱子“只于动察以外补之以静时之涵养,则其涵养乃成不自觉之盲目者,空头者,所谓平时之庄敬涵养只成外部地养成一种好习惯而已”。(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第132页。)
12.向世陵认为,朱子“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作为程颐对立面的王弼的‘故动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见也’的思想成分”。(向世陵:《理学与易学》,长春出版社,2011,第194页。)由本文的分析来看,此说应当是值得商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