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890年,瑞典裔德国学者欧拉·汉森(Ola Hansson)就曾写过《尼采与自然主义》一文。他把“自然主义”理解为一种以左拉为代表的现代文艺流派,并试图在文章中探讨尼采与这一文艺流派之间的关系。与欧拉·汉森一样,许多早期研究者都把“自然主义”看成是一种简单的,非哲学的思想。因此,他们要么像奥古斯特·多尔纳(August Johannes Dorner)那样,认为尼采的“自然主义”虽然独特,但却不是一种哲学观点;要么像雅斯贝尔斯那样,认为在尼采貌似简单的自然主义背后还隐藏有哲学深意。
尼采
近年来,布赖恩·莱特(Brian Leiter)、理查德·沙赫特(Richard Schacht)、克里斯托弗·贾纳韦(Christopher Janaway)等英美学者试图让尼采与分析哲学传统对接,重提尼采与自然主义之间的关系,重新把尼采定义为自然主义者,从而引发了学界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尼采究竟是不是一位自然主义者?如果是,那么他的自然主义是何种自然主义?尼采的自然主义与现代科学的契合程度有多大?以及他的研究方法能不能与科学的经验方法对接?
布赖恩·莱特认为“因果关系和因果性解释”(Causation and causal explanation)是尼采自然主义的核心。在《尼采论道德》一书中,他把自然主义分为方法性自然主义和实质性自然主义,并认为,无论在方法性上,还是在实质性上,尼采都是自然主义者。理查德·沙赫特批评认为,莱特试图将尼采的自然主义科学化,然而,科学自然主义却是尼采所鄙视的东西。与其说尼采的哲学是一种科学自然主义,不如说他的哲学是科学自然主义的解毒剂,也就是说,尼采在寻找一种科学自然主义的替代性方案。基于此,沙赫特给尼采的自然主义下了一个定义:“尼采可以被理解为一位自然主义者,因为他对一切人类事物的说明和解释,不与科学相冲突”,甚至在某些地方他“还受到了科学的影响”,并且他的说明和解释“不涉及到其他任何超越于此岸世界之外的东西”。可见,沙赫特将尼采自然主义的特征归纳为如下三点:1,尼采只关注此岸世界;2,尼采对此岸世界的论述与科学不冲突;3,尼采的某些论述受到了当时科学的影响。然而如果尼采的自然主义不过是沙赫特所归纳出来的这三点的话,那么我们当下的每个人似乎都能够称得上是尼采式的自然主义者了。沙赫特显然已经意识到,把尼采与经验科学严格对接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他试图在一种更加宽泛的意义上来解释尼采与科学的关系,以便使自己显得不像莱特那么激进。
赫尔穆特·海特(Helmut Heit)在《自然化视角:论尼采实验性自然化的知识论》(Naturalizing Perspectives. On the Epistemology of Nietzsche’s Experimental Naturalizations)一文中提出了用自然主义来定义尼采时遇到的两难:如果我们放宽自然主义的内涵,使人人都是自然主义者,那么自然主义这个概念就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而如果我们明确地限定自然主义的内涵,那么尼采是否是自然主义者就是成问题的。于是海特认为,虽然把尼采与自然主义联系起来不能说是全错,但在论证尼采是自然主义者的同时,研究者却需要提供许多限定性条款来避免指责,这些逃避指责的附加性条款如此之多,以至于常常会超出了研究的必要性而成为一种恶。因此,与其用自然主义这样的标签来定义尼采,倒不如通过研究其哲学特色来丰富尼采。海特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依此来为尼采撕掉“自然主义者”这个标签,却未免矫枉过正。因为,早在1873至1874年间,尼采在思考“伦理自然主义崇拜”的同时,就曾经明确地宣称,“我们是纯粹的自然主义者”。虽然如海特所言,“自然主义”这个词在尼采著述中出现的次数并不多,而且前后出现时的内涵也颇有不同,但它却是一个经过晚期尼采审定过的概念。尼采在他发疯前亲手审定过的最后一本书《偶然的黄昏》中提出“回归自然”和道德“自然主义”绝非偶然。如果说尼采早期在《悲剧的诞生》中使用“自然主义”更多遵循的是当时的惯常用法的话,那么,到了晚期《偶像的黄昏》那里,尼采就将这个概念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使之成为了一个可以与“超人”、“永恒轮回”、“权力意志”相提并论的尼采式的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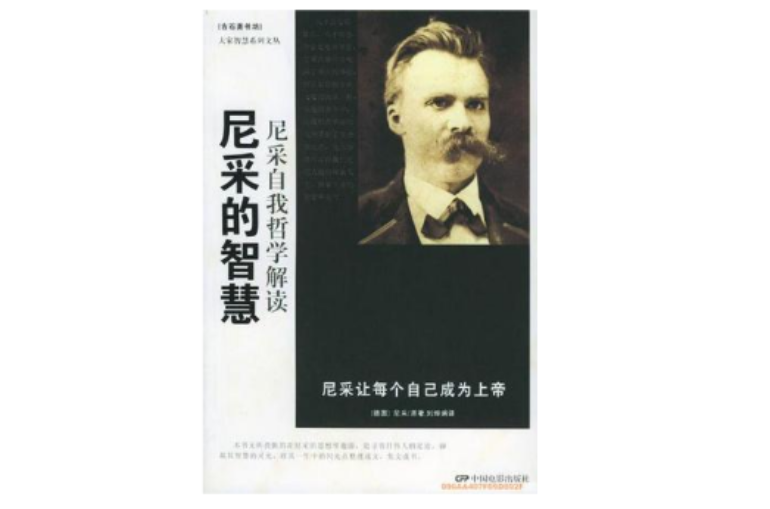
无论我们承认或者不承认尼采自然主义者的身份,尼采的“自然”思想都是研究者无法忽视的。列奥·施特劳斯、洛维特等都曾对尼采的“自然”思想有所论述。比如在《注意尼采谋篇》(1973)一文中,施特劳斯认为,尼采试图把人类历史整合到人的自然化进程当中去理解,因此,自然在尼采那里具有历史属性。当然,尼采的自然思想并非施特劳斯关注的重点,他只是想借此来阐释尼采未来哲学与传统哲学(比如柏拉图主义)之间的延续性,而不像法国新尼采主义者那样,强调尼采哲学与传统哲学之间的断裂性。
洛维特与施特劳斯不同,他把尼采的“自然”概念看成是对“上帝死了”这一事实的弥补。因此,尼采的“自然”或“自然世界”在洛维特那里就具有一定的形而上学味道。洛维特认为,尼采的“自然”只是上帝的一个功能性替代品,自然作为永恒整体的必然性与人作为有限个体的偶然性之间的矛盾,只有通过“所有事件当中的绝对同质性(die absolute Homogenität in allem Geschehen)”才能够解决,这也就意味着,处于永恒轮回中的相同者(das Gleich),无论在类型上、还是力量上,都绝对的相似或者相等。
新世纪以来,布赖恩·莱特等一些英美学者为了让尼采与分析哲学传统对接,开始重新思考尼采与自然主义之间的关系,重新把尼采理解为自然主义者,以此来否定他的“形而上学家”和“后现代主义者”身份,但他们却忽视了尼采思想中不可通约的神秘主义元素。尼采虽然在思想上有过所谓的实证期,也主张过“快乐的科学”,但是他所说的科学绝不是追求经验实证的自然科学或科学哲学,而是以康德的严格现象论为基础,糅合了语文学、心理学、生理学的现代成果和方法,并且具有一定神秘主义倾向的“科学”。这是尼采为自己量身打造的“科学”。也就是说,这种“科学”只属于尼采自己。
尼采的自然主义是一种现象论吗?
既然尼采的“科学”是以康德的现象论为基础,那么,他的自然主义是一种现象论吗?或者更确切的问题是,尼采是一位康德式的现象主义者吗?
“现象论”或“现象主义”(Phänomenalismus)这个词在尼采公开出版的著述当中出现过两次,一次在《快乐的科学》里,与视角主义一词并列。还有一次则出现在《敌基督者》里,和尼采对佛教的理解关联在一起。尼采将佛教称为“唯一真正实证的宗教”,而将佛教的知识论称为“一种严格的现象主义”。也就是说,在尼采看来,现象论本质上是一种与视角主义及实证主义相关的知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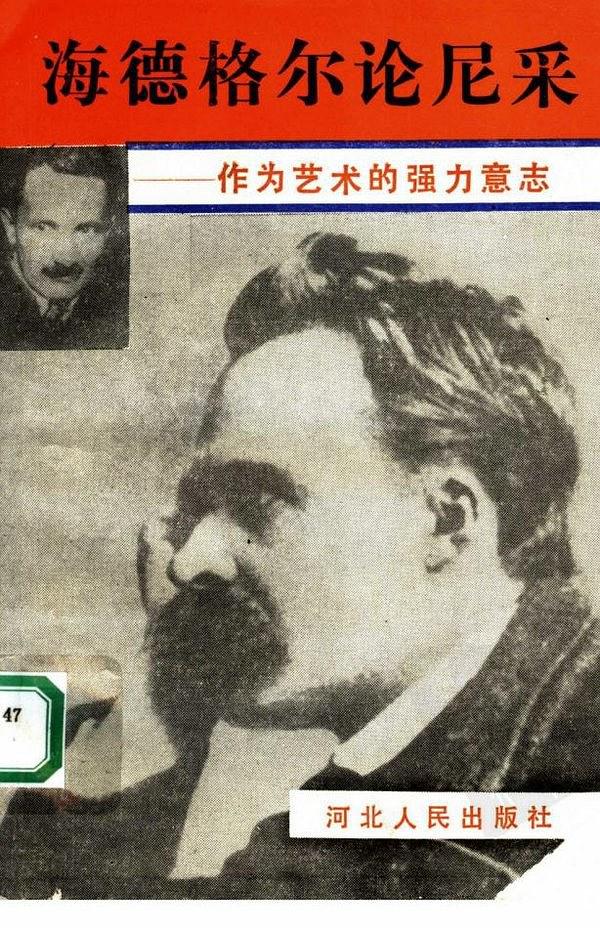
此外,在1885至1889年的遗稿中,“现象论”一词还出现了8次之多,这表明尼采晚期确实对康德——叔本华的“现象论”有过集中的思考。不过,尼采把“现象论”视作他思考问题的起点,而并非是终点。也就是说,康德——叔本华“现象论”是尼采要超越的对象,而不是效仿的对象。
例如,在1885年秋至1886年秋的遗稿中,有这么一段话:
后来我意识到,道德怀疑论走的有多远了:我从哪里重新认识自己呢?
决定论:我们并不对自己的本质负责
现象论:我们对“物自体”一无所知
我的难题:从道德以及道德的道德性中,人类迄今为止得到了何种伤害呢?精神伤害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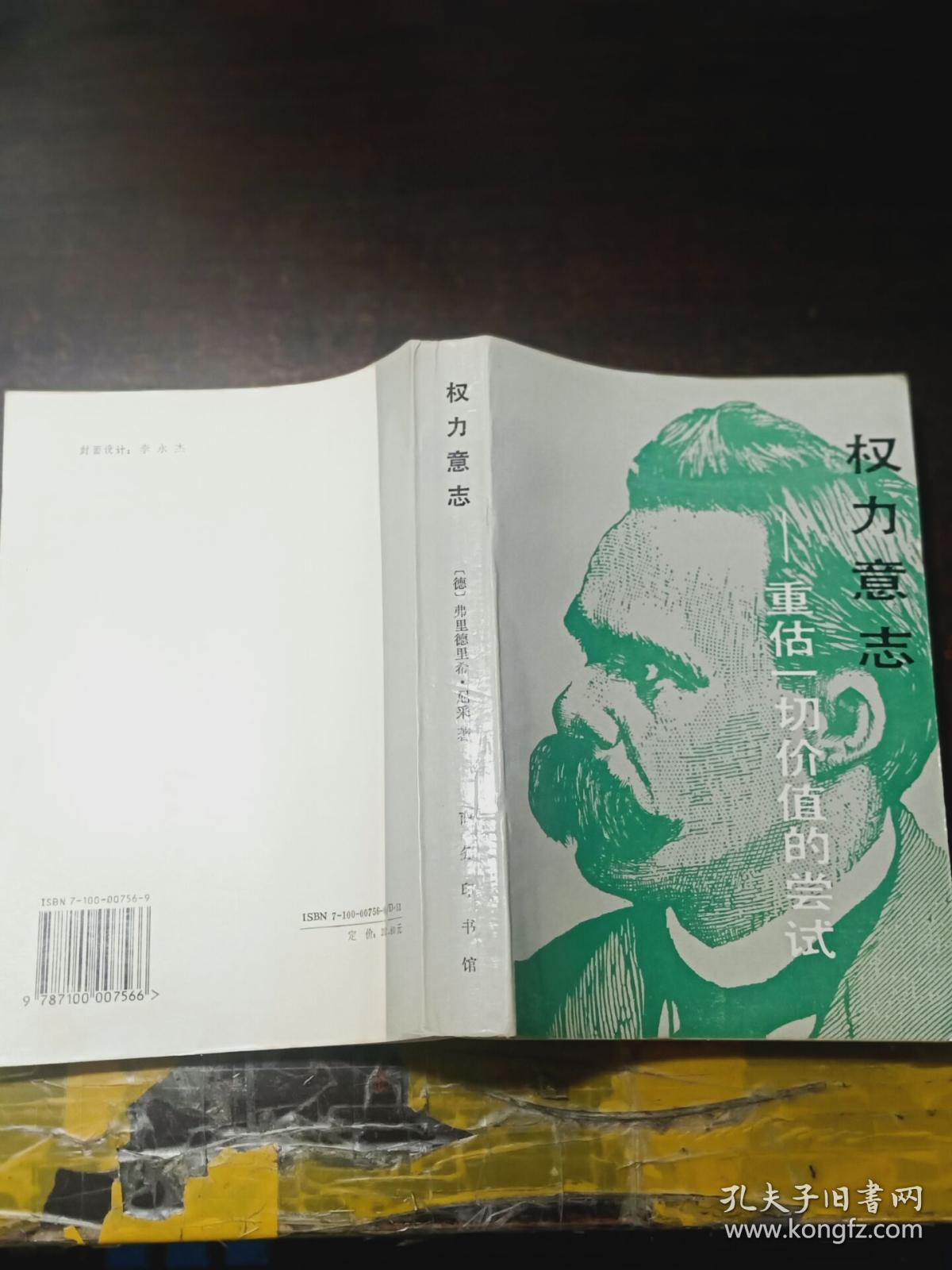
我对一位作为旁观者的智者的厌恶
我的更高概念“艺术家”(KSA12.158)
这段遗稿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揭示出,在尼采那里,“现象论”和“决定论”是“重新认识自己”和开展道德批判的两个重要前提,也就是说,“现象论”和“决定论”是尼采“价值重估”的起点;同时,它还揭示出,在尼采那里,“艺术家”是一个比“旁观者”(智者)“更高的概念”。尼采试图借助“艺术家”来超越“决定论”和“现象论”。
“决定论”是18、19世纪科学界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它认为,有因就有果,万物由因果关系联系在一起,其运动则由确定的自然规律决定。如果我们把这种机械的“决定论”贯彻到底,将之运用到“自我认识”领域,那么得出的结果就是:我们不能够对自己的本质负责。因为,我们的本质在实现之前早就已经被各种因素决定了。人如果不能够对自己的本质负责,那他又如何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呢?因为人的行为也是被各种原因提前决定了的。尼采在这里所接受的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决定论”,即与“自由意志”相排斥的“决定论”。“自由意志”这个概念无论在奥古斯丁那里,还是在康德那里,都是为了让人背负责任。然而“决定论”却通过废除“自由意志”而免除了人的责任。人不再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同时,人也不再是康德所说的目的。人只是“绳索”和过渡。如果把人当作目的,那么尼采的“超人”就是不可能的。
“现象论”是康德以来德国哲学界颇为盛行的知识论观点。它区分了现象和物自体,认为人所有的知识都是关于“现象”的知识,对于“物自体”我们则一无所知。尼采认为,我们不仅对“物自体”一无所知,我们对于“现象”的知识也是可疑的。因为,如果把“现象论”坚持到底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像笛卡尔或康德那样,通过自我审察(Selbst-Beobachtung)的方式来寻找知识的客观性。根本就“没有一种自我审察的现象论”。因为自我也是被建构出来的“现象”。“没有什么比我们用著名的“内感官”(inneren Sinn)审察到的内在世界更具现象性,(或者更直白点说)更具欺骗性的了”。彻底的现象论应该是,“一切被意识到的都是现象”,没有什么现象(包括快乐和痛苦)能够被确立为事件的原因或者行为的动机。
毋庸置疑,尼采确实受到了康德——叔本华“现象论”的影响,他也确实以“现象论”为基础开展了对意识领域的分析和批判。但是,能否依此认定尼采那里有一种“意识现象学”(布莱恩·莱特)?或者说,能否依此认定尼采是胡塞尔意义上的“现象学”先驱(萨弗兰斯基)?却值得商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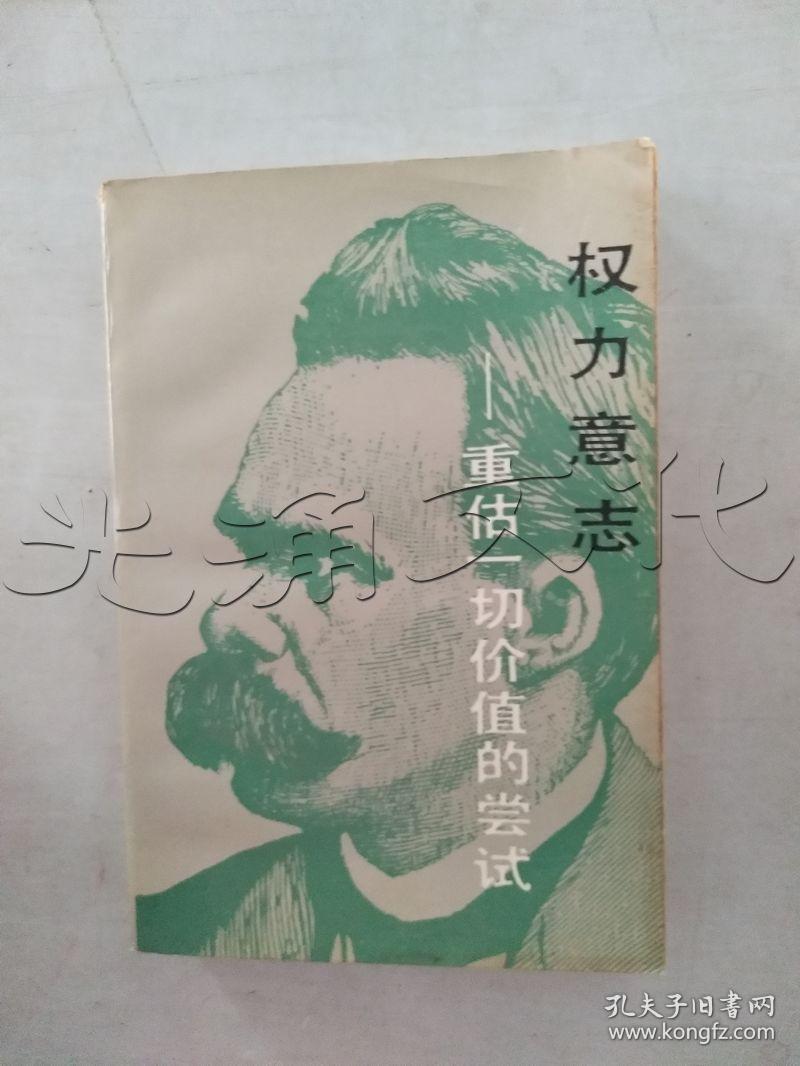
胡塞尔现象学(Phänomenologie)与康德现象论最大的不同在于,胡塞尔把康德对认识和实践问题的研究,改造成为对意识行为和意识内容的研究。他把研究范围聚焦于意识本身,并试图通过分析意识的意向性活动和意向关系,来把哲学建构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就此而言,尼采更接近于康德。尼采的意识理论以康德现象论为基础。他试图通过对意识领域的分析和批判,把所有本体论问题和认识论问题都还原成价值问题,从而指出价值的虚构性、欺骗性以及权力意志在价值确立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在康德那里,“因果关系”属于知识领域,而“自由意志”则属于实践领域。尼采通过彻底的“现象论”否定了因果关系,又通过彻底的“决定论”否定了“自由意志”。于是,人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认知上都变得不再可靠甚至不再可能。人陷入到了前所未有的虚无之中。当然,这里并不是说“现象论”和“决定论”导致虚无,而是说,它们揭示了理性主义的虚无本质。
那么,“我应该如何决定自己的行为呢”?尼采的解决方案是:“回归自然”和“积极的虚无主义”。“积极的虚无主义”与叔本华的消极虚无主义不同,叔本华想通过意志的自我否定来避免生命的痛苦,达到所谓的哲学旁观,而尼采则要通过意志的自我肯定来将生命提升为比“旁观者”更高的“艺术家”。因此,“积极虚无主义”与“自然主义”、“艺术家”等概念同构,是尼采对康德——叔本华“现象论”的一种超越。
如何理解尼采的“自然”或“自然主义”?
尼采虽然受到近代科学成果的影响,但是并不能够依此断定,他的“自然主义”是一种与科学相契合的自然主义。
例如,尼采认为在自然世界中“力”(Kraft)是普遍存在的。但是,他却拒绝把“力”客观化。他认为,力必然是要去克服什么,战胜什么的,“一定量的力即一定量的冲动、意志和作为——确切地说,力无非就是这些冲动、意志和作为本身”。因此,力不是客观的、抽象的,它不是牛顿力学所讲的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力就其本质而言无非是追求胜利的意志(权力意志)。力作为求胜的意志,首先应该表现在肌肉的紧张、身体的强壮、精神的高昂之上。这种与肌肉、身体、精神相关联的力,不应该被物理学上客观抽象的力所取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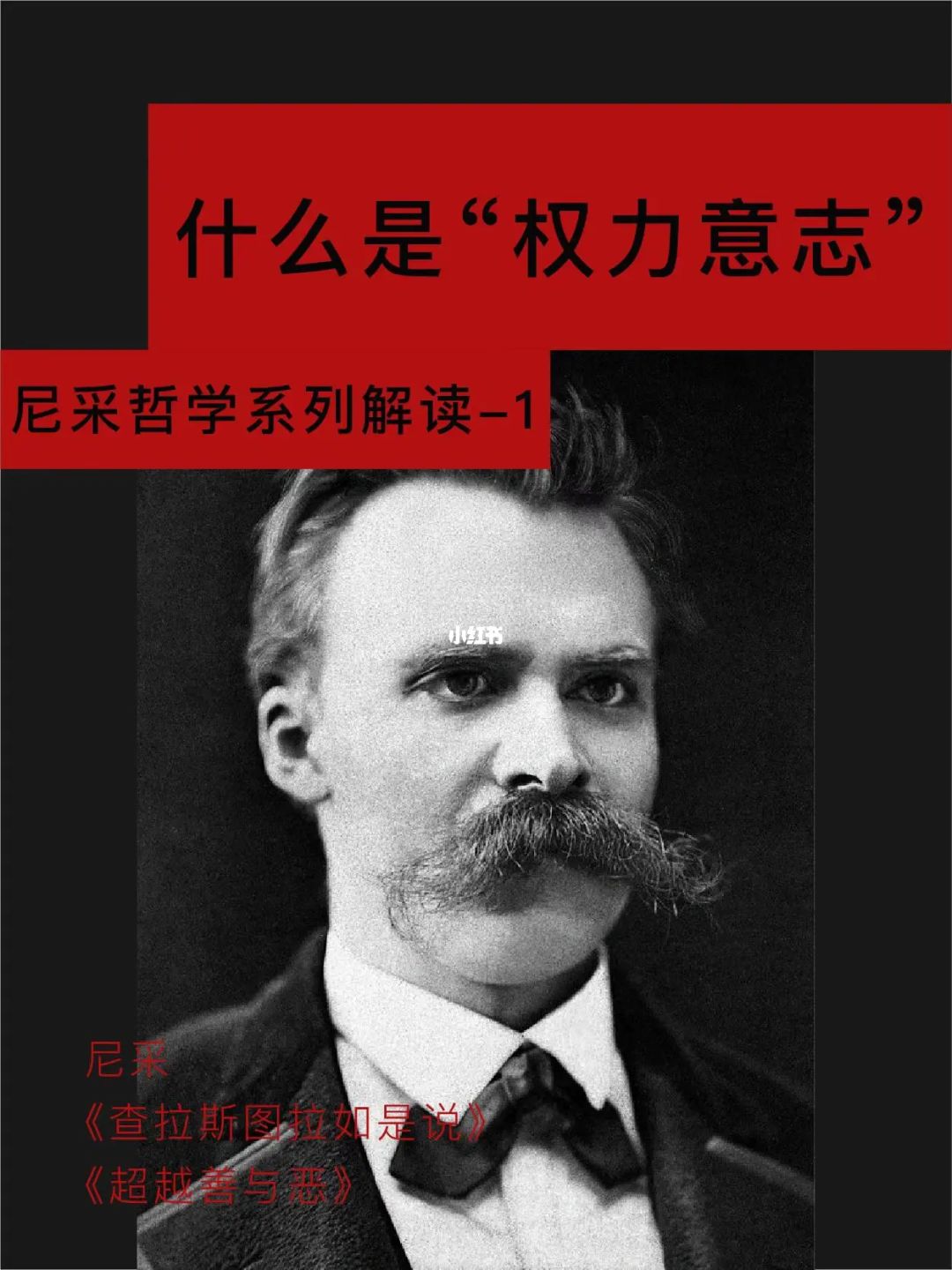
由此可见,尼采的自然观很难能称得上是科学的。他有选择地吸收现代科学成果其实是想让它们服务于自己的哲学目的。
德勒兹认为“力”(意志)是尼采自然思想的核心,并进而围绕着“力”(意志)将尼采的自然思想归纳为如下几点:1,力的存在是多元的、差异性的。不存在单个的抽象的力,力必然与其他力共在。2,在力与力的相互争斗、相互作用中,事物不是物理学上的“没有活力的客体”。相反,“客体本身也是力”,客体是力“第一次和唯一一次的显现(apparition)”。3,各种力在一定距离之内相互作用。距离是把力与力关联起来的“区分性因素”。4,力在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中表现为意志(权力意志)。力与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即意志与意志之间的关系问题,亦即支配意志(主人意志)与被支配意志(服从意志)之间的关系问题。由此,尼采的自然哲学步入了道德批判领域。
德勒兹把“力”(意志)当作尼采自然思想的核心,无疑是正确的。在《善恶的彼岸》第36节,尼采把“一切起作用的力”都视为权力意志。他认为,力或意志并不作用于“物质”,而只作用于另一个力或另一个意志。因此,世界中最基本的关系不是意志与物质之间的关系,而是力与力、意志与意志之间的关系。尼采不赞同把自然看作自然物的集合,更不赞同把自然简单地二分为自然物和自然规律。相反,他更倾向于把自然放到力与力、意志与意志相互争斗、相互作用的关系中去理解。在力与力、意志与意志相互争斗、相互作用的关系中,力(意志)就是权力意志。因此,在1888年的手稿中,尼采把权力意志思考为“自然”和“自然法则”。把权力意志思考为“自然”和“自然法则”,就是把力或意志的相互争斗、相互作用思考为“自然”和“自然法则”。在此,尼采接近了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争斗是自然的常态。
总之,尼采并不试图以一种科学的方式理解自然,而试图以一种哲学的方式理解自然。所以,不能说尼采的自然思想是科学的,而只能说尼采把现代科学囊括到他的自然思想里去理解和把握。“权力意志”和“永恒轮回”是尼采对自然的两个基本描述。权力意志(力与力、意志与意志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争斗)与自然的生成、流变有关,而永恒轮回则与自然的必然性、确定性有关。永恒轮回是自然对其自身(生成和流变)的最高肯定。以此为基础,尼采构建了他肯定生命之流变和命运之必然的自然主义哲学。
本文节选自韩王韦著《自然与德行——尼采伦理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出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