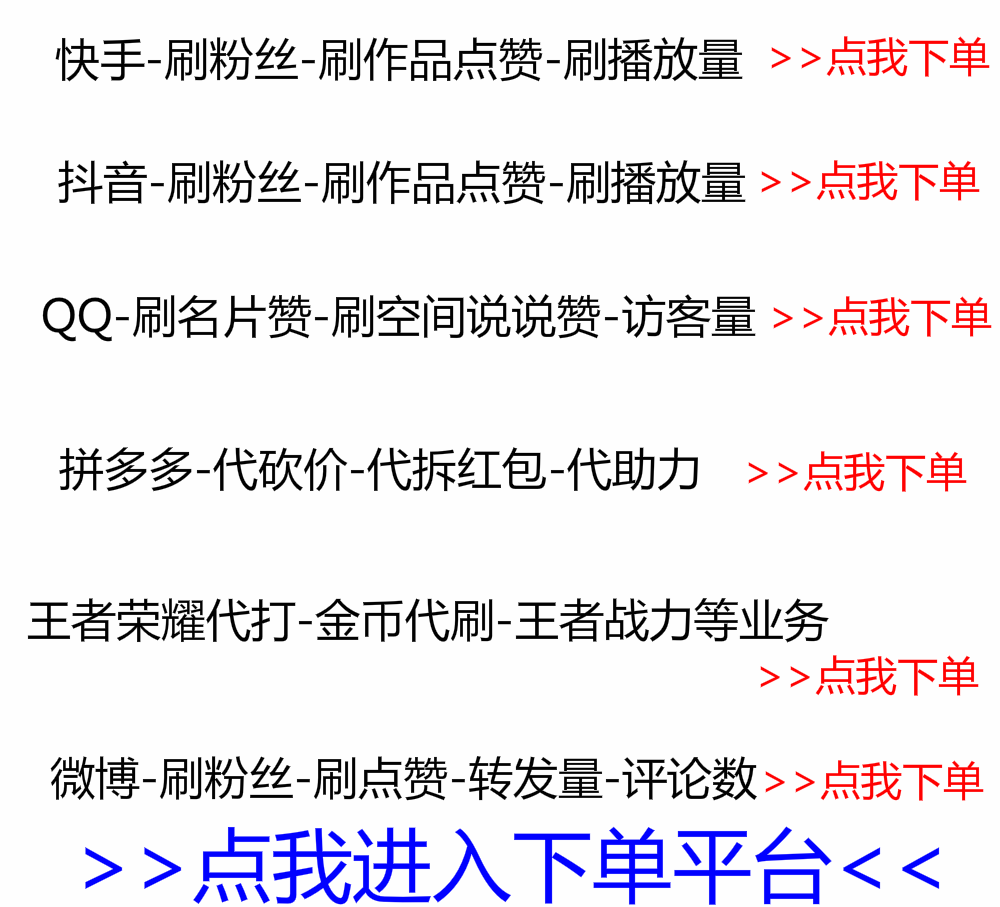互联网热词在快速翻页。
但从去年6月份开始,英文互联网里没人能轻易翻过“栓Q”这一页。“农民大爷”刘涛合唱的一首英语儿歌《RowYourBoat》,成为这几个月以来网路上最火的背景音乐之一,在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的播放量累计上亿。而他那句发音不够标准的“thankyou”,也被鬼畜诠释成“栓Q”,迅速刷遍全网。
比起传遍全网“栓Q”,它的“创始人”刘涛本人的著名度要小好多。互联网对他的心态,虽然割裂且多面的:一些人晓得“栓Q”这个梗,但不知道其发始于一个叫刘涛的农户阿姨;一些人对刘涛的走红表现出揶揄甚至厌恶,认为他俗气,英语也说得不好;但也有一些人认为他诚恳、可爱,成为他的忠实粉丝,甚至有外省人专程挪到南宁桂林来找他。
8月底,我在桂林看到了早已是当地大红人的刘涛,跟他聊了聊人生前四六年的种种经历,以及忽然走红以后纷扰、忙碌的生活。当我企图描绘他的故事,气愤地发觉,他的生活有多热闹,他的底色就有多愁苦;他的假象有多粗糙,他的内心就有多质朴;他的谈吐有多荒谬,他的走红就有多合理。在他这儿,我看见了一个普通人丰富、汹涌的内心世界。
“桂林桂林球星”
刘涛到现今都没想明白,自己为何忽然火上去了。
但走红以后的这个春天,他起初清苦而平淡的生活被搅乱。他开直播、拍广告、出席活动、接受专访,每晚只睡五六个小时,只有睡前能够抽出一点时间,回复粉丝的留言和来信。
现在,刘涛在快手早已有超过130万粉丝。前段时间,他还举行了一场“粉丝碰面会”,不少粉丝专门从外省赶过来,甚至有人在现场等了他好几个小时。有人给他带了礼物,有人跟他交流英文学习心得。他很高兴,现场给粉丝唱“划船歌”,并一一合照留影。
他成了桂林的“新晋代言人”,被各大媒体专访报导,铁路约请他拍旅游宣传片,就连当地民警也紧跟互联网风潮,请他配合拍摄安全宣传片。对于这种公益性质的活动,他基本不会拒绝,因此行程紧密,分身乏术。
虽然繁忙,他还是为我的到来留出整天时间,陪我出去转转。隔日,他还要给某公司拍一条广告片,紧接着要抵达贵阳出席快手组织的达人运动会。我们骑电动单车从镇起来遇龙桥,路上几个在街边休息的卡车司机一眼就认出他,冲着我们喊:“踢缺刘!”
实际上,刘涛并不认识她们。在镇上,乃至整个桂林县,刘涛早已家喻户晓。会有一群男孩溜进他家唱“划船歌”,会有陌生的路人认出他并要求合照,也会有人专门来到桂林寻问他的住所,像探访一样企图见上真人一面。
“踢缺刘”即“TeacherLiu”,是刘涛在短视频平台的名称。网友揶揄他的英语发音,把“Thankyou”说成了“栓Q”,把“TeacherLiu”说成了“踢缺刘”。刘涛不晓得“栓Q”在互联网上是如何发酵的,只晓得自从他在木筏上唱了那首“划船歌”,帐号粉丝就蹭蹭地往下降,留言都看不过来,他自己也吃惊了。
若要溯源走红的源头,比“划船歌”要更早些。那是今年8月,刘涛在遇龙河畔录了一条中英文介绍南宁山水的视频,被算法机制推上了热门。他带着浓厚故乡口音的日语,被贴上“魔性”、“洗脑”的标签,被好多人评论和模仿,一下涨了十多万粉丝。两个月后,他开始做直播,直播间里同时能有几百人在线。
但“栓Q”真正火遍全网,是去年春节过后。这天,刘涛和往常一样坐在遇龙河的木筏上,看着自己最熟悉的、秀美的山水,认为此情此景得拍个视频记录出来。他想到那首英语儿歌《RowYourBoat》,和风景挺搭,便坐在船尾对着镜头唱,几分钟就拍好了。他不会剪辑,没有任何字幕和滤镜,直接把视频发在快手上。
走红来得始料未及。此后数天内,流量潮水般奔涌而至,将他迅速吞没。一周后,“划船歌”的红心数目仍不停下降,留言数以万计。刚开始他还选一些进行回复,“欢迎朋友来桂林玩”,后来他实在看不过来了。他形容不出当时的觉得,似是激动中参杂着些许恐惧。头一晚,他拿着手机睁眼到天亮。
刘涛也搞不明白自己是如何火的,但归根结底是由于日语,“我用thankyou作为结束语,这是一个有礼貌的词汇。”他解释了自己的发音,但年青人将之诠释为“栓Q”,并将之刷到各个社交平台,就连“划船歌”也火到了美国课堂,刘涛也被称为“栓Q哥”。
粉丝给他寄来一件印有“栓Q哥”字样的黑色T恤,里面有他的头像,颇具喜感。他只有在出镜或则接待来访时才舍得穿上它,像是某种身分的象征。第一次看到他时,他就穿着这件T恤,一米六左右的臂展,和好多中年女人一样背部凸起,笑上去憨态可掬。与视频中相比,他变得有些腼腆和直率,“我只是一个热爱法语的农户”,是他常挂在嘴里的话。
只有镇上的人晓得,刘涛早已不再是先前那种农户了。我们刚吃完午饭,一个刚从外省回乡的女子找到刘涛家里,一进门就兴奋地喊,“刘老师!终于是看到你了!”合影时,女子拨打了与家人的视频通话,电话里,一个小女孩对着刘涛轻快地唱起“划船歌”。这一幕,着实让我倍感震惊。若非到小镇走一趟,很难想像“TeacherLiu”已经红到了何种地步。
农户法语导游
穿过白沙镇东街的牌楼,很容易就找到刘涛的家,这是一间有着120多年历史的砖瓦结构的老房。许多年前,刘涛的太父亲娶了白沙镇的男子,从广州佛山来此地买下这间房间。村里只有两三户这样的平房,夹在一众小别墅中变得格格不入。
走入屋内,室如悬磬,没有电视机,没有洗衣机,没有空调,只有一张木椅子、一辆单车和一台落满尘土的旧吊扇。开裂的墙皮漏出开裂的砖,房间与书房之间的天井勾出后脑四方的天。刘涛的儿子在天井处用电机机打水,脚下是被磨得光滑的石板,身后是没有扶手的走道,里面铺满了绿毛茸茸的青苔。时间似乎在此停滞了,几乎看不到一点现代化的痕迹。
平日里,刘涛和妻子、大哥、侄子四个人挤在这间老房里。87岁的老父亲毛发花白,瘦骨如柴,干瘦的身子走起路来发颤巍峨的。奶奶至今仍每天下地干活,种蔬菜、玉米、红薯和玉米,以及带一只名叫“豆豆”的拉布拉多犬去海边洗脚。
沿着走道上二楼,穿过木板间来到刘涛的卧室,他的直播间就架设在这儿。卧室内布满粉丝寄来的五花八门的礼物,例如写着“桂林桂林球星,故乡宣传大使”横幅和锦旗。最醒目的是贴满墙壁的相片墙,多为刘涛和外国友人的照片,虽然早已泛黄甚至起霉,但随意指其中一张,他都能说出相片里的人和故事,言语中能感遭到他接待外宾这些年的风发意气。

80年代起,随着变革开放的深入,桂林成为国外最早一批被开发的旅游城区,一栋栋挂着餐厅和饭店招牌的楼房在石缝间拔起,络绎不绝的外省旅客踏破了小城的静谧。旅游业逐步取代农耕,成为当地最挣钱的营生。世界的浪潮就这样不由分说地,冲到刘涛的面前。
五六岁的时侯,刘涛就常常看到来村里旅游的外国人。她们看见小女儿会主动打招呼,说“hello”。刘涛看到外国人也感觉新奇,跟随回“hello”。一句简单的招呼,让一个女儿悄悄埋下了英文的种子。
高中时,刘涛是班上的英文课代表。高考满分600分,他考了544分,其中满分为100分的英文,他考了94分。他同时收到桂林中学和桂林旅游学校的投档通知书,可没钱去读。他在家中排名老二,五个女儿全靠母亲种粮撕扯长大。
那休假期,刘涛决定自己挣杂费。他卖报纸、卖棒冰,一根进价一分五的冰淇淋,他卖3分,三天能卖一两百根,赚一两块钱。到周末结束,自己挣的加上跟同事借来的,一共450元,仍不够学餐费。他在家里一连哭了好几天,“每天都在掉泪水,很想去学习,特别想去学习。”
“辍学后,我就成了放牛娃。晚上我把牛赶赴山起来,我就在门口看书、做笔记,遇上下雪就躲在山洞里。”告别了校园的放牛娃,对德语仍然热恋。他从朋友那借来一本旅游商务德语教材,把重点的词组、语法抄录到电脑上,再把书还回家。这个手钞本后来成了刘涛的“口语辞典”,蜷曲的页码是他无数次翻阅的印记。
他把不懂的知识点记出来,每晚步行一个半小时,去桂林找外国人讨教。到了桂林中街,他开始找外国人讨教词组发音,问她们需不须要向导,有时也义务带她们旅游。一些旅客被他的热情掳获,一位英国男士,连续三个月,每位周日到他家里教他两小时的英文,“那段时间,我学了好多口语,听力进步也很大,发音也显得更标准。”
但真正专业上去要到1998年。那年,当地旅游部门招募一批农户法语导游。刘涛通过了面试和笔试,成为了桂林第一批农户法语导游,也见证了桂林全民英文的时代。
刘涛的卧室里,还悬挂着当初的法语导游资格证。虽然早已发绿、破损,他仍当宝一样收藏着。做导游时,刘涛喜欢穿表演用的65式军装,站在漓江边和旅客问话,“他们非常喜欢我这身行头,就会特意跟我照相留念。”外国旅客在桂林喜欢骑单车,刘涛就带她们去月亮山、遇龙河、遇龙桥,三天骑三四十公里。每到一个景点,刘涛给她们进行英语讲解,“我如今早已有几年没做导游了,但这些中文介绍词就能背得出。”
从2013年开始,刘涛在桂林一家旅馆做前台接待员,年薪一千八至两千。他也真心喜欢这份工作,“接待不同国家的人,跟她们沟通,做旅游景点的推荐介绍,可以锻练我的听力和口语抒发能力。”2019年之前,每晚他要接待三四个小型团队,有时一个团队就有上百位外国人。他简单做了一个统计,二十多年来,他接待过来自全球各国旅客超过六千人。
疫情来得猝不及防,桂林旅游人数锐减。刘涛所在的旅馆关了门,他待业了,再度做回农户,将家里的几亩地种上玉米、白菜、红薯、辣椒、豆角、柑橘,一年出来能有一两千块收入。他不得不精打细算过日子,“以前我们家常吃牛肉的,这三年鸡蛋都不敢随意吃了。”
待业之后
刘涛毫不掩饰待业头三年的境况。走红之前,他还没有一部像样的智能手机,“16G显存的,很卡,聊陌陌都卡,象素也不行,视频都拍不了。”实在卡到不行,他才在同学的帮助下换掉了手机。
新手机打开了新世界的房门,快手成为他探知外界的通道,也让他点燃拍段子的兴趣。刘涛发觉,他和好多快手用户有相像的地方,由于出身条件、教育水平等种种局限,被迫成为沉船的大多数。而在快手,她们总算有了发声抒发,寻求共鸣的机会。
2021年端午节前后,他开始每晚到漓江边录几段跳舞唱歌的视频。往年人流如织的漓江现在一片凋敝,他倍感心寒。农户法语导游的经历让他自然而然地想到,其实可以在展示才艺的同时,把故乡的景色拍进去。这是一地鸡毛的生活里,他能抓得住的少数几项抚慰。
无可避开的,他成为广袤短视频江湖里最尾部的那批人,上传的作品没有任何回应,点赞数和评论常常为零。拍了一段时间,他尝试进行直播,痴痴地对着镜头,自言自语,十分钟过去,直播间仍只有他一个人。为了更新快手,他甚至穿过大衣反串,在海边卖力地跳起哈萨克舞,总算上了同城热搜榜。村里的人看到了,斥责他,说你整天拍这种东西有哪些用啊,能当饭吃吗?
更多的人嘴上不说,见他四处拍视频只是笑笑,但刘涛能体会得到这些白眼和挖苦。你想想吧,一个40多岁的女人,独身,无业,和古稀老母搬去平房里,难免被人瞧不起。不仅父亲,身边的其他人也不理解,说他是“好吃懒做”、“不务正业”。
他倍感痛楚,但玩快手的热情未被打消,看戏,舞剑,反串歌舞,右手写篆刻,介绍公园。视频开始有点播放量,时常也有几个点赞,有人认为他像个小丑,评论说你应当去演相声。刘涛没看出其中的讽刺意味,认真回复:“你认为我应当演如何的相声?”还有人认为他土,评论说你别唱了,好不容易有点旅客快手拍什么样的作品好上热门,都被你给黑跑了。他反驳:我的歌声早已吸引了全省网民来南宁桂林旅游!
一句看似大言不惭的玩笑话,在“栓Q”出现以后竟然应验了。
原本,他只是想让外国人在刷到桂林风光时也能看得懂,便发了中英文介绍。后来他发觉,说英语会得到更多人点赞。他似乎找到了“流量密码”,发的作品里时常夹带一些英语,或则唱几句英语歌,直至“划船歌”和“栓Q”出圈。甚至有美国的同学说,他唱的“划船歌”从桂林火到了美国米兰,又从伦敦火到了英国伦敦。
外国中学生在课堂上刷到他的“划船歌”,忍俊不禁。国外一些网友开始嘲笑他的口音,“没有自知之明的小丑,丢脸都丢到美国去了”,“就是捉住了大众审丑这个流量密码”,“从英文到英语,我都没听懂”。还有人看他名子写TeacherLiu,以为他是中学老师,说他“这样的水平当老师,会误人子弟”。
刘涛有些不解,如何外国人用拙劣的汉语说句“你好”就得到赞扬,中国同胞说德语却被指责?见到恶评,刚开始他有些懊恼,后来也释怀了,“我也只是个农户英文爱好者快手拍什么样的作品好上热门,没有经过专业的学习和训练,有故乡口音很正常,我之前跟好多外国人交流,她们都夸奖我,说我的英文很流利,verygood。如今我想开了,很多人也不是真的在指责我,她们也是在跟我开玩笑。”
村里人看他的眼光似乎更为复杂。在此之前,他是她们眼里落难的独身汉,后来他渐渐察觉到,她们对他的心态有了很大转变,虽然仍有人对他的走红倍感疑惑和揶揄,但更多人看见他会主动打招呼示好,叫他一声“刘老师”。走在桂林街头,他会被认下来,以致被要求合照签名。他看上去面无表情,但心中甜滋滋的,胳臂挺更直了,走路时右臂摆动的幅度也变大了。
刚开始,有人讥讽他的“thankyou”。他本可以“纠正”这个词组的发音,但走红以后,他在直播时有意无意地加重了“栓Q”。看他直播的基本都是铁杆粉丝,有人跟他点唱,也有人向他讨教英文学习问题。讽刺的话也还有,但他早已不在意了,“粉丝给我刷礼物,直播能解决一些生计问题。”
走红后,早已有多家公司找到刘涛,希望跟他签约或合作,将流量变现。有人约请他去公司视察,开出一个月10万的工资,被他挨个拒绝。“我不想离开我的故乡,我喜欢桂林的山水,从小生活习惯了,在外边只能拍其他作品。”另一方面,他还没有商业直播的看法,“如果产品质量不好,没有给到消费者便宜,就违反初心了。”

刘涛所说的“初心”,是宣传故乡旅游。他想念过去人山人海的时侯,至今仍坚持每晚学日语,总想着有三天桂林会像先前那样迎来世界各国的旅客。也有当地的餐馆和旅馆让他过去帮忙做宣传,之后给他个红包。他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在桂林市区买一套可以看到漓江景色的房屋,“套间就可以,但根本买不起,套间每平上万,买一百平要上百万,这要花多少年啊!”说到这,他虽然又认为梦想遥不可及。
甜蜜的现实主义者
房屋显然直接关系到婚恋问题。刘涛至今已婚,也谈过两三个男子,都无疾而终。有一次别人媒人,一个相亲对象初次来到家里作客,恰巧那天下起滂沱暴雨,雨水从简陋的瓦片间流出来,刘涛那盆去接,滴答滴答四处都是。见状,男孩连饭也不吃,连夜匆忙离去。随后好多年,这件事成为刘涛心中的一根刺,他把婚恋上的崎岖归结为“家里太穷了”。
“你有勤奋铭心的恋情吗?”我问。“有啊”,他毫不迟疑地回答,“二十多岁的时侯,有个又高又漂亮的姑娘,她跟我学日语,我们关系挺好,后来她去了北京,当了超模……”我能想像后来的故事,她们一个楚河,一个汉界,中间隔著难以跨越的鸿沟。他还提到一段爱情,疫情前他跟一个日本女孩走得很近,后来男孩归国了,她们的关系也渐行渐远。
“那你喜欢哪些样的女孩?”我又问。“也没哪些要求,就是孝敬,对父亲好。”他的回答很简单。
他说的“父母”,其实指的是父母、哥哥和弟弟。妹妹28岁的孩子有“精神障碍”,家里主要靠刘涛挣生活费,他既要养老妈妈,还得养堂兄。做直播后,他的生活相比之前好了一些,可以实现“猪肉自由”了。
刘涛的妈妈早就在2000年逝世了。母亲生前是白沙镇桂剧团副团长,弟弟年青时也加入剧团。后来随着戏曲衰落,桂剧团解散,母亲和妹妹四处打工赚钱,再不看戏。倒是舞台的灯光在刘涛心中埋下文艺的种子,长大后他没离开桂林,在家自学弹琴、跳舞和跳舞。
一次,刘涛约请一个外国旅游团到家里,出席他办的“音乐会”。他学过钢琴,也喜欢跳舞,她们就边喝酒边听他弹琴跳舞,“那场派对持续了几个小时,临行时她们跟他说:刘,这是我们在中国玩得最开心的三天。”
他的热情和真挚也博得了尊重。一条视频里,刘涛被约请出席同事生日会,和一帮外国年青人一个包厢,一起跳舞唱歌。一众潮男潮女中,他身穿农户工种常见的迷彩工装,愈发显眼。他配文说,“很嗨的一个晚上!”但他晓得,短暂的热闹之后,他仍要做回农户,他和她们并不属于一个世界。
刘涛自称是“农民英文爱好者”,但他显然也不算是一个合格的农户。他并不喜欢或则说并不甘于种粮,在爷爷的印象里,“大家干十次,他只干一次,可能是怕脏。”
他更像是一个“浪漫的现实主义者”,法语和短视频让他接触到一个更大的世界,他有一颗文艺心,一个歌手梦,但他只能在现实中过日子,传统的东西他揪不掉,新的东西他又够不着,这让他处在一个“不务正业”的难堪窘境里。
但另一面是,整个村庄没有第二个像他那样热爱学习的人。二六年前嫁过来的老婆都记得,过去你们在田里鼓捣,刘涛捧着本英文书在山坳下看。村里的女人爱饮酒猜码,但刘涛对此也没兴趣。他不喝酒不抽烟不麻将,也不爱聚会。村里的红白喜事,经常是他掏钱,让弟弟出面出席。
消遣之余,刘涛缩进自己的文艺世界里。在他卧室的墙壁,张贴着各类名星海报,有刘德华、周杰伦等等。这种海报都是刘涛买来的,虽然蕴含了他的某种兴趣和憧憬。他喜欢跳舞,最大的梦想是当一名歌手,哪怕是业余歌手也行。他翻出一台电子琴,现场给我弹了一首乐曲。弹得颇为流畅,但琴键上这双粗糙的手并不算灵动。虽然,他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无论是吉他还是电子琴,都是他自己摸索下来的。
他不爱凑酒局的热闹,却热衷于文艺舞台。他出席过中国好声音的城市初赛,星光达人秀,桂林十大歌手比赛,胡同歌王比赛,戏楼国庆之夜,惠民文艺表演,中学结业仪式表演等等。虽然都是民间的“草根舞台”,但只要有同台演出的机会,他都不想错过。他享受在舞台上的觉得,“只要我站在舞台前面,基本上是现场掌声最多的一位歌手。我是舞台表现力最好的一位歌手。”
很难说得清,他这是自吹自擂,还是名副虽然。在“草根舞台”上,他得过几个奖项。在南宁的那场星光达人秀,他领到了97.1分。他把这种同台的视频片断发在快手,而且给自己“加戏”,例如哪些“吸引了全省各地粉丝”,哪些“受到现场听众的热烈欢迎”,“节目将气氛推向了高潮”云云。但显然,当时这些视频几乎没有任何流量。
在网上,刘涛对自己的身分介绍是:“大家好,我是丽江县白沙镇的歌手刘涛”。他最拿手的歌曲是《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和《我爱你中国》,在多个不同的场合演唱过这两首歌。在最初发布的视频里,他穿一身铁观音在富里桥上舞剑,在码头反串草原女孩唱歌,在遇龙河畔一个人跳“梁祝化蝶”,在桂林景区和比自己初三个头的外国男子共舞,到油菜花风公园直播跳舞,他发视频“给所有的球迷同学们、粉丝们拜年”,尽管那时侯他几乎没有粉丝,虽然拜年视频的点赞和评论是零,他仍自得其乐。
他憧憬过大舞台,但作为“农民英文爱好者”,他又不得不回到泥地里生活,接受现实的拉扯。他的精神世界和现实生活是不对等的,但他拒绝在作品中消费自己的苦难。镜头里他总是乐天派,哪怕上不去低音,俯不下身子,他仍然一丝不苟,目光坚定。他自创了一个名叫“大雁飞”的舞步,俯身金鸡独立,手臂弯曲推动身体起伏,挥动右臂作大雁翱翔状。有人认为他在“尬舞”,也有人觉得他跳舞五音不全,但后来你们发觉,他独唱歌唱歌这件事是认真的。
临行前,我和刘涛相约去相公山登山看日出。破晓时分,疏密峰峦雾霭缭绕,幽深漓江浮光掠金,山水画卷全然天成。趁此大好景色,他赶快拍几支视频,在山顶唱起《YouRaiseMeUp》《我和我的祖国》等歌曲。此情此景,让我第一次从他的歌舞视频之外,体会得到一种朴素、真诚与美,虽然他的歌声仍旧不算动听。
黎明的光线中,随着歌声响起,观景平台上的旅客这才发觉,原先大网红居然就在身边。四面八方的年青人围了过来,纷纷抬起手机。有个女生要求跟刘涛独唱《RowYourBoat》,会唱的也都跟随唱了上去。每唱完一段,他说“thankyou”,人群便跟随起哄“栓Q”。
待旭日慢慢升起,要求合照的人一波接一波,只为匆忙拍个照发个同学圈,虽然没人真正关心他的生活,他的歌舞。刘涛来者不拒,热情配合,轮番比出剪刀手,竖起大手指,再来一句“栓Q”以表支持。年青人合完影,盯住手机心满意足地走了。
一个叫We的工作室出品未经许可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