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晚,第四届译想论坛(2021)译论一“思想之镜——管窥近年来的人文译著”在武汉卓尔书店举办。“理想国译丛”主编梅心怡,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图书出版人、专栏作家范庭略,对近年人文社科领域的译著出版状况发表了看法。以下为经澎湃新闻修订的现场实录。
梅心怡、任剑涛、范庭略在活动现场
没有一个国家是一个孤岛
范庭略:今天我们谈翻译对中国思想的影响,实际上就是在谈一句老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思想的传播,从时间维度说,是通过不同语言呈现人类历史的进化;从空间维度说,是全球思想在不同地区的本地化。我们第四届译想论坛的第一场“思想之镜”,邀请“理想国译丛”主编梅心怡老师和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老师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思考。
梅心怡:我目前负责“理想国译丛”,虽然这个译丛正式启动于2015年,但早在2010年“理想国”成立的时候,我们就邀请了梁文道、许知远、刘瑜、熊培云四位老师一起讨论,在2010年的那个当下,中国的读者需要什么。其实“理想国译丛”的想法非常简单,就是希望中国读者可以看到他人的经验,借由他人的故事、思想,真正地理解对方,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共存于这个世界。无疑,中国与世界,自我与他人是密不可分的,世界在变化,中国也在变化,尽管我们与他人的命运、中国与世界的命运在一些时刻未必完全一致,但或许在某个时间点,二者会重叠交错。
有朋友会问,为什么我们会出版那么多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译著?当然目前我们并没有处在世界大战中,我想在座的各位也都没有经历过战争,但阅读那些二战中个体的命运,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在那些时刻做出的决定,我们会发现,他们与我们有着类似的心情、类似的顾虑。我们希望大家通过阅读他人经验,意识到自己并不孤单。去年疫情以来,有不少讨论说,我们每个人都在孤岛中,而“理想国译丛”的初衷,就是传达这样的信息:没有一个人是一个孤岛,没有一个国家是一个孤岛,没有一个时代是一个孤岛。你总是可以看到别人,可以从别人的身影中看到自己。我们不希望仅仅传递知识,今天通过学术书籍,通过网络,可以非常方便地获得各种知识和信息,我们更希望的是读者在阅读的“理想国译丛”过程中,获得感触和共鸣,获得由他人经验传达出的人性。
这两年,理想国的确出了不少历史类的书。不可讳言,这当然与国内近年的世界史热相关。过去,我们对世界其他角落的理解,往往会通过阅读通史、断代史类的书籍;如今这样的书已经不能满足国内读者了。大家想要更深切地了解美国的种族问题、阶级问题,东南亚为什么有民族冲突,巴以的纷争背后到底是宗教问题还是民族问题,还是单纯的战略问题。我们感受到了读者的这些渴望,它与我们译丛的初衷十分切合。
范庭略:我觉得有个有趣的现象,你们关于二战历史的出版,以德国、日本、苏联题材居多,我之前也看到国外媒体报道说,涉及希特勒的书总会畅销,纳粹头子几成显学。为什么第三帝国会是一个长盛不衰的题材?是不是有某种出版的逻辑在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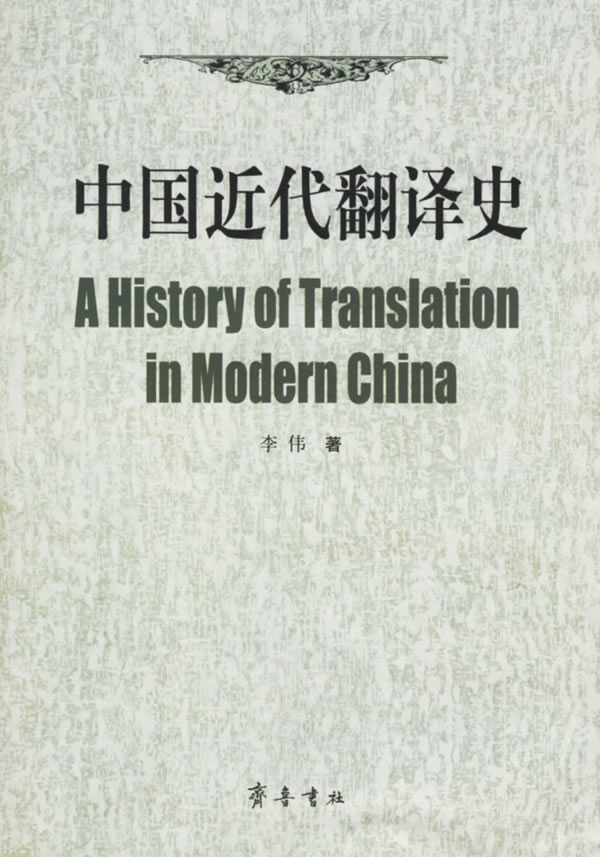
梅心怡:其实我们“第三帝国三部曲”(理查德·埃文斯的《第三帝国的到来》《当权的第三帝国》《战时的第三帝国》)版权买了挺久,因为都是大部头的著作,所以也翻译了非常长的时间。当初并非有意识地要集中出版这个题材。
范庭略:我看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这几年也在不断再版。或许大家都非常好奇那个时候的生活方式、人们的思想变化,德国怎么就从一个战败的郁闷状态,一下变成众志成城、一定要干翻英法的状态。而碎片化的信息已经不能满足我们,于是便想系统地阅读这些书。
梅心怡:关于二战,我们最早出版的是伊恩·布鲁玛的《零年》《罪孽的报应》,布鲁玛虽然是荷兰人,但对日本历史和文化有非常深入的理解,另外我们还出了小熊英二的《活着回来的男人》。大体上,我们是先从日本开始切入的。无疑,二战和日本现代史,尤其对中国影响巨大。我们期待读者能全景式地理解历史,这并不是说从头到尾描写过去发生的一切,而是呈现正反两方的视角和叙事,包括日本那边是怎么看待、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日关系的。
范庭略:我去年在长春参观了伪满洲国的皇宫,事后找了一些相关的书来看。原来当时日本侵略者对这个伪满洲国首都的城市规划,和东京大地震后的时代氛围有关。那时日本建筑界整体有一种求新的心态,想找到一种新的规划城市的方式,他们便在域外的土地上做尝试。举这个例子我只想说明,我们或许会在旅行中遇到不解,产生好奇心,而对一个陌生地方的历史的阅读,往往能够填补我们知识和视野的空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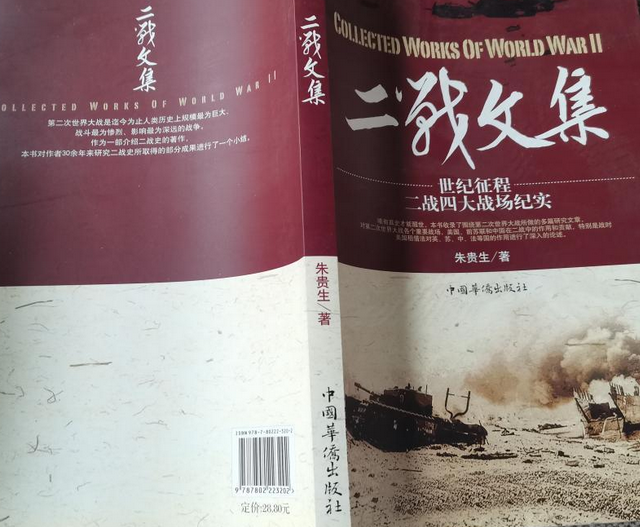
梅心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在西方依然是出版的热门。每年都会有新发现的集中营幸存者日记、回忆录问世,这些书不仅能让人们理解自己的祖辈,更重要的是,它们有助于我们看清二十一世纪的当下的世界局势——今天的世界是二十世纪结的果。去年波兰出版了一本书,非常轰动。波兰有一位女性,一直被视为二战的地下英雄,她帮助大量犹太人逃离苦海,但这本书揭露出,她其实和纳粹进行了很多合作,通过情报交换旅行护照。这在波兰引起轩然大波,颠覆了一代人的想象,甚至危及价值观:到底怎么样才能正确地认识身边的人?
范庭略:我们说历史有时候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你说的这个故事,犹如小姑娘的前身被发现。下面我们请任剑涛老师谈谈他的想法,尤其是他怎么看福山在国内的译介。
英语在学术出版市场的主导权
任剑涛:我们这个论坛叫“译想论坛”,所谓“译想”,我的理解就是通过译著让作者、译者、读者的思想碰撞在一起,而它的意义已经不止于打开知识的大门。翻译所带给我们的思想和思想所需要的翻译,自晚清以来在中国都关系重大。翻译类著作近十年左右在中国读书界无疑是巨大的存在,其中最重要的热点之一是国际政治。美籍日裔政治哲学家、政治史家弗朗西斯·福山被翻译成中文的两大本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可以说,通过中国的热心译者,通过中国最有眼光的出版社,全球最前沿的思想被传递到了我们愿意睁眼看世界的中国读者面前。如果说以往我们睁眼看世界,主要是因为落后挨打,不得不然,今天,当中国人解决了物质上的绝对贫困,甚至我们的GDP跃升到了世界第二,我们能不能在世界思想文化的这个管弦乐队中,占据一个首席小提琴手——或者至少要在前排——的位置,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外的人文社科著作依然是打开我们知识大门,帮助我们审视地球村状况的重要手段。而福山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他不仅关心政治问题,也关心医药问题,关心科技对人类未来的影响,凡此种种,这些都会对我们有重要启发。
今天我们或许过于沉迷物质,被琐碎的生活羁绊,于是,文史著作的透彻洞察和活泼文字便犹如解毒剂,提醒我们人在历史之中可以这么活,人生意义可以这么寄托。而对于现代生活中的意义问题,中国古典资源很可能帮不上太大的忙,通过翻译进入国人视野的西学反倒大有用武之地。甚至在我看来,如果你一辈子没有读过一本重要的译著的话,你对人生意义的理解是非常成为问题的。
范庭略:其实阅读译著也可能让我们收获特别好的体验。比如我个人特别喜欢看丘吉尔回忆录,就好像我和他两个胖子面对面,侃侃而谈,他跟我说很多话,我相信他不会跟我掏心掏肺,但毕竟他把他所有想法的来源都讲出来了,所以即便他在为自己洗涤、辩解,也没有关系,慢慢地他就会把心里话说出来,这个时候,这本书就值回票价了。相比之下,我们刷抖音是免费的,却没多少营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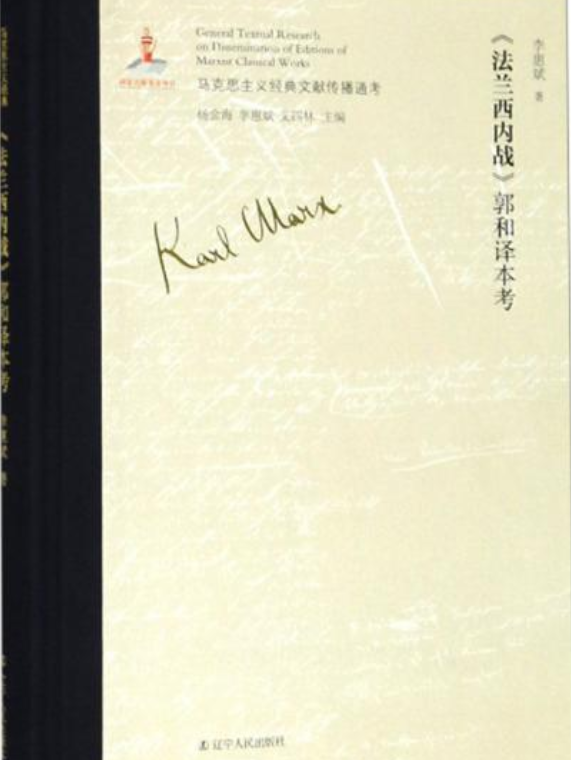
梅心怡:理想国最早出的三部曲,我称之为“”——曼德拉的《漫漫自由路》、萨克斯的《断臂上的花朵》、图图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这三本书涉及的时间有很多重叠的地方,都在讨论南非的种族隔离及其后果,它们的特殊之处是,都是当事人的回忆录,作者不是职业的写作家,却文采斐然,情感丰沛。不同于研究种族隔离的社会学、政治学著作,这些回忆录里没有任何学术理论,作者只是从切身经验出发,娓娓道来他经历了什么,碰到了什么人,如何面对仇恨,他觉得他的一生可以给他人提供什么样的参考。这个阅读体验就和范老师所讲的类似,我觉得这种感觉只有通过阅读才能获得——超越时空,听到第一手的声音,而非经过旁人的转述,你与远方的作者直接的对话,你自己下判断,他的人生对你有什么样的借鉴。
范庭略:好像今天小语种、非通用语种,或者干脆说非英语的作品,引进的还是不多,或者说引进后,反响也比较有限。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这是不是一个文化影响力的问题?
任剑涛:我想,小语种的可靠译者的不足是一个比较大的限制。因为中国近代以来被动挨打,我们难免会为了挣脱落后的厄运,首先诉诸先进国家,所以一段时期俄文被大量翻译,一段时期英文被大量翻译,从而限制了我们对那些充满智慧的小语种国家的伟大作品的汲取。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最近几年,我们被迫跟美国打贸易战,当然有其负面性,但也附带产生了一个相对正面的效应:美国或英语世界的作品的引进受到了一定限制,一些非英语语种的作品反而可以冒出来了。比如意大利,有古罗马的渊源,一直以来都是西方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基地,我们最近制定的《民法典》的源头就和罗马民商法,但我们对意大利语的学术资源的了解太有限了。
范庭略:除了社会科学,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作家就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多有借鉴,这种影响持续至今。
梅心怡:我这几年去国外书展,发觉英语世界,尤其是美国学界还是人文社科著作的主导力量。比如前几年大红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其实早在法国出版了,但一定要在它的英译本在美国出版,被美国学界肯定后,它才走红全球。不得不承认,过去几十年里,美国在知识生产上始终有非常大的话语权,大家都默认,某本书得到了美国市场的认可,它的品质应该就是有保障的。至于靠我们自己去挖掘小语种的作品,其实相当不容易,这要求编辑有能力、有管道来发掘小语种的好书。所以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引进方面,除了英语,法语、德语、日语相对多一些,西班牙语主要偏文学,连西班牙语的人文社科作品也比较罕见,更不用说意大利语这些了。这里可以预告一下,我们最近正要出版意大利微观史学家卡洛·金斯伯格的名著《奶酪与蛆虫》,我早年在台湾地区从事出版工作的时候就非常想把这本书引入中文世界,可是一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有相关专业背景的译者。现在国外版权市场上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是,法语或德语出版物想要扩展全球市场,出版方通常会事先准备英语译本,寄给你参考。
阅读译著的三个台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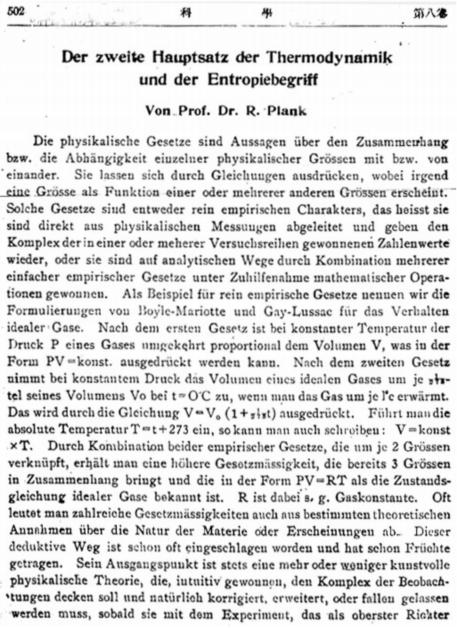
范庭略:想问一下两位老师,有没有哪本书你们认为特别有出版价值,但目前还没有引进?
任剑涛:这简直不胜枚举。比如当今欧洲第一思想家哈贝马斯新近出版的、用德文写的哲学史,有一两千页,很可能是他最后一本书,就非常有价值。在我们政治学领域,剑桥学派的思想家斯金纳、波考克,都有多卷本的大部著作,也特别值得翻译引进。但我估计,译者都不好找,未必有人愿意接手。
其实,除了译的方面,就通过译著来提高我们的思想品质而言,读也很关键。在我看来,读译著要迈过三个台阶。首先你要能够读翻译体的语言,翻译语言跟我们母语的日常表达是有距离的,严复所谓翻译要信、达、雅,但现实中很少有译者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我记得北京万盛书店的老板曾经说,百分之六十的中译本都不值一读,因为译得不好。我的观点是,没有必要这么焦虑。第一步还是要鼓励大家去读,读译著就意味着改变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从而能进入第二步:有判断地选择译著阅读,从有思想的描述性著作入手。为什么历史学译著最有市场?因为相对而言,除了历史哲学,历史学主要就是讲故事,是带有历史判断的故事,它比较容易进入,我们刚才提到的埃文斯的第三帝国三部曲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当你的阅读面足够大以后,你才能迈到第三步:你以读者兼译者兼判断者的身份,为译著定位,如此,你也就达到了一个专业读者的阅读境界。我想,在迈过了这三道门槛之后,作为读者的你,应该会对中外思想、对人类的普遍处境,有比较通透而深刻的理解。
梅心怡:虽然我们现在有所谓世界史热,但历史领域毕竟范围很大,所以我在选择是否出版某本书的时候,还是会有很多犹豫和担心。比如要让读者接受一本关于中世纪宗教的著作,其实需要很多背景知识的铺垫,循序渐进,最终他可能会意识到,了解中世纪的宗教对他理解现在的国家有什么帮助。但这会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说白了,我们会追问,现在的市场到底需要多深入的书。我们之前出过一本《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很受欢迎,去年又出了一本《救赎者:拉丁美洲的面孔与思想》,借助九位拉美历史人物的人生线索,勾勒出一百五十年来拉美的政治思想面貌和历史探索轨迹,但可能些读者觉得这本书有阅读障碍。因为他们没有读过其中讨论的文学作品,或者对里面讲述的阿根廷的某个阶段的历史感到很陌生。这多少有点令我们烦恼,总之文化传播需要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范庭略:我之前读过甲骨文出的《天国之秋》,它确实颠覆了我对历史的看法。这本书第一次把太平天国运动和美国独立战争、英国纺织工业革命联系在了一起。同一时期,美国暴发南北战争,棉花收不上来,这导致英国工业革命的布没有原料;英国想把布卖到中国南方,但江浙又被太平天国占了……这本书从一个横的关系上来谈太平天国,和我以前读到的纵的谈法很不一样。我觉得有时候译著能改变我们的思考方向。
梅心怡:现在国内译著的出版速度越来越快,译本出版的时间点距离原书出版的时间点越来越近。为什么《天国之秋》和比如说史景迁的《太平天国》的写法不一样?因为前者有全球史的观念,后者则可能是从汉学出发。翻译的加速让我们可以尽早把国外的研究成果和视角带进来。

任剑涛:在我看来,我们民族的阅读习惯还有待进一步培育。在古代社会,阅读很大程度上是科举考试的手段,而到现代社会,因为忙于改变被动挨打的状况,对数理化生的阅读占了很大比重,甚至我们用来形容读书有感觉的表达——“如受电染”——都来自自然科学。我还是期待普通读者能够去阅读人文社科著作,第一要读,第二试着读进去,第三再争取读得懂,哪怕只能囫囵吞枣地读,我也给你竖大拇指,因为这多少能使你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就像太平天国,既有农民起义的风景,也有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冲突的风景,唯有通过阅读你方能领略到。不读万卷书,即使借助发达的交通工具,行了万里路,周游了全球,你照旧是井底之蛙。在这个意义上,人文社科译著打开的不仅是知识和思想的窗口,更是生活的窗口。我说了这么多,就是希望能够把大家从手机拉回书本,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不该只是一个刷屏的民族。
范庭略:任老师说得非常好,但有一点我觉得可以补充。屏幕和云端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我们一些人藏书难的问题,对知识的传播和普及也有功绩。一本《论语》,最早刻在竹简上,后来印在羊皮上,到现在装在手机上,可能连一兆都不到,但《论语》还是《论语》。当书本可以被如此便捷地携带,就为更多人创造了接触书的机会。我最后还想问梅老师,最近理想国有什么新书要推出?
梅心怡:有一本书我们预告了两年,最近终于要出版——英国经济史学家亚当·图兹的《滔天洪水: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全球秩序的重建》。我们之前出的书大多集中在二战或二战以后的世界,一战相关的只出过一本《ç:一战中东,1914-1920》。图兹这本书借用了国外近年流行的全球史的概念,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的霸主的地位如何从欧洲转到美国。过去我们总认为,二战之后二十世纪才进入了美国的世纪,但按照图兹的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已经对欧洲十九世纪累积起来的财富和人口造成了极大的损伤,当时欧洲为了尽快恢复,向美国借债,并且同意用美元来偿付,这便使美元在二十世纪初就已经开始成为重要的国际货币了。
我感觉前几年出版的历史类译著还是更偏重故事性,而非思想性。现在这个局面开始发生变化。我看到甲骨文最近也预告了要出版著名的晚期罗马帝国宗教史家彼得·布朗的《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大家越来越重视挖掘十九世纪前的历史,主题也越来越多元。当然我相信二战和冷战还会是热门。
任剑涛:随着译著数量的增加,我们中国读者的口味越来越刁钻,这对出版机构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法国知识界总体非常左倾,右翼学者很罕见,但右翼学者一旦出现,往往就堪当“伟大”二字,比如《论法的精神》的作者孟德斯鸠。二战以后,法国知识界的旗手是左翼的萨特、波伏娃,但他们的同班同学人雷蒙·阿隆是右翼。阿隆的回忆录追述了二十世纪法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一直到七十年代,这本书国内出国三个版本,销量非常大。最近甲骨文又翻译出版了阿隆最重要的国际政治著作——《民族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因为目前中美关系相对紧张,这本书与我们有切身的相关性,阿隆苦口婆心、耳提面命:战争不是个好玩的东西,但必须要思考战争才能够保障和平。
或许在短期内,汉语学术要跻身人类学术的前列,还有待艰苦的努力,所以大量翻译著作引进出版的趋势还不会改变。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如今译著选题的多样性、作者的多元性、思想的深刻性都有明显的加强。让我们相互共勉,读更多的译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