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刘云杉,女,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
基金项目:
北京市教科院“创新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研究”。
致谢:
在本文的写作中,应星、渠敬东在理论资源拓展与核心概念的提炼上给予启发,陈向明、康健、刘坚、高峡、郭华参与专题讨论并提出诸多批评意见。在论文的后期修改中,编辑部提供的匿名评阅意见以明确的问题意识不断地把文章拉回与现实的直接对话中。我的学生们——无论是在秋季的“涂尔干读书会”,还是春季的“赫尔巴特读书会”,他们像勤奋而灵敏的蜜蜂,不断采集花粉,酿蜜成为我们共同的事业。就此意义而言,这篇文章远不是个人的作品;当然,文章中的不足之处完全由作者负责。
摘要
本文探讨了当下基础教育出现的一种不同于传统的理念型教育模式——“博放教育”。这不仅意味着中国社会的中上阶层与中下阶层在继承人的培养与精英的塑造策略上出现明显的分歧,也意味着教育最核心的部分发生了断裂:即教书与育人的分裂。本文先检讨了博放教育的制度逻辑——减负简单地将兴趣与努力对立,选课以差异性替代了共同性的培植,走班制提出集体之外成长;继而剖析博放教育背后的民情风尚:惟新是从切断了时间链条,平等否定了纵向的秩序,也否定了教育的权威性;最后诘问:看似摇摆于外在的严苛与内在的虚妄之间,实则严苛与虚妄内外合一,无根与无限互为因果。在此情势下,教育的正当性究竟何处安放?
一、 问题的提出:作为理念型的“博放教育”
中国当下基础教育领域,尤其在某些最具有典型性与影响力的高级中学,无论是对优质教育的理解,还是具体办学的实践,出现了两种看似不同的取向,准确地说,是两种对立的“理念型”:一种为“精约教育”,它强调严格的制度与纪律,养成习惯,砥砺品格、磨砺意志,用“苦中苦”或“苦中乐”以实现“人上人”的目标;另一种为“博放教育”,它致力于将约束降到最低,主张解放学生,让学生在集体之外成长,让每一个学生可以变得伟大。(博放教育来源于白壁德[Irving Babbitt] 对人文主义的一对描述概念——博放时期[era of expansion]与精约时期[era of concentration]。“博放”与“精约”二词取自《学衡》,系徐震堮1924年译定。主导博放时期的是解放运动,对感官、才智的解放,它以勃勃的生气打破传统的镣铐和束缚,但易滑入无纪律与无序状态以及自我的张扬与放纵。[白壁德:《文学与美国的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1页] 教育史上在精约与博放之间,常出现钟摆式运动:严苛的精约之后,反拨以博放;失之博放之后,又摆回精约的收敛与严厉。这是一对既相互修正、又相互依存的孪生概念。)两种“理念型”教育模式之间存在明显的分歧并且反映出中国社会的断裂:大城市的人尤其是社会的中上阶层开始体验与享受素质教育的成果,而中小城市、乡村的人与社会中下阶层信任与选择的仍是应试教育。中国社会的中上阶层与中下阶层在对继承人的培养途径、对精英的塑造策略上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应该谨慎地去体认“理念型”与现实的区别,理念是对现实高度的抽象与概括,理念型是以漫画的笔法勾勒事物的典型特征,即传其神而非画其形。本文的写作旨趣在于从真实、自然且丰富的教育实践中抽离出带有典型特征的“理念型”并加以剖析讨论,而非详实地记录与评价某所或某几所中学,这是非现实版的故事,但它们并非虚构的故事,而是比现实更真实的故事;这并非“别处”的故事,而是以丰富的具体形态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每一所学校。)
这对理念型教育模式的背后是主导中国基础教育近三十年的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之争。作为一个概念,素质教育产生于1980年代中期,其诞生伊始便是应试教育的对立物,是针对应试教育且向应试教育开战的旗帜(王策三,2004)。吊诡的是,应试教育作为批判的靶子,不同的力量虽各有侧重,但却指向清晰、贴切且有力;素质教育作为建设的目标,内涵却是纷乱的,面目是模糊的——素质教育更准确的定位是作为批判的武器依附于应试教育的躯壳上。就此而言,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早已成为一对相互依存的阴阳合体。在对应试教育漫长的围剿中,逐渐形成了三股立场鲜明且分工明确的力量。
其一,对应试教育最直接且切肤的批评来自温情的独生子女家长,他们多为朴素的人本主义者,希望孩子能有更为轻松、自然且自由的童年。中国社会独生子女的家庭结构为人本主义者提供了坚实的情感基础,因其广泛的影响和动员力,他们充当了围剿的“马前卒”。他们尖锐地批评应试教育是“精致的暴政”。(参见蔡朝阳:《做一个不被世界改变的人》,载《中国青年》2014年第12期。蔡朝阳是浙江绍兴稽山中学老师,2010年出版《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一书,引发社会对于小学语文教材的反思。作为一线教师,他对语文教学与传统教育的尖锐批判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同时,他自称“文艺中年、资深奶爸”,喜与顽皮男孩“菜虫”一起成长,以“虫爹”的形象区别于强大的“虎妈”“狼爸”,代表另一类家长及其教育观。他相信:儿子菜虫有权一生虚度光阴,不必活在虚妄的责任里,不需要出人头地,也不需要平步青云,因此,菜虫有权一事无成[《菜虫,你有权一生虚度光阴》,载《当代教育家》2015年第3期]。他坚持一种无能的力量——成年人以为自己力量强大、可以用绝对权威与暴力管教孩子时,其实是无能的;但是面对生命的奇迹,面对造物的恩宠,成人必须在无能中寻找力量[《我是“虫爹”》,载《中国青年》2012年第9期]。)人本主义教育者坚信:想象力是第一生产力,儿童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是民族的未来,要坚持“儿童优先”的原则,保障儿童的教育权利——要善待儿童,保护儿童的想象力、创造力,给儿童提供免于恐惧的教育。人本主义教育宣言:从应试教育突围,为生活重塑教育(杨东平,2015)。
其二,知识界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在中国现代性思潮发展的历程中,反专制主义、反权威主义、追求思想与个性的解放一直具有深刻的影响力,此为人本主义者的思想资源与精神灵魂。中国新文化奠基者——“五四”一代即提倡儿童的“蛮性”,提倡“童话精神”,创造“新青年”,把对老大帝国的反抗不假思索地转换为对新的少年中国的热情讴歌。自由主义的论述建立起儿童与知识、童年与学校的对立,集中体现在鲁迅所描述的“百草园”与“三味书屋”的意象中,这对隐喻直指教育世界对儿童自然世界的剥夺——他们所受教育的全部目的就是把他们天生的好奇心和探索热情全部抹杀掉,这些从睁开眼睛就忙着背书、做习题的孩子,已经没有时间欣赏自然的“黎明”之美,又从何体验精神上的“黎明感觉”?因此,要保卫童年,保证他们在自由的时间、空间里成长的权利和欢乐的权利(钱理群,2012)。(钱理群先生与杨东平先生多年来以理想主义的情怀与现实主义的精神,关注教育、参与教育,是笔者非常敬重的师长。然而,置身于中国社会与民情的复杂性与丰富性,面对教书育人这一专业领域内所独有却又常被忽视的细微精致的实践感,我们不仅需要政治的激情与道德的情怀,更需要细致地体察真实教育如何发生,小心地辨析现象与概念之后的真与伪,谨慎地在主观的热望与现实的冷峻之间作严格的区分,这需要坚持韦伯所说的学者的“理智的正直诚实”[韦伯:《学术与政治》,三联书店1998年版]。)
其三,新世纪初,教育部公布《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课程改革成为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改革课程体系与评价制度,整体推进素质教育,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与全民族创新能力(刘坚,2013)。至此,素质教育从批判的武器转变为建设的纲领,它宣称要概念重建,建立起“学科、教师、讲授”与“经验、学生、探究”三者之间的对立:首先,以经验对抗学科,主张在基础教育阶段淡化对学生的学科专业训练,强调学生整体素质或综合素养的形成(钟启泉等,2001);其次,以学生主体替代教师主导,在师生平等中彰显教育民主的价值;再次,以探究替代讲授,“自主、合作、探究”推动学习方式的变革。(见《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2001]。)
据此,人本主义的前锋与自由主义的灵魂合力于“破”——对应试教育具有摧枯拉朽之效;阵地战由新课程改革来完成,它致力于“立”——素质教育落地生根时究竟是什么形态。于是有了博放教育的关键词:学生兴趣、选课、个性化的课表、走班、取消行政班、社团、俱乐部、为自己的成长负责……内涵模糊的素质教育呈现出来的现实形态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它几乎是20世纪早期活跃于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简单移植;说陌生,中国版的进步主义教育又增加了若干本土经验:帮助学生在集体之外成长,集体主义教育成为负资产;教师权威被扭曲为“警察”的权力与“保姆”的琐碎之后,认同于服务业的教育有了新身份,学校成为供货充足的课程超市。于是,在我们时代“博放学校”的校门镌刻着无字的箴言:这里提供你感兴趣的一切,这里成就你想拥有的一切。
然而,故事一定还有更纵深的层面: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活跃在1910—1950年之间, 反映着其时的个人主义倾向。进步主义一直受到质疑与批判,尤其是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之后,进步主义教育所主张的“儿童中心论”更是饱受非议,批评者认为姑息儿童的日子太久了,国家变得懦弱了(乔治·F.奈勒,1982:70-92)。在美国教育思想史上,既有儿童中心的人本主义、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又有人文主义、永恒主义的教育理念与实践作为制衡;在欧洲教育思想史上,不仅有启蒙以后的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而且有始于古希腊、至今仍有深刻影响的人文主义传统。两派既相互对峙,又相互制衡。中国教育在宣称与世界接轨时,怎么只取其一脉而无视另一传统与实践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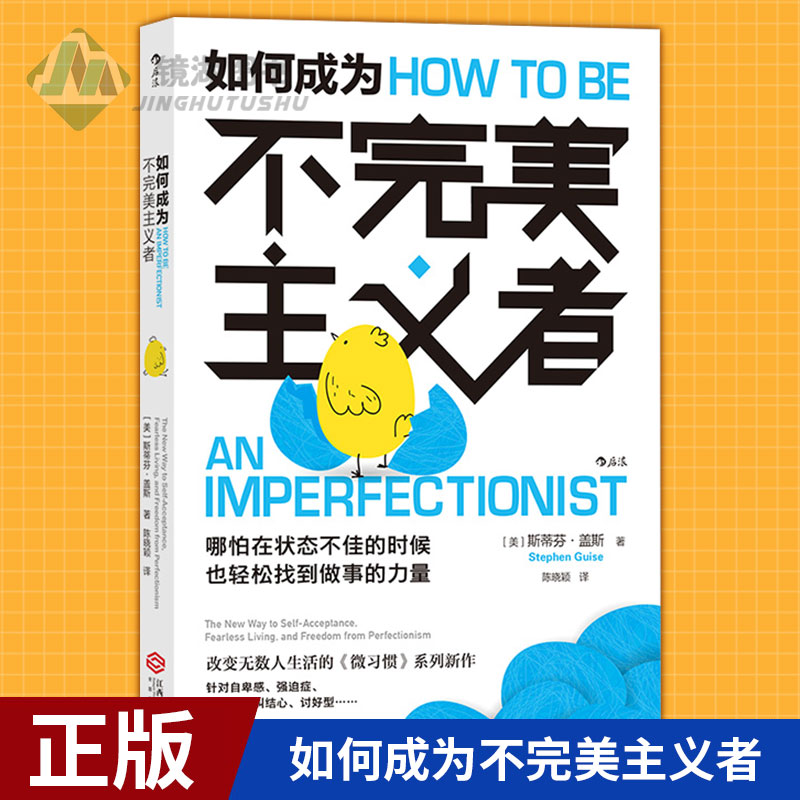
素质教育化解中国教育自身的困境了吗?学生的学业负担减轻了吗?学校减负后,素质教育由谁、在哪儿、又以何种方式进行呢?学校减负了,家长们忧虑了,校外培训机构却高兴了。减负将学校的主阵地让渡,将教育的关键责任外包,在自主且愉快的校园,在多元的评价中,学生们是没有区分度地普遍地好;然而,核心竞争已经移步校园之外,在课余,在假期,在各种贵贱不等的培训班和补习班中,在奥数、英语、书法、钢琴等各种考或不考的技艺与特长的培训中。此“减”彼“增”意味着教育的育人与择人的两大功能分离:在应试教育中,学校既培育亦筛选,学得好就能考得好;而今在校园浅表的愉快背后,有多少身心疲惫的孩子与负担沉重的家庭?温情的人本主义者此刻已成为急躁的功利主义者,纸上谈兵的“虫爹”完全败给精明强干的“虎妈”“狼爸”。家长们不心疼孩子吗?不懂拔苗助长的道理吗?“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既是培训机构蛊惑人心的广告词,也是家长们彼此绑架、推高投入的心魔(刘云杉,2014b)。
在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对峙中,出现了教育之培育功能与筛选功能的离奇分裂,这还只是教育变革大戏的第一季。如今,剧情的第二季已深入学校的内部,博放教育的出现意味着在教育最核心的部分发生了断裂——教书与育人的断裂,既有无教育价值的学习,也有无教学根基的育人。在教育学的奠基之作《大教学论》的扉页,夸美纽斯写到:“懂得科学、纯于德行、习于虔敬。”习知识、修德行、致信仰,这是教育的内在秩序。假如抽离德性与信仰这两个维度,教育的大厦塌陷了,裸奔的知识教育或者左倾,知识的权威与教育的专制窒息了心灵的活力,是为精约教育;或者右倾,兴趣的易变与知识的碎片以及平等的权利诱惑着欲望以及意志的肆意生长,是为博放教育。然而,精约与博放看似为不同的形式,实则既高度合谋又内在一致。说高度合谋,是因为绚丽的博放教育实验高度依赖于校外教育培训机构中的精约教育,体制内的素质教育与体制外的应试教育离奇地组合在一起。说内在一致,是因为严苛的制度躯体同样沉溺于博放的迷梦中,准确地说,中国当下的精约教育徒具严苛之形而内在的严肃堪忧,博放看似精约的逆反,实则为精约教育“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励志版。失去内在严肃性的精约教育不过是博放教育的亚类型,博放才是其化蛹成蝶的目标所在。
摇摆于精约的严苛与博放的虚妄之间,教育内在的严肃性究竟何处安放?其后是什么样的制度逻辑以及何种民情风尚?
二、 博放教育的制度逻辑(一) 减负:兴趣与努力
过重的学业负担是中国基础教育的沉疴。纠正课程内容的繁、难、偏、旧,教学过程中的死记硬背、机械训练,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验,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这是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出发点。(见《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2001]。)如何减轻学业负担成为一个见仁见智的实践热题。博放教育认为,强迫学生学习不喜欢的东西才会感到负担,感兴趣的东西会让他们着迷,他们会在学习中感受极大的愉悦。托马斯·爱迪生对传统教育的控诉是:人类大脑发展的可能性几乎是无限的,但重要的是不要让小孩子去学习他们不喜欢的东西,如果学习不如玩耍有兴趣,那就变成了一种伤害。如果你让一个孩子学习他不喜欢的东西,并且一直持续到14岁,那他的大脑就被永久地损害了。由此,道尔顿教育计划的目标是:让学校变得像游戏一样吸引人,让教育像游戏一样寓教于乐(帕克赫斯特,2005:20)。博放教育强调儿童的兴趣,儿童只有把所学的东西与自己的兴趣结合起来,才能主动、快乐地学习——兴趣是乐学的基础。
在一所学校的人文讲堂张贴着学生对来校讲座的教育专家的质疑:
教授说兴趣是你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那么,兴趣与随心所欲有什么区别?学习如同工作一般,是必须完成的。把兴趣作为工作与学习的前提,是可疑的。教授讲天才与学校的关系,引用郑渊洁的案例,写作是他的兴趣,他虽然就小学毕业,却有了不起的成就,他对教育充满不满与不屑。然而,这些“幼时不学的名人”是小概率事件,推及一般,以此否定学校,这是不客观的!教授还强调“高智商的人”应该怎样做,我不只一次听到专家告诫:如果你智商够高、能力超强,你应该适当地回避现在的教育,你最终还是能获胜。很遗憾,我不属于教授所说的“高智商”的人。这么说来,“兴趣至上”的理论是不适合我这样大多数的普通人的,那么,针对中国众多人口所制定的教育又怎么能依据这种培养少数“英才”的教育理论来改革?同理,中国未出诺贝尔奖,借钱学森之问来否定中国的基础教育是站不住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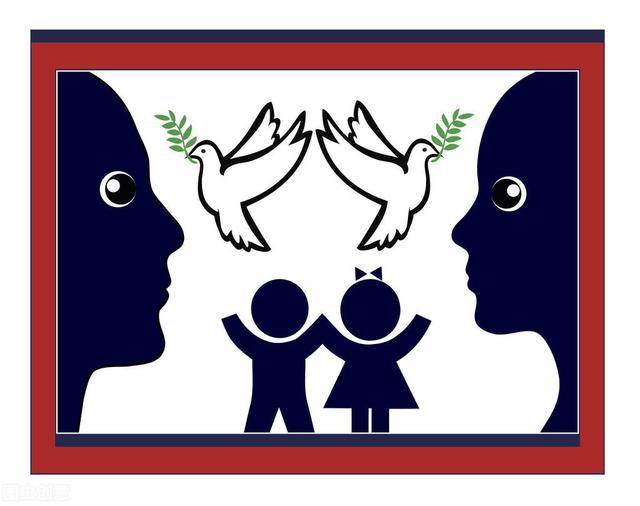
这段文字密集地质疑博放教育中的关键词——兴趣、天赋、高智商与英才。儿童天生的、自然的兴趣可靠吗?外在的兴趣可能是一般的好奇与猎奇,也可能是嗜好与欲望,更可能是浮皮潦草的浅尝辄止。赫尔巴特指出,“不要在有趣的事物中忘记了兴趣”(赫尔巴特,2015:50),可以理解为:不要让“兴趣”迷失在“有趣”中。他区分了“有趣”与“兴趣”,不能将有趣等同于兴趣。在他的论述中,兴趣首先与限制联系在一起,把纷繁杂乱的涉猎限制到兴趣上来;其次,兴趣与专心相连,“正因为人的专心能力太弱,不能在许多地方仓促逗留而有许多成就,所以我们必须防止草率的逗留,想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有所作为。这种分心将使人格也黯然失色”(赫尔巴特,2015:47);其三,兴趣体现为耐心,他提出“具有耐心的兴趣”,浓厚的兴趣体现为能理解且等待事物在时间的自然之流中所呈现出的冗长,能克制自己接受甚至忍受冗长中的单调与乏味。杜威也看到了这一点。他指出,幼儿不耐烦,急于看到结果,一击幻想中的魔杖就把理想变成现实,因此幼儿同样需要工作;同时,这一工作必须区分苦役(在工作中须作不寻常的艰苦努力,甚至精疲力竭)与贱役(本身就是一项十分讨厌的活动,它是在某种纯属外部需要的强制下执行的)(杜威,1981:124)。只有在工作与努力中,兴趣才能成为持久、稳定的内在兴趣;进而,它才可能与责任结合,成为内在动机。遗憾的是,在博放教育“保卫童年”的逻辑中,却将兴趣与努力、训练对立起来,或者以兴趣替代努力,或者指责训练扼杀了兴趣,或者虚张天赋的神秘——既诱惑又贬抑普通孩子平凡的心智。教育的园艺隐喻对儿童的自然本性、天然能力充满着信任,蒙田针锋相对地用肥沃的“闲地”与“野草”来比喻儿童未经规训的性情与易变的兴趣:“正如我们看到一些闲地要是肥沃富饶,就会长满千百种无益的野草。”儿童的奇思异想与胡思乱想看起来都很炫目,“若要加以利用就必须翻地播种,才能对我们有用……思想也是如此。如果不让思想集中在某一事物上,不加指引,无所约束,就会漫无目的地迷失在幻象的狂野中”(蒙田,2009:24)。疯长的性情常将幻象与真实颠倒,而野草般自生自灭的兴趣只会导致狂妄与懒散的性情、浮躁的忙碌以及浅表的快乐。
兴趣还是努力?天赋还是习惯?乐学还是苦学?这组对立的旨趣反复出现于教育观念的流变中,教育实践也如同钟摆。回顾历史,可以看到永恒主义者责问进步主义者:准许儿童易变的兴趣对他所学的东西发生这么大的影响,岂不荒唐?今天的兴趣可能与昨天的报纸一样无聊,一个孩子想当牛仔,对他这种兴趣能够让步到多大程度呢?如果他想要射击印第安人,对他的这种兴趣又能鼓励到多大程度呢?(乔治·F. 奈勒:1982:72-80)永恒主义者检讨,儿童成长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理智的增长,大多数美国青年人的头脑从来没有真正受过学习理智教材的锻炼,这是因为教师漠不关心并且没有抓紧这种锻炼。由儿童明显的懒惰和肤浅的爱好来决定他们学习什么,实际上妨碍了他们去发现自己真正的才能。自我实现要求有自制力,但如果没有外铄的纪律就不能养成自制力,每个人身上都潜在着一种或几种高尚的兴趣,但如果不下大量的苦功夫,这些兴趣在通常情况下并不能显露出来(乔治·F. 奈勒:1982:69)。
在天赋还是努力的问题上,有一篇影响甚广的文章指出:努力才是真正的天赋。天赋决定一个人上限,努力决定一个人的下限,也决定了一个人当前所能达到的高度。就目前大多数人努力程度之低,还远远达不到比拼“天赋”的地步。努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天伏案十多个小时学习或工作,看似简单,其实很难,因为日复一日的劳作,至少需要三点保证:集中力、精力和耐力。坦诚地讲,学东西上手的快慢,其实大部分人都差不多,但是想要精通某事,比拼的就是集中力、精力和耐力了。(胡小鹄:《努力就是天赋》[2015年7月],见某中学主页。此文具有代表性。)这几乎是要素主义观点的翻版——学习的本质要求刻苦,并且往往要强迫自己去专心致志。与进步主义强调个人兴趣相反,要素主义强调努力:在正常情况下,较高与较持久的兴趣并不是一开始就能感觉到的,而是通过大量的刻苦用功才能产生的,虽然儿童一开始对这种刻苦学习并不感兴趣(乔治·F. 奈勒,1982: 88)。与进步主义主张儿童的自由相反,要素主义坚持纪律的重要性,他们不强调儿童眼前的兴趣,而极力主张儿童要献身远大的目的。学校正是用一套严格制度,将生活的节制、纪律的约束融进学生的身体与行为惯习中。教育不是空洞的鼓励与信任,也不是淡漠的隔岸观火,教育是具体且细致的,它不仅将向上的动力如同一部发动机一样安置在学生的心中,同时还用一套细致且严密的制度,确保其完成身心的蜕变,养成终身受用的习惯和品格。(作为博放教育的对立面,精约教育既饱受舆论的批评,又被众多学生、家长乃至教育工作者所认可,论证其教育理念与实践的合理性。参见叶水涛:《平凡的极致》,载《华夏教师》2014年第10期。) 康德在《论教育学》中特别指出训诫的重要性,训诫是把野性从人身上去除的活动,它防止人由于动物性的驱使而偏离人性,这必须及早进行。因此人们把孩子们送进学校时,首要的目的并不是到那里学习知识,而是让他们能由此习惯静坐,严格遵守事先的规定,以便他们在将来不会随便想到什么就真的马上去做什么(康德,2005:4)。
训诫最可靠的方式是习惯的养成,在西方教育观念史中强调的另一个核心概念是习惯。蒙田说得很真切:习惯最大的威力就是抓住我们不放,蹂躏我们,以致我们靠自己力量很难摆脱(蒙田,2009:104)。习惯是习俗内化在我们身体上的强制,构成了我们的第二天性。因此,习惯的养成需要反复、单调甚至枯燥的练习,一定的练习甚至适当的苦学是必要的。洛克强调习惯养成的艰苦性与细致性,教学是反复的练习,“(那些)只靠一次有关音乐和绘画的演讲就培养出来的优秀画家或者即席表演的音乐家,靠一套法则说明正确推理的步骤就培养出思考有条理的人或者推理严密的人,是很难有希望的”(洛克,2007:16)。在洛克看来,幼童不是经过(知晓)规则就可以教育好的,规则往往会在他们的记忆中消失。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创造机会,让他们通过必不可少的练习,把事情做好。这种方法能够在他们身上形成习惯,习惯一旦养成,做起事来便轻易而自然,无需再借助记忆(洛克,2005: 134)。以技艺的习得为例,只有在不断重复的练习中,技能与技巧才会迁移到学习者的身体上,譬如工匠的手艺、舞蹈家的肢体、画家的眼光,也正是在这不可省略、不可偷懒的反复枯燥的练习中,教育潜移默化地发生着——用习惯把抽象的概念变成身体的记忆和动作的倾向,形成持续、稳定的兴趣与内在驱动力。
习惯既具体落实到个体的日常举止、生活惯习中,又借“习俗”勾连传统与社会,达成教化。好的习惯如同被精心耕种的良田。夸美纽斯指出,对青少年来说,持重、节制、坚韧与正直是最为重要的德行。对生于安乐的年轻一代,难道可以轻率地否认节制、坚韧这些德行以及忍劳耐苦的训练吗?节制要求应当教孩子们在饮和食、睡眠与起床、工作与游戏、谈话与缄默方面,在整个受教期间实行节制——“一切不可过度”;坚韧要求从自我克制里学习,要压制游戏的欲望,要抑制急躁、不满足和愤怒。应当使儿童不受冲动的指挥,而是根据理性去行动,因此要求他们学会忍劳耐苦。既避免过度的压力,又有勤奋的性情,使身心不断有事可做,使人活泼,受不了惰性的安逸。夸美纽斯引用辛尼加的话作小结:“培养成高贵心理的是劳苦。”(夸美纽斯,2014a:146)
这样我们才能理解苦学的必要性。“这孩子很聪明,只是不够用功”,这句话麻醉了多少人?似乎智商更重要,努力不过是笨人的功夫。殊不知,不努力,怎么配得上有天赋?法国哲学家阿兰(Alain)坚持古典主义教育,针对西方现代教育对儿童的兴趣与本能的推崇,他辛辣地批评道:
什么儿童乐园,什么寓教育于娱乐之中的等等发明,我是不太相信的。他们既然沉湎于这种易得到的快乐,他们就丢失了稍鼓勇气、稍加专心即可到手的那种更高的快乐。发现一种高卓的快乐,还有什么比这经验更能使人提高的呢?谁不在开头吃一些辛苦,谁就将终久愚昧无知。……不可能指望儿童像尝蜜饯那样的尝一尝科学和艺术的味道,人是靠辛苦的陶冶而成其为人的。他必须自己去赢得自己的真快乐。他必须自己配得上这快乐。先付后收,这是规律(阿兰,2001:267)。
(二) 选课:差异与共同
“不见树木,只见森林”,是批评传统教育弊端的用语。博放教育的使命是发现森林中每一棵具体的、独特的树,学校所面对的学生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整体,而是在志趣与性情上有着种种差异的、具体与鲜活的个体,学校要为学生的个性发展创造条件,“个性化课表”为每个学生“私人定制未来”。博放学校建设了庞大的课程超市,既有分层也有分类,既有综合也有专项,甚至还提供一对一的特需课程。
学校要办成满足不同学生不同需要的超市吗?在课程内容上,博真的就好吗?在课程组织中,是立足于培养共同性还是尊重甚至放纵差异性?如何面对知识的碎片化、学习的浅表化?教学的教育价值究竟是什么?下文将加以讨论。
首先,博还是专?这里指的不是知识的种类,而是教学的过程。学生面对庞杂的课程,很可能浅尝辄止,诸多知识皆有所涉猎,却只知皮毛。读书不走心、不开悟、不养性,正是因为教与学太庞杂、太匆忙了,所学的知识并未真正嵌入学生的心智结构中。用夸美纽斯的话说:“这些东西只是通过了他们的脑子,却没有牢固地固定在那里,如同把流水泼到筛子上去。很少有人离校时受到了彻底的教育,多数人所记住的只是一种外表,只是真知识的一种影子而已。”(夸美纽斯,2014:93)怀特海所谓“呆滞的思想”(inert idea)所指也是这些毫无活力的知识,如同电脑中磁盘的碎片,占据了内存空间,使主机失去活力,它们是人脑中的垃圾知识。(怀特海,2012:2)
教学是极为谨慎的工作,无论教学的内容、教学的时机还是教学的方式,都需要谨慎选择。教学的原则有基本的要求。其一是谨慎。要谨慎地挑选最基本且重要的知识。没有一个希望在他的田地、果园和花园里面结出果实的人会去种萎草、苧麻、蓟草和荆棘,他只会去种良好的种子和果树(夸美纽斯,2014:94)。其二是专心。肤浅地涉猎对人的心智与性情的影响极坏,学习应心神专注、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此即夸美纽斯之教学的彻底性原则。学习不在量多,不在速捷,而在“静”与“敬”,在于由“静”达“敬”。只有“静”,才能让人心沉静下来。中国最早的师范教学创办者张謇指出:凡教之道,以严为轨;凡学之道,以静为轨(张謇,1994:318)。其三是秩序。教与学应遵循秩序,循序渐进,不能随意打乱。模块课程如同积木,可以随意拼搭,看似方便学生,却根基脆弱。“模块”隐喻了知识的“破碎性”(fragmentation);“模块化”带来的不仅是知识组织的“去中心”,更是知识选择的无序化,对一个成长中的学习者而言,这不啻为一种不堪承受之重(吴刚,2009)。
其次,学校真的要提供一个由学生的需要、趣味主导的课程超市吗?校园中出现了“水课”与“虐课”之分:“水课”的主导思想是广泛涉猎,鼓励学生走走看看,多是一些入门性的简介,缺乏知识的系统性,学习难度降低;“虐课”则相反,多是一些基础课程、必修课程,要求严格、内容艰深甚至枯燥,这一部分知识用严格的教学“融化”到学生的认识、心灵与性情之中。麦克·杨(Michael Young)对课程社会学的研究指出,知识与教学组织有难易、高低的层级之别,其中,书面、文字的学习高于口语的学习,独自的学习高于合作的学习(Young,1971)。博放的课堂教学推崇合作学习、小组讨论、动手操作、口头发表,专注、独自的阅读与解题被贴上应试教育的标签而被贬斥,学生多活动而少学习,教学的难度降低了。与“虐课”相比,“水课”既学得轻松又能拿高分。课堂教学中要求教师少讲、精讲,给学生的自主学习留下空间,这合理的要求在具体实施中却引起了讲授法遭遇“有罪推定”(丛立新,2008)。将学生主动地学习与教师引导性教学相对立,讲授法能被简单地质疑为教师的个人秀吗?学生选课还重释了教学的内涵,重构了师生关系,当学生拥有知情权、选择权、表达权与评价权时,他们成为课程商品的购买者与消费者,他们真能成为学习的主人吗?
一名学生数学题做错了,老师让他改错后再做两道同类的题目,他做了一道,抬头和老师商量:老师,我做一道行吗?
为什么?老师反问他。
我想去操场玩会儿球。(本文的楷体字部分皆引自博放学校的相关材料,后文不再一一注明。)
怎么才能让学生喜欢我的课?选我的课?博放校园中出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现象:学生与教师碰面,许多老师会主动先向学生问好;老师与学生说话,非常在乎学生的感受,常常向他们:“这样可以吗?”博放校园已成为一个卖者不得不取悦买者的市场,教师迎合学生的趣味,纵容学生的懒散,教师忙于亲和、妥协,怕被指责为“权威主义”的严师。学生的喜欢能成为最高标准吗?快乐是有高下之分的,今天的喜欢不等于明天的珍惜。学生的所有快乐、一切需要都需要尊重吗?面对所有的快乐一律平等、应该受到同样尊重的诉求,苏格拉底反驳道:有些快乐来自高贵的好的欲望,应该得到鼓励和满足,有的快乐来自下贱的坏的欲望,应该加以控制与压抑(柏拉图,2002: 338)。什么是儿童的需要?儿童的需要不是耽于游戏与嬉闹,而是成长——摆脱无知无力,获得自主与自由的需要,成长的雄心是儿童的精神动力。阿兰指出:“儿童有儿童的轻浮,儿童有运动和吵闹的需要,这是游戏的一部分;但是,儿童还必须在从游戏到工作的变化中感到自己的成长。这壮美的过程,远远不是使它不知不觉,我愿它是鲜明突出的,庄严隆重的。你强迫过他,儿童会感激你;你奉承过他,儿童会蔑视你。”(阿兰,2001:268)。
其三,差异还是共同?必修课程是普通高中学生发展的共同基础,根据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统一设置,《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中要求,必修课应占学分数的61%。(必修课程是普通高中学生发展的共同基础,由国家根据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统一设置。必修课88学分,占全部144学分的61%。参见《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2003]。) 某所学校开设了265门学科课程,30门综合实践课程、75门职业考察课程,还有272个社团,60个学生管理学院岗位课程。学校压缩必修课,以提供给学生最大限度的选择性,其中只有17门必修课,占课程门类中的2%,其余98%都是选修课。能将共同的必修课程视为标准化工业生产吗?必修课程仅是“让每一个人全都躺在那张一样大小的魔床上,把他们锯得一样长”吗?博放教育坚信教育的本质是解放人,解放人的智力和心灵、思维和情感,而不是束缚人、压抑人和限制人。如何逃离魔床呢?个别化的教学、个性化的课表、特需课程甚至“一生一案”。二百多年前,针对“在可塑的年龄阶段把儿童偶然突出的表现看作通过教育能更大地发挥出来的标志”,赫尔巴特辛辣地讽刺道:“这种保护畸形者的做法是从宠爱发展到放任的产物,是低级趣味所推崇的。
光怪陆离与荒诞无稽的爱好者准会欣赏一群驼背的人与各种残疾人发狂地相互嬉闹,而不愿观看发育良好与匀称的人步调一致地行动。这就好像发生在这样一个社会中,这个社会由那些具有彼此不同思想方式的人组成,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以他的个性来炫耀自己,而且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别人。”(赫尔巴特,2015:59-60)在学生所谓的个体需要与爱好面前,一切时代的智慧都变成了毫无价值的东西,任何对这种爱好的制约都是不合理的限制,任由学生完全根据自己的性情和独特需要做出选择,可是青少年对自身及其才能的看法很可能会随着某一时刻的印象而动摇或改变,白璧德将上述教育观称为“教育印象主义”(educational impressionism),看似炫目但极不可靠(白璧德,2011:33)。赫钦斯(Robert M. Hutchins)引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休厄尔的话:“这不是教育,这不是人的教育;因为所唤起的不是人本身的东西,也不能将人与人联系起来。这不是培养一个人的人性的教育,而是对他的个体性的纵容。”(赫钦斯,2001:43)赫钦斯指出,西方教育多建立在个体差异学说的基础上,人是不同的,我不忽视它,但我否认它;我不否认个体差异这一事实,但我不相信它是关于人的最重要的事实,或是教育制度应该建立在其之上的事实(赫钦斯,1997:74)。
他批评美国教育将共同人性的培植与差异性的发展相混淆,前者是首要的、必不可少的,而后者是第二位、在多数情况下并非必要的,这种混淆最终导致最坏的教育。而教学过程的分裂最终将导致社会的分裂。赫钦斯还指出,课程的丰富多样以及选课制度剥夺学生共同的心智文化,它让美国的学院文化趋于贫瘠,足球与其他课外活动在美国学院之所以占有主要地位,大部分缘由在于只有这些活动才是学生共有的(Hutchins,1972:60-62)。
由于实施了选课制,刚性的时间变成了柔性的,空间和时间上对学生的限制缩小了,学生不必局限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计划安排自己的学习,甚至可以决定在哪个时间段学习哪门学科,师从哪位老师,在什么地点学习,是在教室,还是在自主研修学院,还是图书馆的阁楼。
德廉美修道院(Educational Abbeys of Theleme)可谓是博放教育的原型(德廉美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作家拉伯雷所著小说《巨人传》中主人公高康大[Garguantua]修建的修道院的名称。在《巨人传》第五十七章,作者记述了德廉美修士的生活方式:“院内整个生活起居,不用法规、章程、条例来订定,而取决于各人自愿与乐意。什么时候高兴,便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心里动念,就什么时候喝酒、吃饭、工作、睡觉;没有人来叫他们起身,也没有人勉强他们喝酒吃饭,或做任何别的事情。这都由卡冈都亚[即高康大]特别规定。他们的规定只有一条:想做什么便做什么。因为出身清白,受过良好教育,惯和良朋益友交谈的自由人们自有一种天然的本性,推动他趋向德行而远避邪恶,这种本性,他们称之为品德。如果困顿屈辱于压迫和束缚之下,人便会改换他原先追求德行的高贵热情,转而从事颠覆和摧毁这种奴隶性的桎梏。因为我们人总想追求违禁的事物,思念弄不到手的东西。”参见吴元训选编:《中世纪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72页),在它的入口处镌刻这样诱人的话:学习你喜欢的一切,做你爱做的事情——象征了个人的绝对自由和个性的绝对解放(白璧德,2004:67)。然而,碎片化的知识如何培育整全的人?教学内容的多元如何铸造学生共同的心智文化?教学过程的分裂如何避免群体的分裂?缺失了共同的文化基础,社会的团结如何奠定?
下文见:自由的限度:再认识教育的正当性(二)(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