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认知资本主义”论的理论缺陷
总体而言,“认知资本主义”论关注经济现实的新变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有重要启示。但是,“认知资本主义”论在其理论方面存在缺陷,特别是在构成其理论基础的非物质劳动、知识产品的本质、技术劳动是否会产生异化等与劳动价值论相关的理论观点上,存在逻辑错误和概念混乱等问题。这些错误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点。
(1)“非物质劳动”占据主导地位以及在认知资本主义下资本积累方式改变的观点。认知资本主义所强调的人的知识生产、脑力劳动并非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变化。脑力劳动是劳动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分析中并没有排除脑力劳动。他指出:“生产活动……都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33)。我们不能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截然分开,也不能简单地把体力劳动等同于物质生产。
“认知资本主义”论将体力劳动定义为物质劳动,将脑力劳动定义为非物质劳动。实际上,作为非物质劳动的脑力劳动应该分为两个部分来分析。一部分是生产性劳动,即物质生产中需要的技术创新、科技研发等劳动,由于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原来属于生产过程中一个环节的技术研发活动独立发展,但其目的仍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价值生产。另一部分是非生产性劳动,例如为价值实现而进行的广告创意创作、生活娱乐类文化产品或精神产品创作等纯粹脑力劳动,这类脑力劳动不创造价值。
亚当·斯密、萨伊和昂利·施托尔希都曾对所谓的“非物质劳动”和“非物质产品”进行分析,集中阐释了非生产性的非物质劳动是否创造价值、其产品价值如何决定等问题。麦克·莱伯维茨(Michael Lebowitz)在探讨传媒资本是否创造价值、是否剥削工人的问题时,认为只有雇佣劳动和生产性劳动可以被剥削;传媒资本所支配的支付工资和未付工资的劳动都不是生产性劳动,传媒公司无法剥削工人,因为他们创造的产品和服务只是资本主义流通过程的一部分(34)。他认为,生产性劳动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者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服务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35)。第二,“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36)。第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进行抽象概括时认为,所有劳动都是生产性的,因为它创造作为劳动的条件和结果的产品。
进行文化产品或精神产品生产的非物质劳动或纯粹脑力劳动属于非生产性劳动,不创造价值。在当前资本主义中,物质生产劳动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是价值的来源;纯粹脑力劳动尽管比重在提高,但仍然服务于物质生产劳动。因此,认为在认知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积累方式转变为依靠纯粹脑力劳动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2)在文化或精神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的创造力是否被剥削的问题。“认知资本主义”论认为,创造力、知识、想象力等认知因素属于人脑活动范围,且无法与脑力劳动者的身体分离,因此在认知资本主义下劳动者不会被剥削。
实际上,文化或精神产品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但不会在消费它的行为中被损害,反而被扩大,转变并创造消费者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环境。这种产品不生产劳动力的身体能力,相反它改变了使用它的人。文化或精神产品生产首要的和最重要的是“社会关系”(创新、生产和消费关系)。只有在生产中完成,其行为才具有经济上的价值。这种行为使得物质生产中被“遮蔽”的东西显现出来,那就是,劳动不仅生产商品,首要的和最重要的是它生产雇佣关系(37)。
“认知资本主义”论认为,物质产品会与劳动者异化,而文化或精神产品不会异化,这是将文化或精神产品的生产者与其所有者混为一谈。“在社会中,产品一经完成,生产者对产品的关系就是一种外在的关系,产品回到主体,取决于主体对其他个人的关系。”(38)在私有制下,商品的生产者和所有者并不直接统一在一个主体上,也就是说,产品生产者不直接是它的所有者或者消费者。产品一旦生产出来,生产者就与产品脱离,产品如何回到生产者手里取决于生产关系。作为雇佣劳动者,脑力劳动者为雇主生产知识产品,知识产品的所有权归雇主所有而非劳动者所有。该知识产品产生的收益归雇主,即使是知识产权,保护的仅仅是雇主对该产品的所有权而非劳动者,因此,劳动者和知识产品之间的关系仍然被异化。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工场手工业中也像在协作中一样,发挥职能的劳动体是资本的存在形式。因此,各种劳动的结合所发生的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协作整个说来没有改变单个工人的劳动方式,而工场手工业却使它发生了革命,工场手工业使工人畸形发展;工人不能生产独立的产品,他只是资本家作坊的附属品。劳动的智力,在许多人那里消逝,而在个别人那里扩大了范围。工场手工业的分工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作为别人的财产和统治工人的力量而同工人相对立。这个分离的过程从协作开始,在工场手工业中得到发展,在大工业中完成,大工业使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而同劳动分开,并使它为资本服务。”(39)
正如劳动力一样,创造力虽然不能与人身分离,但它生产出的产品也会由于私有制而与劳动者相分离并异化。知识产权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强化了资本所有者对文化或精神产品的所有权,并对他凭借该所有权获得经济利益的权利进行保护。因此,信息和知识在全社会的分享和自由流通依靠的不是信息技术本身,而是打破信息私有权藩篱的社会运动。声称知识劳动不会被剥削、人人共享的理念实际上是“点—新自由主义”(Dot-Neoliberalism)(40),即在信息技术条件下新自由主义的另一种表现。
(3)当前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发生重大调整,无产阶级被“知产阶级”取代,资本家与民众共同创造价值的观点。基于对在认知资本主义下劳动不会被剥削的判断,“认知资本主义”论认为无产阶级化的两个条件消失,这种观点也与现实相悖。
首先,认知资本主义下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对资本的隶属程度加深。认知资本主义建立的基础是信息技术、数字网络技术,技术变革对生产的影响是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划分的重要标准。信息革命是继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正在经历的第三次革命。这次革命的实质是在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融合的基础上,通过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整个经济体系的自动化和网络化控制。在信息化的过程中,传统的机器体系开始向自动化机器体系发展。新的机器在传统机器的三个组成部分之外,加入了一个新的部分,即自动化控制系统,它的主要功能是搜集和处理外部信息,并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自动调节自己的运动,从而克服人脑在感知和处理信息上所具有的生理局限性,使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空前提高,为最终将劳动者从机器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创造了技术上的可能性。但是,像历次科技革命的结果一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力,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提高都转变为资本对劳动进行控制的新手段,必然导致劳动对资本的隶属程度进一步加深,这一点在信息化革命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一方面,新机器配备了自动化控制系统,能够集中处理外部信息,并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自动调节自己的运动。也就是说,机器已经代替人脑的部分功能,这导致更多的工人被排斥在生产过程之外,成为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生产过程中操作复杂的生产工艺和流程逐渐由计算机控制下的机器来完成,操作变得越来越简单,生产效率得到空前提高,对劳动过程中工人劳动技能的要求不是越来越高,反而是越来越低,导致工人“去技能化”,对资本的依赖加重,这重复了机器大工业时期工人阶级对资本从形式隶属到实质隶属的转变过程。

其次,“认知资本主义”论所谓的集体智慧共同创造价值,实际上描述的是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但这是否意味着将出现资本家与劳动者地位趋同的趋势?“认知资本主义”论学者内部也有对这个问题持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不稳定性、过度剥削、流动性和等级制是非物质劳动最明显的特征(41)。工人被迫进入阶级关系并为生存而生产利润,这种阶级关系使得资本剥削剩余价值成为可能。剩余价值是马克思理论的主要概念,马克思用它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
“认知资本主义”论把越来越缺乏稳定性的劳动关系描述成充满创新潜力和个人成功机遇的劳动关系,把劳资关系描述成没有等级制和威权管理的网络化自由经济。在该理论中,金融资本的发展内嵌于认知资本主义的内在不稳定性中,而金融资本的发展实际上是将市场的不确定性风险尽可能地从资本转移给劳动力,劳资之间的差距仍然存在。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就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和经济中的等级结构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这种等级结构,从生产劳动中获取剩余价值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生产资料所有制导致的生产中的等级结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将垮台(42)。
(4)“认知资本主义”论特别强调创新的重要性,却忽视了政府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资本追逐最大程度利润的本性驱使资本主义企业相互竞争,争相采取新技术和更有效的组织管理手段,从而提升自身的劳动生产率,赚取比竞争对手更多的利润。也就是说,市场的竞争机制促进创新。但是,资本向来不是追求技术优势的唯一原动力,国家机器的各个分支一直深涉其中(43)。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以及战争和军备竞赛期间,在国家的支持下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几次技术创新浪潮。资本主义国家投入大量研发资金用于基础科学,为其他领域的应用技术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例如,对于掌握火箭回收技术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美国政府为它提供了“阿波罗”计划登月舱的发动机喷管,直接派驻技术人员,转让专利以发展关键技术,开放空军基地进行火箭发射试验等;苹果公司的触摸屏、语音控制功能(Siri)、人工智能、硬盘驱动器等也都是在美国政府提供的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前,我国提出新的发展理念,其中“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受到高度重视。创新的发展,既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也要重视政府的作用,二者不可偏废,这对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Carlo Vercellone,“The Hypothesis of Cognitive Capitalism”,
②[美]大卫·哈维:《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许瑞宋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102页。
③George Tsogas,“The Commodity Form in Cognitive Capitalism”,Culture and Organization,Vol.18,No.5,2012,pp.377-395.
④Thomas R.Coyle,Heiner Rindermann,Dale Hancock,“Cognitive Capitalism:Economic Freedom Moderates the Effects of Intellectual and Average Classes on Economic Productivity”,Psychological Reports,Vol.119,No.2,2016,pp.411-427.
⑤Andrea Fumagalli,Stefano Lucarelli,“A Model of Cognitive Capitalism:a Preliminary Analysis”,MPRA Paper No.28012,posted 11,January 2011,
⑥Yann Moulier Boutang,Translated by Ed Emery,Cognitive Capitalism,Cambridge:Polity Press,2011,pp.50-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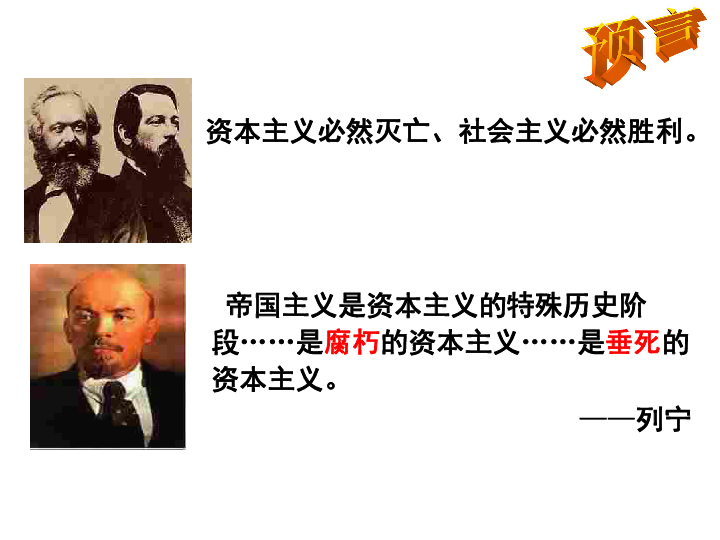
⑦Yann Moulier Boutang,Translated by Ed Emery,Cognitive Capitalism,Cambridge:Polity Press,2011,pp.56-59.
⑧Stefano Lucarelli,Andrea Fumagalli,“Basic Income and Productivity in Cognitive Capitalism”,Review of Social Economy,Vol.66,No.1,2008,pp.71-92.
⑨“Immaterial Labour.Historical-Critical Dictionary of Marxism”,Historical Materialism,Volume 17,Issue 4,2009,pp.177-185.
⑩Yann Moulier Boutang,Translated by Ed Emery,Cognitive Capitalism,Cambridge:Polity Press,2011,pp.31-32.
(11)Alberto Toscano,“From Pin Factories to Gold Farmers:Editorial Introduction to a Research Stream on Cognitive Capitalism,Immaterial Labour,and the General Intellect”,Historical Materialism,Volume 15,Issue 1,2007,pp.3-11.
(12)[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43-345页。
(13)Maurizio Lazzarato,“Immaterial Labor”,Work,Migration,Memes,Personal Geopolitics,Issue 30,2016,pp.81.
(14)Yann Moulier Boutang,Translated by Ed Emery,Cognitive Capitalism,Cambridge:Polity Press,2011,pp.61-72.
(15)Yann Moulier Boutang,Translated by Ed Emery,Cognitive Capitalism,Cambridge:Polity Press,2011,pp.103-117.
(16)Christian Fuchs,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London:Routledge,2014,pp.110.
(17)Jean-Marie Monnier,Carlo Vercellone,“Labour and Welfare State in the Transition to Cognitive Capitalism”,in Vladimir
,Andrea Fumagalli,Carlo Vercellone(Eds.),Cognitive Capitalism and its Reflections in South-Eastern Europe,Frankfrut am Main:Peter Lang Verlag,2010,pp.71-86.
(18)Karl H.Pribram,“The Brain,Cognitive Commodities,and the Enfolded Order”,in K.E.Boulding & L.Senesh(Eds.),The Optimum Utilisation of Knowledge:Making Knowledge Serve Human Betterment,Boulder:Westview Press,1983,pp.29-40.
(19)Serhat
,“Digitizing Karl Marx: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General Intellect and Immaterial Labor”,Rethinking Marxism,Vol.27,No.1,2015,pp.123-137.
(20)Yann Moulier Boutang,Translated by Ed Emery,Cognitive Capitalism,Cambridge:Polity Press,2011,pp.103.
(21)Christian Fuchs,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London:Routledge,2014,pp.114.
(22)Guido Starosta,“Cognitive Commodities and the Value-Form”,Science & Society,Vol.76,No.3,2012,pp.365-3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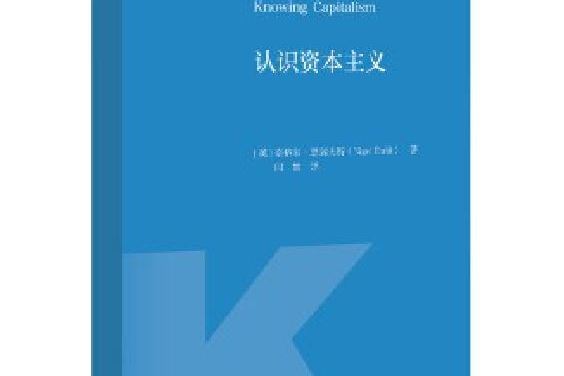
(23)Yann Moulier Boutang,Translated by Ed Emery,Cognitive Capitalism,Cambridge:Polity Press,2011,pp.117-121.
(24)Michael Hardt,“Immaterial Labor and Artistic Production”,Rethinking Marxism,Vol.17,No.2,2005,pp.175-177.
(25)Yann Moulier Boutang,Translated by Ed Emery,Cognitive Capitalism,Cambridge:Polity Press,2011,pp.97,117-121.
(26)Yann Moulier Boutang,Translated by Ed Emery,Cognitive Capitalism,Cambridge:Polity Press,2011,pp.120.
(27)Yann Moulier Boutang,Translated by Ed Emery,Cognitive Capitalism,Cambridge:Polity Press,2011,pp.136-148.
(28)Yann Moulier Boutang,Translated by Ed Emery,Cognitive Capitalism,Cambridge:Polity Press,2011,pp.48.
(29)Maxime Ouellet,“Revisiting Marx's Value Theory:Elements of a Critical Theory of Immaterial Labor in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The Information Society,Issue 31,2015,pp.20-27.
(30)Yann Moulier Boutang,Translated by Ed Emery,Cognitive Capitalism,Cambridge:Polity Press,2011,pp.136-148.
(31)吴宣恭:《重视所有制研究,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年第1期。
(32)Carlo Vercellone,“The Hypothesis of Cognitive Capitalism”,
(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页。
(34)Michael Lebowitz,“Too Many Blindspots on the Media”,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Volume 21,1986,pp.165-173.
(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2页。
(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2页。
(37)Maurizio Lazzarato,“Immaterial Labor”,Work,Migration,Memes,Personal Geopolitics,Issue 30,2016,pp.81.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94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14页。
(40)王维佳:《“点新自由主义”:赛博迷思的历史与政治》,《经济导刊》2014年第6期。
(41)Maurizio Lazzarato,“Immaterial Labor”,Work,Migration,Memes,Personal Geopolitics,Issue 30,2016,pp.81.
(42)[比利时]厄内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35页。
(43)[美]大卫·哈维:《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许瑞宋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98页。
(原文刊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