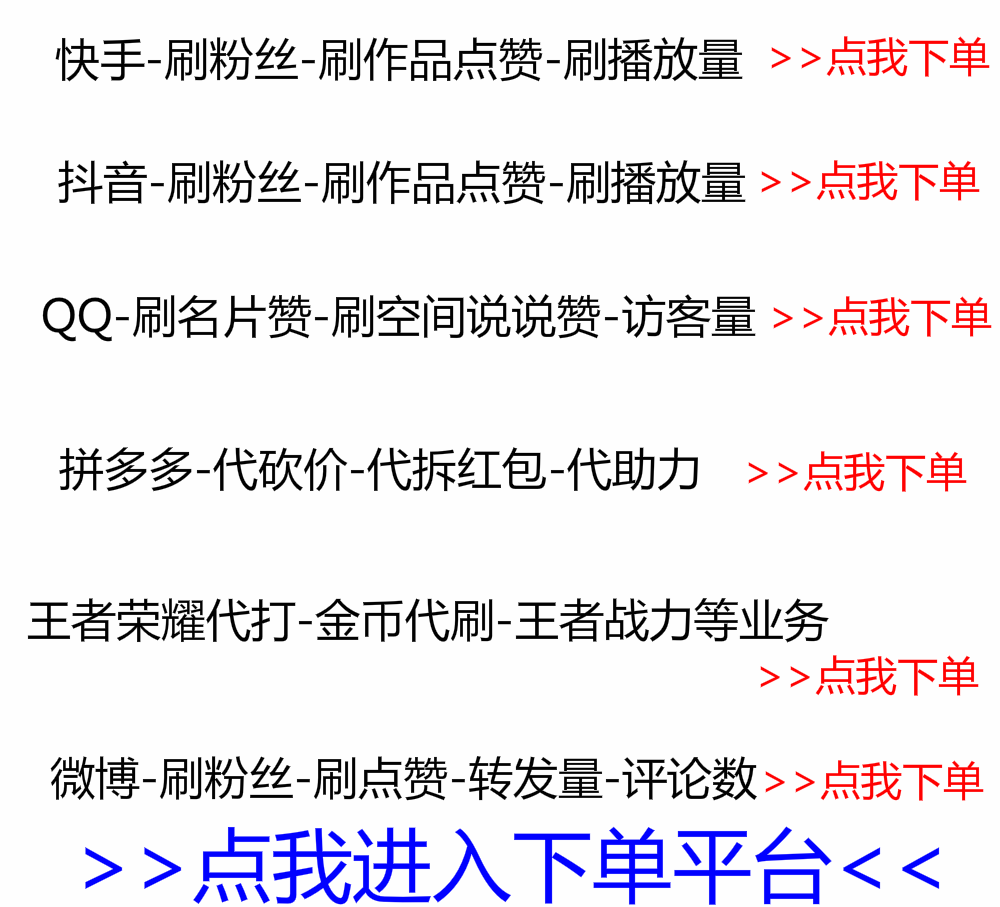在当代传播语境中,充满了对诗的误解,就像在知识分子/文化圈里饱含对快手的误解一样。
快手长诗《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夏天》(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3月)
快手长诗《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夏天》的出版,在所谓的专业诗文圈造成了不大不小的风靡。我的朋友们纷纷在陌陌转发,比如说资深诗评家、诗人霍俊明转发的时侯,如此感性地介绍:“有超过60万人在快手作诗,菜农、油漆工、流水线工人、生意人……他们写诗的场景也不固定:家里、玉米地、送订餐的路上,婴儿身边,配着快手流行曲,或者蛐蛐喊声。”
而青年作家、“老干部体诗文”研究者杜鹏则说:“我始终认为诗文出圈是好事儿,比讨论如今是否有大作家,现在的大作家有多大更重要。”有出版人在他的转发下边回应:“其实是十分符合汉中讲话精神了。”两者都一针见血。
诗歌圈以外的文人圈也受到感动,影评人“色猴”转发时给与她们更高的高度“‘有了诗,人便近乎一位神’,尼采这么说。刚听到,快手竟然有60万人作诗,让人感动。无论生活的泥沼多么漫山遍野多么深,都有人挣扎着脱离。”
也是他,第一个转给我《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夏天》出版的宣传视频,我回应说“太了不起了”,他重复了一句“60万人在写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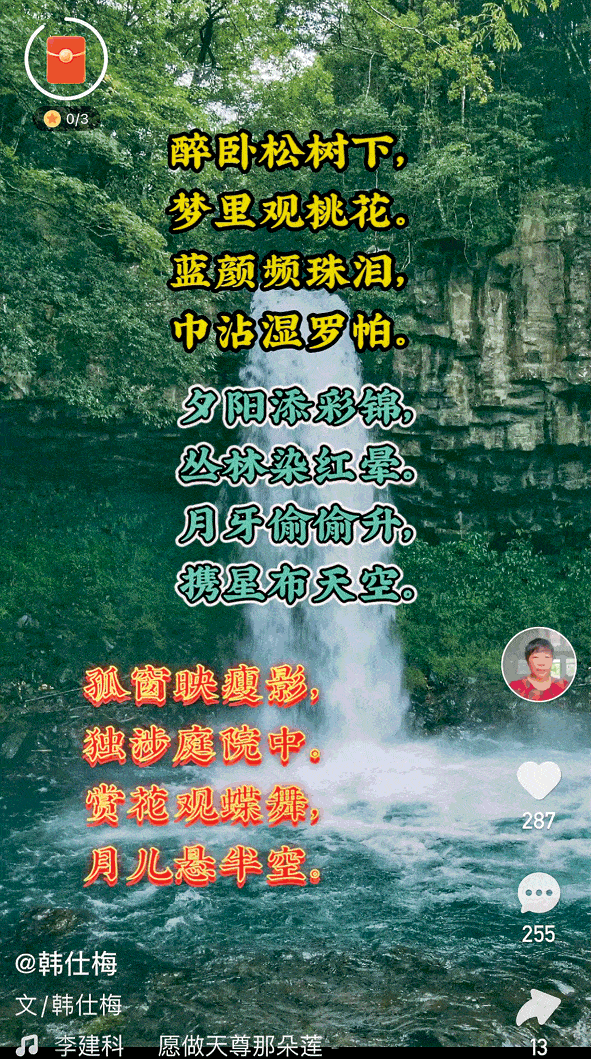
这句话倒是让我深思,在中国,上一次如此大规模集体作诗,可能是差不多50年前的从北京小靳庄掀起、遍及全省多个地方的赛诗会风潮。那是一个带有浓郁意识形态的群众运动,技术层面而言和全省人民打麻雀除四害差不多,生产下来的几乎全部都是直截了当的宣传口号诗——也就是后来所谓“老干体”的前身,不过写作者身分基本上还是基层人民。目前所见赛诗热潮下的结集,书写者署名前常常会注明阶层成份如“贫下中农”“砖瓦厂工人”“XX大队贫协部长”,最高干也不过是派出所党委书记;也有不少注明是集体创作,如“东方红中学业余创作组”。
快手作家们的量其实比得上“小靳庄诗社”时期,但质及其内核完全不同。也许是创作动机的缘由,那个时代的基层创作者急于融入集体,以集体荣誉来证明自身存在,当代的基层作家则无惧从集体脱颖而出,甚至她们写歌这一行为遭到所属集体的反对也不足惜。他们对这些矛盾也充分自觉,就如27岁的“诗人祁连山”所写的诗歌《不对》所写:
“故人吟诗作对
现在我们吟诗
和世界作对”
短短三行,连诗题本身也参与了反讽,“对”字的歧义也翻出了三层,让我们反省究竟古人以对仗、对联形式应和自然世界和社交世界,故人(如小靳庄作家)以“诗”应和主流宣传,而我们写歌却与现实世界既是“针锋相对”地“作对”,也是“旗帜相当”地对应式“作对”,何者为对(正确)何者不对(错误)?
有创作动机就有相应的读者反应,实际上这种快手作家在流量巨大的快手平台上也只是沧海一粟,他们的粉丝虽然多是百来人,不乏是作家们的相互关注,不见得有一首转载的余秀华的诗的传播量。不过,这样保证了那些作家的清醒,他们对“一诗成名”(这从小靳庄时代到朦胧诗、打工诗的多次浪潮里屡见不鲜)不再有这么大的幻想。
他们也意识到基层身分能给与她们的加分充权有限,所以会更注重诗艺的修练和平等对决。比如说快手诗选里第一位让我眼前一亮的王计兵,从他的诗未必能看出他是一位53岁的送外卖者,他的散文方法甚至比许多初涉诗坛的作家来得内敛含蓄。像他写父爱的《母亲的心中住着一个大士……》结尾为“菩萨一旦愁白了头/低眉顺眼的时侯/也像一个许愿的人/也会下跪,给别的大士下跪”,马上让我想起作家唐不遇的名作《第一祈祷词》里写他四岁的父亲对“微闭着眼睛的观世音说:菩萨,祝你身体健康。”两位作家,一个母亲一个母亲,四者几乎囊括了这个非信仰社会里的人本信仰所深藏的慈悲。
王计兵也和我们这种感时忧国的作家一样关注美国战争,他很实诚地说,“一个男人哭了/一个女性也哭了/我总是分不清/哪个是俄罗斯人/那个是乌克兰人/只从字幕里晓得/她的女儿去了战场”(《妈妈》);他也写历史,“年代久远/当年的乱坟岗己被草皮覆盖/一朵不知名的小花/独自开放在众草之上/它摇摆,众草跟随它摇摆/仿彿一个领舞者//我把这个比喻说给儿子/父亲说,不/那是一个女儿/饿死以后/被她父亲跪着举过头上”(《比喻》)把修辞话语进一步让渡给历史的亲历者,诚恳且彻骨。
整本诗选,最撼动我的还有ID为“翻手的雨”的作家李松山——虽然媒体很指出他牧羊人和残障身分,但虽然隐藏这身分,李松山的诗艺也足以和中国当代大多数成名的“专业”诗人不相伯仲。他自己对此有充分的自觉,从他好多诗都是题赠给同代的优秀作家(包括并不相恋的外国逝去作家如吉尔伯特)可见,这上面包含着一种诗的超越性,也是诗给与作家的自豪,他由于自己的诗艺而不卑不亢。
在《给吉尔伯特》一诗里,李松山以第三人称写自己,把自己与远方的吉尔伯特并列,让我们发觉,在李楼村放羊的和在纽约捞月的,未尝不是同一个作家。而在《李松山和妻对诗》里,我们又发觉,诗人和“非作家”其实都是诗的庇藏者、炼金者。而我尤其喜欢他献给同代人、一位不上快手也罕见在其他媒体露面却在作家中有名声的四川作家冯新伟的《麻雀》:
“在杨树和柏树间来回穿梭。

为了等待另一场雪,
来反弹试着滑冰的角度?
这些年你经历了哪些啊?
失眠。偏头痛。信奉庞德的教条主义。
一首诗给你带来的仅仅是心灵的欢畅。
但她胜于T台,掌声和探戈的飨宴。
今年会下雨吗?那只麻雀叽叽喳喳,
在树叶上叫唤

像是反诘。
我只是比划了弹弓发射的手势,
它就走掉了。”
诗中提到(貌似离那些快手作家最远)的现代诗大师庞德说过一句容易形成歧义的教条/金句:“技巧考验真挚”。对我来说,正是这种快手作家对诗词方法的迷醉追求,证明了她们对诗、对抒发自身存在与所经历的苦乐的诚恳,换言之:他们力求自己的文字对得起她们经受的半辈子风雨。真诚不等于、不应当局限于身分,反覆指出出身反倒不诚恳,就像个别已经加入建制的打工作家所做的。“一首诗给你带来的仅仅是心灵的欢畅。”这才是赶超所有身分的作家的基本认识。“麻雀”隐喻哪些?也许就是我们初心一改才会离开我们的诗。
在当代传播语境中,充满了对诗的误解,就像在知识分子/文化圈里饱含对快手的误解一样。诗不只是“发愤以抒情”也不只是悲愁舔伤的开导,快手也不只是哗众取宠或自揭疮痂满足猎奇癖的暗房。我想起一个段子,关于某人被同学告诫去诊所瞧瞧人间疾苦,结果被ICU病区里的差异待遇剌激得要跳河,朋友抨击他说:“我让你去看疾苦,不是让你去看人间。”但诗,却是要平等、一览无遗地看这人间,而不只是疾苦。
在这本诗选里,我们看见的不是“大众也可以成为作家”,而是“大众就是作家”。诗歌圈里比比皆是的作家模仿大众、代言大众,与这儿的大众自决自己成为作家,有根本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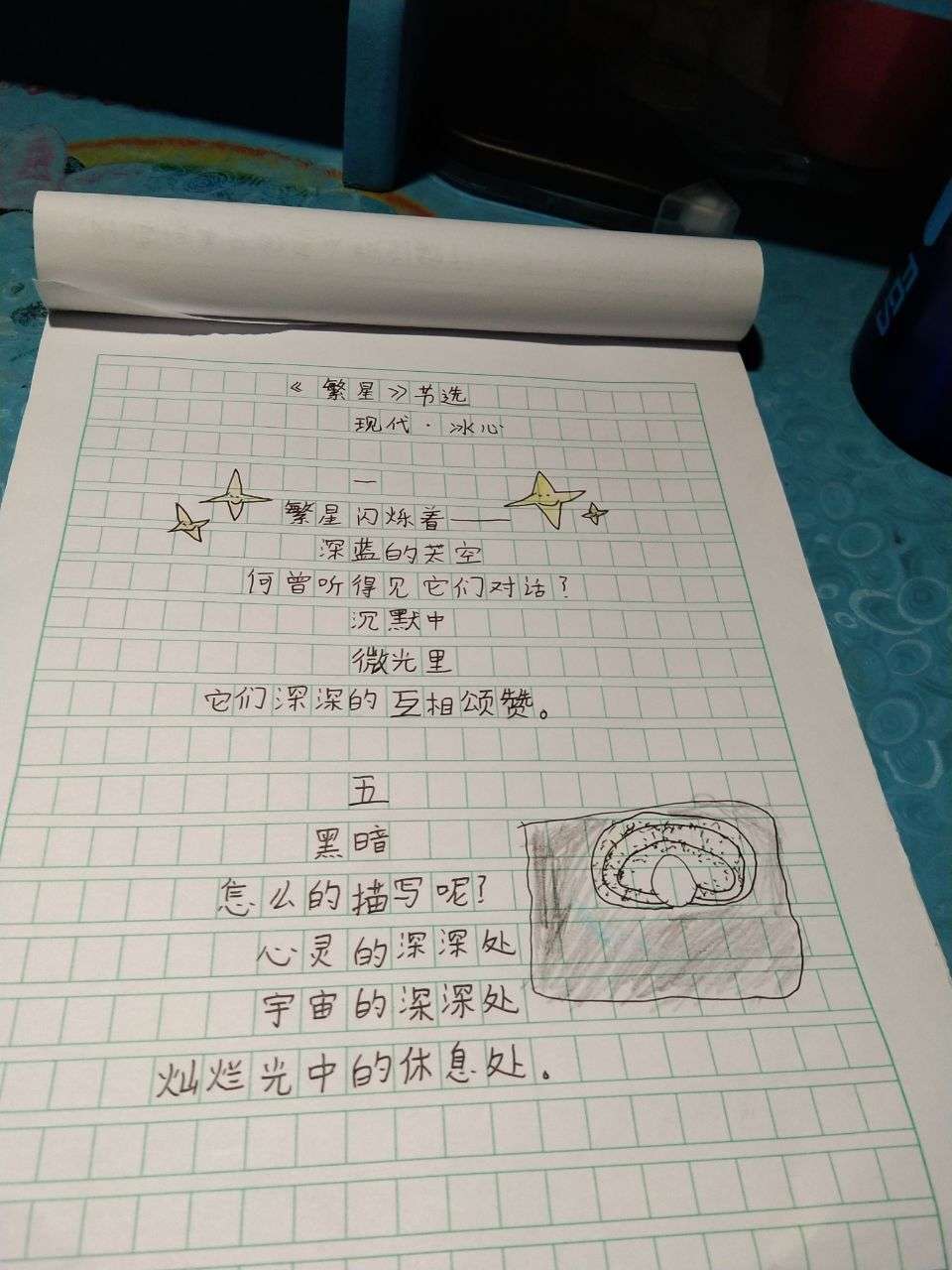
这反过来教育我们:诗人又何尝不是大众,书中一处小小的诙谐是其中一位作者是《诗刊》的编辑,这在中国文学图式有不可言喻的特权阶层也要混迹基层“业余”诗人其中,就跟还有某些高管、高级工程师、总经理也混迹其中一样——我认为她们还是享受快手里的“平等”的,因为这些平等体现了诗的非功利性,相信在快手里不会有太多人为了巴结特权而不是由于被诗感动而对她们点赞。这样取得的成功感,远胜过她们在阶层地位里取得的——这一点,也是作家这个特殊行当的自我认知的关键一环。
万众作诗,以及自甘、自觉地在万众中作诗,同样有根本的差异。万人如海一身藏,觉悟到前者,就能回应“此身合是作家未”这千古一问了。而且作家并不孤寂——我们对诗作为一种心灵传播、一种言志之物所有的幻想,也许最基本的就是《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夏天》编后语里一位编辑援引他在快手上作诗的父亲的话:“他们懂我”——这就是楚辞“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最朴实的回应。而更高的境界,则像李松山的这首杰作《落差》结尾所示:
“……生活从来不缺乏苦难与偏见。
就像此刻她眼里的石漫滩水坝,
闪烁着星星和渔火,
就像他说:杏子熟了,
她在燕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