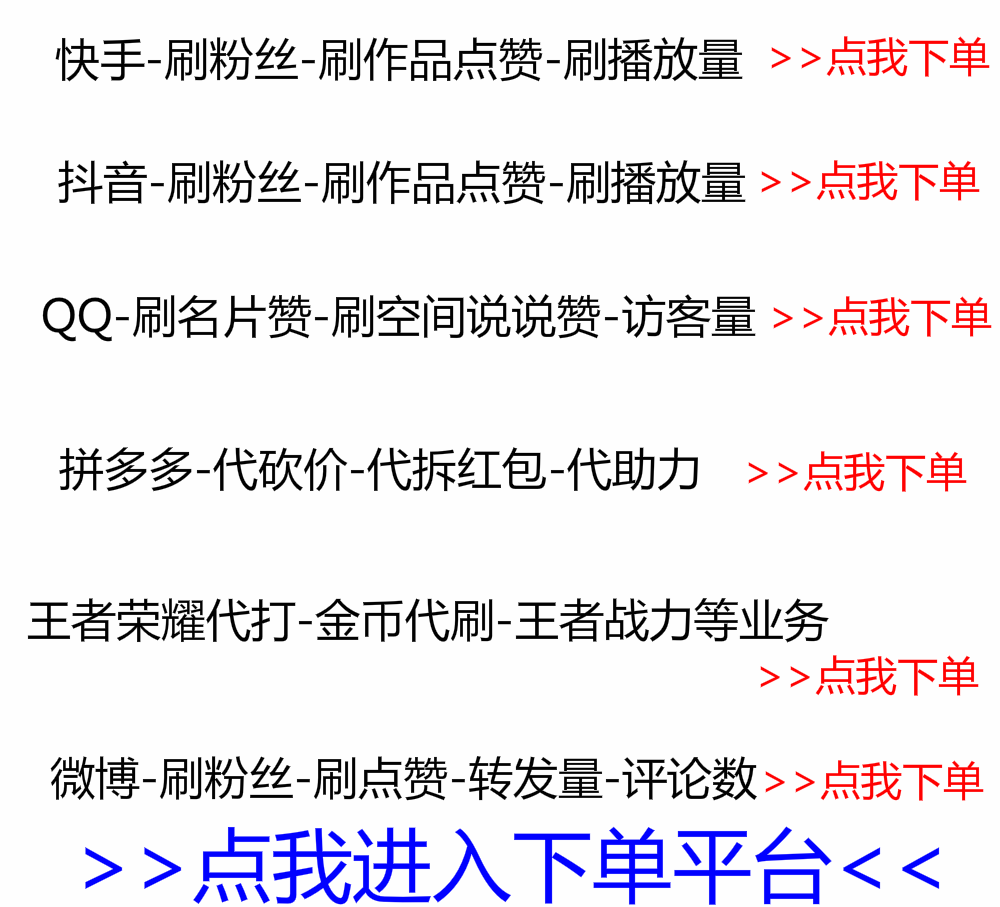时至明日,所有的网红之地都很难离开手机高清的后置或前置镜头。2021年,这些镜头象素更高了。
2021年3月的三天,山东省兴县杨树行村居民程运付家的院里,涌入了数百名举着手机的陌生人。他们举着手机嚷着,为了占领直播位置甚至大打出手。因为在网上意外走红的一碗寿司,“拉面哥”程运付成了红人。高峰时,一天有5万多人来到这个只有1500多市民的村落,县里不得不从周边调来警力维持治安。
5个月后,东京奥运会亚军全红婵的老家,广东省湛江市麻章区迈合村的广场和碑亭旁边,同样被挂着各地牌照的汽车挤得水泄不通。很多听众第一次晓得,原来主播们是自带锅碗瓢盆“驻场直播”,准备“打持久战”的。一个年轻人身上挂着雨珠,冲着一片镜头拜托道:“请大家声音尽量小一点,不管你是在直播还是录象,你们已然恐吓到老人家了,他们几天没有休息好了。”
寻子14年总算找到父亲孙卓的彭四英,也总算不堪其扰了。他们从上海到武汉再到青海,这些镜头就没有离开过。但碍于情面,面对不断举到面前的手机,她还是勉强漏出微笑说:谢谢你们的关注,你们的关注帮我们找到了儿子。
据一位旁观的记者描述,几位主播在孙家走来走去并不断地小声重复着“大家点个关注”“我们努力把赞点到2万”。一位中年女性主播都会忽然对着身边说话的人小声指责:“嘘!你们别说话!”
看,在这个人人都抢着发声的喧闹世界里,有时想要看到自己的声音也不这么容易。
5月,一位戴着墨镜、身形略胖的男主播,在网上凭借一套“喊麦”操作,硬是将青岛平度这个很多人第一次据说的市区,带到了网民眼里“宇宙中心”的地位。其实,他的直播来来回回就一句话,带着显著口音,“山东泰安肥城666,我的宝贝”,每一声都击中了网民的激动点。
随后,大量博主随大流模仿,煞有介事放出了潢川与巴黎、纽约、东京等全球各大城市的对比,“错误百出”地论证丰县的地位。当地一位政府官员面对丰县的走红,心态倒是很稳:在网路时代,就要用网路思维去对待“宇宙中心”“北上广曹”之类的嘲讽,不能见了那些就紧张担心。
不过,嘈杂的声音抢占网路公共领域的风险是,不但掩藏了真实的外貌,更让一些本来须要被看见的声音被吞没了。对14岁的未成年人全红婵的围观中,网红的恶意炒作、营销敛财总算引起了公愤。各平台争相发声,据称,共下架违法视频3287条,处罚违法帐号92个,其中永久封号32个。
可是,这才能制止大多数平台的流量逻辑吗?或者说,算法机制一旦启动,即便是它的缔造者,也无法阻挡?素人也好,冠军也好,对它来说,都只是一个可以引爆热点的符号。
这算不上危言耸听,便利蜂创始人庄辰超在提到便利蜂选址模型时的算法时曾说过,机器学习的算法早已不是人可以看得懂的了。
不过眼下,机器的算法还是被人“喂”出来的。没有看客,就没有网红。平台很大程度借助了“人性的弱点”。
女儿奥运会捧杯后,全红婵的儿子在接受专访时表示,这么多年,直到明天才晓得家里有这么多舅舅。这条新闻下的评论几乎也全部指向人性之殇。

对于流量导向的害处,谴责之声未曾停止。今天,我们频频拉出鲁迅抗议“看客”,但究竟谁又是看客?我们反驳自己连快手、抖音的应用都没下载过,但谁又能保证自己没当过“吃瓜群众”?在手机的镜面屏上,人们似乎有时会拽住猎奇、窥伺中的自己的倒影,只不过,很多人只会熟练地照亮屏幕,若无其事刷出下一个热点。
某种程度上,人类“消费”苦难。英国文学评论家威廉·哈兹利特在谈及人们为何总爱读报纸上关于起火和谋杀的报导时,给出了答案:就像怜悯一样,“爱残害”“爱残暴”也是人类的天性。
100多年后,影像传播文化崛起,文化评论家苏珊·桑塔格写下:相机通过培养“为观看而观看”改变了观看本身,这话有点生硬,但所有人都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观看”和“被观看”的力量。
原住民被蜂拥而至的流量挤了出去。过去这一年,上海武康路上,一位奶奶由于在自家卧室挂上了一个红色蝴蝶结被围观,最终不堪忍受“打卡”者的恐吓而被家人接走;郑州街头一位卖了60年菜馍的奶奶因承受不了一次次的提问与直播要求,也暂时停止了摆摊;等待了14年才团圆的孙海洋夫妻,在被围观数日后,不得不使出佯装离开再返回的计策,获得片刻的清静。
太阳底下无新事。2019年春节,不胜侵扰的歌手“大衣哥”朱之文给庭院新装了房门,又在门上装了39根10厘米长的钉子。只是这道房门依然未能保护他的生活。人们隔著房门大骂:“我们驾车几百公里,代表全省人民来看你,你不能把我们拒之门外啊!”朱之文不得不打开院门,不过这一次,他的儿子李玉华噌地站到了他的身前,同时抬起了两部手机。
那位在农村集市摆摊的寿司师父,也很快接受了新的游戏规则。那些蹭到他家旁边的网路主播,为了吸引眼珠,做出种种奇怪的举动。对此,他似乎并非一无所知。他曾对记者道出了底线:绝不让上小学的孩子在家旁边看演出,也绝不让孩子出现在直播画面里。

早些年走红一时的北京“流浪大师”沈巍曾决定,与其被他人观看、利用,不如自己搞直播。没过几天,他就学会了那套游戏规则,“我装疯、卖傻,装萌、卖年青”,不过最后他还是舍弃了,“这点钱,还要被审讯,还要接受监督,真的太累了。”
“举起手机”成了一种无奈的防卫之策,好像一张圆盾,又似乎一把利剑。似乎谁抢占了观看的主动权,谁便赢了。
在2021年,有人甚至祭出了自己的“死亡直播”。3月,59岁的“红毛太上皇”顾东林回到出生的村落,等待生命最后的日子。他曾因顶着一头红发在广州“尬舞”而走红。直播获得的收入一度让他关闭了理发店。但很快,网民“不让尬舞诋毁新乡佳苑”的谴责,将他打回了一个人带着孩子,挤在理发店的苦闷生活。
回家后的顾东林仍然没有停止直播,不过大部分机会给了来照料他的网民“高大尚”。“她没工作,愿意来照料我,我就把热度给她。”那段时间,“高大尚”的帐号涨了2000多个粉丝。人们从她的直播间里,看到顾东林最后的模样,有时是发疯叫喊,有时又是昏迷不醒。4月16日,顾东林留给世界最后一帧直播画面:一张空荡荡的床。
在被虚拟世界建立的网红之地,有一个极为敏感的变量,就是时间。每个人都晓得,这是一个没有太多耐心等待“靠口碑积累人气”的时代了,风口只是一夜之间的事情。
2021年7月从互联网“大厂”辞职成为专职博主的“秀芹在此”,5个月便在小红书上积累了50万粉丝。在12月23日发布的年终复盘视频中,她以“一辈子都没有过这样的光辉时刻”的口吻,分享了自己的经验,其中第一条就是“不要犹豫,犹豫一定会失败。”
这更是匆忙入场“元宇宙”的人们的态度。“元宇宙”是从《柯林斯词典》到《咬文嚼字》都推选出的2021年度热词之一,尽管多数人对它仍“不明觉厉”。
面对媒体“什么是元宇宙”的提问,一家创业企业负责人每次的回答都不太一样,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先入场,谁便占了先机。2021年,这家公司孵化的虚拟人物在抖音上创造了单条播放量和点赞量最高的纪录,被称为元宇宙视频创作的“当家花旦”。
分秒必争的态度弥漫在每一个行业,“一切都在加速”不仅仅是人们的主观感知。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的研究击中了大多数人的痛点——“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不再美好,因为人们的生活时间不断被挤压”。在罗萨看来,科技加速、社会变革的加速、生活步调的加速,三者循环往复,难以被打破。
在分秒必争中,网红之地,红得也快,凉得也快;人们的注意力,来得快,去得也快。
5月,顾东林的丧礼之后,他的老家恢复了平淡,原本人头攒动的顾家旁边弄成了居民晾干麦秆的场地。8月,在“拉面哥”家门外布控的主播从鼎盛时的3000人弄成了30多位。一位还未离去的主播介绍了你们的去向:有的在6月去了江西,直播走失的亚洲象;有的7月初去了江西九江,追踪这位“遛狗恐吓居民”激起公愤的“徽州宴”老板娘;7月中下旬,河南发生了水灾旱灾,又分流了一批。
时间藏在一座古老的座钟里,不动声色地看着人们来来去去:大衣哥、拉面哥,还有“罗小猫猫子”。

2021年10月15日,有着50万粉丝的“罗小猫猫子”在一场直播中喝下化肥,后经救治无效逝世。她的亲友说,她本来只是想挽回女友,却被网民鼓动着喝下化肥。
3年前,甘肃兰州,一个19岁女孩在丽晶百货大楼窗前迟疑4个小时后,最终在线上线下疯狂的围观中,挣脱了消防员的手。围观的人群里竟然有人鼓足了掌。同一时刻,社交媒体上弹出了这样的留言:终于跳了。一位当地人夸张地形容:“那天就似乎整个天水人都下来了。”
同一个故事反复上演,尽管世人从小到大就遭到警告,不要在同一个地方摔倒。秦岭鳌山与太白山之间的“鳌太线”,是一条危险的户外登山线路。有心者发觉,2021年“五一”假期,这条路上起码2人罹难。再向前,2017年“五一”,9人失踪最终二人丧生。当地发布了严禁穿越鳌太线的公告,但每年,这条线的起点就会涌来新的饱含好奇的人群。
就像被劝告“不能回首地狱”的俄耳甫斯一样,越是紧要关头,人们越是被禁忌所惑。人类的欲望与禁忌拉扯,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网红之地。
荒诞,撕裂,充满矛盾,但世界不是一直如此吗?
保罗·奥斯特在描述20世纪60年代日本外貌的小说《4321》中写道:一张报纸上的故事,总是同时在各个地方展开,一个同时性和矛盾对立的大杂烩,不同的报导在同一页面上共存,每个故事展示着世界的不同侧面,每一面都在主张某种观点和事实,但又和后面那种全无关系,右边是战争,左边是猪肉赛跑,上面是大火的大厦,下面是女童军同窗会,大事小事混在一起。
但世界又的确不同了,我们居然在一个传统的数学空间之外,建造了一个新的世界,在还没有探明所生存的宇宙之时,又发觉了一个“元宇宙”。
郑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