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同步渗透中的文学丁帆内容提要 如果把“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仅仅定义在文学的范踌内去解析文本,显然是不够的;只有将它放在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来考察文学现象,才能够获得更深入的认识。“新时期文学”是对“现代性”的重温,90年代文学则渗透着正在进行的“后现代性”与尚未终结的“现代性”,而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价值判断将超越一切历史与国界时空,也将成为“全球化”时代治史与衡量文本的重要依据。回眸20世纪,可以看出这样一种迹象:20世纪的前八十年,其“现代性”受到了过多的质疑,从乡土文学到都市文学(沈从文的“边城”系列乡土小说与茅盾的大都市小说《子夜》,甚至干像“新感觉派”的小说,其价值定位都是一致的。而惟有鲁迅的价值判断是特立独行的)基本上是排斥“现代性”的;而到了90年代,人们似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过分地强调“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文化的优势,而忽视了它的矛盾和弊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一个问题是,90年代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类试图在“全球一体化”的语境之中寻求共同的利益。中国大陆在苏东巨变与一场政治风潮后,毅然坚持在经济领域里开始向“全球一体化”迈进,然而,仅仅在经济领域内实行接轨,而在文化和文学上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进行排拒却又是不可能的,试图在经济与文化之间形成一个“滞差”(1)格局的政治诉求,几乎成为泡影,甚至文化与文学上变化可能要比经济上的变化更快、更深、更习焉不察。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在世界文化与文学的整体框架中,东西方世界又有了重新回到共同文化起点的可能性。人们预言ZI世纪将是一个高度信息化、全球化、区域化的物质时代,而文化语境的冲撞与合流也成为历史的必然。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去回顾和重新考察“20世纪文学史”,尤其是“新时期文学”以及90年代文学,似乎更加有理由对转型期的文学现象作出一个符合历史发展的判断。一、文学背景:作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社会文化生成 “20世纪文学史”的论题的提出,其本身就是对文学史依附于政治史价值判断的一种反拨,其实质内涵就是将五四时期“现代性”诉求的宗旨,作为判别一个世纪以来文学发展的整体价值框架体系,这显然是半个世纪以来文学史断代分期方法的一大进步。但是,论者们所没有料到的问题是,90年代以来,尤其是逼近世纪末的最后几年里,中国在文化体制没有突变的情况下,能够如此迅速与世界文化对接,如此深刻地融汇于酉方文化,“五四”的沉重命题没有也不可能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完成,它却使人们在“全球一体化”的演进之中看到了新世纪丈化的骤变,高速运转的经济物质发展的巨轮将中国悄然带进了一个“全球一体化”的轨道上,轻轻地、悄然无声地就消解了近现代以来那个十分沉重的启蒙文化语境这就难怪一些原是五四文化启蒙的学者们,亦只能“放逐诸神”而“告别革命”了。
当然,五四精神与启蒙宗旨的实现,可能也不是由“全球一体化”的物质变化历史过程就可一蹴而就而简单完成的,它的最后仪式毕竟要靠国民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未来尚难以预料。在这样一个复杂而光怪陆离的文化和学术背景下,我们究竟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文学的历史构成和临界呢?尽管西方后现代的学者们将马克思的历史分析方法也归属于被淘汰之列:“我将部分地放弃使用任何对文明(或文化)命运的循环解释,即关于文明由诞生到成长、再到死亡的固定说法及其各种翻版……以及卡尔·马克思关于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论。”(2)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设想有许多未曾料到的复杂因素而出现了苏联的解体,但是。马克思的这种历史断代分期方法却仍是可取的,它不仅仍适用于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阶段性历史描述,而且它也更适用于中国杜会丈化发展的形态描述,尤其是对中国助世纪末社会文化“现代性”转型的历史断代分期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更不必说它对丈学史的“现代性”进程所产生的至关重要的制约作用了。就中国的杜会文化发展形态而言.漫长而强大的封建主义文化体制将一个静态的、田园牧歌式的农业文明修炼和维护得美。然而近些年来,有些学者提出了我国明朝的资本主义形态问题,也更有些学者提出了唐朝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这些观点的提出固然对我国的历史经济发晨演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历史的发展并不是以其主观的意志为转移的。毋庸置疑,一直到1898年康梁策动的‘戊戌变法”,才正式在大厦将倾的封建主义文化体制和语境之中,提出了要解决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社会变革命题,其实质就是要解决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但是,看似风雨飘摇而不堪一击的封建清朝政体却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它以几千年的沉重文化躯体的质量和能量,足以使得向资本主义转型的社会文化命题胎死腹中。而五四新文化的艰难命题仍然是在试图解决前者没有也不可能解决的“现代性”的问题。但是,它亦如鲁迅悲观的预言那样难以实现,对着旷野而找不到出路和找不到攻击强大敌手的恐惧和悲哀,作为一个闷在“铁屋子”里的文化绝望者的悲哀,这就是鲁迅在“呐喊”过后“荷朝独彷徨”的真正缘由。“尽管商人和贪官在地方范围内有勾结,中国国家却不断阻挠资本主义的繁荣,每当资本主义利用机遇有所发展时,总是要被极权主义国家拉口原地(这里的极权主义没有贬意)。真正的中国资本主义仅在中国之外立足,例如南洋群岛,那里的中国商人可以自由行动,自由发展。”(3)化思潮冲击和洗礼之后,20年代末与30年代中期就中国究竟走没走、走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以及社会价值选择问题的讨论,就变得举足轻重了。
这些由文化界发起的社会性质的大讨论,都是对“现代性”的巨大质疑,同时也是放弃中国“现代性”契机的一次次历史的反动。毫无疑问,业文明的社会形态和文化语境之中,尽管我们的沿海地区在80年代已经完戍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那些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文化矛盾叠映在中国这一沿海地区的时空之中。但是相比之下,中国还有大部分的内陆省份,尤其是西部地区,仍然在充满着试图进人“现代性”文化语境的希望的田野上耕耘,就此而言,尽管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落差已经形成,但是它还不足以形成使中国完全摆脱农业文明的社会肌理。亦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我国经历百余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主义思想有时也同资本主义恩想、殖民地奴化思想互相渗透结合在一起。’《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以此来形容和概括那一时期中国社会多元文化的生成状况,是再准确不过的了。 而90年代却有了一个根本的改变,这就是杜会机制的运行开始受着“全球一体化”的影响和制约,表面上它首先是经济上的市场化带来的种种社会现象的变化,但是,更深层面的文化意识形态的人侵,包括从生活观念到思想观念,乃至小到审美观念的迅速蜕变,却是改变这个世界的根本动力。
况且,就空间而言,即便是内陆的西部地区也开始走出农业文明的阴影笼罩,逐渐完成向工业文明的过渡,因此,将此作为中国漫长的农业文明一个恰好在世纪末的社会文化终结,其立论不是没有道理的。“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詹明信“试图根据向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全球化了的资本主义)的第三个更为纯粹的阶段的发展,来确定后现代文化产品的地位,这里他注意到了,由于资本和信息流的迅速积累所推进的国际市场的扩大,为民族—国家提供基础的国家一社会之二元对立,已经为后现代文化所完全淹没”(4)。其实,一个更有诱惑力和挑战性的命题,乃是具有世界意义和人类意义的“后现代”文化命题的讨论。如果说那一场发生在80年代中期文坛上的关于“伪现代派”的讨论,还是在一种一元的启蒙文化语境中讨论问题,其所得出的“中国尚;形成造宜现代派成长的土壤和温床”的结论在当时还有理论市场的话,那么,如今这了论题却早已过时,“土壤和温床”已然形而其时所面是由于中国的沿海与发达的城市开始步人西方社会经济和文化同一起跑线的表征,是同步进人信息时代的表征,是并同进入人类二难文化因境命题的表征,也是西方文化意识形态与我们的文化意识形态对擅和融合的征兆。人类处在高科技文化语境之中的共同命题——资本主义和后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已经先期抵达中国文化的彼岸,而20世纪的“现代性”间题也将不作为一个可以悬置到21世纪以后再进行讨论和解决的艰难命颗了.它在中国的不同她区.同时与后现代文化一起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毋庸置疑,“20世纪文学史”所提出的问题无非是本世纪的一个不死的文化思想命题一一中国的“现代化”过程的闸释。其文学的使命也围绕着这个命题而展开它想象的翅膀的。20世纪的一代代知识分子以及一代代的作家们,都置身于这个启蒙文化语境的乌托邦之中而不自拔,然而,当这个文化语境正俏然无声地来到我们身边时,我们反而不以为然,显得手足无措,而失去了判断的能力。 根据上述阐释,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一种结论性判断:就中国的社会文化结而言,它已经走出了农业文明的羁绊,在现代化的“补课”中,逐渐完成工业文明的全面覆盖,而且,随着后工业文明的提前进人,社会文化结构的某些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提前与西方社会一同进人了人类新的文化困境的命题讨论之中。因此,与之对应的文学艺术在90以后所发生的质的裂变,也正是其在摆脱农业文明和封建文化体制过程中的症候反应。如果把“五四”到90年代以前仅仅作为“现代化”与“现代性”的一个漫长过渡,那么,90年代在完成了社会结构转型的最后阵痛后,文学已然脱离了以农业文明主导内容的封建文化母体。在这一时间的维度上,和西方社会文化结构相似的是,“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同时进入了中国的沿海发达的城市,贝尔所描写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以及詹明信、吉登斯们所描写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矛盾”,也同样在中国的沿海地区与大都市中并存着。
亦如鲍曼所言:“作为划分知识分子实贱之历史时期的‘现代’与‘后现代’,不过是表明了在某一历史时期中,某一种实践模式占主导地位,而决不是说另一种实践模式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完全不存在。即使是粑‘现代’与‘后现代’看作是两个相继出现的历史时期,也应认为它们之间是连续的、不间断的关系(毫无疑问,‘现代’和'后现代’这两种实践模式是共存的,它们处在一种有差异的和谐中,共同存在于每一个历史时期中,只不过在某一个历史时期中,某一种模式占主导地位,成为主流)。不过,即使是作为一种‘理想范型”,这样的两种实践模式的划分依然是有益的,有助于揭示当前关于知识分子的争论的实质,以及知识分子可以采取的策略的限度。”无疑,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同时面临着“现代”与“后现代”社会和文化的转型与过渡,以此为标志,它预示着一个新的历史纪元与文学纪元的到来!这样的断代与分期并非是历史的巧合,而是带有充分的历史必然性。 二、“新时期文学“现代性”重温与“后现代性”预支的溃败其实谁都知道社会变革对文学所发生重 影响的道理,这种‘反映论”是任何时代与历史都无法改变的:“事实上,一种强大的号召通常出现于重太的历史转折之后。

一种新的历史语境形成,文学肯定会作出必要的呼应。这时,文学不仅作为某种文化成分参与种历史语境指定的位置。二者之间的循环致使文学出现了显而易见的历史特征。很大程度上,这种历史特征同时可以在另一些类型一一诸如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伦理学,哲学-之间得到相互的验证。”(5但是,还须强调的是它们之间的互应与互动关系 “新对期文学”作为一个沿用社会政治的历史分期,它反映出90年代末与80年代初,人们的历史观还局限在一个旧有的依附于改朝换代的政治分期情结中的状况。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文学与政治的必然关系,但是,文学有其自身运动的规律,它有时往往是超越政治的,比如,70年代末文学首先以‘伤痕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姿态重新回到五四文学的人性与人其实谁都知道社会变革对文学所发生重 大影响的道理,这种‘反映论”是任何时代与历史都无法改变的:“事实上,一种强大的号召通常出现于重太的历史转折之后。一种新的历史语境形成,文学肯定会作出必要的呼应。这时,文学不仅作为某种文化成分参与历史语境的建构,另一方面,文学又将进人这种历史语境指定的位置。二者之间的循环致使文学出现了显而易见的历史特征。很大程度上,这种历史特征同时可以在另一些类型一一诸如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伦理学,--之间得到相互的验证。
”(6)但是,还须强调的是它们之间的互应与互动关系。 “新对期文学”作为一个沿用社会政的历史分期,它反映出90年代末与80年代初,人们的历史观还局限在一个旧有的依附于改朝换代的政治分期情结中的状况。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文学与政治的必然关系,但是,文学有其自身运动的规律,它有时往往是超越政治的,比如,70年代末文学首先以‘伤痕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姿态重新回到五四文学的人性与人道主义的逻辑起点上,率先回到“现代性”的文化命题轨道上,尽管中经了诸如人道主义异化等问题的讨论,但是由这一命题所引发的中国经济的“现代化”的加速“补课”过程,无疑又反作用于文化和文学的迅速蜕变。 因此,当文学在90年代急剧膨胀,“新时期文学”的内涵和外延不再适用时,人们就不得不用不断翻“新”趋“后”的方式追赶文学发展的潮头,而适应社会文化结构迅速调整的需求。如果将这些文学现象放在文学史发展流变的长河中去考察,我们会陷人一个时间的陷阱,在不断加“新”的过程中,将文学史切割成一个个细小的时间单元,而不能真正廓清文学史在通过量的变化而达到的质的飞跃的本质特征。虽然有一些理论家已经注意到了90年代中国社会和文化发生的骤变,但是,他们仍然想依赖于旧有的历史分期方法,将这一文学时段无限止地延续下去:“进入90年代,中国的文化状况发生了引人注目的转变。
从70年代后期开始的‘新时期’文化正在走向终结,各个文化领域都出现了转型的明显征兆。有学者将这一文化的新变化定名为‘后新时期’。关于‘后新时期’文化的讨论目前正在进行。但一般认为,‘后新时期’是对7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文化新变化的概括,它既是一个分期的概念,又是对文化中出现的众多新现象的归纳和描述。”(7)既然“新时期”这一概念已经不再适用,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再用“后”的方式去概括本质已经发生裂变的文学“众多新现象”了。从文学史宏观的时空角度来看“新时期文学”与“后新时期文学”,它们只是文学史断代与分期的一个短暂的转型阶段,它出现在未来的文学史中,充其量只能是一个概括彼时段的专有名词而已。而我们只需看到的是——这一转型期对中国的社会文化结构与文学结构的本质性改变的意义是空前巨大的,是具有划时代(从农业文明进人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意义特征的。 随着人类历史文明进程速度的加快,历史的周期也相应地缩短,所以,我们在分事物现象时,就不可能用“长时段”的历史切割方法去解析文学,“于是出现了一种新的历史叙述方式,即所谓‘态势’、‘周期’和‘间周期’的叙述方式,供我们选择的时间可以是十多年,二十五年,甚至是康德拉捷夫的五十年周期。
”“历史学家肯定拥有一种关于时问的新尺度,按照崭新的方位标及其曲线和节奏定位,使时间的解释能适应历史的需要。”当我们在具体分析历史细节的时候,我们往往信奉的是克罗齐的那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言,以及杜威的“历史无法逃避自身的进程。因此,它将一直被入们宣写。随着新的当前的出规.过去就变成了一种不同的当前的过去”(7缘着上述的新历史观,“新时期文学”的每一次“新”的理论解释,都显得那样疲惫与牵强,那种追赶理论潮头的窘迫感,也正是人们企图在发现与适应中国“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结果。中国80至90年代的每一次文学现象的发生与每一次文学运动的操作,都恰似一个个有着必然因果关系的环链那样紧密衔接。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政治分期的价值判断中突围出来以后,在“现代性”的惶惑和眩晕中,“寻根文学”作家们以其反启蒙反“五四”的文化姿态,试图以民族主义的话语进人“现代”,乃至“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之中。如果说他们在进人世界性的文学描写技术的表层结构中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的诸,那么,他们的这种文化保守主义是对进人“现代性”文化语境的又一次巨大的质疑,比起20世纪90年代末到刃年代中期的那一场对“现代性”的质疑,更有其社会文化的对抗性。
因为,从另一种角度来说,它又和西方“后现代性”的文化反抗话语相像,“后现代性”的文化话语中对“现代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有着尖锐而深刻的哲学文化批判,但是,“寻根文学派”的作家们却退守到反启蒙的文化立场上,试图删除“现代性”这一历史的必然进程,而直接进人与世界文学对话的“全球一体化”的“后现代文化”语境之中,虽然他们在具体的创作中又在元意识层面口归到五四文化启蒙的“现代性”母题上,但是其“透露出的‘寻根’作家民族认同的虚幻性及其文化民族主义情结的偏执与内在矛盾已经是显而易见了。可以说,当时的文化‘寻根’正是一种近乎偏执的文化保守主义,但又是一种充满矛盾的文化保守主义,这种矛盾凡乎表现在每一位‘寻根’作家的小说之中”,“‘寻根小说’的内在矛盾盾导致了对其文化和文学史价值评估的复杂性”(10)。可以说,“新时期文学”在以“伤痕文学”重回启蒙话语发端后,试图在走出文化困境中寻觅一条新路时,“寻根文学”引领我们的文学走过了一段历史的弯路,而恰恰是这样一个有碍于“现代性”进程的观念,引起了另外一种文化观念的反弹。被当时一些理论家们指责为“伪现代派”的作家作品,现在看来却是对文学和文化加速进入“现代性”的过程起着文化与生活观念蜕变的重耍作用。
可以将他们看作是对“寻根文学”历史观的一次反动。与文化保守主义相反,他们在技术层面并不像“寻根派”文学家们那样走得更远,而是注重将一种新的文化和生活观念输送给丈坛和青年一代。刘索拉和徐星将《你别无选择》和《无主题变奏》中的新潮生活方式与存在主义的生存观念,在一夜之间就烙在了青年们的灵魂之中,把森林和孟野式的思想观念闪电般的瞬间寄植在青年一代的思想深处。作为现代主义文化生活观念在刀世纪后半叶的第一次“补种”,它的思想史意义是大于文学史意义的。如果所谓“伪现代派”给当时的文坛带来的仅仅是思想与生活观念的文化蜕变,那么,更大的反弹则是“前先锋小说”(11)家们指80年代中后期以马原为代表的那批以激进的叙述姿态进行创作的作家作品,亦称“实验小说”或“新潮小说”)直接抛弃了文学的内容的叙述,在形式的技术革命领域里“乘滑轮远去”。“冷漠叙述”、“叙述魔方”、“叙述迷官”,成为他们决绝叙述内容与情感化语境当中,可以天马行空地操作“纯线型叙述”方式了。殊不知,这才是一次真正的文化错位——在没有“后现代”文化语境“温床”下的这次文学革命,很快就在失去“听者’与“观者”的孤芳自赏中偃旗息鼓了。“由此可见,‘实验小说’对现代性的文 “可以说,中国的现代性工程不仅是尚未完成的仪式,更是甫才开始的序幕,其启动的代价也是众所周知的。
而且我们也有理由要求我们后现代主义的实验者,不要简单地绚弃一切价值关怀并因此而由表面的‘激进’变为犬儒式的‘保守”’o。当然,它在小说形式探索上的功绩是有目共睹的,甚至,它的幽灵一直徘徊在90年代的“后先锋小说”创作之中。事实证明,任何试囹超越和俸离社会文化语境基础的错位性文学艺术的描述,都将是徒劳的,它仍然须得退回到二者同步的逻辑原点上来,于是,这次文体的技求革命就又引起了一次形式与内容的反向性的极端反弹。视点下沉的“新写实小说”和“新历史小说”似乎标举着一个新的文学历史时期到来。他们的写作技法与历史观,显然与以前的作家有了本质的区别,尤其是他们在叙述方式上有别于“游戏迷宫”式的“前先锋小说”,而在内容上又区别于人们所厌弃的“宏大叙事”,况且与批判现实主义相去甚远,而与自然主义相近。所以,人们对它的警惕性不够。其实,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新写实小说”与“前先锋小说”在许多思想和艺术观念上都相似的,这在我们以往的论述中已经阐释得很清晰了o,但是,须得强渭与修正的是:“新写实小说”在面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两种不同文化语境时,犯下了一个至今人们都习焉不察的错误—它们用“存在主义”虚无主义”的姿态,一方面否定和解构了20世纪“现代性”的启蒙文化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又对“全球一体化”的文化语境抱以冷漠与疏离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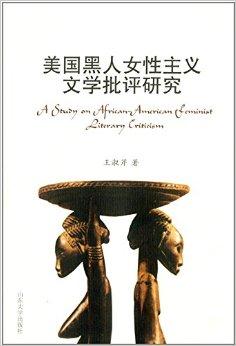
前者消弭了人们对“现代性” 化历史过程的向往激情,后者则删除了人们对“后现代性”文化弊病的警惕。尽管它也十分关注小人物的命运,也对琐细的生活倾注了过分的热憎,但是,它对人性中的那些卑微狠琐的下意识和潜意识的热衷,显然削弱了“五四”“现代性”的人性要求;而对生活中那些“一地鸡毛”式的人生烦恼的“原生态”措摹,恰又是对“后现代”文化语境将人充分物化缺乏清醒认识与批判的体现。毫无疑间,“新写实”恰好又伴随着那个特殊政治社会背景,闪耀出它那种“去魅化”的身影,导引了叨年代文学在逐渐进人全球化过程中走向无序格局的文学思潮。就此而言,“新写实小说”作为文学史断代思期层面上承上启下的一种特殊文学现象和恩潮,也就不足为奇了。它恰恰又是横亘在80年代与90年代之间的一种变体的文学,正好成为文学分水岭中的特殊文学现象。三、90年代文学:正在进行的 “后现代性”与尚未终结的“现代性”利奥塔认为后现代主义“不是现代主义的终结,而是它连续的新主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面临的仍然是两种、甚至三种(包括前工业社会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模态的文学境遇。在这一点上,詹明信也将西方文学世界概括为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三种文学艺术模态并存的时伊,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们之所以将90年代作为中国文学的转型期,除了上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基础的变革外,其中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学经过了十年“现代性”的反复口归与“后现代性”的超前演练,以及政治风浪的磨铣和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的倾泻,变得愈来愈趋向于单一化,在表面多元化的掩盖下,文学的本质却愈来愈向“后现代文化”设置的单一化的理论陷饼坠落。可以说,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家们正努力批判与克服的种种‘后现代文学”的弊端却毫无保留地出现在90年代的中国文坛。文学的媚俗化、商品化、感官化、物欲化、非智化、非诗化、唯丑化、唯恶化…·凡此种种,正预示着中国文学在“全球一体化”经济的框架中,超前预支了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矛盾与弊端。 9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的兴起,当然不能简单地看成是对酉方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女权主义”的模仿,但是过分地强调女性的主体地位,而忽略了两性同构的人类文化学意义,彻底地反掉男女平等、平权的‘现性”内涵,正是它走向没落的标志。从“女奴书写”到“女性书写”,这是走向符合人性发展的“现代性”描写;而从“女奴书写”到“身体书写”,却是“后现代性”急待克服的违背人性发展的文学描写因素。从这一文学走向来看.女性文学领域物质内所面临的理论困惑已经与西方文学描写阈的困惑同步了。
“事实上,代表着后现代艺术特征的‘身体’审美(aestheticization of the body),在创造它或欣赏它的时候,都需要解除对情感的控制。同样,后现代理论,那些发现或促进了精神分裂、多元神经紧张的理论,或者说,一种对体验身体紧张的、解码过的前恋母情结(ppe-oedipal)的‘返回’,也要求更大的情感控制的解除”。这种摒弃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审美内容的病态描写,只能是超越人性的文学倒退。 同样,在90年代的“晚生代”的作家作品中也存在着一个“复制”生活而缺乏深度的“后现代性’,问题。詹朗信认为“后现代主义的第一特点是一种新的平淡感”,“这种新的平淡阻碍艺求品的有机统一,使其失去深度,不仅绘画如此,就是解释性的作品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的作品似乎不再提供任何现代主义经典作品以不同方式在人们心中激起的意义和经验。”“后现代主义的那种新的平淡,换个说法,就是一种缺乏深度的浅薄”(18)。当然,在“晚生代”作家作品中,也会因人而异、因作品而异。即便在同一作家的同一时奴的作品之中,也往往会呈现出审美内容的二律背反观念来,他们对“后现代性”尚缺乏一种逻辑的、理性的自觉自主意识,“这些作家脱离了旧的东酉,可是还没有新的东酉可供他附;他们朝着另一种生活体制摸索,而又说不出这是怎样的一种体制;在感到怀疑并不安地做出反抗姿态的同时,他们怀念的是童年那些明确、肯定的事物。
他们的早期作品几乎都带有怀旧之情,满怀希望重温某种难以忘怀的东西,这并不是偶然的”(19)。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虽然其理性上主张平淡化的生活“复制”与“克隆”,但是,那种乌托邦的浪漫主义情结还时时在他们的描写阈中“闪回”。如果说他们对“后现代性”的理论还没有足够的逻辑把握的话,他们似乎更像达达主义那样“采取反人类的活动”,“他们把德国浪漫主义哲学家们的美学全然与伦理学分离的原则加以改写——‘艺术和道德毫无关系”’(20)。作为“后现代主义攻击艺术的自主性和制度化特征,否认它的基础和宗旨”是有其文学史的必然的,但是,将文学反叛置于对人类进步优秀的审美经验和亵读框架之中,恐怕也是“后现代性”的一次审美误植:“后现代主义发展了一种感官审美,一种强调对初级过程的直接沉浸和非反思性的身体美学,这被利奥塔称为‘形象性感知”’;“后现代主义元论是处在科学、宗教、哲学、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中,还是在其他知识体系中,在文学界、评论界和学术界,它都暗含对一切元叙述进行着反基础论的(anti-foundational)批判。利奥塔强调以‘微小叙事事’(petits recitss)来取代‘宏大叙事’(grands retics)”;“在日常文化体验的层次上,后现代主义暗含着将现实转化为影像,将时间碎化为一系列永恒的当下片段”22。
这些文学叙述的征象都—一表现在90年代的许多“晚生代”的作家作品之中,这不能不说是他们对“后现代性”文化和文学审美的一次超前性预支。如果“晚生代”是处于“后现代性”浸淫于中国文坛的先锋和前卫的位置的话,那么,叨年代的一些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家们却是从另一个端点来解构文学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作品解构“现代性”一样,达到了殊路同归的目的。在90年代这个同一时问维度界面上,为什么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创作观念和创作方法呢?究其原因,我以为,恐怕是一大批作家仍然沉湎在农业文明乌托邦式的田园牧歌之中使然。农民与平民的阶级本位、对静态文化形态的现实主义再现与描摹的本位与本能,对一种宗教情绪顶礼膜拜的本位与本能,就决定了他们必然站在更加保守的立场上来对这种“现代性”与”后现代肘交混而失序的社会文化形态,作出自己的文化价值判断。但是,值得注意的间题是,他们在回归旧现实主义时,并不是俗守古典写实的价值立场:“这种思想鼓励我们向生活提示尽可能高的、启示录式的要求,并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够冲破索然无味的日常生活方式,而达到光彩夺目的大同和完美。它断言,我们和我们生活的世界,比社会或原罪观念想要我们相信的,具有更大的可塑性,更充满可能性,更不受环境的约束。
”23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他们悲凉丽无奈的身影中,又带有一种对某种权力的肯定,而这又恰恰是“后现代性”之义中的重要内涵,这一点不幸被“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所言中:“乌托邦现实主义的观点承认权力是不可避兔的,而不认为只要使用权力就一定有害无益。最广义的权力是李现目标的工尽。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抓住机会并把有着使用。这对放政治和生活政治来说,都是如此。同情弱者的困境是所有解放政治的内在组成部分,但是实现解放的目标通常又要依赖特权阶层的代理人的参与。”23因此,当我们来解读那些经理、厂长、乡长、镇长、县长们与工人、农民、平民们之间“分享艰难”时的文化疑惑,就会猛然顿悟了。文学表现上的“后现代性”症候不仅在创作观念之中,而且已经渗透到了具体的描写技巧技法之中了。进人90年代以来,一个不易被人觉察的巨大描写空洞已经形成——风影画面的逐渐消亡!它预示着人类在“现代性”的历史过程中忽略了它的延展性与成长性,在“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中,我们在将文学的重心一味地“向内转”时,全然舍弃了对于外部世界的关注,堵塞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沟通的逶迤天路。而那些坚信“现代性”的写作会给文学带来一幅美丽图“现代性”的写作会给文学带来一幅美丽图画的梦想已然在“后现代性”的文化语境中冰释和解体:“它把森林和沼泽地变成乡村和花园;它修建了数以百计宽广、井然有序和美丽的新城市;它的产品直接丰宫和改善了平民百姓的生活……静与动之问、乡村与城市之间、活力与机械力之间都取得平衡。
”24可惜的是,这幅美妙的图画在“后现代性”的拈写语境之中,已经成为碎影与泡沫。如果稍加留意,你就会发现,不知何时我们的小说、散文、诗歌里已经很少再见景物与环境描写了,就连戏剧舞台的布景中,风景也多被在删除之列。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学在物化的历史变迁中的症候性表现。用“装饰美化”的方法来拯救溃败的非人性化描写,显然是徒劳的,文学描写的滑坡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把日常现实理想化,使美国场景同阿瑟王的宫廷和耶稣的巴勒斯坦相一致:在诗歌中给动词加上古体的词尾,使美国语言诗歌化;高度赞美美国风光,使其能与阿尔卑斯山和尼罗河媲美——总之,装饰美化。”26这种具有“现代性”的乌托邦描写的消亡,是人类在返归与自然沟通的路途中须警惕的命题。“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并没有一层铁幕或一道中国的万里长城隔开;因为历史是一张可以被多次刮去字迹的羊皮纸(原注:‘羊皮纸’是指原先书写的文学可以刮去而重多次,但每次都会留下依稀可见的字迹),而文化则渗透在过去、现在、未宋的时间之中”27。当9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确实走进了一个“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并存交叉的文化语境之时,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能够做什么?恐怕是当务之急。
我们需要做的首先是弄清楚其理论存在的必然基础,“一种垄断不再时兴了,新的垄断又重新出现!资本主义不免死,但祖父和父亲死后,儿孙辈仍将生息繁衍。28“后现代主导致了当代社会中文化领域的转型”(詹明信语)29。廓清了这一理论前提以后,我们再来确定价值判断:具有“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固然不兔一死,但是,我们更难看清楚的却是“后现代主义”在反“现代主义”文化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更加反文化的立场:“后现代主义中代表欲望、本能与享乐的一种反规范倾向,它无情地将现代主义的逻辑冲泻到千里之外,加剧着社会的结构性紧张与恶化,促上述三大领域(笔者:系上文所指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三大领域)进一步分崩离析”30许惟有这样,才可能进入文化批判的层面,最终解决同时袭来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与“后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无疑,一历史的发展,包括丈学史的发展,都必须遵循人类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的需求,尤其是要符合人性的规范,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用人性、人道主义和美学的眼光来治史,是十分必要的。它作为超越一切历史与国界时空的文学史惟一能够永存的衡量标准和价值判断,将成为我们今后治史与衡量文本的重要依据。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