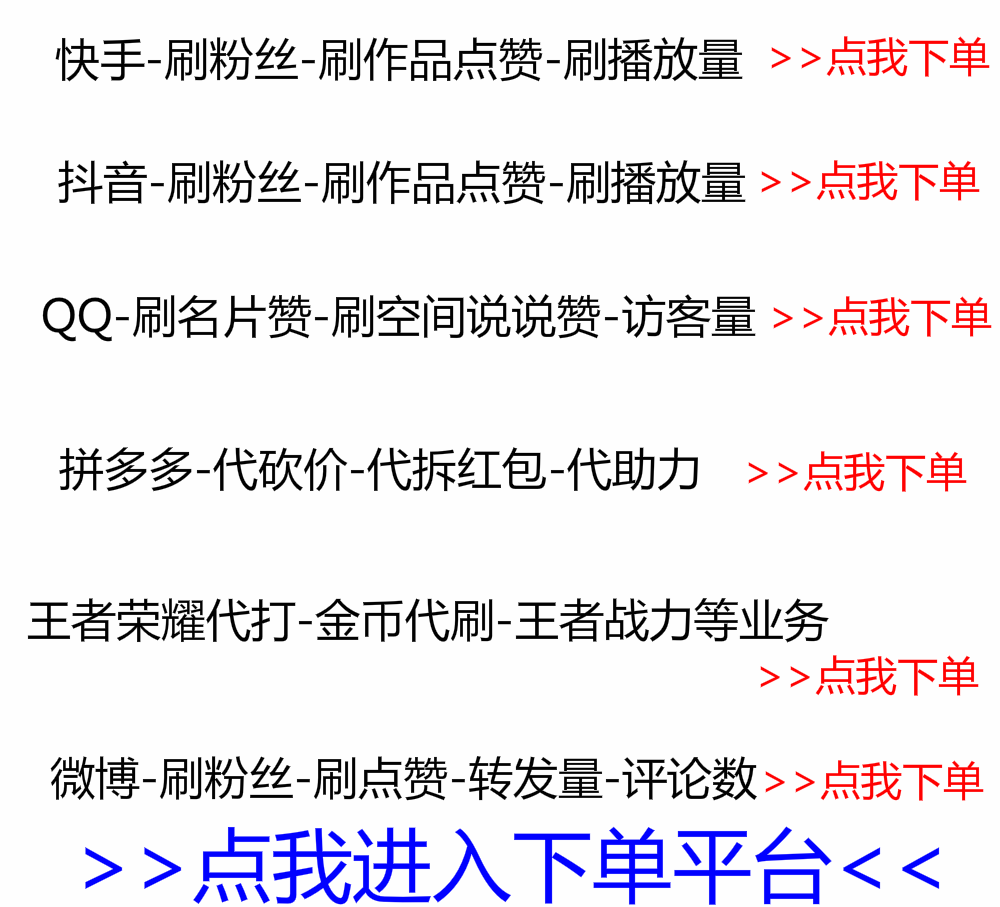2017年11月,快手的累计注册用户数突破7亿;2018年9月,日活跃用户数达到1.3亿。作为中国十大应用之一,快手足以代表中国最广大最主流的人群。它的内容非常丰富和宽泛,乍一看,不太容易晓得它真正代表的是哪些。
“真实故事计划”原创团队企图描绘快手上每一个个体的故事,溯源每一个人的命运去来,这时你会惊奇地发觉,有些荒谬是多么寻常,有些粗糙也只是生活本身。他的谈吐有多难理解,他的动机就有多合理。
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转载真实故事计划(ID:zhenshigushi1)的原创特稿,走入快手观看者的内心世界。
每位人都是一座孤岛
山东泰安人姚哥在欧洲最大的奢华邮轮诺唯真喜悦号上工作,这是一艘长334米、20多层、可容纳3850人的巨型船只,船上包括了20家餐馆,15间茶楼、酒吧和酒廊,以及900平米的免税购物区。
他和手下的73个兄弟负责维护整船只的救生设备。在这船只上,他拥有一个15平米的卧室,上面有床垫枕头、空调、衣柜、沙发和卫生间,船上的奢华自助餐、健身房及戏院均可免费享受。每晚只需工作6小时,即可月入6亿元。
挣钱是他成为船员的最大动力。他家境贫穷,小时候看着朋友吃蛋糕,自己只吃过父母买回去的蛋糕边,那时侯,他对于财富的想像是“有三天我一定会吃里面包中心”。
但当他真的物质无虞,却很难获得心灵的满足。置身于皑皑大海,最大的恐吓来自孤单。
他日日夜夜地想念妻儿,在随身携带的电脑笔记本上给儿子寄信,写对她的想念、写自己要努力多挣钱养家、写耳朵里残存的还在一起的景色,写了十多万字之后,二人还是结婚了。
无尽的孤单里,姚哥在瑜伽房慢跑、三个月掉了三十斤,在船舱上看一望无际的大海、一天抽一包半的烟,一年内看了两百多部影片,《海神号》——一部述说海难的片子,他看了六遍。不要妄想和岸上的人有多少交流的机会,船上仅有的两台卫星电话,要精确到秒来收费,一分钟电话至少要十块钱。
如今,姚哥用以消解孤单的方法是:开直播。在大海上开直播,要付出每小时250元的流量费用,粉丝多了,钱倒不是问题,稀缺的是讯号的庇佑。
当他拿起手机,第一个打开的APP就是快手。卫星讯号成为了虚拟的桥梁,将船与陆地联接了上去,他似乎重新置身于人声喧嚷之中。
这个常年飘泊在海上的海员觉得自己“一只脚站在了地上”,陆地上生活的人们羡慕他的生活,他有了粉丝、拥趸甚至钦慕者,“一个星期起码五天有人告白”,但他不怎样理睬,“没意思”,他说。
人们透过屏幕,见到的大海纯净、蔚蓝、浪花翻滚、波光澹澹,船员生活也和优渥、闲适挂上了钩,但这些景仰的男孩,甚少有人读到他虽然一直没有得到减轻的孤寂。

海上的姚哥盼望陆地上的生活,而在这个国家最深的内陆,少林和尚释延根也如同置身于一个孤岛。
他8岁入少林寺,这在当时就是一种逃出——他出生在一个重组家庭,父亲是带着三个儿子的寡妇,丈夫是结婚后下嫁的女人,这样的家庭在30年前的农村是不吉祥的象征。
在少林寺学了一身工夫下山以后,他当过兵,也扛过水泥、卖过菜、看过夜总会的场子。但这个世界总是向他展示惨白一面,他几乎没留下哪些美好的追忆,他认为这个社会被金钱所奴役。
也耿耿于怀于进军队第一年交的入团申请书,到了第三年离开的时侯才批出来,并作为自己不被社会所接纳的例证。
现在他又回到少林寺,教40多个儿子工夫。他没有存款,也决定不再下山,只是在快手上发布一些日常教课的视频,时常,他隔著屏幕注视山下的世界,快手就是他和这个世界之间的安全距离。
而华北科技学院的大二中学生郝士柏以前揶揄于注视快手。在知乎上,郝士柏评价“每次打开快手时我总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中国广大的底层中学生早已没有未来没有希望了”,这一回答为他获得了10223个赞。
他以前在上海市西城区一所盛产高分考生的名校就读,由于中考落败才脱离“清华清华梯队”。此次失败的影响延续至今,在华北科技学院,他一个人喝水、上课、看书,没有任何一个交心的同事。
几乎是有些怕事地,他指出自己并不须要社交,“自己的生活只要能吃饱穿暖,别的不这么重要,重要的是知识”。
但另一面的事实是,当他试着“把自己放进去语境”、“以快手深度用户的视角”来重新看待这个软件,他发觉这个软件给了他前所未有的轻松感,他在快手里分享自己打游戏拿了第二名、喂野鸭却反被追着跑、去北京吃麻辣香锅——这里展示的是更本真的自己。
而作为一个男孩只占八分之一比列的理工高校里的腐女,郝士柏保持的最高纪录是30天没和女孩讲过话。作为某种补偿,他在快手关注的744名用户中,有近400位是帅哥主播。他以前看了足足三个半小时的直播,就为了一个爱笑的男孩对着镜头跳舞。
时常相互遥望
开客车是一份熬人的工作。在小镇上做水泥生意的谢先志常常要开着五米多长、荷载20吨的卡车在路上行进8个多小时。
客车危险度高,必须时刻关注车的声音,他因而不能听音乐、玩手机,惟一的娱乐是,假如旁边错车的正好是个女司机,他会谄媚地按一下扬声器。

这个生活在神农架山区的女人以前在上海打工,但自从2006年娶妻生子,不仅去过700公里外男友的老家,他就几乎再也没有出过镇子了。有在北京打工的同事回去,聊天的时侯,谢先志问她们:“那个轻轨是在地下边还是地里面跑的?”
在信息的孤岛里憋了太久,快手成了他难得的和外界接触的窗口。在快手上,你几乎可以找到任何人,三分之一的少林和尚都玩快手,除此以外,有三十多位列车司机、国家击剑队的队长、赵本山的十多个师父、来自海外的超模。
谢先志关注了八十多个在美国的用户,顶管机的、造船的、电焊的,看她们发视频,在台湾、在日本、在美洲。这个早已十多年没离开大山的人,也能随口点评上好几个国家的著名建筑。
有些时侯,人们想要观看的世界并不这么遥远。到天安门看升国旗对相当一部份中国人都具有莫大的意义,但即使在交通这么发达的当下,一直有数目庞大的人无法完成这一旅程,她们是一些身体虚弱的老兵,一些困在农村的妇女,一些流水线上的年青人。
某种意义上,“北漂”汪宽就是她们的双眼。每晚日出之前,汪宽就会打车到天安门,用手机镜头直播升旗的画面。
由于日复一日地直播,这个天津人在上海早已看过289次升旗,他甚至总结了升旗的规律:看升旗疗效最好的位置是旗杆侧边2米左右,旗杆31米高,有36名护旗手,护旗手从金水河到天安门踢齐步是138步,升旗时间是两遍军歌、2分钟7秒。
当生活在乡村的人憧憬首都中轴线上的一次升旗,城市里脚步飞快的白领也在憧憬着牧歌式的田园生活。
每晚早晨,第一缕曙光洒向乌苏里江,坐落祖国最东方的扶余抓吉乡要比全省大多数地区更早睡醒。
在这儿生活了32年的渔船张鹏习惯了下午四点钟早起,架起烤架烧上水、把沸水灌进暖瓶、揣上干粮就登船下江,在海岸线边搭塑胶窝棚、启动船只、撒下鱼网,追逐乌苏里江“游动的黄金”——大马哈鱼。
由于常年在水面上曝晒,张鹏皮肤惨白、眼睛总半眯着、陷在深深的脸颊里,他戴个绒毛礼帽,说话的时侯大咧着嘴、露出来上下两排牙。
粉丝认为他特逗,小耳朵,黑皮肤,眼手链滴溜溜地转,脾气直,有点楞楞的,管他叫“打鱼界的宋小宝”。
张鹏出生于渔船世家,从太奶奶辈起世代打渔,渔船的生活“年吃年用”,一年到头攒不出来哪些钱。乌苏里江是全省仅有的几条未经污染的大江之一,但是,“每年的鱼都不值钱,没人晓得这个地方有如此好的鱼。”
在快手上玩短视频之后,张鹏积累了107万粉丝,相当于故乡讷河县全部人口的十倍。张鹏下网捕鱼,丈夫多多就在门口举着手机做直播,第一次直播,这对夫妻赚了20块钱。靠粉丝的礼物,她们攒了20万,离婚三年之后,总算在市区按揭买了新楼房。

镜头前,张鹏捧起打到的鱼咧开嘴唇、露出板牙,喜气洋洋地喊一喉咙:“年年有鱼啊老铁们!双击评论666啊,干就完了!”、“天亮了,我在好好干,大家不管干啥工作的,也好好干!”
琐碎生活里的高光时刻
在快手,每位人躺卧在自己的孤岛上,对另一个世界发出了远远的远眺。但当你无意间回头,会发觉自己的生活中也有某种值得深深注视的东西。
快手上教做家常菜的阿龙,前半生按部就班,到了年龄就相亲、觉得合适就结了婚、然后是生小孩,养小孩,在外人看来也是幸福和谐的婚姻,只有回到家里才认为那里不舒服。
做大堂总监的他每晚说了太多的话,上班回去他只想安静出来抽根烟,和母亲三人总是相对无言。直至开始在快手上做家常菜教学,两个人难得有了交流的机会,对话是从“今天做个哪些菜发快手”开始的,有的时侯,做到晚上3、4点。
爱人也在一旁陪着,他嘴上不说,心中也认为感动。29岁的他早已自诩是肩负重担的中年人,但父亲买来的情侣装,尽管他认为“幼稚”、“不符合我的年纪”,他还是勉强穿上了。
有的时侯,开一场直播似乎并不能让多少人看见,只是一场有些荒谬的自娱自乐。晚班司机大文置于同龄人里算得上潮流,他烫了一头卷毛,喜欢夜店、麻将和KTV,喜欢在早上出车,晚上十点之后,街上晃荡着的大半都是酒鬼。
西北人爱酗酒、也能饮酒。大文和13个同学聚在一起喝水,杀死了5斤黄酒、60瓶饮料。餐桌上几个人聊快手,商议着“能不能开个直播”,结果整个椅子上只有大文有直播权限、他粉丝最多——349个。
于是,大文当场开了直播,直播间进来8个人,5个都是同一椅子上喝水的。直播开了十多分钟,同学们给他刷了700多块钱的礼物。直播为这场酒局蒙上了一层光晕,致使平庸的一夜也有了被谈论的资本。
一种实现梦想的可能
人们盼望某种超出日常的东西,一点点新鲜的事物也能让人心弦振动。
我的专访成了令刘勇君激奋的事,他特地在快手上上传了我约访恳求的截图,配乐“我的未来不是梦”,在访谈当日,他骑着摩托车挪到了18公里外的大马路上,只由于哪里有稳定的电话讯号。
他的快手头像是自己67岁的姐姐,姐姐站在自家花生地里、垂着眼睛看向镜头下方,后背上挂了三条显著的皱纹,胡须和耳朵外侧仅存的毛发都白了。
在快手上,刘勇君分享自己“深山里的生活日记”,视频的主角是父亲,86个作品里,父亲出镜了53次。父亲第一次吃西瓜、爷爷自己剥了皮蛋、爷爷在喂小鸡……
这种日常生活里繁杂的片断被记录在了镜头里,成为了父亲难得的人生影像:过去67年生命里,他只有不到5张相片,其中一张还是身分证。
4岁的时侯,刘勇君没了母亲,而后,父亲改嫁、远赴广东打工,他和哥哥、奶奶一起生活在七个卧室的旧房屋里。房屋是用土、木头和瓦片搭的,刚用处在一处凹地,站在屋内旁边,四围望过去是层层叠叠的山。
由于房间老旧,每次下雪都成了难捱的坎儿:屋顶四处都在漏雨,墙角的柴火浸湿,锅碗瓢盆一同上阵接水,就连一只半径二十分米的碗都派上了用场。但是,这早已是修修复补多次的结果,在屋顶上,能看到密密妈妈竖着的条形木头,几乎塞不下新的木头来挡洞了。
刘勇君把漏雨的视频发在快手上,被网友质疑“怎么让爸爸妈妈搬去这样的房屋里”。他心中认为难过,把这几段视频都点击了隐藏。他希望能把牛奶生意做上去,整修一下这座老房屋。
快手上,刘勇君聊得最多的一位粉丝大刘只大他两岁,出生在距他一百多公里外的小村庄里,两个人有着同样的童年经历。如今,大刘在上海买了房屋、已经移居美国,刘勇君的视频激起了他对于童年时期乡野生活的追忆。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类需求根据阶梯从低到高排列,自我实现的需求成为最高层次的人类渴求。人们想要实现,想要赶超,而快手给这些其实从来没有实现机会的人提供了舞台。
23岁的李成鹏早已自学唱歌15年,这个村庄里惟一会唱歌的小孩拍了个《农村达人秀》:自家的庭院就是舞台、三个用啤酒袋子做的纸板取代评委亮灯,旁边坐成一排的母亲、父亲和对门邻居,分别对应成了范冰冰、周立波和伊能静。
对着镜头,李成鹏跳了一段机械舞,三位评委举上去手上画着“√”的纸板,代表演出通过了考评。
李成鹏最大的梦想是站在《中国达人秀》的舞台上,母亲饰演的“周立波”变成真正的主持人周立波,给全省的听众演出唱歌。
而在一年前,村庄里甚至没有人晓得这个迂腐的女孩会唱歌。在农村,唱歌属于奢华的事业,没有谁会把儿子送进去一堂课几百块钱的街舞班。
李成鹏自学唱歌靠的是在网咖看街舞视频,在打游戏的、摔按键的、骂人的、抽烟的人群里一遍遍播放机械哥的视频,回到家,自己闷在屋子里一遍满地练。由于没有人指导,入门级别的太空步,他练了两个星期。
最新的视频里,李成鹏在镜头最前方摆个纸板,里面写着:村里人的希望。李成鹏相信,唱歌才是他命中注定的事,他计划今年一定要去出席卫视的《黄金100秒》,这将成为他第一次离开西北。

生活里的行为艺术
有的时侯,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上快手的人,有的为了挣钱,有的为了减轻孤单,有的为了实现梦想,但还有一些人一些事,变得匪夷所思、令人吃惊。
太平沟人吴小虎在快手上宣布“我明天要把这山给夷平了”,60多万人围观了这一视频,他成了“全网移山第一人”。那些日子里,每晚吃过晚饭,吴小虎戴顶安全帽、拿个洋镐就往山下边跑,顶着正午的大太阳刨上两个多小时,107天出来,大山早已挪了一米远。
去年31岁的吴小虎没来得及读完小学就退学了,他当过兵、开过运客车、在饭店、歌厅和浴池都打过零工,最远还去到过上海,结果跟随姐姐在簋街吃了一顿饭就花了500块钱。考虑到“消费水平不一样”,吴小虎回了村庄,成了村里为数不多留守的年青人。
大多数时间里,他无所事事,移山之后,这个仍然没哪些存在感的农村青年也拥有了自己的粉丝,有记者去到了他家里,“有人关注,如同个名星,做事情有成就感”,坐在五菱客车上,吴小虎说。
重庆筠连的黄糠开始在网上直播每晚向河边扔一块石头,自诩“填海第一人”。他倍感自己的行为无法解释,“我也不晓得为何,莫名地想要去填这条河”。
有的时侯,他饱含雄心壮志,相信自己可以塞满这条河,之后接着塞满黄河,“填海就是我的事业”,有的时侯他又变得理智一些,“我晓得这是不可能的”。这个22岁的女孩是屋内独子,他酷爱摩托赛车,总想一鸣惊人,他说自己的下一个主意是“把煤焦洗白”。
网友“水滴石穿第一人”倒挂了一个塑胶射手,水从瓶中乘势滴在圆形沙石上,木板上写着“水滴石穿”;新乡新乡的新乡根则在镜头前直播磨铁杵,约请网友一起见证“铁杵磨成针”。移山、填海、滴石、磨针,她们被并称为了“快手四大闲人”。
在晚上,新乡根是广东一家外企鞋厂里的数控技工,每晚面对着两米多宽的车床。整个厂子里三千多人,他一个同学也没有。在这儿,大多数人埋首做工,仅有的时间都投入在了加班赚钱上,聊天被觉得是破坏秩序、浪费时间的事。
下午,新乡根变身快手“四大闲人”之一,他直播“铁杵磨成针”,一蹲就是一个多小时,眼睛里只有钢筋和磨刀石磨擦的声音。在这个时侯,他才有机会说话,对着手机屏幕里来自粉丝们的留言,聊自己的工作、生活、聊磨针是为了“锻炼自己的毅力”。
一下午的直播,郑州根絮唠叨叨,说的比在厂子里一礼拜都要多。
这是她们打发时间的方法,一种在生活中的行为艺术。一个有着无数种活法的APP上,有许许多多的人,许许多多的事,它们几乎包含了中国最广泛的生活形式,用尽了生活的千万种可能。
木心说:“生命好在无意义,才容得下各自赋于意义。”这大概是给那些使劲生活的人们的最好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