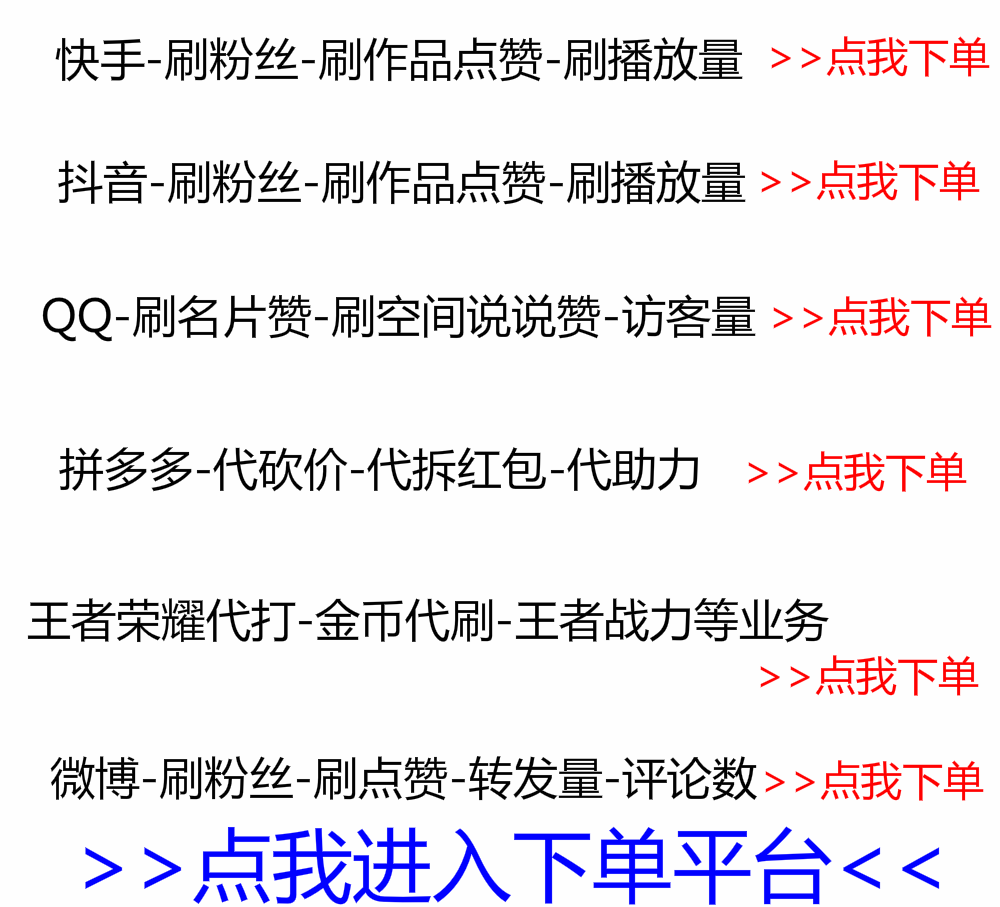新楚风第467期
朋友圈
杨光举/文
01
自从有了智能手机,手机便成了年轻人生活的一部分。手不离机,机不离手。
不得不承认,手机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观念。没有手机解决不了的问题。
我向来不喜欢玩手机,也不喜欢看到他人成天抱着手机,那样子似乎比亲爹后妈还亲,怎么看如何不顺眼。
然而,不是我不想玩就可以不玩的。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学生不得不在家上网课。没办法,只得给儿子买了一部华为手机,办了一张电话卡,还特意拉了一条网线,装了一个路由器。
下载好老师指定的钉钉软件,我对母亲说,手机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打电话接电话,通讯工具而已,上网充其量是它的附加功能。不要把手机当笔记本用,也不能当游戏机用。还约法三章,说,学生时代连陌陌都不能玩,更不要提吃鸡,王者荣耀。
刚开始几天,她上课很认真,上罢工就做作业。隔壁的一个小学生来看她上课,想玩会儿她的手机,她把头摇得能滴得下露水来,任他把坏话说尽,她硬是没答应。上网课的事,看来不用我太操劳了。接到单位下班的通知,我就放心地下班去了。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阳光明媚,和风徐徐。我一大早从镇上回去,老远就看到几个儿子围在一起,坐在场子里晒太阳,每个人手里手里拿着一部手机,不停地点啊点。
我气不打一处来,停好车,打开门,人还没出来,劈头盖面就是一句:“说得好好的不玩手机的呢?”
几个女儿嬉皮笑脸地看着我,不说话。别人家的孩子我管不着,我就当没看见,凌厉的眼神直视我家小孩。
女儿抬头看我一眼,说:“爸爸,我在看杨老师的视频回放。”
哦,原来是这样,错怪小孩了。我记得,杨老师在微信群里说过,第一遍没听懂,可以再看一遍回放。
还是不对劲,孩子读书没那么认真过啊。晚上躺在床上手指头不停划拉。就连喝水那点儿时间都不放过,好像喝水就是一个顺带的活儿,饭碗置于桌上,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着牙签,呼啦呼啦往嘴巴扒拉两口饭,赶紧扭过头来,心不在焉地嚼着饭,眼睛盯住手里的长方形物件,眨都不眨一下,脸上表情生动,投入得很。筷子几次伸到两只碟子中间,好像他妈悉心烹调的鱿鱼、酱牛肉、韭菜盒子,既不是面食也不是副食,无色无味,只是可有可无的摆饰,而他的饭菜叫手机。
我想发火,想伸手过去把手机拿过来瞧瞧她究竟在看哪些东西,这么认真,但又转念一想,孩子都十几岁了,没必要看如此严,于是,我忍了。
忍了三天、两天、三天……一周以后,我再次回家,她还是那样,我总算忍无可忍。晚饭时,趁着一家人都在餐桌,有见证人,我打算跟她严肃认真地说一说手机的问题。
我感冒一声,清了清喉咙,问她:“网课上得咋样啊?”
她的视线极不甘愿地从手机上移过来,看了一眼我的面色。我面无表情,往嘴巴扒拉了一口饭。
“挺好啊。”她笑笑说。又扭过头去看手机。
我说:“不是吧,杨老师说你近来学习极不认真啊,学习成绩下降厉害啊。”跟打麻将一样,其实,我这是玩的一个诈和。杨老师还在上海,我看不到她,也没打电话问过女儿上网课的事。
她起身看我一眼,没说话,夹一牙签菜塞入嘴巴,继续看手机。
我把牙签往餐桌上一拍,眼一横,牙齿咬的咯嘣响,愤愤地说:“手机给我。”
她吓了一跳,赶忙拿起手机,慌慌张张地点了一下,放下牙签,双手递给我。

我接过手机一看,妈呀,这手机上真热闹,微信,QQ,快手,抖音,快乐斗地主,掌阅,王者荣耀……桌面上摆的满满当当。
“谁给你弄的?”
“我自己弄的。”
“我问,谁教你弄的?听懂没?”我拍着凳子,调高了音量,歇斯底里般小声叫喊。
她红着脸,低着头,小声说:“这么简单的东西,不用人教啊。”
哎呀妈呀,这小孩。我手机上弄个陌陌,从下载到安装,从注册到登陆,再到添加好友,发信息,可都是办公室那种女大学生小赵手把手教我几天才玩转的呢!
我冷静出来,想了一会儿,没好意思问她这话是真是假。
女人看了我一眼,说:“别管她,现在的女儿那个不是这样。”
缓过神来,气消了大半。
我说:“现在,你还是要以读书为主。考不上学院就回去种粮,要么下地帮父亲打猪草,要么上山帮父亲扛木柴,别指望我给你拉关系找事做。”说着,把手机还给了她。
她接过手机,放在椅子上,诧异地瞧瞧我,又瞅一眼他妈,认真地说:“爸,现在手机上也可以看书,你别以为只有捧着书本才是读书。”她说着,打开手机,点了一下,递到我面前。我扫了一眼内容,貌似跟《三国演义》有关,我看见了孙权、刘备的名子,同时也看见了项羽、刘邦的名子。什么玩意,分明是穿越嘛。
女儿见我没吭气,继续说:“爸,不是我说你,你得跟上时代时尚,用现今的一句话说,你早已被out了。现在各类软件如此便捷,你如何就不常用呢?譬如说,你若果是在有网路的情况下,用陌陌给我打语音或则视频,不存在长途话费的,省得你每次打电话总是讲两句就死掉。你看我舅就三天两头跟我视频。有哪些事情你想跟好友分享一下,你还可以发朋友圈。你还可以在朋友圈里跟好友点赞评论。”
她又划拉了一下手机,接着说:“你看,前几天我都加你陌陌了,到如今你都没同意。通过一下啊,天天都没看手机啊?”
这小孩,智商不低,嘴挺能说,《三国演义》没白看,几句话把她妈拉到他阵营里去了,让我顿时丧失盟友。我嘟囔餐具,回他一句:“我双眼远视,不能长时间看手机。”
02
吃罢饭,孩子又开始鼓捣手机。女人收罢餐具,打开电视机,看一个没看完的搞笑片,故事大约是这样的,一个特种兵跟一个空少第一次约会,特种兵偷偷地亲了空少一口,空姐又偷偷地亲了特种兵一口,就此打住,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故事,告诉我们凡事不要老想着占人实惠,可接下来,那空少却从特种兵的白色偷了一颗手榴弹,特种兵大惊失色,紧张地说,千万不能拉破片。太牵强附会的一个故事,一点意思都没有。我说,妈的,那不叫破片,那叫保险销。
闲得无趣,穿了件衣服,到场子里闲逛闲逛。
孩子说我跟不上时代时尚,这话也不是没一点道理,比如,到目前为止,我没点过订餐,不会打游戏,网上购物虽然也会,但我的原则是能在实体店买的就在实体店买,我觉得,网上的东西不一定都靠谱。这并不是说现代化的东西我一点都不会,起码,我会在12306买火车票,在天猫上买客机票。基本办公软件不仅设计、编程以外,做表格发邮件哪一样我不会?我没发过朋友圈不是我不会,而是由于没学,也懒得向别的人讨教。我就会在支付宝上打开共享自行车。我就会刷脸支付。
我的业余爱好是读书,再就是瞧瞧电视转播的体育比赛,除了中国篮球,别的联赛都看,只要有输赢。最爱的是足球,CBA、NBA都成。看啥电视家长啥都好说,关键是小孩小时候跟我争电视,她痴迷动画片。媳妇以前跟我争电视,追看日剧,她调一个频道我又换一个频道,换着换着就大打出手。现在他们不跟我争了,他们都看手机或则笔记本,电视归我一个人。媳妇的日常用品大多网购,连防盗裤头都是网购的,我真想不通商场里的裤头跟网上的裤头有哪些区别,裤裆里有哪些好偷的,还要防盗。每次节假日大促销,她像过节,买猪肝、虾仁、百香果,家里天天来包裹,小区门口的丰巢,有三天她去了五次。孩子不跟我争电视,她只看手机。她说手机上下载的有书旗,可以看各种各样的书,我懒得多说话。手机屏幕这么小,看书能得劲吗?
变天了。起初挂了一阵风,接着阴云密布,天地间像拉了一块内幕,不一会儿居然飘起了雪花。最开始是几朵小片的雪花探头探脑地飞舞在我的身上、头上、身上,见我没怎样大惊小怪,便有些肆无忌惮了。雪花越来越密,路面变白,开始滑上去。风冷嘶嘶的,打额头生疼。
家里静悄悄。孩子的卧室门也没关。我去卫生间洗手,经过她旁边,看见她戴了麦克风,手机仍然捏在手里。睡了还是没睡呢?人呈“大”字躺下,老半天一动不动。
懒得说她。
媳妇捂在被窝里看朋友圈。我脱了衣裤揭露毛毯,看见她胸口两个沙包一样的东西还是那样理直气壮地挺着,心里有些搔痒,便伸手去摸。她晓得我想干啥。我每次想那事时都是这个动作,这些年来始终这么,是一个暗号,是一种默契,她一次都没拒绝过我。可此次她却一把把我的手推开,小声说:“莫啊,老老的了,万一让儿子听到了,丑哩!”我说:“丑啥丑,有证呢,又不是偷人养汉。你看电视和小说,董事长弄小秘书都不丑,我弄下自己的男人还丑了?”她指着我的耳朵说:“你呀你,天天看黄色小说写黄色小说,人也黄得不得了。”我说:“还记得不,今天是哪些日子,不应当记念一下?”她恍然大悟,说:“哦哟,今天是我们三十几最后一个生日,是该记念一下。明天就四十了。”她忽然扭一下脖子,面向我,接着一本正经地问:“你记不记得我们一共做过多少次了?”我说:“不记得,又没数,估计你也不记得吧。”她嘶嘶一笑,说:“我记得,墙上画着正呢,做一次画一笔。”在她笑的那一刹那,我腿一翘,翻个身,压在她脸上,灯都没顾得关。
我还意犹未尽,想再来一次,她却一侧身,屁股对着我呼呼地睡觉了。我毫无睡意,从床垫下边把高老师的那本签名书拿下来看。散文集,题目叫《春暖花开》,写得真棒,不像我,一下笔就是粗言秽语。

看了十几分钟,眼睛累了,左眼里似乎总有一个虫子在飞。去襄阳人民医院看过,医生说,飞蚊症,目前没哪些非常有效的药可吃,关键不能疲劳用眼。闭了双眼,怎么都睡不着,越睡越清醒。打开电视,今晚有CBA联赛。可惜的是,八一男篮对阵广东宏远,加上客场在东莞大朗,整场大赛,似乎成了易建联一个人的表演秀,没多大看头。关掉电视起身,还是睡不着。
我干脆从床上溜出来,歪在椅子上,也打开了手机。谁不会呢,动动手指头的事情。我也有微信群,也有朋友圈。同学群,老乡群,工作群,美女聊天群,多的很。只不过通常潜水,不发言,也不在他人发的朋友圈留言。最看不上那个三天发好几次朋友圈的。微商广告,滴水捐,公众号,拉选票,晒房屋,晒面包车,晒情人,晒宝宝,晒小吃,晒旅游……没完没了,就差直播上公厕了。说不定哪天一高兴,做爱时也录一段视频发个朋友圈。分明是在演出,活给他人看的。
我想再打开电视,又害怕声音大了,影响他人休息。关键没哪些想看的。那就还看手机。我好友一千多,退出的群聊和还保留着的群聊加一起,少说也有上百。老熟人或则新认识的说要加你好友,你如何好意思拒绝?仅仅是简书粉丝就有好几百。女儿说我土,跟不上时尚,我不服气。点个赞、献朵花,嘻嘻哈哈,谁不会?我发觉我认识的几个同龄人喜欢在晚上十点钟之后发朋友圈。他们像我一样睡不着吗?幸福的睡眠似曾相识,不幸的睡眠各有各的不幸。都不容易。那就给她们都点个赞吧。手机字小,看不太清楚,管她们发的哪些,点个赞表示我也在关注你们。点完赞,关灯午睡。
03
周一下班,餐厅里异常冷清。准确地说,吃饭的只有我和老张。这很不正常。一般来说,周一晚餐,机关的人到得很齐。周一上午十有八九开会,不用特意通知,多少年的惯例。周二开始,下基层的下基层,去学习的去学习,跑外交的跑外交,单位的饭店,用餐人开始降低。而明天是周日。这确实不正常。一般情况下,我不喜欢跟老张在一桌喝水,他肝炎三阳,单位人都晓得,吃饭尽量避着他。今天早晨特殊。我把餐具端到他旁边,他有些意外,向我点下头,小声问我:“你也没去?”
我愣了一下,问他:“没去哪里?”
他盯住我,看了起码5秒钟,回我一句:“装傻?”不再说话,低着头跟饺子白粥拚命去了。他快速把饭吃完,也不再跟我打招呼,端碟子走人。老张还算讲求,来饭店喝水总是自备厨具。他肯定晓得他人忌讳跟他一桌喝水。
我不明白他哪些意思。我确实不知道单位出了哪些事情。
这个下午没开会。人相继上来,我很快晓得为何晚餐人少,也明白老张为何说我装傻了。
分管人事的王组长,老娘跨鹤西游了,今天早晨丧礼。婚丧婚嫁是敏感事,虽然单位没人即将通知,但你们基本都去出席了挥别典礼,据说在单位的人都去了。
我问坐我办公桌旁边的那种副科长:“你们怎样晓得消息的呢?”
副科长说:“王书记发了朋友圈的,在朋友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吹手向北》,表达了对伤者的深切悼念和真切的想念,一直用第二人称,并没明说老子走了。”
话说到这儿,事情的前因后果早已很明了了,只怪我没仔细看朋友圈。
王主任这家伙叫王帅领,比我小五六岁,矮矮的,胖胖的,留着短发,一副跟瓶底一样厚的镜框前面两只小眼睛,平时总是嬉皮笑脸的,像和珅。中文系专科结业,当过几年兵,平时也爱写写画画,弄几篇自以为不错的文章,他还说那是正能量。在我看来,那根本就没有哪怕是一点点的文学性,心灵鱼汤而已,一开始就是喊标语,阿谀奉承,左右逢源,逢场作戏,算不上诗歌,甚至连散文都算不上。去年年末的那篇论文,还是我给他代笔。就他这水平,还跟我一批转正,还人事部长。
不知是单位里非但就没有一个懂文学的人,还是这个世界的文学观变了,在一次单位内部组织的征文大赛中,他那篇类似于倡议书的狗屁不通的破文章,居然得了银奖,荒唐至极,可笑至极。看着他成天嘚啵儿嘚啵儿的样子我就气闷。难道我这个工会主席要始终干到离休?。不过,把话说过来,我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想想那老张,五十好几了,还是一个副科级,后勤一管就是这么多年。
平时单位下班考勤严格,开会不来,请假理由要当众宣布。王组长近来两次缺席单位周日会议,会议通报缺席情况,都讲明他是请请假在诊所护理重病老奶奶,所以当他在朋友圈抒发悲愤时,正常人应当马上就能猜测出了哪些情况。
王组长极少发朋友圈,偶尔露下头,一般都是相关新政剖析,跟他工作有关的。他在朋友圈说哪些了?打开手机向前翻,才发觉我不但缺席了应当参加的场合,简直可以说就是闯祸了。我在人家王组长的伤心下边点了赞!单位那么多人,居然只有我一个任点了赞!居——然——点——赞!!
说实话,单位人在朋友圈留言的并不多,就几个人,都是右手合十在祷告,也有人在说“保重身体”“节哀顺变”。只有我一个人在点赞!这心态太恶劣了,人家老子走了,我还点赞?!
我不能宽恕自己。摸着第三颗纽扣说句良心话,我绝对没有幸灾乐祸的意思,只是没认真看朋友圈的内容,一不小心就点错了赞。
三天或则五天丧礼,是本地风俗。一定有人私下问过王组长,在下边相互交流了消息。周末休息三天时间,交流这点信息,时间足够。即使出差在外的,肯定也会另有办法抒发自己的追思。退一万步,说一句“节哀顺变”总可以吧?这是人之常情。我大肆点了赞,别人其实能看出我的心态,谁就会荒谬地问我去不去出席丧礼?
我没法指责同学不跟通气。
我跟王组长,曾经在人事办公室大吵大闹过一次。事情是这样的,不知怎么回事情,我的档案年纪被改大了两岁。虽然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跟我解释,但我挺长时间想不通。档案上写着的出生年月日,整整比我大了两岁,那时候我老爹、老娘还没离婚呢,有她们的结婚证为证。王组长给我的解释是我当初的一份申请书日期出了问题。在年份上,字迹不清,有改动。他说他也没办法,档案不能随意涂改,只能这么,谁都一样,工作难免会出错。狗屁,废话,老子给你写论文时,你说话可没那么有胆气呢。我没要他一包烟,他也没给我买一瓶酒。我恨不得骂他忘恩负义,卸磨杀驴,但话到嘴里又随着一口唾沫咽了下去,好歹也是吃国家皇粮的人,不能这样没素养。
他说,这不是哪些大事,但在我看来,这事比天还大。我据理力争。我上中学的年纪,我的毕业证书,我的身份证,等等。难道我四岁就上中学了?我不是神童,从来没跳过级,跟你们一样,挨个年级念完的书,一步衰落。大两岁意味着将来我要提早三年退职。工龄、涨工资、住房社保等都受影响,一直影响到离休收入。谁摊上就会有意见,没有意见算不上正常人。我在人事办公室说话的声音可能大了些,还吹胡子瞪眼拍了椅子,门外有人看到了。人在兴奋之中,高声大嗓是在所难免的。
年终选优时,王校长比前一年少了两票。他会不会以为我没投他票呢?我无法解释。投票是匿名的,越描越黑。还好,是两票。如果是一票,我更说不清了。也许我曾在旁人面前显露过对他的意见,我记不得了,但可以肯定的是,我绝对不会在人家老子逝世的时侯幸灾乐祸。我耳朵斜视,又有飞蚊症,没看清楚,手滑了,点错了赞。应该补救一下。可是,怎么补救呢?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也许就是到他的办公室去,表示一下自己确实不知道,表达一下自己的缅怀之情。这是人之常情。我再如何不圆滑、不世故,再如何像他人说的书生气,这点最基本的人情世故还是懂的。
回想起老张看我的眼神儿,他也觉得我对王组长有意见吗?有意见归有意见,跟他老子有哪些关系呢?人死众家伤嘛。我晓得的是,他而且正儿八经地对王组长有意见,这个全机关都晓得。老张是从基层提拔上去的党员,乡下的日子过惯了,他想找机会再回农村,几次主动申请下乡脱贫,都没批准。老张不光肝炎三阳,还有糖尿病,要打胰岛素,很多年了。哪个单位能派这样的病号去帮扶?他早已接近退休年龄,一直盼望再提一格。他如今是副科级,再提一格,当上正科级,哪怕有职无权也行,退休待遇有提升呀。大概他仍然觉得,不同意他下乡,包括至今没能再提拔一格,是王主任在作祟。连我都明白根源根本不可能在王组长,而在前面的头儿。当局者迷,老张糊涂了。但这些事情我如何跟他交流?我跟他关系没到这步。换位思索,当人事处长也不容易,有些事情,你坚持了原则,可能就惹怒人。
04
我去敲人事办公室的门,没有人应答。门推不开。这样的日子,王校长不可能来。
打电话说这事,有点唐突,不合适。以后有机会再说。
那天早上回去,我跟女儿发了火。她卧室里,乱七八糟,一塌糊涂。床上乱得像狗窝,书本随意扔在床边地下,袜子丢在床前的书房上,满房间发臭的。
让我发火的缘由,不单单由于她房间里太乱,关键是她的手机屏幕坏了,嘟囔着跟她妈说要换屏幕。正月份上网课刚买的新手机,才多长时间,手机就坏了?就不能用了?头天白天不还好好的吗?我的手机一用好几年还好好的呢?
她说:“我躺在床上看杨老师的直播课回放,看着看着就睡著了,手机掉地上,碎屏了。”
火冒三丈,气不打一处来。我脸一黑,牙一咬,态度呆板,气愤恨地说:“败家子玩意,自己想办法!”
话一出口,连我自己都惊叹。我记不得在家里多长时间没那么死板地说过话了。我老婆对外常常说我是暖男。我做家务,帮她干活,不吸烟不抽烟,工资卡上交。孩子小时候,我陪他去补习班,一起寻思物理题。业余有点时间,也就当个书虫,看看书解闷。偶尔看电视,基本上看一会儿就关,不多费电。我跟家里人说话一般比较平和,很少发火。媳妇和儿子,都是我的亲戚,我跟她们发哪些火?有哪些不对的地方,好好说不行吗?
虽然老婆说不上漂亮,但也是一个不错的男人,上慈下孝,对我百依百顺;孩子不仅玩手机以外,别的没哪些毛病,听话得很,我应当知足才对。媳妇眼神中的苦恼不解,孩子食不甘味的样子,让我有些懊悔。
但我不想马上在他们面前示弱。
下乡检测精准脱贫一星期,这段时间工作进展很快。扶贫户都迁往新屋去了,该拆的老房子也拆了。
从乡下回到家里,孩子还是在看手机。我竖着耳朵瞟了一下手机,手机屏幕好好的。钱都是婆婆管着,我晓得他们孙儿肯定背着我修了手机。兵法上说,这叫先斩后奏。既然手机早已修了,何必再招惹人呢?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当没看见。
孩子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说:“爸爸,修手机没用家里的钱。”
“那你在哪里弄的钱?”
“我和我妈天天刷抖音,玩快手,拼多多,一天挣一百多呢!”孩子很自豪地看着我说。
唉,这男人,咋说呢,二十以内的加减法不用手机硬是算不清,四则混和运算不知道先算啥后算啥,搞得一塌糊涂,一年级的物理题就能算出正数,偏偏玩手机比我在行。
事已至此,我啥都不想说。一个女孩子,十几岁了,她妈都不说她,我还有啥话可说的?干脆顺水推舟,做个顺手人情,也给自己一个台阶下。
我想了想,说:“朋友圈里天天都有抖动音赚流量的,没见大家孙儿发朋友圈啊?”
女儿看了看她妈,不说话。
女人笑了笑说:“怕你看到我们抖动音又要吵我们,所以在朋友圈里把你给屏蔽了。”
“哦?微信还有这功能?”我有点错愕。
女儿一脸得意地说:“这个还不简单?权限设置里点击不让他看啊!”
看来,玩手机的水平我真不如这小孩。
我忽然想起了同学圈里点赞的事,也为了缓和一下紧张的氛围,我诚恳向父亲讨教:“如果我在他人的朋友圈点错了赞,是不是可以撤回来?”

我掏出手机,把让我揪心的那种赞找下来给他看。
女儿看都没看,不假思索,果断地告诉我:“信息两分钟之内可以撤回来,超时就撤不回去了。朋友圈点赞随时都可以取消,短时间内他人没看见还差不多;时间一长,别人都看见了,取消了也没哪些意义了。”
好吧,只能这样了。
三天后的一个早晨,我吃罢饭躺在办公桌上正打算休息一会儿,突然,“滴溜”一声,手机响了一下。我从裤兜里拿出手机,打开一看,是父亲发来的一个红包,还有一条信息:“爸爸,这是我刷抖音赚的五十块钱。我晓得,我们一家人都靠你那点死薪水。为了我们,你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这点钱你就收下,饿了买点东西吃。”
我很是感动了一阵子,心想,这个小妞没白养,十几岁就晓得关心她老娘了。
大约过了半刻钟,我半开玩笑地给她回一条信息:“现在不要想着赚钱,好好读书就行,有时间了学着干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这钱你就留着自己用。等我老了,你能挣大钱了再养活我不晚。”然后是一个会心的笑容。
女儿几乎是秒回我的信息:“你就收下吧,我一个小孩子不会用钱,留着也没用。”
王组长下班了。
我拿着一份该存档的脱贫资料去他办公室。资料下边有一本书,书里有一个信封,里面是我的一点“心意”。按我最初的看法,我跟他说句话就行了。后来想了想不对,证明不是故意晚的诚心是哪些?还是用钱表示吧。虽然王组长看起来还是挺廉洁的,他儿子前年满十二岁,没大酒大席的操办,别人表没表示人情我不知道,反正我没表示。
敲了几下门,才看见王主任低沉着喉咙说了一声:“进来。”
看见我,王校长的身上写满了惊叹号。如果我没记错,这是我档案被改动以后,第一次主动登他办公室的门。
我一只手拿着书 ,一只手把信封递给他,说:“王书记,你晓得我不怎样看手机,技术不熟练,那天早上稀里糊涂的,没看清楚,对不起。您节哀。这是一点意思……”
我这个人有点怪毛病,说起笑话来一套一套的,一到正轨场合就口吃。这叫驴肉上不了正席。为了说好这句话,我想了很久,然后写在纸上,删改了好几遍,又像背台词一样背了一个晚上,记得滚瓜烂熟。还行,没结巴。
王组长吃惊地看着我,一脸严肃地说:“谢谢你关心。心意我领了,这个绝对不行,这是原则问题!”
他很严肃,很坚决。按照预先想好的,如果他推托,我把信封放在他办公桌上,转身就走。但他摁住我的手,不让我动,仍旧严肃地说:“你这钱我不能收。除了原则,也还有风俗,据说这些事情不能之后补的,如果我收了,对家里人不利。有这样的说法。”
有这样的说法?王组长的话让我错愕了。这说法超乎我预料,我没考虑到这一层。我真的不懂。真有这样的风俗?那下边该如何讲?事先没想到这层啊。
有人敲门。我只得把信封放进书里。老张进来了。我对他笑笑,把资料交给王组长,嘱咐他务必要帮忙存一下档,然后转身离开。
信封没送出去,毕竟该说的话说了,我觉得自己办妥了一件事,心里轻松些。
时间过得真快,八月份很快就过去了,又到了开学季。这学期,学校正常开课。
我和老婆一起驾车把孩子送到中学。学校封闭式管理,必须寄宿。孩子在中学一住就是一星期,还是有些不放心。分手之际,女儿先拥抱他父亲,然后拥抱我,叮嘱我:“老爸,在乡下要多珍重!你也没在农村生活过,你要努力好好学习啊。”
她给我一个鬼脸,我轻轻拍一下她的下巴。我在心里苦笑。你要努力好好学习啊——这是每次送她去念书时我跟他说话时的话,这句话一说就是好几年。现在,我不想再说这句话了。
我想了想,说:“孩子,你比我聪明,好好研究研究,怎么能够把发出去的表情或则说出去的话,随时都能撤回,别就这么两分钟。”
孩子和她母亲,不约而同嘿嘿笑了。看上去都像摊手。这件窘事,我没隐瞒她们。
再有一天,我又要到另外一个村去帮扶了。那个村的几个驻村脱贫党员工作不力,房屋回迁不彻底,经县委扶贫办的领导研究决定,我们单位的脱贫党员跟那种单位的脱贫党员对调。
这次,我们单位派我和老张一起去。他早已申请了好几次,他乐意下乡。虽然我并没主动申请,但每次下乡都少不了我,我是刺头,是老油条,没有一个领导拿正眼瞧过我,我也没把任何一个领导置于眼中,于是,下一回黑手,干脆把我打发到乡下,眼不见心不烦。
分管帮扶的头儿找我谈过一次话,跟我讲:“老张身体不好,虽然名义上他是主任,但你要多负起责任,毕竟你学历高,也比他年青。写材料哪些的,你就多动手吧。”

我老婆不愿意我下乡,她说:“那地方太偏僻,跟竹溪交界,属于三不管地带。听说老张还肝炎三阳。你跟他在一起,吃东西可千万当心哪!不行的话,再去打个卡介苗。”
“我都多大年龄了,还打卡介苗?你放心吧,我会注意的。我喝水用你给我打算的餐具。再说人家老张平常挺自觉的。”我继续开导她,“我不时常在家,没人打呼噜,你昨晚就可以安安稳稳睡大觉了。”
我和老张去村里报到这天,分管脱贫工作的头儿去外县开会了,王校长代表单位送我们俩。从单位到帮扶村,开车大约两个半小时。王校长开私家车送我们,让我有些小感动。本来我说自己驾车的,但王校长坚持要驾车送。那就送呗。也许,送我们也是他的工作职责。
下高速,经过一个村庄集市,王校长找了地方停车,我们一起逛了会儿。王组长在集市买了一只土鸡,他说老爷爷身体也不好,回去给老人家炖了吃。
老张喜欢照相,是县摄影协会会员,拿着手机在集市上拍来拍去。他拍了一些土特产,洋芋泡、葛粉、红薯干之类,很快发了同学圈,九宫格填满了。
以后,我将和老张朝夕相处了,应该跟他抓好关系,是不是可以给他的朋友圈点个赞?但一想到点了赞很多人都能看到,自己刚才犯过错误,见证人就在身边,所以,伸出去的手指头又缩回去了。我可不可以立誓,以后不给任何人点赞?不点赞又怎样?各种各样的“赞”那么多,不差我一个。
上车,继续赶车。王组长车技不错,尽管十八弯的大路忽上忽下,但车开得平平稳稳,不知不觉中,我居然睡觉了。如果不是老张推我,我还在梦中:“兄弟,醒醒,下车了。”
我挣开双眼,让自己赶快精神上去。我以为会有人迎接,至少是对接,村里的头儿应当在吧?但是,没有。车停在一家挂了蓝幌儿的二层酒店门前——“西域全羊宴”五个大字把我吓着了:这是哪些意思?!没帮扶先来吃人家?这不对呀!
和老张对视一眼,他的额头也是困扰。他大约一路上都在捣鼓手机,没怎样看路,也以为王校长会把我们带到帮扶村,没想到会停在酒店旁边。饭店门口站着一个年龄跟王组长相近的汉子,跟王校长热烈地握手,捏着他的手用力摇用力摇。握伏诛,王校长扭过头来用力把我俩往门里推:“进去再说,进去再说。”
包间的圆桌转台上,已经摆好了手把羊肉、烤羊排,我们落座之后,又上来两道莴苣,还有大盆的拉面,以及馒头、蒙古馅饼。王组长笑呵呵地解释说:“对不起兄弟,没征询你俩同意,我私自作主带你俩到这里来吃顿饭。是这样的,这旅馆的老总是我在军队的战友,我几年没见他了,甚是思念,人家三番五次给我打电话说要来看我,可我太忙,家里还赶上事,没时间呀,正好你俩出来,我找个由头送你俩,拐个弯到这站一脚,我这是公私兼顾了。话说回去,咱们如今这个时辰到村里,人家还得给咱打算饭菜,太添麻烦了,是不?”
理由说得过去。我没当过兵,但听说过“战友情,一辈子”。既然这么,就不客气了。这家的猪肉,做得是真不错。餐馆的生意也不错,虽然是早晨,包间外边早已传来饮酒、划拳的声音。山里人古朴热情,大都喜欢饮酒,酒风兴起。我和老张都不能饮酒,真要喝的话,我们应付不了的。再说如今是早晨,严格说是工作时间,喝酒不宜。王校长跟战友重逢,也许会喝点小酒,我早已做好了替他驾车的思想准备。我不是一个不通人情的人。
出人意料的是,王校长并没喝茶,只是跟我们一起吃猪肉、喝豆汁,吃得红光满面。一顿饭吃了两个来点儿,中间他出去跟战友单独呆了半个多小时。我们走的时侯,老板下来送我们,跟他再一次热烈握手,还拥抱了一下。
到村里早已是下午三点多。跟村里接过头,王校长午饭都不吃,连夜驾车回家。当天早上,我和老张就搬去了村部。
两天以后,我和老张也回来了。单位来通知,上级要来考评,所有在外边的都得回来投票,不得事假。
村主任让我开他的日产轩逸回镇上。老张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拿着手机不停地拍外边的景色。窗外不仅田就是山。山一座连着一座,曲折起伏,绵延不断,千篇一律,毫无新意;田地里不仅糜子就是烤烟,没哪些好看的,不知道有哪些拍头,但他就是热爱这个。他不省心。老张年龄比我大,他是如何克服花眼的呢?摆弄手机多累双眼啊。我很好奇。
我想跟他说,如果此次是考评党员,是不是要给王组长投个赞成票?王组长这人,总的来说还不错。人家亲自驾车送我们出来,用自己的关系请我们吃猪肉,够意思。当然,他请我们喝水,也有搞关系的嫌疑,毕竟他在年终评比时少了两票。工作关系,他可能晓得近来要有一次考评。但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对吧?
我想了想,话到嘴里又没说出口。有些事情是不好讨论的。
在离镇上不远的地方,我发觉车里油不多了。加了油,起步不远,车轮还在加油站的场子里,车头刚上道路边沿,一辆丰田霸道风驰电掣般奔过来。不料正前方正行驶着一辆大卡车,于是,一扭方向盘,快速向我那边冲过来。我看都没看过来,还来不及踩刹车,就听到嘶嘶一声,撞车了。
交警正在处理这起突发交通事故,来电铃声忽然响了。竟然是我母亲的号码。
女儿在电话里问我:“爸,我给你发了链接,你如何不理睬我?”
“我追尾了,正在跟警察推诿,没顾得看手机。”
挂了电话,趁警察现场照相的空当打开陌陌,果然看到一条母亲发来的链接。他们中学搞活动,评选最美中学生寝室。里面有她的寝室,要我投票点赞,还要帮忙发一个同学圈拉一下选票。我看了一眼她的寝室图片,比她暑假回去时的卧室很多了,东西都在应当的位置,被子叠得有棱有角。我给她寝室投了票,然后发了个朋友圈,给他语音留言:我耳朵花,好像点错了,投给他人了。
女儿发陌陌问我警察咋判的。
我回她说,直行优先,我左拐弯没让左转,要负全责。
女儿问,你好歹也是个公务员,在职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就没别的办法?
我说,真没有。
女儿说:“老爸,别只抓盐不看秤,你得玩转朋友圈。这社会,那一行都有朋友圈,微信有陌陌同学圈 ,政客有议员朋友圈 ,文学界有文学界的朋友圈。想想你,干了这么些年的革命工作,还是一个小科员;写了几十万字的小说,也没见你上过一次大刊。”然后是一张调皮笑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