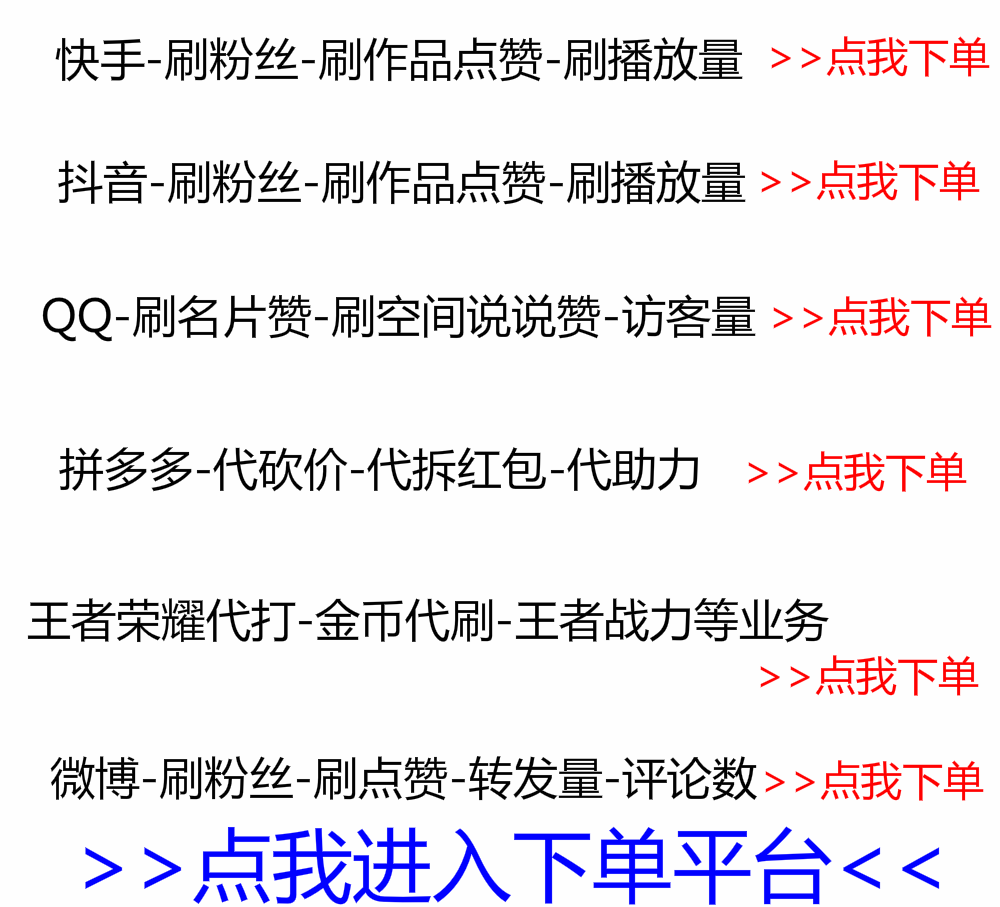耀视纪电商大学的学员正在上课。新京报记者王昱倩摄
正在直播卖货的店家。新京报记者王昱倩摄
早上3点,通往北下朱的每条路,都被拉货的四轮车、面包车围堵得水泄不通。骑四轮的人穿着鞋子,一边喝酒,一边等着警察疏散公路。夜晚,这种开四轮车的人又换上了宝马、奔驰、宝马等豪车。
这个距温州国际工贸城2.2公里的普通民居,被媒体冠以“中国微商第一村”“网红直播第一村”,村里每位商铺上面,就会有正在直播卖货的主播。镜头前,她们嘶声力竭地喊着,“宝宝们,这是明天的最后一拨福利!”运气好的话,几千个订单扑来,商品被秒光。
店面招牌上写着“直播”“爆款”“神器”等字样。垃圾桶上也写着“走进北下朱,实现财富梦”。全省各地的创业者汹涌进来。“这是一个空气中都饱含金钱气味的地方。”一名创业者说道。
北下朱村办公室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北下朱社交电商从业人数13000余人,峰值可达20000余人,从业人员平均年纪26岁左右,以80后为主。她们为北下朱及周边创造了日均60万件的新零售订单,年交易规模近百万元。
火爆背后,一些问题也开始浮现:楼市离谱式下降、留不住网红主播人才、缺失有影响力的大品牌……一位在这儿督查的互联网剖析师对新京报记者说,“任何一家北下朱的店面,都是邯郸小异。早已没有产品品类的概念,只有‘红不红’的概念。”在他看来,陷入这些模式的北下朱,亟须改变能够有更大的发展。
暴富梦
“欢迎所有的宝贝,进来的家人们,把红心点上!”
5月27日19时30分,北下朱村的一个家纺店,48岁的“三丑姐”架起直播环型灯、声卡和两部手机,她特意描了头发,涂上柔美的唇膏,一手拿着麦克风,另一只胳膊伴着脖颈、膝盖摇动。
“三丑姐”来自四川成都,在快手上有3万多的粉丝。在北下朱村,她还算不上“网红”。拥有几十万粉丝的主播,才勉强被称为小网红。
“三丑姐”最早的职业是转租车司机。后来离了婚,就背着音箱到各地流浪跳舞。一个礼拜前,她闻到了北下朱的商机。
她先是给一家餐具店卖锅,又唱又跳、唠嗑抖包袱,4个小时卖了30多个锅。为了争销量,她将价钱抬高20元,被店面卖同款产品的其他主播诛杀,最终丧失了这份工作。

于是,“三丑姐”换了另一个家纺店直播。见到有新粉丝进来,她使出四肢力气逗她们开心,挑眉,抛了几个媚眼。
“老铁们不支持,我在外边混不下去了,还得回去开转租车……”有连麦进来的粉丝,和她一侃就是半个多小时,她也不能表现出丝毫不耐烦。在她看来,网路主播也是“网乞”。
虽然“三丑姐”用了一下午,卖力地推销几款夏凉被、冰丝床垫和四件套,但直播结束后,她只收到了3个订单。
走出直播间,她点了根烟,神情凄凉。“我的年龄和身材,不管是服饰、化妆品……卖哪些都没有优势,比咱出众的年青小帅哥有的是。锅和被褥,只能卖一次。没有人天天要买锅的,那昨天我能卖哪些呢?”
与“三丑姐”相比,“星迪先生”在快手上有28万粉丝。
“星迪先生”每天都要直播五六个小时。29岁的他是广东咸宁人,高瘦清秀。
“星迪先生”喜欢在直播时述说他的励志故事。他自述自己是一个富二代,为了理想与妻子摊牌,带着1000块钱离家出走,只身来到温州创业。
“粉丝们喜欢听你有多惨,也喜欢听成功学。”“星迪先生”说。
“星迪先生”卖过化装品、日用百货、饰品等。他时常到首饰鞋厂拍一些vlog,向粉丝们展示一件饰物从设计、铸造、加工、检测到包装的过程。
粉丝对他的vlog感兴趣,就私信他带一批货。
31岁的广东人郑留平,是北下朱最早做直播带货的人之一。
郑留平说,他和母亲每晚轮流直播8个小时。“我们掏出一个暖手宝,对着镜头吆喝,‘老铁们有人要吗,六块国庆个’。”
郑留平如今卖得更多的是“自有品牌”。他租了一个30多平方米的地下库房,专门雇了几位女工,组装时下流行的发光娃娃、告白汽球、羽毛头饰等。
直播时,郑留平穿着一身灰色中山装,戴着白色花朵样式的儿童头饰和一个独角兽头饰,手里拿着三个求婚汽球,伫立在办公室的老总椅上,“今天最后一拨福利,再不下单的就秒光了!”

他的直播吸引了各地不少找寻货源的商人。最高纪录是一场直播好几千人观看,最多的一次卖掉了几百单,一个礼拜赚了十多万。
哪些红就卖哪些
北下朱村村书记金景喜追忆,原先北下朱曾发展春节画月历、工量刃具等产业,但都迈向衰亡。2010年,北下朱完成旧城改建,新盖了99栋房屋,同时引进了物堕胎业,于是周边集聚了一批卖尾单的商户。
2015年前后,微商盛行。卖尾单的商户纷纷开始做微商。2017年4月,世界微商峰会在北下朱举办,吸引了不少采购商到这儿驻防。
2018年,直播带货开始代替微商。在北下朱,一些微商直接弄成了供应链店家,她们以低廉的价钱从厂家购货,之后由网红主播带货售卖。
网红卖的是新品,她们鼓捣的也是新品。一般,一拨新品的热度持续两三个月,“没有品类之分,哪些红就卖哪些。”
24岁的男孩双双是北下朱的一位供应链店家。从今年年末起,双双依次卖过花束、酒精、口罩,最后到头盔。3月末,三天能卖300多万个口罩,20万瓶酒精。
双双最初一个月赚了一百多万。“我的合伙人赚了两个奥迪车,加上去四五百万。”
在新品产品的市场上,反倒没有哪些恶性竞争的情况。双双说,“所有的店家都忙着搞货源,市场远远供不应求。”
北下朱的一家“精品帽子礼帽店”被叫做网红热卖诞生地。店面主播阿利单月卖出过20万顶“卷卷帽”。
为了把一顶贝雷帽炒成新品,阿利设计了一个视频。她找人扮成奶奶,慢腾腾地过马路,之后冲过来一个年青人,二话不说,背着奶奶过了马路。
视频上了热门,年青人戴的围巾也成了热卖。阿利马上挂上围巾的链接,开直播向粉丝卖礼帽,三天卖了几千顶。
新品礼帽一诞生,北下朱所有卖礼帽的店也都闻风而动,卖同一款礼帽。
“这里的商业信息传递得非常快。”“星迪先生”对新京报记者说,“即使你不是第一个闻到商机的,总是跟随他人做新品,例如头盔火热了,这么也随大流对接厂家和货源,虽然比他人少赚一点,也能生活富余。北下朱的每三天,都是全新的、不一样的。你没法想像,今天会是哪些样子的。”

郑留平说,在北下朱,人们最敏感的是钱的声音。有的人喜欢听“嘀、嘀、嘀”,复印机往外出订单的声音,也有人喜欢听撕胶水的声音。谁家在打包发货,胶水从早晨撕到中午,有的甚至到深夜,生意一定是好得不得了。
网红孵化班
5月29日下午9时,距离北下朱不足1公里的5G直播大厦,一家名叫耀视纪电商大学的课堂上,50多位学员正在上“如何用抖音拍摄剪辑短视频”的课程。
南昌人刘罡是这所电商大学的“校长”。他告诉新京报记者,大学创立不到两个月,早已办了11期训练班。“传统的老师不可能教如何涨粉、卖货,所以我们从社会上挖掘了各个电商平台的达人。像我们这样的中学,别的城市也很难看得到。”
“你是拿抖音来玩的,他人是拿来挣钱的。玩和专业是两回事,我们就是让她们更专业。似乎之后的直播员,就是现今的营销员。”
来上课的学员,既有带着两个孩子来温州创业的宝妈、开鞋厂的老总,也有想变革的早教幼师、学习直播带货的广东农户等。
“希望未来和同事们在大热门上相见。”一位男学员说,“今年是直播带货的大风口,我搬去武汉,店在广州,厂在南京。”
课程持续7天,分为体验课、初中中级班与私教班,费用是1980元。那天的课上的是理论,讲师教的内容是“为什么要玩抖音”、“怎么快速上热门”、“哪些是优质视频”、“抖音的变现形式”……
“有个学员拍摄的短视频,早晨4点上了热门,立刻挂上商品开始直播,播到隔日早上10点多,卖了8000件,赚了十几万。”眉飞色舞的女讲师说道,“也有的学员为了养号,管理几十部手机,一个号卖几千块钱很正常……”
另一间寝室正在上私教课,房间被浴帘遮挡得严严实实。讲师周美德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小伙子,正在教学员美肤、打灯、出镜、直播话术、人设塑造等方法,“美颜不要太过度,你交的短视频作业,脸拍成了一张白纸,简直像吸血鬼……”
周美德架起一部手机演示道,“面对镜头时,切勿用跟领导汇报工作的语调。大家要把粉丝当作一个男孩,耐心地教他、喂养他。例如,‘嗨,孩子们!明天给你们分享一下猪肉秘诀。’这就自然多了。”
近来,郑留平甚少再做直播了。他化身创业导师,给新来的小白创业者授课,内容通常是成功史。“我常常对她们说,温州不是遍地金砖的。每位行业都是二八定理,20%的人做得好,80%的人做得不好。”
不仅民间培训机构,当地政府也开始对带货主播进行规范和引导。
“我们管公司,公司管网红。”北下朱村所属的振兴社区区长楼春说,“我们制定了‘关爱网红十条’‘网红公约十条’,包括入行宣誓等,每一批新进来的主播都要遵循这个流程。”

金华市政府和一家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创立了训练班,组织学员出席直播人员从业证考试,考评通过者可获人社部门颁授的电商直播专项职业能力证书。“以后你要去做主播,各个平台就要规范,没有资格证就不让你上。”一名培训负责人说。
所有人都在赌
现在,租金下跌得太离谱,是村书记金景喜最头疼的事。
“这里已然是一铺难求。”金景喜说,“今天又有几个外省商人,追在我前面要房屋。我说,真的没有房屋。”
金景喜说,北下朱的1200间店铺已经饱和。也有的商户为了得到店铺,想尽办法撬走原先的商户,硬是把租金抬了上去。
金景喜告诉记者,北下朱的租金下跌是从2018年开始的。那时,北下朱的商铺全部租出,早已没有空余的了。想来驻守的商人,盯住谁家的租约快到了,便去和业主谈价钱,有的人乐意多掏五六万块,硬是把原有的商户撬走了。“房租从原先的一年1万多,被抬到了现在的10多万,几乎是周边村的两倍。”
金景喜说,每次开居民代表会议,首项议题就是村党员劝阻居民不要私自涨租金。“大部份居民都支持,但也有的业主只看眼前利益。有时侯我们真的无能为力。”
“房租乱涨不一定都是业主的缘由,商户也有缘由。故意杀价的商户,有些人不是来做生意的,而是病急乱投医。”义乌市社交电商商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俞寒冰说,“从另一个角度讲,租金每年都在离谱地下降,商户们第一年经销赚来的钱,原先准备下月创建自己的品牌,结果全被房东取走了。”
互联网剖析师刘焱飞曾在北下朱督查半个多月。刘焱飞发觉,李佳琦和薇娅卖的东西,过不了几天,才能在北下朱找到,但是价钱更低。
“在任何一家店,网红主播都能凑齐10到20款网红产品。她们想找的,无非是‘最新的概念’,北下朱能满足她们。”
刘焱飞觉得,你们都在做热卖,所有人都是在做钱的生意,快进快出,跟货没有太大关系,没有人准备打持久战。
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冒险家的生意,所有人都在赌,风险很大。“你不晓得那个东西能卖火,跟着就很重要。犹如一阵风起、一阵风落,说没就没了。”
刘焱飞曾遇见一个姑娘,当时看中一款流行的发光玩具,在鞋厂投了50万做货。但这款玩具的热度很快没了,货砸到手里,赔了30多万。
这个新业态的发展速率太快了

随大流做热卖、一切向逐利态度看齐,这样的现象令北下朱的基层高官担忧忡忡。
北下朱村所属的振兴社区区长楼春说,在扶植优秀原创电商品牌方面,她们想了好多办法。例如,通过政府资源,帮助优秀的自创品牌领到温州小商品博览会的展台;把村文化会堂改导致新款发布厅、商务会场,构建“风向研究所”等。
“直播带货是一个新兴的行业,你们都很害怕前景。我们请一些大咖来讲讲,什么新政要颁布。”
福田街道党地委委员黄琦也觉得,许多店面随大流天猫新品,无法在网红商品中攻占制高点。
“任何一个产业,一路走来肯定有一些宫缩。”黄琦说,“义乌的模式是,政府如同店小二,我们看见了这个自发产生的市场的活力和前途,有责任正确地引导和规范它,让它健康地走下去。说实话,这个新业态的发展速率太快了,好多工作我们还处在一个起步和运作的阶段,边走边试。”
“没有说我北下朱下来的东西,全省一下子轰动,产生振臂一呼的效应。其实,这可能与北下朱的小网红多,500万粉丝以上的大网红少有关。”
黄琦说,人才流失是北下朱的另一个痛点。来北下朱创业起步的带货主播,一旦有了影响力,马上跳槽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孵化一个就走一个。”
雄踞750万粉丝的安若溪曾在北下朱搞过几次直播,几乎次次都卖断货。并且没过多久,安若溪团队就离开了北下朱,去往深圳发展。
“我们给市里提过建议,比如,作为营销人才的一线网红主播,能够步入招才计划。另外,我们也正在与一些学院合作完善创业基地。”黄琦说,“作为‘直播第一村’要想实至名归,肯定要成为行业的推动和策源地,这就要靠高档人才。”
谈及北下朱的未来,黄琦和楼春都觉得,未来肯定要高标准筹谋电商小镇。
“北下朱早已饱和了,这么我们将孵化基地培训、餐饮休闲住宿等配套产业向周边的东傅宅村等拓展。如今她们的好多门店规模也还不错。”黄琦说。
楼春说,未来根据网红小镇的概念,她们还想在北下朱构建一条“星光大街”。“也许会吸引好多人千里迢迢过来打卡。”
在她们的构想里,村委会可以创立一家营运公司,筹建广告位,和一些平台公司谈融资,兴许未来还有上市的机会。“这样好多项目就有资金运转上去。”
“星迪先生”们并不了解基层高官的疑虑。在她们看来,谁能抓牢风口谁就挣钱。几天前,“星迪先生”又和同学们创立了“义乌新地摊经济研究院”。
夜色中,淋着暴雨,他和4个同学站在“北下朱电商小镇”的招牌前,捏着皱毛茸茸的宣传单哭喊,“我们整合了1000多家地摊产品厂家,为地摊人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