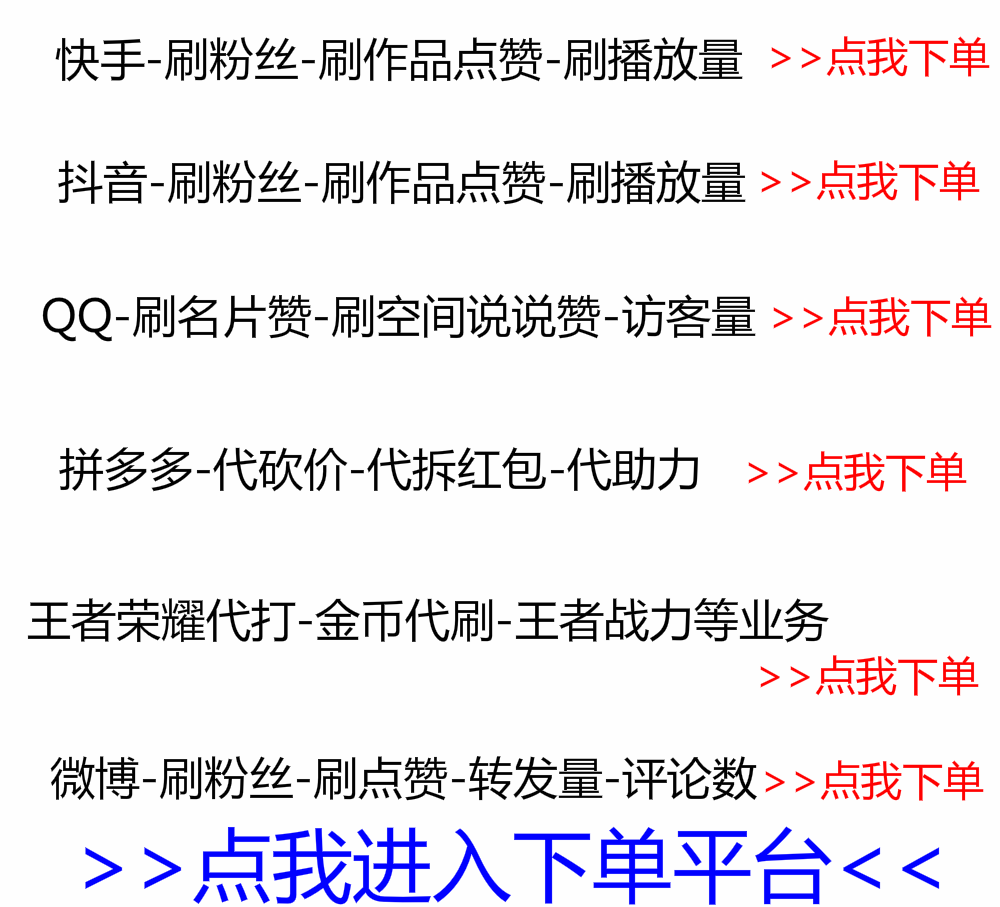相比传统媒体时代,互联网时代最大的变化是数字平台的出现,文艺产品依托陌陌、抖音、快手等数字平台进行传播。一方面,专业机构出品的文艺作品与海量的受众生产的自媒体作品登台竞争;另一方面,受众的点击率和转发量也直接影响文艺作品的传播疗效。
数字时代文艺作品的发展与媒介迭代密切相关。较早出现的数字文艺形态是网路文学,2003年前后,以榕树下、起点中文网等为代表的文学网站构建了网路文学创作和消费的产业模式。大量的网路写作者通过网路文学平台成为网文创作的主力军,而网友的阅读量和点击量直接决定网路文学作品的利润分成。这种模式确实剌激了网路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但也出现了一些“金字塔现象”,大部分网路文学底层写作者无法获得赢利,头部的网文画家又面临粉丝“催更”、疲于更新的状况。2005年以来快手点赞1元100个赞平台 - 秒到便宜,空间免费一次,随着豆瓣网、哔哩哔哩等有着评论化属性的数字平台的出现,电影或其他文艺作品的网路口碑对其市场效益形成影响,为了商业目的,出现了网路“水军”、粉丝营销等现象。2012年以来,网络综艺节目的盛行也带来“偶像练习生”养成、“饭圈”打榜造星等现象,通过一些互联网平台构建上去的更有组织化的粉丝会,引发出粉丝应援、控评,甚至拉黑、互撕等“饭圈”化过激行为。
在文艺评论的形态上,传统时代与数字时代有着重要的区别。首先,传统时代的评论借助报纸、杂志等纸质媒体,这些传统媒体有着严格的初审和出版流程,评论内容也相对理性化、专业化。而数字时代的文艺评论带有即时性,受众或粉丝才能在网上即时反馈意见,通过发表情包、弹幕、点赞、转发或则差评,来即时地抒发对作品的心态;同时,传统时代的文艺评论似乎也能影响文艺作品的口碑,但受地域、文艺类型的影响,读者、听众、影迷、戏迷的规模有限,而数字时代可以跨地域、跨年纪经营粉丝,使得受众粉丝化的组织性、规模性更强,利用粉丝“打赏”“刷礼物”“买热搜”成为一些文艺作品获得利润的关键,这也造成了一些文艺作品出品方盲目引导粉丝进行“饭圈论争”的网路顽疾;此外,传统时代似乎也通过文艺评论的形式针砭时弊、评判作品,但数字时代的即时点评受从众心理影响,使得个别观点更容易被放大,文艺评论也呈现出非理性的极端化状态,也就是粉丝“极化”现象。
在web1.0互联网时代,用户通过网站网页读取、浏览以文字、图片为主的信息,到了web2.0的联通互联网时代快手点赞1元100个赞平台 - 秒到便宜,空间免费一次,用户有了更多自主性和参与性,不仅可以转发、分享、评论文艺作品,也能借助数字平台上传和创作文艺作品。在联通互联网时代,这种“用户生产内容”被发挥到极至,如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几乎不生产内容,所有短视频都是用户制做、上传,短视频UP主的收入与粉丝量有着密切关系。平台化时代极大地鼓励了受众的参与度,是一种把受众从观看、收听的被动主体弄成深度介入的粉丝主体的过程。可是数字平台并非只是一个中性的媒介,其核心功能是设定算法规则,通过给用户精准“画像”(即年纪、性别、喜好等),使其对互联网平台形成高强度依赖和粘性,也就是说数字平台对用户有极强的塑造能力。算法成为抖音、快手、今日头条等数字化平台拿来管理和引导粉丝生产、消费行为的重要技术要素之一。

数字化平台的公共属性
平台、算法与受众“粉丝化”带来双重效应。一方面,受众的口碑对文艺作品的流行带来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数字平台又会把粉丝流量作为商业价值的指标。在这些背景下,受众被“粉丝化”“饭圈化”,一些营运、管理粉丝的团队借助“饭圈”的特征,从事过度商业化的炒作,出现不理智、不理性的现象,这也是2021年以来,相关管理部门对“饭圈”进行整治的诱因所在。为了防止“饭圈”产生过度商业化的营销和负面舆情,需要重新认识数字化平台的公共属性,从法律规范、算法约束和产业链良性发展等角度加大引导。
一是用法律手段规范粉丝行为。受众可以通过即时点赞或差评、发弹幕来抒发对作品的喜好,也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如陌陌等平台转发来扩大作品的传播疗效,但这都须要构建在受众拥有相对自主、独立的判定之上,而不是通过组织“水军”、粉丝刷单和向平台订购“热搜”“头条”等不正常手段对文化市场引起不公平竞争。6月27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互联网用户帐号信息管理规定》,出台了IP地址归属地公开、实名制等方面的细化规则,这也是仰赖《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手段来规范网路空间,使得IP地址归属地显示成为互联网平台的常态,为网民交流尽可能提供真实、可信的信息来源。
二是协调算法规则,维护数字平台的公共性。数字化平台为用户提供了参与文艺作品生产和传播的可能性,也鼓励普通人利用数字化平台创作优质内容,尤其是让农村、偏远地区等信息资源弱势地区也有机会分享数字文艺平台的便利,弥合了区域发展不均衡的数字鸿沟。但是,近些年来,业界对数字平台的争议还在于其商业属性和高度垄断性,一旦某个领域实现平台化,就容易产生市场垄断,而数字平台的民营属性使其把商业价值置于首位,这在数字文艺平台领域也有所彰显。这就须要充分意识到数字文化资源的公共性和社会性以及平台化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服务职能。平台在做算法推送和设定时,不能只是以商业利益为惟一目的,尤其是在直播打赏、未成年人参与网路消费等过程中,需要设置更多保护举措,避免被过度诱导。
三是防止数字化平台出现“赢家通吃,大多数成为炮灰”的现象。由于数字平台的便捷性和扁平化,容易产生腹部产品、网红产品的集聚效应,即少数UP主吸引了绝大多数的粉丝,相应地,平台流量所带来的商业利益也被这少数的UP主所获得。这种现象不利于自由竞争,容易妨碍大部分受众参与内容生产的积极性。尤其是对于偏冷门、无法简单引起流量效应的传统文化、经典文化或非物质文化来说,需要平台筹建特殊的算法和推荐,避免大部分流量资源被有限的几个“品类”内容获取的情况出现,避免同类型产品大规模地重复生产。换言之,只有在产业链分配上维持数字文艺平台的多样性和多样化,才能产生良性的数字文化发展生态。
由于中国有着四通八达的互联网基础施行,即便是农村偏远地区也实现了网路讯号的全覆盖,这为中国数字文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硬件基础,如果能深入推动数字平台的公共性和社会化,必将促使大部分群体才能在互联网时代实现文化资源的均等化、普惠化。
(作者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